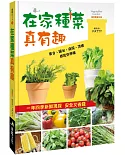前言 旅程
每個春夏的早晨,剛睡醒的我爬下床時,第一件事就是走到臥室的窗台前,那裡可以俯瞰整座擁擠的花園全貌。我搓揉並眨眨惺忪的睡眼,目光梭巡整片庭園,彷彿縱纜東方國家的捲軸山水畫,每個令人讚嘆的細部都活轉過來,也都擁有相等的份量與比例。
我從不是如筆下陳述的能幹主婦。每天早晨必定可見浣熊隔夜留下的慘重災情:石塊掘開,池面還飄著廚房的食物,我遺留在露台桌上的珠鍊,如今掛在某棵樹梢上。
我衝下樓,三步併兩步推開後門,走到水池邊,撈起咖啡、報紙和書本。我經過露台,在食用香草花園裡深深的吸了口氣。我赤足走上沾滿露珠的綠草地,觸摸蘋果樹以祈求好運,然後走到曬衣繩底下。我駐足觀察罌粟、艾菊、玫瑰花圃,猜想今天有哪些植物萌芽了,又有哪些需要特別關照。最後,我在池塘旁邊的砂岩平台上暖和腳趾,向金魚(乃至向盛開的荷花)致意。
我坐在我們命名為「假日晚宴劇場」的小小涼亭桌邊,打算開始幹些粗活;只要讓自己投入渾然忘我的園藝工作裡,我就幾乎停不下來。
從這座爬滿了藤蔓植物,半邊藏在紅色舊屋裡的隱匿處,我的視線掠過種矮牽牛與老鸛草的花架,穿越葡萄、鐵線蓮與牽牛花所組成的網幔,再到另一道奧氏蓼的簾幕。去年夏天,這些小白花形成的雲霧,籠罩在花徑上高聳的電話柱頂,點綴了此處遠眺落磯山脈的前景。
夜裡,我們坐在引水入池處的岸邊長椅上,聆聽自竹管傾洩潑濺的「流瀑」聲。這裡是月光花園,今年,某株曼陀羅在幽暗的角落發出強烈的香氣,喇叭狀的大白花也反射著月光。
到了早晨,曼陀羅花奄奄一息。升起的陽光洗刷過晚宴劇場外的小屋花圃,照亮翠雀、尾穗莧、小白菊、大波斯菊、玫瑰、金光菊、耆草、雛菊等。
我現在靜不下來,喝著咖啡。我努力不讓書頁和報紙被風吹亂,漫步在小屋花圃沿石塊盛開的燦爛光景間,以及通往菜圃的板條步道上;那裡今年種了南瓜、番茄、萬壽菊與歐芹。上了墨竹釉彩圖樣的高瘦花瓶,打破許久並重新黏合,用來裝旋轉式的灑水器;我以爬滿花園的軟管權宜充數,也算是魯柏.郭德堡所謂的某種「體系」吧。
若是在五月底或六月初,鳶尾花佔據了前、後院的大片美景時,整片初綻放的罌粟,以及中國與「莎拉.柏恩哈德」芍藥也將偎著朝氣蓬勃的菜圃,宛如火紅與粉紅的砲彈。只要是鳶尾、罌粟或芍藥花,再怎樣開也不嫌多。
待季節更深時,這片花床又將化為簇集或穗狀的,一枝黃花、天人菊乃至其他菊類花叢。
中央的菜圃什麼都可以種,包括觀賞花卉。它不偏不倚地刻在草地中央,抹除了肯塔基六月禾的最後範圍,並以匙葉草、緞花、俄羅斯鼠尾草、山蘿蔔和婆婆納為邊界。鳶尾花和普羅旺斯薰衣草,在角落是很好的守護者,那些地方總是暴露在腳步或手推車輾壓的風險中。
原本是我在分株球莖時,欲移植到許久前所回收、有金屬頭和踏板的床架可支撐處,卻不慎遺忘的劍蘭迷株,如今薄葉破土而出。
走過草地步道,就是另一片填高的花園,邊緣圍繞著紫花的庭薺,我偏好在此種植矮生菜類,如用來做沙拉的綠色蔬菜或過度生長的甘藍,以及羅勒和胡荽等。
五月,在候鳥大舉遷移後,假如我起床得夠早,我就會帶著我的咖啡和書本,獨自坐在神秘花園的茶屋裡,欣賞鶯或鶲類穿梭於梨樹、葡萄藤、耬斗菜、香豬殃殃和凱特池塘附近的美姿。有兩種走法可以進入神秘花園,我最愛的一條則是穿過人造林間的李樹樹蔭下。假如下雨了,樹林地面就會長出黃褐色的蘑菇群。
我的房子兩邊皆為和我一樣建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住家,改成供臨時房客承租,通常是些學生,(我們的房屋可能是本街區上僅存的單一家庭住戶。)這顯然是交到好運,因為房東們注定缺席,也沒有隔壁的園丁會來關切我的不安於室或擅自闖入。
在東邊,屋主種了太多松樹,種得太緊密又忽略澆水,結果只有一棵活下來。這些枯松的殘骸構成神秘花園的葡萄藤架。我們之間主要以我的李樹來區隔,直到最近,我仍未見過任何人出沒於該棟住屋,也幾乎不曾撞見屋主。偶爾現身的房產經理人,從割草季節結束後就不再出現了。
往西走,屋主任其花園自生自滅,而「隔壁的蘇絲」就是住在西邊的房屋。(聽起來多正式呀,因為這是她在電話裡自我介紹的稱謂。)當蘇絲搬進來時,她那股活力立刻感染鄰里之間。
六月前,所有點綴人造林前緣的黃與橘色國王鬱金香蹤跡,全都隱匿在一發不可收拾的紫羅蘭地毯下。我的晨間漫步路線,最近改成筆直通過那片空地,通過芸香、鼠尾草、塊根紫芹、珊瑚鐘、芍藥和薰衣草形成的邊境,到達新造的岩石花園、梯狀小丘,以及蕨類和玉簪的狹坡。我凝視整片植被,思忖是否該加一道彎弧、細碎的樹皮小徑來呼應神秘花園裡的那條,還有藍亞麻布是否可以讓羽狀的蕨類更加輕盈優雅,同時又能襯托出玉簪的寬闊葉片?
我沿此處走過更多鳶尾花,玫瑰藤蔓,忍冬以及一棵花楸樹,靠近以波斯丁香和蒙古杏樹為界的涼爽、掩蔽的前院,則有奧地利山松與矮生的山松。這裡是氣味濃郁的藥草花園,有犬薔薇與藥用法國薔薇,還有長在長春藤和蔓長春花毯之間的野生百合;小徑便自其間切分,通往佈滿多肉植物、高僅逾膝的石板矮牆。
在走道和街道之間,我則栽種唯一純正的「旱地植物」花園。春天,從銀灰的地被植物下竄出驚人的盎然綠意,但在夏天將盡之際,這片「渴望雲霓」的花園卻凹凸不平。處理這塊乾燥氣候區的原生植物,代表某種持續不斷卻往往令我挫折不已的挑戰;如今我又枯坐在前門階梯上,思索著該種什麼、或該移除什麼,才能在炎熱而缺水的夏末維持其盛景。
前院比庭院別處更加合乎規範,因此較不需要我投注心力。然而,它是如此紛雜的綠色,以至於抹除了房屋的界線,彷彿我們的住址並不存在,就這樣神奇地從地上蹦出來似的。茂密的植物吸收了人車的噪音,每當我在準備早餐時,我經常在露台上進行,加拿大鐵杉、老氣的紫丁香和桑橙枝椏斜刺入門廊欄杆裡,長春藤蔓延到門廊地板上。這裡是我所能擁有最接近既是室內、也是室外的空間,是花園的房間,我們在自然萬物的庇蔭裡,卻又完全為草木所擁抱。
循著我的房屋與蘇絲家相鄰迴廊的舖石小徑,完成了早晨的巡禮;在繁花盛開的野生蘋果樹下(讓我回憶童年的日本櫻花祭);穿過圍籬門抵達多蔭的蕨類與磯松花園(並在此修整任意攀爬圍籬的苫壁藤)。
我又帶著我的書本和咖啡杯,邁著大步穿過庭院,從攀緣的玫瑰間鑽回屋裡。不用多久,我就會脫下睡袍,換上園藝用的粗質衣物。
每天早晨我所穿越、勘查的花園,是我的心靈地圖,更是我那「幼年流浪」的教養地誌。
我的父親是一位美國外交官員;再往上一代則是從愛爾蘭和丹麥來到新大陸的移民,我的親人不論遠近,整個家族綿延遍佈世界。
讀者將遭遇到我那些(過於)枝繁葉茂的親戚,包括我母親的兄弟如奧沙、奧馬利、奧康納和奧哈拉等,那些我們叫「奧」字輩的舅舅。我外婆的愛爾蘭沙文主義,在她要替女娃兒命名時就黔驢技窮了。我母親的名字叫做桂妮薇,她的孿生姊妹叫做奧古斯塔;艾瑪琳在我出生前即過世。
雖然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但幾乎每個姑姑或叔叔、伯伯,都是我敬重的對象,而我的凱特姑姑始終和我最親密,從孩提時代起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好歹也是個新移民,在長大後才回到美國定居。在我的孩提時代,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返回美國休假,有一年,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租了棟房屋,同個時期,我的父親也出任某些神秘的差事,可能是在國務院裡的險惡職務。
我生於澳洲,長於日本、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印度、阿富汗、西班牙等國,還有某段特別難熬的青春期歲月,被父、母親送到瑞士唸書。在蒙特勒(Montreux)大莊園式的女子寄宿學校裡,我只學到兩件跟花園有關的事:一是如何攀爬佈滿荊棘的高聳圍牆,以換取短暫的自由和男友幽會,二是哪裡可以躲起來,和其他女孩一起吞雲吐霧。
不管住在哪裡,我們都享受1950、1960年代駐外生涯的種種優渥福利,包括一名園丁的配額。(從客居異鄉到定居美國的落差,就像從貴婦降級為主婦。)
母親不太可能被廚子發現猝死在廚房,因為她和園丁如膠似漆。天剛破曉,她就穿得破破爛爛,頂著在日本買來的寬大笠帽,三步併兩步衝進庭院,與我們的園丁並肩幹活兒;往往惹得他火大不已,但也不時有說有笑。
快到中午時,她就會再度現身,以「香奈兒」套裝與平頂女帽的盛裝打扮,準備赴午餐或其他正式行程。從那個神奇的時刻開始,她不再是那個渾身泥巴的花園苦力,而是一位公主,如假包換的灰姑娘。
園藝既是母親、也是我的藝術形式。然而,我並不知道母親確實視它為藝術,起碼園藝是她少數畢生投入,而且完全留給自己的活動之一。她從來不謙虛,唯獨關於花園,她謙遜而熱切的聆聽與學習。園藝無疑是她的某種治療之道,而它也是我們所有人的。我更相信,雖然母親從不曾這麼說,園藝也是她的靈性功課。
我的家庭熱衷參與,也似乎完全融入我們所旅居國家的本土風俗與假日,尤其我的母親,是儀式與劇場的愛好者,更不遺餘力保留──甚至刻意美化──她所出身的傳統。這麼做時,她也能將我們這個迷你旅行團連接先人們的偉大世界,否則我們將對那些難得見一面的家族成員毫無所悉;至少她希望透過這些儀式,我們之間可以有所連結。而少了這些聯繫,我們都將陷於心靈缺乏寄託的危機。
我們的儀式多半不是什麼宗教節慶。更確切地說,我們的家族儀式都與花園、園藝日曆,以及花園從萌芽、生長,到死亡這些外在循環的直接狀態有關。
我的母親沒有強行在我的腦袋裡灌輸宗教,而是透過根本的示範,傳授我園藝之道。如何種花蒔草,更重要的是,如何樂在其中。花園中自有信仰與奉獻,以及視大自然為神聖的根本信念。
我的母親集農婦園丁與貴婦園丁於一身;她所出身的那些「寒酸的愛爾蘭佬」基因,使她栽種實際的食用植物苗圃。但母親對美情有獨鍾……她渴望出人頭地,更在乎外人觀感。
在我的愛爾蘭家族裡,充分理解園藝事務正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你不但必須知道何時或如何種植作物,更必須知道它們能不能吸引神靈,帶來好運或不幸,乃至於植物的民俗、法術、日常料理與醫療用途等歷史掌故。
我曾有幾個不同版本的花園,即使在我相當年輕時。剛離開家的那幾年,我在紐約、華盛頓特區和波士頓的公寓只有鐵條圍住的窗台空間。我渴望綠色植物,渴望擁有一片領地,讓我能毫無限制的開創一方綠地,並赤足漫步其上。解決之道則是擅自據地;我熱心地接管公寓庭院的共同空地,在既有的公共花床上拔草或種花,在空地上到處掘土播種,或在隱密的角落裡移植向熟人強要來、或植樹節所分贈的樹苗。今日,友人和許多陌生人無不奔走疾呼,要將耗竭的都市用地還給花園,或者挽留可能遭受建商或庸俗政客染指的社區庭院。
當我是一名都市園丁時,我在冷漠的窄窗上掛滿許多花盆,將滿是植物的層架緊貼著玻璃。我裝設植物生長燈與保溫器,有次,聽從某位來自田納西州的電工技師建議,在懸吊式花盆裡倒著種番茄,還真的結了一、兩顆果實,最後整個盆栽因太重而垮下來,把一大塊天花板都扯破了。也有那種可以種活任何植物的朋友,無論到哪裡,他們都能將陽台化為花園,將公寓化為溫室。而我的大多數努力,誠如他們所說,只怕都是「願望勝於實際」。我的綠拇指在室內顯然不太管用。
我的第一座充分發展成形的花園,是在賓夕法尼亞州中部的某片農地上。我客居異鄉時所擁護的政治信念,似乎在嬉皮運動裡表露無遺,於是我立刻一頭栽進去。經過幾年城市激進活動之後,我毅然而然「回歸土地」……回歸那片無邊無際的土地,我完全不知該如何運用,也沒有園丁可供差遣。我是天之驕女,向來有人替我們做好所有的粗活與苦力,因此一時落得手足無措。
農場上養了許多牛、?、羊、豬,還有一座果園,以及將近一英畝的蔬菜園。日子過得很辛苦,但那是一段相當美好的回憶,我充滿熱誠,相當年輕,又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我還常揹著其中一個在農場上幹活兒。真不敢想像讓我們在喀布爾、東京,或波哥大時認識的園丁看到我當時的模樣會怎麼想!我變成冒牌「村姑」(campesina;因為駐外時園丁為外籍)啦。
我操作農具、鋤草、擠奶、劈柴、取水、醃製食物,甚至學著織被。我為食用的番茄、豆類,和豌豆搭蓋搖晃不定的棚架,並嚐試茹絲.史陶式的私房技巧,如在厚厚的報紙下栽培馬鈴薯;甚至當我們為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而搬到科羅拉多州時,田地上和水溝裡還漂著《費城詢問報》的碎片呢。所謂「正式」,是說一份可以獲得「正式」酬勞的工作。
我們搬到波德城的這棟住宅,二十年的老照片,見證著這座乾癟、枯黃和貧瘠的庭院。我常常挖到一半便無疾而終。
但在搬到那裡幾年後,我就離婚了,我變成兩個孩子的唯一支柱。花園變得形同虛設而靜謐無聲。我根本抽不出片刻空閒。
在我成為單親媽媽的前幾年裡,我和好友吉米合夥開造景公司,命名為「綠色女神庭園施工」。年節應景的工作項目主要是整理墓園、修剪和移植草皮,是一份須在冬天再兼些女侍和報導記者等零工才能維持的工作,直到後來我才得到報社的全職工作。中年回憶往昔,我真不敢相信我和吉米竟然如此冒險犯難,敢赤足爬上木棉樹用鏈鋸修剪枝幹。我是打哪來的愚夫之勇?
(恐怕是皮革似的腳丫長滿防滑的老繭,才讓我們不至於摔下來吧!)畢竟,我曾經夢想當一個海盜。
沒有時間營造屬於自己的花園,我卻教育孩子們不可缺的基本嚐試,例如怎樣發現仙女圈(蘑菇在著生處自然形成的圓圈)以及製作罌粟或蜀葵娃娃,雖然我忙得沒時間種罌粟或蜀葵。我的父母常常來訪,並為我種這些植物,然後又煩惱我會讓這些花草自生自滅。還好,不論罌粟或蜀葵都沒那麼容易就枯死。
我又結婚了,小孩也長大離家、各奔前程了。突然間,在強烈的能量與熱情驅使下,我開始補償我所失去的時光。我曾經和母親站在約旦河這端,敬畏、且驚恐地眺望以色列。我們站在熾熱的沙漠上(那僅有的儲水皆已抽取殆盡),凝望青翠與肥沃的田野,並以沿著壕溝架設的帶刺鐵絲圍籬阻隔,上頭有個標示:「歡迎來以色列──請止步!」
儘管以、巴政局仍然無解,但我永遠忘不了那個畫面。我下決心,我也要將自己的荒漠,化為一座甘美的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