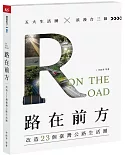這本書的內容主要脫胎於我的博士論文:「中山北路:地景變遷歷程中之國族與情慾主體建構」。一個有著相當冗長副標題的論文題目,某個程度暗示了這個論文主題可能的詰屈聱牙。
每當人們問起,我只能簡短地應答是研究中山北路的歷史變遷。
我逃避進行更為細節的說明,除了懶惰,不太願意面對可能才是主因。
畢竟,我已經預設了,在台灣當下的時空裡,討論性別議題、國族國家建構、或是集體記憶中的殖民經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因為那不會是個太愉快的經驗。
「殖民歷史」、「情慾想像」是本研究的關鍵字,一般人憑著直覺與經驗,大致可以猜測其內蘊。但在我的博士論文裡,另一個必須對學術分工與生產有點交代的專業名詞是「地景史」(history of landscape),這個詞構成另一個說明上的「障礙」。
「地景史」一詞在學術理論的發展上可以說還是個襁褓中的小孩。此一「發展中」狀態除了尚未累積足夠的經驗研究與論述資料來支撐外,該研究取向試圖以跨領域視角建構對空間研究向來較為疲弱之意義詮釋工程,亦增加了其論述工具使用與研究方法上建構的難度。
以一個研究領域言,新興發展未嘗不是好事。代表有極大的嘗新機會。我挑選一個看似很挑戰大家常識神經的題目——中山北路,進行論述工具與觀看視角上的冒險。但與其說我有什麼理論建構上的野心或企圖,實在不如說,我對於中山北路長期以來在大眾常識上所累積的集體情緒與樣態,太過好奇,我想找個可以說服我自己的詮釋方式,來理解這樣的集體意識是怎麼一回事。
我相信,這個「好奇」,本身便是值得探究的。但召喚讀者願意跟隨我的觀看視角重新認識中山北路地景所內蘊的後殖民意涵,應該是此一論述實踐的莫大期盼。因此,在後面篇幅裡,我盡量把「詰屈聱牙」的理論辯證部分簡化,以期在歷史閱讀的沈重裡,偷得一點點文本閱讀的愉悅。
II
這個研究的起點是中山北路的地景變遷,但在這個問題意識的起點上,同時也是對台灣國族主義論述中性別化意涵及性壓迫結構的質問。
我的基本論點是,我們均處身於一個不加省察的權力脈絡下,共同結構了這個社會的權力網格,並共同維繫其運作不墜,這也就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強調,社會同意(consent)乃是構成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得以在既定社會中支配性地位的關鍵。特別是歷史地來說,雖然我們能夠逐漸習得從不同的社會群體與邊界位置,舉凡階級、族群、性別、性取向等等主體位置來觀看權力運作的邏輯,但一直潛藏在我們社會集體意識中的殖民記憶,事實上已經累積了過多的能量,實質地掩蓋了我們對權力意識運作模式的感知能力——權力慾望投射方向已然確立,若我們欠缺歷史性的觀照,必將難以連結殖民力量歷時性地對不同社會界限編派的滲透;因此,我企圖透過解析兩者之間相互交織與穿透的作用,以從批判既有性∕別權力關係的觀看角度,重新詮釋戰後迄今的這段歷史。換言之,我嘗試在這個文本中建構另一種觀看角度的地景詮釋歷史。
從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分枝發展而來的地景研究,對「地景」(landscape)此一意念提出批判指出,「地景」並非只是以往自然地理學家眼中的地表形貌,或是經驗上的、物質化的客體,而是一種文化再現的形式,「地景是一種文化想像,一種以圖象再現、結構或象徵環境的方式。」(Daniels and
Cosgrove,1988:1)。不論是寫作或繪畫、自然生長或是人工建造,地景意義來自其所由生之社會的文化符碼。這些符碼是深藏在社會權力結構中。
考斯洛夫將地景描述為一種「視覺意識形態」(visual ideology)(Cosgrove, 1984),是一種「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們依其所在之社會與視覺位置來觀看與理解地景,並代表了某種偏差的世界觀。……(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