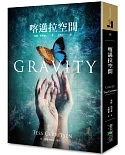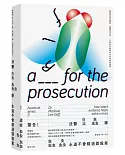正義與人性的界線:說書者的抉擇
莎拉?派瑞斯基
美國知名犯罪小說家。1947年出生於愛荷華州,在堪薩斯長大,擁有堪薩斯大學歷史博士和芝加哥大學財經MBA學位。1960年代末移居芝加哥,在金恩(Martin Lucher King)博士籌組民權運動的所在地從事社區工作,同時在保險公司擔任行銷經理。1982年出版第一本犯罪小說《索命賠償》(Indemnity Only),打造出知名的冷硬派女偵探維艾?華沙斯基(V. I.
Warshawski),立刻引起偵探迷的廣大回響,並於1988年以同系列小說《Blood Shot》贏得英國犯罪寫作協會的銀匕首獎,作品暢銷世界二十一國。派瑞斯基對於獎勵學子不遺餘力,曾在堪薩斯創立兩個獎學金,並在芝加哥內城的市立學校助同儕指導,1986年與友人共同創立了犯罪寫作姊妹會(Sisters in
Crime),幫助其他有志寫作的女性,並出任第一任會長,該協會目前在全世界擁有三千多名會員。1996年,因她對中西部文學的傑出貢獻贏得馬克.吐溫獎。除犯罪小說外,也撰寫短篇故事和散文,目前專職寫作。其他重要作品包括:維艾?華沙斯基系列的《奪命碼頭》(Deadlock, 1984)、《Killing Orders》(1985)、《Bitter
Medicine》(1987)、《Burn Marks》(1990)、《Guardian Angel》(1992)、《Tunnel Vision》(1994)、《Hard Time》(1999)、《Total Recall》(2000)、《Blacklist》(2003)、《Fire Sale》(2005),小說《Windy City Blues》(1991)、《Ghost
Country》(1998)、《String Out》(1997)等。
幾個月前,我收到一封讀者來信,她憤怒地寫滿四張信紙,質問我為什麼我的書裡「寄生了」政治議題。她這樣寫著:「當我買推理小說時,我要的是娛樂。但是在妳加入有關遊民的議題之後,妳並沒娛樂我。」
我想要回信跟她說,推理小說是很政治的。彼特.溫西爵爺(Lord Peter Wimsey)1堅定地捍衛著英國這塊土地,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安居樂業。菲力浦.馬羅(Philip Marlowe)和山姆.史培德2活在一個充滿性政治的世界裡。如同馬羅在《小妹》(The Little Sister)中抱怨的: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筆下的女人都有性的臭味;達許.漢密特(Dasbiell Hammett)筆下的女人,例如布麗姬.歐香尼西(Brigid O’Shaughnessy),則都會引誘好男孩做壞事。但是馬羅和史培德對這些女人來說都太教條了。
推理小說就像警察故事一樣,恰好就處在人性最原始的根本需求與法律和正義的交界之處。推理小說在定義上是很政治的。這也是我喜歡書寫和閱讀它們的理由之一。
不過呢,由於這問題實在一言難盡,所以到最後,我還是像平常對付憤怒的讀者那樣,把那本書的錢寄還給那位女士,然後繼續我的工作,也就是做一個說故事者,一個作家,她的故事是發生在法律、正義和社會的世界裡。
後來,當我在蒙加哥紐波瑞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辦讀書會時,我又想起了這位來函讀者。當時有一群女士,總共九位,在其他人都離開會場之後還留了下來。然後她們告訴我,她們嫁給煉鋼工人,他們的男人已經失業十多年了,因為全球化經濟把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往國外送。這些女人每人得兼兩份差以維持生計。那些都不是什麼偉大的工作。她們有的是便利商店的收銀員,或是小餐廳的女侍。她們告訴我,自從高中畢業以後,她們就沒讀過什麼書,一直到她們當中有個人從收音機裡聽到,我的偵探小說的女主角,維艾?華沙斯基(V.
I. Warshawski),也是來自她們那個街區,南芝加哥。維艾也是在鋼鐵工廠的陰影下長大。雖然她是個藍領階級的女孩,但她拿到獎學金進了芝加哥大學。這些女士們說,在她們讀到我的書之前,她們從沒想過居然會在某本書中看到她們自己的生活。「我們都買精裝本。」其中一位這樣說。「維艾幫助我們面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可怕事情。」
我的第一個衝動是想說:不要,不要把妳們辛苦賺來的錢花在精裝本上。但是幸好,感謝上帝,我沒有脫口而出,因為我看得出來,買書是一個重要而有形的試金石。
我的第二個比較下流的衝動是:回去寫信給那位來函的女士,我得告訴她,看吧,這就是重點:我是一個說故事者,我是一個表演者,但是我訴說的故事一直都是屬於那些沉默的人群,而非權勢者。這些南芝加哥的女士們從中得到了娛樂,因為她們可以從無止境的工作、從家事、從憤怒沮喪的先生、從失業的青春期兒子、從早婚卻無謀生能力的女兒身上,逃開幾個小時。我的書娛樂了她們,同時也給了她們勇氣。
我不喜歡社會政治小說,寫那些書只是為了要證明四條腿的比兩條腿來得要優秀,或者,男性都是受睪丸素制約的壞蛋,或者女性一貫地用身體來推翻男性道德觀。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作家最為人所知的是巴斯特納克(Boris L. Pasternak)和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而不是哥禮巴契夫(Gribachev),他是《勝利集中農場之春》(Spring in the Victory Collective Farm)的作者。巴斯特納克可能想要點出一個最廣為人知的重點,那就是有關人類自由,有關個人在社會變遷中所感受到的迷惑,以及該如何應對這些迷惑有多困難。但他想要描寫的對象是紅塵中的人類,而不是理想的政治典型。
我不會坐下來寫社會或政治評論的書,身為讀者和作家,我是跟著故事走,而不是跟著意識形態跑;我在周圍人物的故事中看見這個世界。只不過,最能吸引我的故事,正是那些無法為自己說話的人,就像那群來自南芝加哥的女士。可能所有作家在寫作時都是因著一股邊緣人的感覺。的確,這對說故事大師狄更斯和艾略特來說,也是如此,而我應該也是。
我生長在五○年代的東堪薩斯,一個被當代道德家指為美國黃金時期的時空,那是在越戰、毒品、女性主義,以及黑人力量動盪世界之前。
那時候,我們女孩子知道婚姻是我們不可避免的命運,當時只有壞女孩才會未婚生子。我是一家子男生中唯一的女生,我的父母──只要一提到宗教或是公民權利的事,他們就成了這塊基督教和共和黨土地上古怪的局外人──嚴格地遵守他們的性別政治。家庭對我個人來說尤其是這樣一個地方,在那裡,我的價值只存在家事和照顧小孩之中,教育是屬於男孩的,與我無關。成長的過程中,我幾乎都是用低於耳語的音量說話,非常害怕我的所言所行會引來任何批評。同時,為了我所創造的女主角以及我所讀到的故事,我很早就鑽進故事的世界,進入公主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生活的世界。
我第一次逃脫那個環境是在六○年代晚期,我來到芝加哥。那年夏天在芝加哥,受人尊敬的金恩博士為了開放住宅和同工同酬的理念而推動組織。我在這個城市的南邊從事社區服務工作。當時他正在組織的地區,很靠近我被派去的那個藍領街區,裡面住的幾乎都是立陶宛人和波蘭人。
那年夏天,該區居民的恐懼轉變成憤恨,他們在馬奎公園(Marquetce
Park)裡丟瓶子和燒車子,讓白人因此賤價售出他們的五房住家、倉皇逃到西部郊區,不管當時或現在,我都不曾為那股恐懼做過辯護。但即便是在我只有十九歲的時候,我也看得出來,無論是銀行、房地產仲介公司或是市政府,全都毫不關心聚集在那些狹小平房裡的夢想或恐懼。我四周的每個人都感到無力,黑人拒絕工作和體面的住宅,剛躋身到經濟階梯中上層的白人,則驚慌地緊抱住這個階梯不放。
那年夏天,我感受到一種迫切的需要,想寫下那些無聲之人的生活。那年夏天過後,我不再想像從此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公主。我開始寫那些平常人,他們的生活像我的日子一樣充滿混亂失落,因為他們沒有聲音沒有力量。即便如此,當時的我仍覺得我是不該發聲的,我又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才試著賣出我的作品;我是如此受到堪薩斯那段孩童時期的教化所影響,我無法想像我能摒除那個家庭的影響而從事寫作,也無法想像我的文字能和其他人溝通。
狄更斯從最遙遠的邊緣──債務人監獄──往維多利亞時期的中心,然後成為當時最傑出的人。豪宅、僕役、貴客、高價巡迴演講和五位數的合約,這些從來沒給過他安全感,它們也沒為他模糊掉維多利亞富庶的基礎,那份富庶是建立在一大堆營養不良、缺乏教育的流浪小孩和血汗工廠上面,因為最卑微的貧窮壓力導致犯罪率節節升高。
狄更斯將窮人的美德傳奇化,但他並不為他們的貧窮景況感傷。就如同我那位來函讀者所寫的,他的書寄生了很多社會政治,但是數以千計的人仍在波士頓的碼頭邊排隊,等待那艘運來他的連載作品的船隻入港。
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過著富足的生活,而且清楚地知道有一大群無家可歸的孩子正在我們眼前遭受營養不良和教育不足之苦;那頭大象就在客廳而我們都裝做沒看見。在我的祖父母一起替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走上街頭示威的一百年後,就在我們這塊偉大的土地上,仍然有血汗工廠存在。我們還是有犯罪,有無家可歸的人,有為了一點錢賣掉自己小孩的父母,還有一大堆的不幸。如果像狄更斯那樣的說故事大師都是在他的環境中找到最令人注目的故事,我又有什麼資格可以對它掉頭不顧?
注釋:
1 彼特.溫西爵爺,英國推理小說家桃樂西.麥兒絲(Dororhp L. Sayers)筆下的末代貴族業餘神探。
2 馬羅是美國推理作家雷蒙.錢德勒筆下的偵探;史培德是美國推理作家達許,漢密特所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