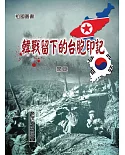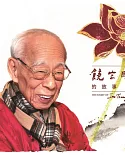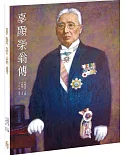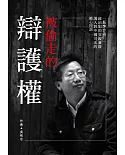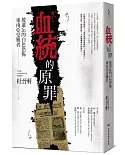「解構而未造成人心瓦解」的族群研究典範
身處於解構的年代,是一種福氣,也充滿著挑戰。我們慶幸自己不再被「教科文本」(text/textbook/textualized
literature)所限制,眼睛變亮,膽子增大,四處敲打學術或社會慣習的門牆。結果,有的被破門後,散成一團,文字打手只管無情地打爛架構,卻不知有情地新建「後文本模型」,可能也是功德一件。自此,好長一段時間內,「文化體」崩解,「族群」範疇浮動,「社區」領域糢糊,個人認同突然也變得神經兮兮,自己懷疑自已。解構解了制式威權論說,大快人心。但是,作為文化體、族群、社區、及個體組構因子的「人」,即使親眼看到了去教本化(de-textualizing)身分配屬(identity
classification)學術社會運動的馬到成功,多數卻在學者們驕傲於自我成就的場域之外,心底惶惶,嗷嗷待哺於往下怎辦的焦慮(如泰雅、太魯閣、及賽德克的分合之爭)。換句話說,他人幫忙解了構,自己的「我是誰?」或「我們是誰?」之困,卻立即現身成為生活思想上的大難題。
大浪潮鼓動之下,Michael Moerman對泰北Lue人,Charles F. Keyes對Thai與Lue,Dru Gladney對回族,Almaz Khan對蒙古族,謝世忠對邵族,及王明珂對羌族,紛紛提出了「到底誰是(Who are)某某族?或某某族是什麼(What
are)?」的解構性問題。繼之,本書作者慈濟大學人類學碩士賴盈秀小姐在其畢業論文上,也問到「誰是『賽夏族』?」很顯然,盈秀並不滿意「賽夏族」傳統的制式族群內容說明(即,總是籠統地說,該族一方面與泰雅相近,另一方面又可能受平埔道卡斯的影響),因此,決定以充分的田野證據,來解開賽夏組構之謎。她的努力,終於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不同的文化系統如何進入賽夏社會領域範疇,又如何以氏族的祭儀專利和角色扮演,來作合「合」(即賽夏全族)中有「分」(即氏族的社會文化分立),「分」中見著歷史過程(即各氏族的相異文化祖源)的內在事實。盈秀與上述「反制式文本」熱潮和列舉學者一樣,基本上是在解構固化了的國家少數族群。不過,她始終是充滿對族群認同的敬意和友愛之心,因此,解構經由她手,不僅未生困頓,反而解了文化史和遷移史的困惑。
盈秀強調,她從不懷疑現今賽夏的事實存在,對該族在近現代被建構之後,造成族人越來越向心的單一族裔認同,自是完全的尊重。她的解構並不如一般解構論者多以「虛構」一解,來涵蓋眼見觸及的政經文化現象。盈秀所要澄清的是,今天的賽夏必有其身為台灣原住民十二族之一的全族「共同性」,而那理應就是當下的「賽夏」認同。在此一前提下,我們解剖賽夏內容,方可安然理得,找到了該族內部絲絲條條的歧支異源,也不會使其現今生活整體性,有任何的解崩之虞。反而,讀者們,當然也包括賽夏族人在內,必定對竹苗山地平坡人群流動的活躍事蹟,以及原住民建成族群家園的精彩歷程,留以深刻印象。
賽夏族源多重,盈秀逐一點出了點地。由於研究者謙遜有禮,又富科學求真精神,復加上全族共同有一根深耀眼的矮靈祭,因此,不怕「後來的」氏族讀了報告而告別認同,也不擔心特定祭儀中「次要的」氏族或「被隔離的」氏族,翻翻書,驚覺自我位置,從而心生不滿嘆曰不如歸去。盈秀的文字,只有豐富賽夏的歷史書寫,而不會使人產生「心底惶惶,嗷嗷等待新版認同的焦慮」,這是解構時代中的新倫理典範。深度的田野,以及金蘭誠心,早已使盈秀成了賽夏族中的「自己人」。在族人信任喜愛中,遨遊族群文化天地。盈秀擁有多數解構者少見的福氣,而她對自我的挑戰,更塑形了另一種人類學研究的參與觀察典範。
認識盈秀已有多年。五年前(一九九九)因緣巧合聘其擔任「台灣原住民影像民族史:賽夏族」撰寫計畫的兼任研究助理,方才慢慢瞭解這位意志堅定的女孩。初聘不數日,正值賽夏矮靈祭時分,兩人同往參加,當教授者職業性地試探一下宣稱自己對賽夏非常有興趣的新任助理,於是臨場問了幾個問題。記得那時對盈秀的回答,並不是挺滿意,只覺「這個學生還待訓練!」如今,過了將近一千九百個晝夜,盈秀在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先進學長教授同仁的培育下,學業突飛猛進,更完成了作為學位論文而且意義非凡的本書。看到女孩的成長,尤其又見其樹立了「解構而未造成人心瓦解」以及「和當地住民有如自家人般的身處田野」兩項典範,個人心中的感佩難以形容。受盈秀之託寫一序言,上文零零總總,就是想表達曾為她工作「上司」和有幸在明媚花蓮參與其論文口試的一份絕對驕傲。
好書人人爭相睹閱,可敬的族群大家一起認識他們,真誠的作者妳(你)我更不應忽略。總之,若欲深度了解原住民,或是覺得台灣族群關係史實在有趣,那麼趕快來看賴盈秀小姐的大作《誰是「賽夏族」?》就對了。
謝世忠 寫於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2004年10月11日 5:19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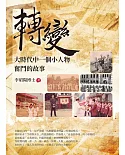

![台魂淚(一):我的半生記[軟精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91%2F51%2F0010915131.jpg&width=125&height=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