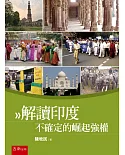作者後記
我對共產中國經濟的研究發生興趣,是始於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任職的時候了。該大學收藏了很多珍貴的書籍,百忙中我每星期總要花上幾小時在那裡的東方圖書館參閱。當時我正全力在產權經濟的理論上鑽研,很想知道共產制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碰上中國大陸的文革一個史無前例的、最極端的共產政制--搞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就希望能在一些大陸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一些啟示。
很不幸,我翻了六大本關於大寨、四大本關於人民公社的書(是日本所編輯的大陸文章),頁頁都載滿了「偉大」的術語,書中除了對毛澤東歌功頌德之外,內容空泛,不著邊際,使我白白花了兩個月的工夫也一無所獲。其他的大陸報章及有關資料更令人反胃。可以說,在那時,我對中國大陸經濟的研究,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同一時期在美國出版的多本關於共產中國經濟的書,都不值一看。可不是嗎?我自己懂中文,能找到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尚且不明大陸的真相;而這些書的作者,只靠著數字圖表之類的「陣勢」,又怎能言之鑿鑿呢?我想,這些書都是廢物!當時不僅我個人是這樣想,其他較有份量的經濟學者也是這麼想。過了不久,經濟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研究失郤了興趣,多個學術基金會都一致地不支持有關的研究了。
是的,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整整二十年間,比較可靠的有關消息,還是得自那些生活於中國大陸的親戚朋友的見聞。我所聽到的每一件關於那裡經濟的事,都使人不寒而慄。雖然我希望那些傳說並非事實,但五花八門的恐怖傳聞如出一轍,其間並無矛盾、可疑之處,於是在心底裡我知道:中國大陸是真的陷於不幸的困境中了。一個慣於作實證研究的人,對資料與資訊的真偽,有外人難以理解的觸角,知道信口開河的資料是犯駁而站不住的。同類可信的恐怖傳聞聽得多,久而久之,就變得麻木了,對中國大陸也就失郤了希望。
因此,到了一九七八年,那裡有比較明顯的開放跡象時,高斯與佛利民(編按,台灣又譯傅利曼)不約而同地希望我能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做點研究工作。我感謝他們的關懷,但提不起興趣。話雖如此,一九七九年夏天,我還是回到廣州及佛山去看看。這是一次難忘的旅程。所到之處,滿目瘡痍,二十多年沒有見面的兩位姐姐還是把我看作小弟弟般的款待我。而事實上大家都老了,提起以往,她們一字一淚地訴盡心中無限事。我也趁便到佛山的英華校址(現名為佛山一中)一行。從一九四五年至四八年,我曾在那裡讀過小學,睹物思人,向校長問起昔年的老師與同學:我提出五、六個人的名字來,所得的回答,都是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就不再問下去了。
不管怎樣說,共產政制的經驗,確是不堪回首。在那次的行程中,我向親戚朋友問了很多關於以往的事,問及他們現在(一九七九)的改進,也看到好些普通人的現實生活與幹部的作風。於是,我對共產制度開始有些理解,雖然比較深入的體會,還是後來在多次的旅程與觀察中才能得到。
一九七八年,我曾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術社寫過一本關於共產經濟的小冊子。他們知道我在七九年到過中國大陸,就急不及待地要我寫一篇題為的短文。我左「推」右「搪」了很久,結果還是在八一年執筆,寫了初稿,長達數萬字,他們在八二年以小書的形式出版。我反對用「資本主義」這一詞(他們堅持要用),不過,我郤推斷了共產中國會走向近乎私有產權一般人認為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那小書內,我推斷在中國大陸會發生的事,可說「百發百中」了。就這樣,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個「中國專家」。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是本書的第二部分。這中譯是不夠完善的。翻譯有時比創作困難得多,更何況譯文的初稿不是由原作者親自動手的。但我認為,對中國大陸經濟有高度興趣的讀者,最好先讀這一篇長文,且不妨多讀幾次。
�在白紙黑字上推斷了什麼會發生,就如買了股票下了注的人一樣,當然對有關的一切特別留心。此所以,從一九八二年起,我對中國大陸的改革,以及改革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困難,不斷地觀察、調查、思考;也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上寫過八、九十篇文章。
�拙作的《賣桔者言》一書內,與大陸有關的題材,雖然幾乎佔了一半,但正式針對大陸而寫的文章,還是由此書--《中國的前途》--開始。八四年十月至八五年五月的七個月內,我一共寫過二十一篇。是當時最後的一篇,可說是我心目中的代序,故置於本書之首。其他二十篇我就不再分門別類,而以發表時的先後來處理了。
張五常
一九八八年秋天 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