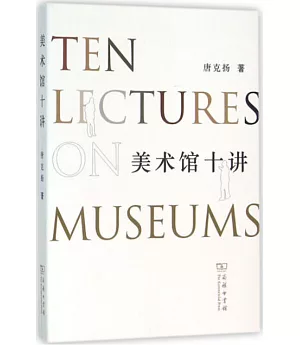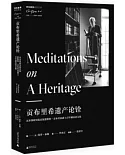《美術館十講》是作者唐克揚作為對現當代藝術理論頗有功底的建築設計師,在過去的數年中搜集大量有關中外美術館資料的基礎上,對美術館這一「文化實體」所進行的鞭辟入里的解析。
《美術館十講》可以作為當代美術館建築的一本入門讀物,它並非就美術館的建築作品本身泛泛而談,也不試圖定義美術館是什麼。
相反,本書將視角對准作為一種文化意象美術館,提出了十個與美術館相關的話題,細述其在當下中國語境、藝術史、現代城市文明乃至中西文化比較等題域中的獨特意涵。通過對美術館建築與城市文明的互動關系,切入現代藝術思想史的核心——個體創作與公共生活之間的關聯、藝術與自然的互動,時間與空間的交錯。
本書將為美術館的策划,建設與使用提供有益的參考。
唐克揚,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芝加哥大學獲藝術史碩士,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獲設計學博士。他既從事策展和學術研究,也是一位建築設計師。主要展覽包括在故宮舉辦的的”典藏與文明之光”特展,2010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國館,以及在奧古斯都的夏宮舉辦的”活的中國園林”特展等。作為一位有着跨學科背景的實踐者,他的作品從展覽策划、博物館空間設計到建築史和文學寫作,有着別具一格的多樣性。他目前主持着中國美術館的建築與藝術研究項目,並在數所大學任教。已出版《從廢園到燕園》《紐約變形記》等。
目錄
緣起
美術館之路
1 「潛影」
中國美術館的前生今世
2 從市場到廟堂
西方展出空間小史
3 美術館的建築類型學
「高等建築」和大眾藝術的啼笑因緣
4 「看」的藝術
空間里的美術和圖像
5 行動的藝術
心,眼,手,腿
6 當大師遇見大師
建築和藝術的遭遇戰
7 輕如泰山,重於鴻毛
展覽空間的物質性和非物質性
8 自然中的藝術,自然中的建築
是世界展覽了我們,還是我們展覽了世界
9 美術館和記憶
時光是無盡的展線
10 去美術館吃早餐
城市中的特殊空間
尾聲
中國明天的美術館
美術館之路
1 「潛影」
中國美術館的前生今世
2 從市場到廟堂
西方展出空間小史
3 美術館的建築類型學
「高等建築」和大眾藝術的啼笑因緣
4 「看」的藝術
空間里的美術和圖像
5 行動的藝術
心,眼,手,腿
6 當大師遇見大師
建築和藝術的遭遇戰
7 輕如泰山,重於鴻毛
展覽空間的物質性和非物質性
8 自然中的藝術,自然中的建築
是世界展覽了我們,還是我們展覽了世界
9 美術館和記憶
時光是無盡的展線
10 去美術館吃早餐
城市中的特殊空間
尾聲
中國明天的美術館
序
緣起
美術館之路
似乎任何和「文化」緊扣的事體,都免不了一方面充滿魅惑,一方面又需要冷靜的眼光和反思的頭腦,「美術館」這樣事物在二十世紀末中國的興起也是這樣。
人們總想賦予美術館明確的定義。可是,變成一個經意構造的文化場后,它不僅賦予人群某種共識,籍此也彰顯了他們分歧的世界觀——就像結晶的過程,一旦晶體從飽和溶液中析出了,它看上去就和它的環境顯得如此的格格不入。當代中國藝術的理論聲稱讓文化植根於它生長的土壤,在實踐中卻時時將它帶離這個星球。在西文世界里,「博物館」似乎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物,人們的心目中,「museum」和「fineartmuseum」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區分,但是中國現下的「美術館」相系的確實是一類特殊的人群和特殊的風尚,就算是古代文物,一旦成為「美術」和「藝術」,放在「museum」里面陳列之后,它也斷然染上了別樣的色彩。
在「藝術圈」的忙碌人群中是看不到美術館之外的世界的,因為他們的眼光免不了還是種孤芳自賞,套用那句大俗話,他們「不在美術館,就在通往美術館的路上」。
我在生平的第二十二個年頭才有機會走在這樣的路上,那是在如此的文化方興未艾的時節。我還記得那是校尉胡同的老中央美院,一個寒冷的冬天,從北京大學所在的海淀區到王府井,需要搭乘公共汽車,轉換2號線地鐵,然后再步行一段,才能找到我所想要去的展廳。中央美術學院毗鄰美國傳教士在二十世紀初葉設計建成的協和醫院,由張開濟在三十多年后設計建成的校舍的風格與之類似,它折衷中西的空間和美術展覽的功能似乎並不完全匹配,但是跨進展廳的那一瞬間,必須說,我着實感受到了后來我在各種「museum」中體驗到的東西。空間里的氣氛是我不熟悉的:外省青年和優雅的藝術家「女主人」的短暫目光交接,是好奇心和好奇心的碰撞,但是其中並沒有什麼交流的可能性,不時有路邊的過客掀開棉布簾子進來,卻很少有熟人間的對話,人們沉默地進入,又沉默地離開,我翻開展廳的留言簿,並沒有看到什麼針對作品本身的只言片語。
通往美術館的路是會是有前提的——這樣的造訪不太可能僅僅是偶然,在我們與它相約之前,我們必須問自己這樣的問題:美術館在哪兒?我們究竟要在美術館中看到什麼?大多數美術館並不「事先」存在,在它們匆忙地建成之前,或者在與它們不期而遇之前,大多數人對這類文化空間的功能並無太多心理預期——至少對於大多數非專業的觀眾而言,觀摩「原作」的現場並不如身臨「藝術」的現境更重要,因為很少「原作」的意象會在他們心中牢牢扎根,他們來到美術館其實是看人,而不是看作品。尤其是在當代中國,美術館已經成了一種混雜的主題公園樣式,或者,套用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Morris)評論紐約的話說,在此美術館是一個圈養着人類的動物園。
對一個來到陌生城市的訪客而言,美術館首先是一個顯赫的地點,它占據着大多數西方城市的中心地位。20世紀,當中央公園在1817年紐約規划中的密仄格柵中卓然自立的時候,這塊特殊的城市預留地里唯一的大體量建築物就是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有類似情況,「中環」(loop)湖濱的密歇根大道以東沒有任何建設,只有芝加哥藝術學院的陳列館(芝加哥藝術館)。更不用說那些年代更為久遠的歐洲美術館,在柏林的老城城址上建成的老國家畫廊得之於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直接授意。建成較晚的美術館不一定能擠進寸土寸金的市中心,但即使如此,它們依然被當成都市復興或是縉紳化(urbangentrification)的重要手段:從一開始,由妹島和世設計的紐約新美術館就被當成改造向來破敝的包厘街(BoweryStreet)地區的關鍵環節。
但是這個地點是一個模糊的地點,美術館只有成為一種形象(image)之后才能更清晰地在城市中存在,也方便訪客的識途。西方建築學之中,建築物的形象首先是指它的外部「立面」(façade)。這種外在的「形象」和我們在藝術史中所說的「具象」(figure)是有區別的,建築和藝術——自然主義或非自然主義的藝術——的很大不同,在於它不以「相似」為意,對於凱文•林奇(KevinLynch)而言形象就是「個性,結構和意蘊」的綜合體。形象,是因特定意涵的「觀看」才從懵懵懂懂的環境之中脫離出來的,由於某種「如畫」(picturesque)的品質和內涵使得觀看的主體和客體彼此脫離,城市不再均質。在這個意義上的美術館不僅和當代藝術也和古典藝術有關,后者更強烈地表達了「框外」和「框內」的不同涵義,暗示了凝視(gaze)的文化根基所在。
自然,當代的美術館設計已經不拘於靜態的、二元的「觀看」了,比如瑞士建築師彼得•卒姆托的名作布列根茨美術館,在那里建築被有意識地遮蔽,卻又並不完全封閉,由於半透的,濾鏡式的建築表皮,它的形象現在是一種介於有和沒有之間的存在,雖然不能使你看到什麼卻的的確確改變了你的「看法」,這點和古典建築並無二致。所以有形的「框景」(framing)之后緊隨着無處不在的「成像」(imaging),它們都是當代美術館的核心觀念。
由於這種確鑿無疑的形象的魅惑,美術館本身成為美術「作品」的一種形式——也許從此開始,我們應該更加考究我們的用詞了,除了「美術館」和「博物館」的區分,到底是「美術館」還是「藝術館」?每種表述都有特定時空的前提,它們使得「看見」和「看到」成為不同的「看法」——對於一個造訪者而言,僅僅是「看見」是沒有意義的。
在中國,只是最近人們才更多地提到「藝術」(art)而不僅僅是「美」術(fineart)。就像英文里博物館不易和美術館區分一樣,「美術」領先「藝術」率先出場,反映出中國美術館內向、遠離的原初語境。現代教育家蔡元培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在解說了「美育」比「美術」更宏闊的基礎上,他提到起教化作用的美育「使參與的人有超出塵世的感想」——就像反對此說的呂澄所言,如此的「美術」觀是「人生的反面」,是現世中的孤島;相信「美術是上流社會的宗教」(王國維)的人們,一開始就讓美術館中的公共性有些匱乏。
於是,中國的「美術館」聽起來就是演奏室內樂的音樂廳,而不是奧林匹斯神廟露天的半圓形劇場;更有甚者,由於中國傳統建築和城市特點的習染,它既缺乏清晰可見的「立面」,也沒有內部的空間層次而導致的截然的「透明性」。在不知當代藝術為何的前提下,大多數中國建築師筆下的當代美術館是孤懸於城市中的封閉的堡壘。
現代城市中的美術館不再是獨立的飛地,它和城市的聯系值得細究。首先,「城市」是復數的系統,美術館輻射周邊區域,它們既是人心的海洋中的離島,也是城市文化交通中的經停站。不用說華盛頓的mall,柏林的博物館島,即使在紐約這樣的私人城市,大都會博物館的周邊也有星羅棋布的畫廊。這也就是為何藝術總喜歡在「藝術區」中存在,強調個性的藝術家們卻總愛「一起孤獨」——除了「城市中的美術館」也可能是「美術館即城市」,除了由眾多單體湊成的大型「系統」(SoHo,798),在自身規模也日益膨脹的當代城市中新建的大型「藝術綜合體」也越來越多了,按照庫哈斯的說法,當代空間中的「大」(bigness)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在其中藝術展示並不一定是唯一的、最主要的功能。
對於我們篇首所提到的那種「人工文化」而言,傳統歐洲城市的小型城市組織已經不敷使用了,新的「大」並不追求和它的環境協同,因為它自身就構成了自身的情境。只要自身的規模容量足夠,美術館成為「析出的晶體」並不是什麼壞事,它的形象越飽滿鮮明,它對於城市的貢獻就越大。
如此,在大都會的茫茫九衢中,一個來訪者找到這樣的美術館也許並不算難,難在如何得其門而「進入」。無論如何,對於每個個體而言,美術館不僅是一個地點,一種公共形象,一個場域——以上都是以「集體」的面貌出現的——也是一個具體的「終極的空間」,而且是一類「私人空間」,需要落實到單數的眼睛和心靈。這樣的空間並不排斥其它的屬性,例如它也自有它的「形象」,也許是某種隱約其辭的「私人形象」——但是「私人形象」這個說法聽起來又是不易成立的。
它揭示着美術館與生俱來的自我矛盾性,甚至大多數人所鼓吹的「公共性」的滋生也莫過於此:公共性恰恰產生於當代社會對於個性的承認,但是藝術對人們心智的系統催化卻又不能不籍由某種體制化的方式來完成。由集體和個性之間的搖擺,當代美術館既是大街上的響亮宣言,也是一個陶冶性情、沁潤其中的容器,它最終的包容性難免隱藏了它着力揭示的社會矛盾和沖突。
除了它顯見的庄嚴和喧囂,美術館的深處其實有個不可見的虛空,那是一類靜默的、思考的空間,這是不太引人注目的方面。從初次跨進校尉胡同的老美院展廳的那刻,我就發現了這個秘密;表面上「公共」的當代藝術,其實又立即是羞澀的和「私人」的,在藝術和觀眾之間有些話未便當面提起,需要轉過頭去交代。
於是,美術館自身也是一條引領人們心智的道路——我們談到的「道路」不僅僅關於長途跋涉到它門前的那條。在傳統的想象中美術館是一座萬水千山外的聖殿,貝聿銘設計的美秀美術館,需要換乘好幾種交通工具才能到達,最終還只能步行進入,它便是如此聖殿的典型事例;可是,在當代城市中,為了打破靜態的展示和動態的生活之間的壁壘,人們不能不時刻「穿行」在美術館所創造的思想領域之中,不光是專程去那里朝聖。這種貌似不可思議的「穿行」有那麼幾個辦法:
——美術館不僅是一個抽象的地點(locale)也可以是一個有其廣度的場域(field)(如此就可以把「點」和「面」合為一體);
——美術館的「形象」不僅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內在的(如此就打破了集體和個人之間的樊籬);
——美術館不僅是一種特別的文化空間,也是一種文化事件的統稱(如此,既可以在美術館,也可以同時在去美術館的路上)
大眾心目中的美術館似乎和「畫」綁定,它本身的建築類型甚至被稱為「畫廊」(gallery,准確地說,英文的「galleria」,暫且翻譯成「藝廊」,並沒有「畫」這個字面含義,把它和「畫」拉上關系又體現了中文的情境),可是,和通常想象的類型學不同,「畫廊」其實並不能導致一種「畫」的至上地位,當代的美術館不再是一種「靜觀」,觀眾觀看的方向和行進的方向總是互相垂直,使得傳統的自然主義藝術的幻覺性再現失效。美術館不再是一座「私人的萬神廟」,一座充滿而盈溢的容器,不斷曲折導引的道路,讓這容器的意義出漏了。
「路」可能是藝術史最青睞的題材之一,羅馬人的早期壁畫或是達芬奇的明暗風景里通常畫不出清晰連貫的小徑,當「空間」在「運動」中浮現時,古典繪畫的主題就為觀眾可以追隨的幻覺性道路所鎖定——無論是霍貝瑪的《楊樹林蔭道》列維坦的《弗拉基米爾之路》還是我們熟悉的《毛主席去安源》。可是恰恰是展示這些作品的「畫廊」把觀眾的身心拖離了這些道路——兩條路,一條是眼前,還有一條是現實中的,一條是冥思之路,另一條則是不得不面對的當代文化的事實:人工的「藝術」所營就的特殊的儀式性場所,已經和世俗性的人生走向分離了——隨性而聚,亦隨風而散。
這就是篇首我們提到的那種情形的意義,人們並不是因為走向美術館才變得「文藝」,在開始這條追尋之路之前,他們的生活已為另一種更大的情境所鎖定,你可以說這種情境是「非」美術館的部分,但你也可以說,美術館之路從那里就已經開始。
除了展覽之外,一個大型美術館的功能至少包括以下的部分:沉思(最「高級」的選項),教諭(最「民主」的美術館也不會去除這一項),教育(平等的「教育」和「教諭」往往相反),交流——最后這一項被看做當代美術館的最新發展。就在可見的將來,或許會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樣的風尚,在美術館吃個「知性的晚餐」和「在蒂芬妮吃早餐」一樣通俗。用不着特別驚奇,這些「逛美術館者」(museumgoer)根本用不着去「看展覽」。
對大多數走進美術館的人們而言,他們只是不停地走過某些作品,最終將它們統統遺忘。
美術館之路
似乎任何和「文化」緊扣的事體,都免不了一方面充滿魅惑,一方面又需要冷靜的眼光和反思的頭腦,「美術館」這樣事物在二十世紀末中國的興起也是這樣。
人們總想賦予美術館明確的定義。可是,變成一個經意構造的文化場后,它不僅賦予人群某種共識,籍此也彰顯了他們分歧的世界觀——就像結晶的過程,一旦晶體從飽和溶液中析出了,它看上去就和它的環境顯得如此的格格不入。當代中國藝術的理論聲稱讓文化植根於它生長的土壤,在實踐中卻時時將它帶離這個星球。在西文世界里,「博物館」似乎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物,人們的心目中,「museum」和「fineartmuseum」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區分,但是中國現下的「美術館」相系的確實是一類特殊的人群和特殊的風尚,就算是古代文物,一旦成為「美術」和「藝術」,放在「museum」里面陳列之后,它也斷然染上了別樣的色彩。
在「藝術圈」的忙碌人群中是看不到美術館之外的世界的,因為他們的眼光免不了還是種孤芳自賞,套用那句大俗話,他們「不在美術館,就在通往美術館的路上」。
我在生平的第二十二個年頭才有機會走在這樣的路上,那是在如此的文化方興未艾的時節。我還記得那是校尉胡同的老中央美院,一個寒冷的冬天,從北京大學所在的海淀區到王府井,需要搭乘公共汽車,轉換2號線地鐵,然后再步行一段,才能找到我所想要去的展廳。中央美術學院毗鄰美國傳教士在二十世紀初葉設計建成的協和醫院,由張開濟在三十多年后設計建成的校舍的風格與之類似,它折衷中西的空間和美術展覽的功能似乎並不完全匹配,但是跨進展廳的那一瞬間,必須說,我着實感受到了后來我在各種「museum」中體驗到的東西。空間里的氣氛是我不熟悉的:外省青年和優雅的藝術家「女主人」的短暫目光交接,是好奇心和好奇心的碰撞,但是其中並沒有什麼交流的可能性,不時有路邊的過客掀開棉布簾子進來,卻很少有熟人間的對話,人們沉默地進入,又沉默地離開,我翻開展廳的留言簿,並沒有看到什麼針對作品本身的只言片語。
通往美術館的路是會是有前提的——這樣的造訪不太可能僅僅是偶然,在我們與它相約之前,我們必須問自己這樣的問題:美術館在哪兒?我們究竟要在美術館中看到什麼?大多數美術館並不「事先」存在,在它們匆忙地建成之前,或者在與它們不期而遇之前,大多數人對這類文化空間的功能並無太多心理預期——至少對於大多數非專業的觀眾而言,觀摩「原作」的現場並不如身臨「藝術」的現境更重要,因為很少「原作」的意象會在他們心中牢牢扎根,他們來到美術館其實是看人,而不是看作品。尤其是在當代中國,美術館已經成了一種混雜的主題公園樣式,或者,套用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Morris)評論紐約的話說,在此美術館是一個圈養着人類的動物園。
對一個來到陌生城市的訪客而言,美術館首先是一個顯赫的地點,它占據着大多數西方城市的中心地位。20世紀,當中央公園在1817年紐約規划中的密仄格柵中卓然自立的時候,這塊特殊的城市預留地里唯一的大體量建築物就是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有類似情況,「中環」(loop)湖濱的密歇根大道以東沒有任何建設,只有芝加哥藝術學院的陳列館(芝加哥藝術館)。更不用說那些年代更為久遠的歐洲美術館,在柏林的老城城址上建成的老國家畫廊得之於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直接授意。建成較晚的美術館不一定能擠進寸土寸金的市中心,但即使如此,它們依然被當成都市復興或是縉紳化(urbangentrification)的重要手段:從一開始,由妹島和世設計的紐約新美術館就被當成改造向來破敝的包厘街(BoweryStreet)地區的關鍵環節。
但是這個地點是一個模糊的地點,美術館只有成為一種形象(image)之后才能更清晰地在城市中存在,也方便訪客的識途。西方建築學之中,建築物的形象首先是指它的外部「立面」(façade)。這種外在的「形象」和我們在藝術史中所說的「具象」(figure)是有區別的,建築和藝術——自然主義或非自然主義的藝術——的很大不同,在於它不以「相似」為意,對於凱文•林奇(KevinLynch)而言形象就是「個性,結構和意蘊」的綜合體。形象,是因特定意涵的「觀看」才從懵懵懂懂的環境之中脫離出來的,由於某種「如畫」(picturesque)的品質和內涵使得觀看的主體和客體彼此脫離,城市不再均質。在這個意義上的美術館不僅和當代藝術也和古典藝術有關,后者更強烈地表達了「框外」和「框內」的不同涵義,暗示了凝視(gaze)的文化根基所在。
自然,當代的美術館設計已經不拘於靜態的、二元的「觀看」了,比如瑞士建築師彼得•卒姆托的名作布列根茨美術館,在那里建築被有意識地遮蔽,卻又並不完全封閉,由於半透的,濾鏡式的建築表皮,它的形象現在是一種介於有和沒有之間的存在,雖然不能使你看到什麼卻的的確確改變了你的「看法」,這點和古典建築並無二致。所以有形的「框景」(framing)之后緊隨着無處不在的「成像」(imaging),它們都是當代美術館的核心觀念。
由於這種確鑿無疑的形象的魅惑,美術館本身成為美術「作品」的一種形式——也許從此開始,我們應該更加考究我們的用詞了,除了「美術館」和「博物館」的區分,到底是「美術館」還是「藝術館」?每種表述都有特定時空的前提,它們使得「看見」和「看到」成為不同的「看法」——對於一個造訪者而言,僅僅是「看見」是沒有意義的。
在中國,只是最近人們才更多地提到「藝術」(art)而不僅僅是「美」術(fineart)。就像英文里博物館不易和美術館區分一樣,「美術」領先「藝術」率先出場,反映出中國美術館內向、遠離的原初語境。現代教育家蔡元培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在解說了「美育」比「美術」更宏闊的基礎上,他提到起教化作用的美育「使參與的人有超出塵世的感想」——就像反對此說的呂澄所言,如此的「美術」觀是「人生的反面」,是現世中的孤島;相信「美術是上流社會的宗教」(王國維)的人們,一開始就讓美術館中的公共性有些匱乏。
於是,中國的「美術館」聽起來就是演奏室內樂的音樂廳,而不是奧林匹斯神廟露天的半圓形劇場;更有甚者,由於中國傳統建築和城市特點的習染,它既缺乏清晰可見的「立面」,也沒有內部的空間層次而導致的截然的「透明性」。在不知當代藝術為何的前提下,大多數中國建築師筆下的當代美術館是孤懸於城市中的封閉的堡壘。
現代城市中的美術館不再是獨立的飛地,它和城市的聯系值得細究。首先,「城市」是復數的系統,美術館輻射周邊區域,它們既是人心的海洋中的離島,也是城市文化交通中的經停站。不用說華盛頓的mall,柏林的博物館島,即使在紐約這樣的私人城市,大都會博物館的周邊也有星羅棋布的畫廊。這也就是為何藝術總喜歡在「藝術區」中存在,強調個性的藝術家們卻總愛「一起孤獨」——除了「城市中的美術館」也可能是「美術館即城市」,除了由眾多單體湊成的大型「系統」(SoHo,798),在自身規模也日益膨脹的當代城市中新建的大型「藝術綜合體」也越來越多了,按照庫哈斯的說法,當代空間中的「大」(bigness)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在其中藝術展示並不一定是唯一的、最主要的功能。
對於我們篇首所提到的那種「人工文化」而言,傳統歐洲城市的小型城市組織已經不敷使用了,新的「大」並不追求和它的環境協同,因為它自身就構成了自身的情境。只要自身的規模容量足夠,美術館成為「析出的晶體」並不是什麼壞事,它的形象越飽滿鮮明,它對於城市的貢獻就越大。
如此,在大都會的茫茫九衢中,一個來訪者找到這樣的美術館也許並不算難,難在如何得其門而「進入」。無論如何,對於每個個體而言,美術館不僅是一個地點,一種公共形象,一個場域——以上都是以「集體」的面貌出現的——也是一個具體的「終極的空間」,而且是一類「私人空間」,需要落實到單數的眼睛和心靈。這樣的空間並不排斥其它的屬性,例如它也自有它的「形象」,也許是某種隱約其辭的「私人形象」——但是「私人形象」這個說法聽起來又是不易成立的。
它揭示着美術館與生俱來的自我矛盾性,甚至大多數人所鼓吹的「公共性」的滋生也莫過於此:公共性恰恰產生於當代社會對於個性的承認,但是藝術對人們心智的系統催化卻又不能不籍由某種體制化的方式來完成。由集體和個性之間的搖擺,當代美術館既是大街上的響亮宣言,也是一個陶冶性情、沁潤其中的容器,它最終的包容性難免隱藏了它着力揭示的社會矛盾和沖突。
除了它顯見的庄嚴和喧囂,美術館的深處其實有個不可見的虛空,那是一類靜默的、思考的空間,這是不太引人注目的方面。從初次跨進校尉胡同的老美院展廳的那刻,我就發現了這個秘密;表面上「公共」的當代藝術,其實又立即是羞澀的和「私人」的,在藝術和觀眾之間有些話未便當面提起,需要轉過頭去交代。
於是,美術館自身也是一條引領人們心智的道路——我們談到的「道路」不僅僅關於長途跋涉到它門前的那條。在傳統的想象中美術館是一座萬水千山外的聖殿,貝聿銘設計的美秀美術館,需要換乘好幾種交通工具才能到達,最終還只能步行進入,它便是如此聖殿的典型事例;可是,在當代城市中,為了打破靜態的展示和動態的生活之間的壁壘,人們不能不時刻「穿行」在美術館所創造的思想領域之中,不光是專程去那里朝聖。這種貌似不可思議的「穿行」有那麼幾個辦法:
——美術館不僅是一個抽象的地點(locale)也可以是一個有其廣度的場域(field)(如此就可以把「點」和「面」合為一體);
——美術館的「形象」不僅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內在的(如此就打破了集體和個人之間的樊籬);
——美術館不僅是一種特別的文化空間,也是一種文化事件的統稱(如此,既可以在美術館,也可以同時在去美術館的路上)
大眾心目中的美術館似乎和「畫」綁定,它本身的建築類型甚至被稱為「畫廊」(gallery,准確地說,英文的「galleria」,暫且翻譯成「藝廊」,並沒有「畫」這個字面含義,把它和「畫」拉上關系又體現了中文的情境),可是,和通常想象的類型學不同,「畫廊」其實並不能導致一種「畫」的至上地位,當代的美術館不再是一種「靜觀」,觀眾觀看的方向和行進的方向總是互相垂直,使得傳統的自然主義藝術的幻覺性再現失效。美術館不再是一座「私人的萬神廟」,一座充滿而盈溢的容器,不斷曲折導引的道路,讓這容器的意義出漏了。
「路」可能是藝術史最青睞的題材之一,羅馬人的早期壁畫或是達芬奇的明暗風景里通常畫不出清晰連貫的小徑,當「空間」在「運動」中浮現時,古典繪畫的主題就為觀眾可以追隨的幻覺性道路所鎖定——無論是霍貝瑪的《楊樹林蔭道》列維坦的《弗拉基米爾之路》還是我們熟悉的《毛主席去安源》。可是恰恰是展示這些作品的「畫廊」把觀眾的身心拖離了這些道路——兩條路,一條是眼前,還有一條是現實中的,一條是冥思之路,另一條則是不得不面對的當代文化的事實:人工的「藝術」所營就的特殊的儀式性場所,已經和世俗性的人生走向分離了——隨性而聚,亦隨風而散。
這就是篇首我們提到的那種情形的意義,人們並不是因為走向美術館才變得「文藝」,在開始這條追尋之路之前,他們的生活已為另一種更大的情境所鎖定,你可以說這種情境是「非」美術館的部分,但你也可以說,美術館之路從那里就已經開始。
除了展覽之外,一個大型美術館的功能至少包括以下的部分:沉思(最「高級」的選項),教諭(最「民主」的美術館也不會去除這一項),教育(平等的「教育」和「教諭」往往相反),交流——最后這一項被看做當代美術館的最新發展。就在可見的將來,或許會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樣的風尚,在美術館吃個「知性的晚餐」和「在蒂芬妮吃早餐」一樣通俗。用不着特別驚奇,這些「逛美術館者」(museumgoer)根本用不着去「看展覽」。
對大多數走進美術館的人們而言,他們只是不停地走過某些作品,最終將它們統統遺忘。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