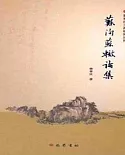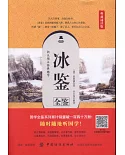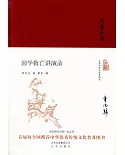本書對《周易》、《論語》、《老子》、三《禮》、《淮南子》、《史記》、《說文解字》、《黃庭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壇經》等十種經典著作作了深入的解讀。全書內容豐富,論述透徹,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這部書原來是我在大學里講通識課程的講義,在理想中,大學應當是理解文化傳統和提倡精神自由的島嶼,閱讀經典也許正是實踐這一理想的重要途徑,布魯姆(Allan Bloom)在《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曾說,閱讀經典可以使人們了解,從古至今“人類究竟面臨哪些重大問題”,以便人們在共同問題和豐富知識基礎上,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聯系”。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聖賢原則是必須遵循的教條,也不意味著古代經典是不可違逆的聖經,畢竟歷史已經翻過了幾千年,因此,對于古代經典,既不必因為它承負著傳統而視其為累贅包袱,也不必因為它象征著傳統而視其為金科玉律。我對經典的看法很簡單,第一,經典在中國是和我們的文化傳統緊緊相隨的巨大影子,你以為扔開了它,其實在社會風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傳里面,它總會“借尸還魂”;第二,歷史上的經典只是一個巨大的資源庫,你不打開它,資源不會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會現實和生活環境,是刺激經典知識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經典中的什麼資源被重新發掘出來,很大程度取決于“背景”召喚什麼樣的“歷史記憶”;第三,經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釋”的,不大可能純之又純、原汁原味,以為我們今天可以重新捫摸聖賢之心,可以隔千載而不走樣,那是“原教旨”的想象;第四,只有經過解釋和引申,“舊經典”才能成為在今天我們的生活世界中繼續起作用的,呈現出與其他民族不同風格的“新經典”。
目錄
序言
《周易》:佔筮與哲理
一、《易經》:“卦象”、“卦辭”、“爻辭”
二、《易傳》:讓《周易》從佔卜變為哲理的“十翼”
三、考古發現:《周易》之謎的破解
四、《周易》之流(一):佔卜術
五、《周易》之流(二):哲理
《論語》:禮與仁
一、瞧,那個人是孔子!
二、《論語》其書
三、從“禮”到“仁”
四、流變與影響
五、孔子‧中國‧中國人
《老子》:“道\〃的哲思
一、《老子》其書
二、何謂“道”
三、“道”之用(一):人生
四、“道”之用(二):社會
五、附說莊子:逍遙的游蕩者如何在“無”中超越?
三《禮》:規範、秩序與理性的生活
一、《儀禮》:古禮儀集成
二、《周禮》:治國安邦藍圖?
三、《禮記》:禮的闡釋
四、三《禮》:價值何在
《淮南子》:牢籠萬象的體系
一、劉安與《淮南子》:一部奇書
二、龐大的體系與結構:中國古人宇宙觀念
三、自然、社會與人:三位一體的交感世界
四、垃圾馬車,還是思想體系:回到歷史中看《淮南子》
《史記》:偉大的歷史著作
一、《史記》:兩代人的心血
二、書名與體例
三、“通古今之變”與“究天人之際”
《說文解字》:認識漢字之門
一、內容與體例
二、怎樣讀《說文》
三、功用何在
《黃庭經》:尋求永恆生命
一、什麼是道教
二、道教經典的構成
三、《黃庭經》解說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佛教袖珍寶典
一、從三藏結集說起
二、佛經的基本思想
三、《心經》來歷之謎
四、《心經》思想的闡釋
《壇經》:中國禪的宣言
一、從印度禪到中國禪
二、《壇經》解說
三、圍繞《壇經》的爭論及其他
參考書目
附錄 舊版序跋
《周易》:佔筮與哲理
一、《易經》:“卦象”、“卦辭”、“爻辭”
二、《易傳》:讓《周易》從佔卜變為哲理的“十翼”
三、考古發現:《周易》之謎的破解
四、《周易》之流(一):佔卜術
五、《周易》之流(二):哲理
《論語》:禮與仁
一、瞧,那個人是孔子!
二、《論語》其書
三、從“禮”到“仁”
四、流變與影響
五、孔子‧中國‧中國人
《老子》:“道\〃的哲思
一、《老子》其書
二、何謂“道”
三、“道”之用(一):人生
四、“道”之用(二):社會
五、附說莊子:逍遙的游蕩者如何在“無”中超越?
三《禮》:規範、秩序與理性的生活
一、《儀禮》:古禮儀集成
二、《周禮》:治國安邦藍圖?
三、《禮記》:禮的闡釋
四、三《禮》:價值何在
《淮南子》:牢籠萬象的體系
一、劉安與《淮南子》:一部奇書
二、龐大的體系與結構:中國古人宇宙觀念
三、自然、社會與人:三位一體的交感世界
四、垃圾馬車,還是思想體系:回到歷史中看《淮南子》
《史記》:偉大的歷史著作
一、《史記》:兩代人的心血
二、書名與體例
三、“通古今之變”與“究天人之際”
《說文解字》:認識漢字之門
一、內容與體例
二、怎樣讀《說文》
三、功用何在
《黃庭經》:尋求永恆生命
一、什麼是道教
二、道教經典的構成
三、《黃庭經》解說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佛教袖珍寶典
一、從三藏結集說起
二、佛經的基本思想
三、《心經》來歷之謎
四、《心經》思想的闡釋
《壇經》:中國禪的宣言
一、從印度禪到中國禪
二、《壇經》解說
三、圍繞《壇經》的爭論及其他
參考書目
附錄 舊版序跋
序
近來常有一種風氣。有人說到“經”,便有意無意地把它等同“經典”,而提起“中國經典”,就急急忙忙把它轉換成“儒家經典”。我總覺得這種觀念有些偏狹。其實,中國經典絕不是儒家一家經典可以獨佔的,也應當包括其他經典,就像中國傳統絕不是“單數的”傳統,而應當是“復數的”傳統一樣。我一直建議,今天我們重新回看中國的經典和傳統,似乎應當超越單一的儒家學說,也應當關涉古代中國更多的知識、思想和信仰,這樣,一部介紹中國經典的書,就應當涵蓋和包容古代中國更廣泛的重要著作。
簡單地說有兩點。第一,中國經典應當包括佛教經典,也應當包括道教經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實在是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歐洲,在文化領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國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國的皇帝,不僅知道“王霸道雜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如宋孝宗、明太祖、雍正皇帝),絕不只用一種武器。因此,回顧中國文化傳統的時候,僅僅關注儒家的思想和經典,恐怕是過于狹窄了。即使是僅僅說儒家,儒家也包含了相當復雜的內容,比如有偏重“道德直覺”的孟子和偏重“禮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視宇宙天地秩序的尋期儒家和重視心性理氣的新儒家。應當說,在古代中國,關注政治秩序和社會倫理的儒家,關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贖的佛教,關注生命永恆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別承擔著傳統中國的不同責任,共同構成中國復數的文化。第二,也許還不止是儒、道、佛,傳統中國有很多思想、知識和信仰,可能記載在其他著述里面,“經典”不必限于聖賢、宗教和學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廣泛些?比如歷史學中的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通鑒》之類,是否可以進入經典?西方人從來就把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算成是必讀經典的,重建文化認同和進行傳統溯源,也從來少不了歷史著作,為什麼不可以把它們叫 做“經典”來重新閱讀?至于古代中國支持經典研讀(那算是“大學”)的基礎知識(也叫”小學”),就是文字之學,其中的那些重要著作,《爾雅》是早就成“經”了的,而《說文》呢,更是可以毫不愧疚地列入“經典”之林的,道理很簡單,古人早說過“通經由識字始”,不識字能讀經典嗎?甚至唐詩宋詞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讓它們擁有“經典”的資格,莎士比亞那些曾被稱為粗鄙的北方人的劇作,不也列入了西方經典之林了嗎?因此,我在這部《中國經典十種》里面,既選有傳統儒家的.經典,也選了佛教道教的經典,既有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說到經典,還必須補充說明,經典並非天然就是經典,它們都經歷了從普通著述變成神聖經典的過程,這在學術史上叫“經典化”,沒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著經典的尺寸和樣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為它寫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覺得它充滿真理,又被反復解釋,還有的被“欽定”為必讀書,于是,就在歷史中漸漸成了被尊崇和被仰視的經典。因此,如今我們重新閱讀經典,又雩要把它放回歷史里重新理解,所謂“放回歷史里面”,就是說,這些經典雩要先放在那個產生它的時代里面,重新去理解,就比如《周易》打一開始,就不是那麼哲學和抽象,在那個時代可能就是佔筮,《史記》在那個文史不分的時代,不必那麼拘泥于歷史學的謹嚴,就是可以有想象和渲染一樣。經典的價值和意義,也是層層積累的,對那些經典里傳達的思想、原則甚至知識,未必需要亦步亦趨“照辦不走樣”,倒是要審時度勢“活學活用”,用一句理論的話講就是要“創造性的轉化”。
這部書原來是我在大學里講通識課程的講義,在理想中,大學應當是理解文化傳統和提倡精神自由的島嶼,閱讀經典也許正是實踐這一理想的重要途徑,布魯姆(Allan Bloom)在《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曾說,閱讀經典可以使人們了解,從古至今“人類究竟面臨哪些重大問題”,以便人們在共同問題和豐富知識基礎上,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聯系”。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聖賢原則是必須遵循的教條,也不意味著古代經典是不可違逆的聖經,畢竟歷史已經翻過了幾千年,因此,對于古代經典,既不必因為它承負著傳統而視其為累贅包袱,也不必因為它象征著傳統而視其為金科玉律。我對經典的看法很簡單,第一,經典在中國是和我們的文化傳統緊緊相隨的巨大影子,你以為扔開了它,其實在社會風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傳里面,它總會“借尸還魂”;第二,歷史上的經典只是一個巨大的資源庫,你不打開它,資源不會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會現實和生活環境,是刺激經典知識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經典中的什麼資源被重新發掘出來,很大程度取決于“背景”召喚什麼樣的“歷史記憶”;第三,經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釋”的,不大可能純之又純、原汁原味,以為我們今天可以重新捫摸聖尋之心,可以隔千載而不走樣,那是“原教旨”的想象;第四,只有經過解釋和引申,“舊經典”才能成為在今天我們的生活世界中繼續起作用的,呈現出與其他民族不同風格的“新經典”。
我希望我所詮釋的“舊經典”,也能夠成為今天生活中起作用的“新經典”。
簡單地說有兩點。第一,中國經典應當包括佛教經典,也應當包括道教經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實在是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歐洲,在文化領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國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國的皇帝,不僅知道“王霸道雜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如宋孝宗、明太祖、雍正皇帝),絕不只用一種武器。因此,回顧中國文化傳統的時候,僅僅關注儒家的思想和經典,恐怕是過于狹窄了。即使是僅僅說儒家,儒家也包含了相當復雜的內容,比如有偏重“道德直覺”的孟子和偏重“禮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視宇宙天地秩序的尋期儒家和重視心性理氣的新儒家。應當說,在古代中國,關注政治秩序和社會倫理的儒家,關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贖的佛教,關注生命永恆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別承擔著傳統中國的不同責任,共同構成中國復數的文化。第二,也許還不止是儒、道、佛,傳統中國有很多思想、知識和信仰,可能記載在其他著述里面,“經典”不必限于聖賢、宗教和學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廣泛些?比如歷史學中的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通鑒》之類,是否可以進入經典?西方人從來就把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算成是必讀經典的,重建文化認同和進行傳統溯源,也從來少不了歷史著作,為什麼不可以把它們叫 做“經典”來重新閱讀?至于古代中國支持經典研讀(那算是“大學”)的基礎知識(也叫”小學”),就是文字之學,其中的那些重要著作,《爾雅》是早就成“經”了的,而《說文》呢,更是可以毫不愧疚地列入“經典”之林的,道理很簡單,古人早說過“通經由識字始”,不識字能讀經典嗎?甚至唐詩宋詞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讓它們擁有“經典”的資格,莎士比亞那些曾被稱為粗鄙的北方人的劇作,不也列入了西方經典之林了嗎?因此,我在這部《中國經典十種》里面,既選有傳統儒家的.經典,也選了佛教道教的經典,既有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說到經典,還必須補充說明,經典並非天然就是經典,它們都經歷了從普通著述變成神聖經典的過程,這在學術史上叫“經典化”,沒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著經典的尺寸和樣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為它寫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覺得它充滿真理,又被反復解釋,還有的被“欽定”為必讀書,于是,就在歷史中漸漸成了被尊崇和被仰視的經典。因此,如今我們重新閱讀經典,又雩要把它放回歷史里重新理解,所謂“放回歷史里面”,就是說,這些經典雩要先放在那個產生它的時代里面,重新去理解,就比如《周易》打一開始,就不是那麼哲學和抽象,在那個時代可能就是佔筮,《史記》在那個文史不分的時代,不必那麼拘泥于歷史學的謹嚴,就是可以有想象和渲染一樣。經典的價值和意義,也是層層積累的,對那些經典里傳達的思想、原則甚至知識,未必需要亦步亦趨“照辦不走樣”,倒是要審時度勢“活學活用”,用一句理論的話講就是要“創造性的轉化”。
這部書原來是我在大學里講通識課程的講義,在理想中,大學應當是理解文化傳統和提倡精神自由的島嶼,閱讀經典也許正是實踐這一理想的重要途徑,布魯姆(Allan Bloom)在《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曾說,閱讀經典可以使人們了解,從古至今“人類究竟面臨哪些重大問題”,以便人們在共同問題和豐富知識基礎上,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聯系”。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聖賢原則是必須遵循的教條,也不意味著古代經典是不可違逆的聖經,畢竟歷史已經翻過了幾千年,因此,對于古代經典,既不必因為它承負著傳統而視其為累贅包袱,也不必因為它象征著傳統而視其為金科玉律。我對經典的看法很簡單,第一,經典在中國是和我們的文化傳統緊緊相隨的巨大影子,你以為扔開了它,其實在社會風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傳里面,它總會“借尸還魂”;第二,歷史上的經典只是一個巨大的資源庫,你不打開它,資源不會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會現實和生活環境,是刺激經典知識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經典中的什麼資源被重新發掘出來,很大程度取決于“背景”召喚什麼樣的“歷史記憶”;第三,經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釋”的,不大可能純之又純、原汁原味,以為我們今天可以重新捫摸聖尋之心,可以隔千載而不走樣,那是“原教旨”的想象;第四,只有經過解釋和引申,“舊經典”才能成為在今天我們的生活世界中繼續起作用的,呈現出與其他民族不同風格的“新經典”。
我希望我所詮釋的“舊經典”,也能夠成為今天生活中起作用的“新經典”。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