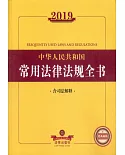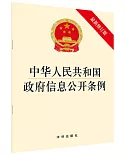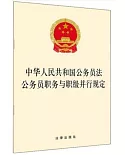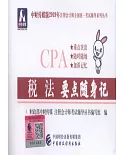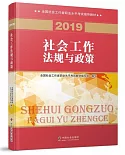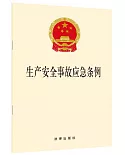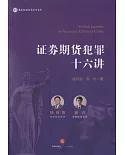本書收錄蕭公權先生1932年移講清華大學起,至1949年去國止,關於憲政和民主的一系列著述,計22篇。曾於1948年題為《憲政與民主》,合集刊布。所論既有憲政與民主的一般原理,對於外域政制的介紹,更多的還是對於當日中國的實際所作的闡發,特別是對於中國施行憲政和民主的現實途徑的剖析,而寄希望於批評,寓建議於分析。先生文風平實,運思細密,將實證與學理溝通,解釋與建構合為一體,足堪垂范後世;其思其慮,不僅有助於省思過去,而且裨益於措置當下,瞻望將來。
本書適合於從事法學理論與憲政研究的學者、教師和研究生學習,同時也適合於對憲政和民主有興趣的其他人士閱讀。
蕭公權先生(1897-1981),原名篤平,自號跡園,筆名君衡,江西泰和人。1918年夏自上海青年會中學畢業,考入清華學校高等科三年級(庚申級),畢業後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專業和康奈爾大學哲學系,192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後返國,任教於南開大學、東北大學、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校。1949年轉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職,凡近二十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鄉村》、《康有為思想研究》等,遺著輯成《蕭公權全集》,計九冊。先生主治政治學說和社會史,學貫中西,調和新舊,蔚然一代大家。
序
前幾年作者留滯成都的時候,承朋友們督促,在教學的余暇,偶而寫點討論時事的文字,在若干刊物上發表。來南京之前,吳惠人教授來信說劉百閔先生願意把作者所寫有關憲政的文字匯集付印,希望從速送稿。自省並無高明深刻的見解,值得重行刊印流傳。但以部分友人每以個人對於黨政的意見如何相問,重復口答,頗覺費辭,現在有這個良機,可以作一種省事的「書面答復」,當然樂於接受。因此到南京後便搜檢著作,把勉強可以見人的成篇,寄交劉先生付印,並且杜撰了「憲政與民主」一個好看的書名。現在行憲業已開始,書中所發的片段零星議論有一些已經過時了。但作者相信個人對於中國憲政的基本認識尚沒有修改之必要。
第一屆國民大會開會時一部分代表發動了一個修改憲法的運動。主張修憲者的最大理由似乎有兩個:憲法的條文不完善和制憲時的特殊環境已改變。一部分的國大代表希望在兩年之後,再度集會時來推進修憲的工作。作者承認任何憲法都可以修改,並且在不能適用的時候必須修改。但同時作者也承認憲法不可以輕易修改。憲政就是法治。憲政的成立,有賴於守法習慣的培養。在我們缺乏守法習慣的中國,嚴守憲法的習慣遠比條文完美的憲典為重要。如果憲法可以輕易修改,任何人都可以借口條文有缺點,企圖以修改憲法為名,遂其便利私意之實。現行憲法縱不完善,似乎還不至惡劣到開始行憲,即需修憲的程度。照憲法規定,國民大會六年必須開會一次。因此至少六年當中有一個修憲的機會。任何迅速的進步,似乎不至於迅速到使得六年可以修改一次的憲法成為國家進步的障礙,「行憲國大」開會時候的政治環境誠然異於「制憲國大」開會時候的政治環境,最重要而顯明的差異就是中國的政治局勢由多黨共同「協商」而轉入於三黨聯合戡亂。「協商」局勢對於憲法最大的影響似乎有兩點,第一是因為各黨的主張,把「五五憲草」所擬定略近於總統制的中央制度改為略近於內閣制的中央制度,第二是略為加強草案所擬定的地方制。這兩個由協商影響而采取的制度是否果然優於原擬,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我們不經試行,實在無法斷定它們的好壞。如果說,不修改憲法而行憲法所規定的制度是以全國的安危作嘗試,那麽試行修改憲法後所立的制度,那個制度既然未經在中國行過,豈不也是以國家作嘗試嗎?
作者久已渴望民主憲政的實現。他在這本小書中的意見縱然可能有許多錯誤,但希望能夠由這些意見而引起了國人對於憲法更大的注意,引出了時賢對於憲政更高明正確的主張,使憲政能夠早日納入正軌,逐步前進。
除了感謝劉百閔、吳惠人兩先生外,作者對於督促他寫這些文字的各位先生和原來發表它們的各刊物主編者,同樣表示謝意。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
序於南京
第一屆國民大會開會時一部分代表發動了一個修改憲法的運動。主張修憲者的最大理由似乎有兩個:憲法的條文不完善和制憲時的特殊環境已改變。一部分的國大代表希望在兩年之後,再度集會時來推進修憲的工作。作者承認任何憲法都可以修改,並且在不能適用的時候必須修改。但同時作者也承認憲法不可以輕易修改。憲政就是法治。憲政的成立,有賴於守法習慣的培養。在我們缺乏守法習慣的中國,嚴守憲法的習慣遠比條文完美的憲典為重要。如果憲法可以輕易修改,任何人都可以借口條文有缺點,企圖以修改憲法為名,遂其便利私意之實。現行憲法縱不完善,似乎還不至惡劣到開始行憲,即需修憲的程度。照憲法規定,國民大會六年必須開會一次。因此至少六年當中有一個修憲的機會。任何迅速的進步,似乎不至於迅速到使得六年可以修改一次的憲法成為國家進步的障礙,「行憲國大」開會時候的政治環境誠然異於「制憲國大」開會時候的政治環境,最重要而顯明的差異就是中國的政治局勢由多黨共同「協商」而轉入於三黨聯合戡亂。「協商」局勢對於憲法最大的影響似乎有兩點,第一是因為各黨的主張,把「五五憲草」所擬定略近於總統制的中央制度改為略近於內閣制的中央制度,第二是略為加強草案所擬定的地方制。這兩個由協商影響而采取的制度是否果然優於原擬,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我們不經試行,實在無法斷定它們的好壞。如果說,不修改憲法而行憲法所規定的制度是以全國的安危作嘗試,那麽試行修改憲法後所立的制度,那個制度既然未經在中國行過,豈不也是以國家作嘗試嗎?
作者久已渴望民主憲政的實現。他在這本小書中的意見縱然可能有許多錯誤,但希望能夠由這些意見而引起了國人對於憲法更大的注意,引出了時賢對於憲政更高明正確的主張,使憲政能夠早日納入正軌,逐步前進。
除了感謝劉百閔、吳惠人兩先生外,作者對於督促他寫這些文字的各位先生和原來發表它們的各刊物主編者,同樣表示謝意。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
序於南京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