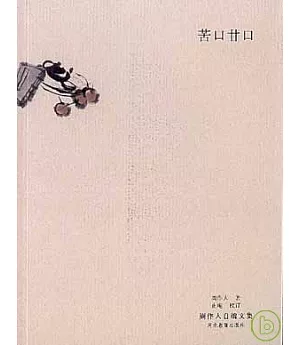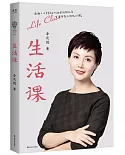《苦口甘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上海太平書局出版。《自序》中說: 「今年夏天(民國甲申,七月廿日)特別酷熱,無事可做,取舊稿整理,皆是近一年中所寫,」即為編集時間。本文共二十一篇,約八萬余字,計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八篇,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八月十三篇,是繼《藥堂雜文》之後的作品,風格亦基本延續《藥堂雜文》,談論思想的 「正經文章」仍復不少,也有一些懷人讀書之作。
從《苦口甘口》起,周氏進入一個「總結時期」。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有分量的是《我的雜學》,作者後來說,「這是一種關於讀書的回憶,把我平常所覺得有興趣以及自以為有點懂得的事物,簡單的記錄下來,」
目錄
自序
第一分
苦口甘口
夢想之一
文藝復興之夢
論小說教育
女子與讀書
燈下讀書論
談翻譯
怠工之辯
希臘之余光
我的雜學
第二分
武者先生和我
草固與茅屋
蘇州的回憶
兩種祭規
讀鬼神論
俞理初的著書
陶集小記
關於王嘯岩
虎口日記及其他
陽九述略
第三分
遇狼的故事
第一分
苦口甘口
夢想之一
文藝復興之夢
論小說教育
女子與讀書
燈下讀書論
談翻譯
怠工之辯
希臘之余光
我的雜學
第二分
武者先生和我
草固與茅屋
蘇州的回憶
兩種祭規
讀鬼神論
俞理初的著書
陶集小記
關於王嘯岩
虎口日記及其他
陽九述略
第三分
遇狼的故事
序
今年夏天特別酷熱,無事可做,取舊稿整理,皆是近一年中所寫,共有二十一篇,約八萬余字,可以成一冊書,遂編為一集,即名之曰《苦口甘口》。重閱一過之後,照例是不滿意,如數年前所說過的話,又是寫了些無用也無味的正經話。難道我的儒家氣真是這樣的深重而難以湔除麽。我想起顧亭林致黃梨洲的書中有雲: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為山覆蕢,而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案此書《亭林文集》未載,見於《梨洲思舊錄》中,時在清康熙丙辰,為讀《明夷待訪錄》後之復書,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則六十七矣。黃顧二君的學識我們何敢妄攀,但是在大處態度有相同者,亦可無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與文壇中人全屬隔教,平常所欲窺知者,乃在於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但所取材亦並不廢蟲魚風月,則或由於時代之異也。此種傾向之思想大抵可歸於唯理派,雖合理而難得勢,平時已然,何況如日本俗語所雲,無理通行,則道理縮入,這一類的文章出來,結果是毫無用處,其實這還是最好的,如前年寫了一篇關於中國思想問題文章,曾被人評為反動,則又大有禍從口出之懼矣。我於文集自序中屢次表示過同樣的意見,對於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意義很是不滿,可是說過了也仍不能改,這回還是如此。近時寫《我的雜學》,因為覺得寫不好,草率了事,卻已有二十節,寫了之後乃益了解,自己歷來所寫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這一點東西,假如把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虛的文字與詞句,毫無價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麽所可取者也當在於思想而不是文章。總之我是不會做所謂純文學的,我寫文章總是有所為,於是不免於積極,這個毛病大約有點近於吸大煙的癮,雖力想戒除面甚不容易,但想戒的心也常是存在的。去年九月以後我動手翻譯日本阪本文泉子的《如夢記》,每月譯一章,現在已經完畢,這是近來的一件快意的事。我還有《希臘神話》的注釋未曾寫了,這個工作也是極重大的,這五六年來時時想到,趕做注釋,難道不比亂寫無用無味的文章更有價值麽?我很怕被人家稱為文人,近來更甚,所以很想說明自己不是寫文章而是講道理的人,希望可以幸免,但是昔者管寧謂邴原曰,潛尤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取禍之道,則亦不甚妥當。天下多好思想好文章,何必盡由己出,鳩摩羅什不自著論,而一部《大智度論》,不特譯時想見躊躇滿志,即在後世讀者亦已可充分了解什師之偉大矣。假如可以被免許文人歇業,有如吾鄉墮貧之得解放,雖執鞭吾亦為之,只是目下尚無切實的著落處,故未能確說,若欣求脫離之心則極堅固,如是譯者可不以文人論,則固願立刻蓋下手印,即日轉業者也。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為山覆蕢,而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案此書《亭林文集》未載,見於《梨洲思舊錄》中,時在清康熙丙辰,為讀《明夷待訪錄》後之復書,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則六十七矣。黃顧二君的學識我們何敢妄攀,但是在大處態度有相同者,亦可無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與文壇中人全屬隔教,平常所欲窺知者,乃在於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但所取材亦並不廢蟲魚風月,則或由於時代之異也。此種傾向之思想大抵可歸於唯理派,雖合理而難得勢,平時已然,何況如日本俗語所雲,無理通行,則道理縮入,這一類的文章出來,結果是毫無用處,其實這還是最好的,如前年寫了一篇關於中國思想問題文章,曾被人評為反動,則又大有禍從口出之懼矣。我於文集自序中屢次表示過同樣的意見,對於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意義很是不滿,可是說過了也仍不能改,這回還是如此。近時寫《我的雜學》,因為覺得寫不好,草率了事,卻已有二十節,寫了之後乃益了解,自己歷來所寫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這一點東西,假如把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虛的文字與詞句,毫無價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麽所可取者也當在於思想而不是文章。總之我是不會做所謂純文學的,我寫文章總是有所為,於是不免於積極,這個毛病大約有點近於吸大煙的癮,雖力想戒除面甚不容易,但想戒的心也常是存在的。去年九月以後我動手翻譯日本阪本文泉子的《如夢記》,每月譯一章,現在已經完畢,這是近來的一件快意的事。我還有《希臘神話》的注釋未曾寫了,這個工作也是極重大的,這五六年來時時想到,趕做注釋,難道不比亂寫無用無味的文章更有價值麽?我很怕被人家稱為文人,近來更甚,所以很想說明自己不是寫文章而是講道理的人,希望可以幸免,但是昔者管寧謂邴原曰,潛尤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取禍之道,則亦不甚妥當。天下多好思想好文章,何必盡由己出,鳩摩羅什不自著論,而一部《大智度論》,不特譯時想見躊躇滿志,即在後世讀者亦已可充分了解什師之偉大矣。假如可以被免許文人歇業,有如吾鄉墮貧之得解放,雖執鞭吾亦為之,只是目下尚無切實的著落處,故未能確說,若欣求脫離之心則極堅固,如是譯者可不以文人論,則固願立刻蓋下手印,即日轉業者也。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