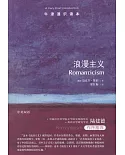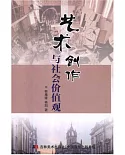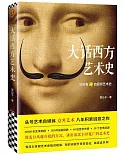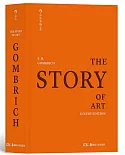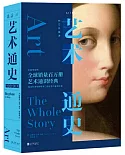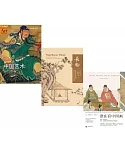長期以來,人們認為藏族佛教藝術,特別是12世紀以前,其主要藝術手法、風格和構思深受印度、尤其是克什米爾學派和波羅一舍那學派的影響。書名中的「早期」一詞的使用是相對而言的,主要是相對於那些一般而言的漢藏藝術。換言之,就是相對於那些幾乎在任何藏族藝術珍藏品中都能發現的17至19世紀的青銅塑像和唐卡作品而言的。
本書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來討論:(1)9至15世紀的漢藏史料,主要介紹藏族風格和在藏的域外藝術家、畫派史和藝術風格研究、敦煌藏族繪畫作品、黑水城、江孜白居寺、飛來峰等;(2)《西夏藏》藏族風格木刻插圖;(3)《磧砂藏》木刻作品;(4)1410年《甘珠爾》插圖;(5)《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6)永樂青銅塑像。
目錄
導言 9至15世紀的漢藏史料
藏族風格和在藏的域外藝術家
畫派史和風格研究
敦煌藏族繪畫作品
斯坦因第32號收集品
藝術家白央
敦煌吐蕃贊普壁畫
黑水城
阿尼哥
飛來峰
居庸關
江孜白居寺
題記
第一章 《西夏藏》藏族風格木刻插圖
元刊
西夏刊
第二章 《磧砂藏》木刻作品
藏族僧人的袈裟
《影印宋磧砂藏經》中的八幅插圖
第三章 1410年《甘珠爾》插圖
第四章 《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
第五章 永樂青銅塑像
歷史背景
三「法王」和五「王子」
噶瑪教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大寶法王得銀協巴
薩迦派第三十二代主持大乘法王昆澤思巴
宗喀巴和大慈法王釋迦也失
塑像
菩提伽耶模型
永樂後期青銅塑像
藏人眼中的明代青銅塑像
三「法王」和五「王子」及永樂時期西藏和中原之間佛像饋贈表
附錄一
二十一救度佛母
附錄二
一、藏文文獻
二、漢文文獻
三、原著圖版目錄
四、參考書目
五、縮略語
六、譯名對照表
藏族風格和在藏的域外藝術家
畫派史和風格研究
敦煌藏族繪畫作品
斯坦因第32號收集品
藝術家白央
敦煌吐蕃贊普壁畫
黑水城
阿尼哥
飛來峰
居庸關
江孜白居寺
題記
第一章 《西夏藏》藏族風格木刻插圖
元刊
西夏刊
第二章 《磧砂藏》木刻作品
藏族僧人的袈裟
《影印宋磧砂藏經》中的八幅插圖
第三章 1410年《甘珠爾》插圖
第四章 《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
第五章 永樂青銅塑像
歷史背景
三「法王」和五「王子」
噶瑪教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大寶法王得銀協巴
薩迦派第三十二代主持大乘法王昆澤思巴
宗喀巴和大慈法王釋迦也失
塑像
菩提伽耶模型
永樂後期青銅塑像
藏人眼中的明代青銅塑像
三「法王」和五「王子」及永樂時期西藏和中原之間佛像饋贈表
附錄一
二十一救度佛母
附錄二
一、藏文文獻
二、漢文文獻
三、原著圖版目錄
四、參考書目
五、縮略語
六、譯名對照表
序
海瑟博士的專著(《早期漢藏藝術》(Early Sino—Tibetlan Art,Arisand Phillips
Ltd.Warminster,England,1975年版)一書由藏族青年學者熊文彬(藏名嘉絨雲沛)經長時間努力翻譯為漢文,在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是值得慶賀的事。這本書的作者、譯者乃至出版者都與我有深厚的友誼,責無旁貸,我應該講幾句個人的看法,交代一下此書翻譯的緣起和經過,給廣大讀者提供一點信息。
1985年8月,在德國慕尼黑北郊一座古代城堡里召開了第4屆國際藏學研究討論會,二十幾個國家的一百多位代表會聚一堂,群賢畢至,少長成集。會議間隙中,旅居德國、在巴伐利亞州科學院中亞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的邦隆活佛送給我海瑟的這本大作。我與海瑟在1981年維也納會議上相識。1983年她在巴黎接待了我,並陪我參觀了盧浮宮、聖母院等名勝古跡;l984年我在北京接待過她和她那可愛的兒子。友人著作,見獵心喜,當即翻閱,十分高興。在藏學界,人們都知道有這樣幾種研究藏傳佛教藝術的專著。
1.杜齊(G.Tucci,l894~l984年)的《西藏畫卷》(Tibetan:Painted Scrolis,Roma,1949年,有由李有義、鄧銳齡節譯的((西藏中世紀史》漢文版本)
2.扎雅活佛的《西藏宗教藝術》(The Religious Art of Tibet,1977年,西德威斯巴登出版,1992年由謝繼勝譯成漢文,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3.劉藝斯的(《西藏佛教藝術》(195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4.文金楊的(《藏族佛教木刻))(195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後來又陸續出版過《西藏》、《布達拉宮》、《大昭寺》、《薩迦寺》、《塔爾寺》、《拉卜楞寺》等各種專題畫冊,最近幾年更有《西藏唐卡》、《西藏文物精華》等巨型藝術畫冊出版,琳琅滿目。這些著作都有很好的研究,閱讀之下,可以得到很多知識。但是,以早期漢藏藝術的題材進行專門比較研究的,海瑟博士確實是第一人。得到這本書後,我經常利用其資料和觀點來充實我的教學內容。當時就希望能有個漢文譯本,讓更多的同道得以參考、利用。後來,熊文彬同志作為碩士研究生跟我研讀吐蕃時期的藏文文獻,我就把此書交給他,讓他作為參考書仔細閱讀。文彬好學敏求,銳意攻堅,孜孜石乞石乞,鍥而不合,不但認真、細致地閱讀了全文,而且查閱資料i核對圖冊,並把它譯為漢文。他在取得碩士學位後被分配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又有機會去西藏基層工作一年,他正好得以在拉薩地區生活,在人民群眾中游弋,得其所哉!他隨身帶著此書的譯稿,隨時向人請教,反復核校,不斷修改,及至全稿完成,用了二三年時間。睹其出版,也特別令我高興。
我在閱讀海瑟博士的這本大著時,留下了兩點極深的印象:
第一,作者不同於西方某些作者;她明確認識到,並且主張藏族原來固存本土藝術,不像某些西方學者,認為藏族藝術就是印度藝術的分支或翻版。藏族藝術絕大部分的確表現為佛教藝術,但是應該知道,沒有本土條件,佛教何以能在西藏升華為藝術?何以能憑空產生這樣一種成熟的藏族佛教藝術?今天,藏族佛教藝術鮮明的特點與獨特的個性已為人們承認,這足以說明藏族佛教藝術是佛教在東傳遷入藏區以後,與當地傳統藝術(或者說苯教藝術)交融、吸收、結合而成的,因此,它富有鮮明的高原色彩和濃烈的民族風格。以飛天造型為例,無論是人物造型、絳紅的袈裟、輕盈美妙的伎樂,還是背景天地、浩渺蒼穹、遠山碧樹、澄湖閃閃、白雪皚皚,都噴發著高原上濃烈的鄉土氣息。以藏族藝術中特有的民族氣質、風俗習慣、思想觀念來統馭或運載佛教,諸天護法、天王、伎樂及至佛陀、菩薩及其眷屬都可發現藏族的民族烙印。事實上藝術上的民族差異和地區懸殊正是人類文化史的精萃所在。海瑟博士敏銳地看到這些,令人欽佩。
第二,強調了漢藏藝術上的交流,豐富和發展了藏族藝術。藝術既要保持民族的特點,又要有其他民族的借鑒,並吸收其他民族的優點來豐富自己、壯大自己,使自己提高到新的高度。有沒有這種借鑒和吸收是大不相同的。從吐蕃時期的文化史來看,藏族是善於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長以補自己之短的民族,是一個向上的、朝氣蓬勃的民族。就以文學(包括佛經文學和非佛經文學)的翻譯來看就有極為崔巍的成就:翻譯了絕大部分的佛教經典(其中有相當部分譯自漢文),翻譯了《尚書》、《戰國策》等漢文古典著作,編了雙語(梵藏、漢藏)對照詞匯表,不難看出學者文人是多麽熱心於學習漢唐以來的文化瑰寶以迅速豐富自己並提高自己的文化層次。藝術,當然也不例外。海瑟能獨具慧眼,認識到漢藏文化包括藝術在內的交流是藏族藝術非常重要的、飛躍發展的因素。也許正因為海瑟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漢語文獲碩士學位後,又從師藏族學者噶爾美先生攻讀藏文,在她身上具有漢藏文化的雙重修養,這本大著顯示出她精深的修養和豐富的學識。歐洲的幾位大有成就的藏學家如石泰安、畢達克和烏瑞都是藏漢兼通的學者,這決非偶然。我們從海瑟所列舉的《西夏藏》木刻、《磧砂藏》木刻和1410年北京版《甘珠爾》、《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的圖版觀察到漢地和藏族藝術相互影響的史實,尤其是最後一章《永樂青銅塑像》的分析更是令人嘆服。總之,海瑟博士的工作值得我們很好地認識、了解,漢藏文化相互影響的研究課題也值得我們繼續深入追蹤。
借用兩句古詩「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來奉贈海瑟博士,並感謝文彬同志的辛勞。
王堯
1993年10月18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座講席
1985年8月,在德國慕尼黑北郊一座古代城堡里召開了第4屆國際藏學研究討論會,二十幾個國家的一百多位代表會聚一堂,群賢畢至,少長成集。會議間隙中,旅居德國、在巴伐利亞州科學院中亞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的邦隆活佛送給我海瑟的這本大作。我與海瑟在1981年維也納會議上相識。1983年她在巴黎接待了我,並陪我參觀了盧浮宮、聖母院等名勝古跡;l984年我在北京接待過她和她那可愛的兒子。友人著作,見獵心喜,當即翻閱,十分高興。在藏學界,人們都知道有這樣幾種研究藏傳佛教藝術的專著。
1.杜齊(G.Tucci,l894~l984年)的《西藏畫卷》(Tibetan:Painted Scrolis,Roma,1949年,有由李有義、鄧銳齡節譯的((西藏中世紀史》漢文版本)
2.扎雅活佛的《西藏宗教藝術》(The Religious Art of Tibet,1977年,西德威斯巴登出版,1992年由謝繼勝譯成漢文,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3.劉藝斯的(《西藏佛教藝術》(195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4.文金楊的(《藏族佛教木刻))(195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後來又陸續出版過《西藏》、《布達拉宮》、《大昭寺》、《薩迦寺》、《塔爾寺》、《拉卜楞寺》等各種專題畫冊,最近幾年更有《西藏唐卡》、《西藏文物精華》等巨型藝術畫冊出版,琳琅滿目。這些著作都有很好的研究,閱讀之下,可以得到很多知識。但是,以早期漢藏藝術的題材進行專門比較研究的,海瑟博士確實是第一人。得到這本書後,我經常利用其資料和觀點來充實我的教學內容。當時就希望能有個漢文譯本,讓更多的同道得以參考、利用。後來,熊文彬同志作為碩士研究生跟我研讀吐蕃時期的藏文文獻,我就把此書交給他,讓他作為參考書仔細閱讀。文彬好學敏求,銳意攻堅,孜孜石乞石乞,鍥而不合,不但認真、細致地閱讀了全文,而且查閱資料i核對圖冊,並把它譯為漢文。他在取得碩士學位後被分配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又有機會去西藏基層工作一年,他正好得以在拉薩地區生活,在人民群眾中游弋,得其所哉!他隨身帶著此書的譯稿,隨時向人請教,反復核校,不斷修改,及至全稿完成,用了二三年時間。睹其出版,也特別令我高興。
我在閱讀海瑟博士的這本大著時,留下了兩點極深的印象:
第一,作者不同於西方某些作者;她明確認識到,並且主張藏族原來固存本土藝術,不像某些西方學者,認為藏族藝術就是印度藝術的分支或翻版。藏族藝術絕大部分的確表現為佛教藝術,但是應該知道,沒有本土條件,佛教何以能在西藏升華為藝術?何以能憑空產生這樣一種成熟的藏族佛教藝術?今天,藏族佛教藝術鮮明的特點與獨特的個性已為人們承認,這足以說明藏族佛教藝術是佛教在東傳遷入藏區以後,與當地傳統藝術(或者說苯教藝術)交融、吸收、結合而成的,因此,它富有鮮明的高原色彩和濃烈的民族風格。以飛天造型為例,無論是人物造型、絳紅的袈裟、輕盈美妙的伎樂,還是背景天地、浩渺蒼穹、遠山碧樹、澄湖閃閃、白雪皚皚,都噴發著高原上濃烈的鄉土氣息。以藏族藝術中特有的民族氣質、風俗習慣、思想觀念來統馭或運載佛教,諸天護法、天王、伎樂及至佛陀、菩薩及其眷屬都可發現藏族的民族烙印。事實上藝術上的民族差異和地區懸殊正是人類文化史的精萃所在。海瑟博士敏銳地看到這些,令人欽佩。
第二,強調了漢藏藝術上的交流,豐富和發展了藏族藝術。藝術既要保持民族的特點,又要有其他民族的借鑒,並吸收其他民族的優點來豐富自己、壯大自己,使自己提高到新的高度。有沒有這種借鑒和吸收是大不相同的。從吐蕃時期的文化史來看,藏族是善於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長以補自己之短的民族,是一個向上的、朝氣蓬勃的民族。就以文學(包括佛經文學和非佛經文學)的翻譯來看就有極為崔巍的成就:翻譯了絕大部分的佛教經典(其中有相當部分譯自漢文),翻譯了《尚書》、《戰國策》等漢文古典著作,編了雙語(梵藏、漢藏)對照詞匯表,不難看出學者文人是多麽熱心於學習漢唐以來的文化瑰寶以迅速豐富自己並提高自己的文化層次。藝術,當然也不例外。海瑟能獨具慧眼,認識到漢藏文化包括藝術在內的交流是藏族藝術非常重要的、飛躍發展的因素。也許正因為海瑟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漢語文獲碩士學位後,又從師藏族學者噶爾美先生攻讀藏文,在她身上具有漢藏文化的雙重修養,這本大著顯示出她精深的修養和豐富的學識。歐洲的幾位大有成就的藏學家如石泰安、畢達克和烏瑞都是藏漢兼通的學者,這決非偶然。我們從海瑟所列舉的《西夏藏》木刻、《磧砂藏》木刻和1410年北京版《甘珠爾》、《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的圖版觀察到漢地和藏族藝術相互影響的史實,尤其是最後一章《永樂青銅塑像》的分析更是令人嘆服。總之,海瑟博士的工作值得我們很好地認識、了解,漢藏文化相互影響的研究課題也值得我們繼續深入追蹤。
借用兩句古詩「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來奉贈海瑟博士,並感謝文彬同志的辛勞。
王堯
1993年10月18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座講席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