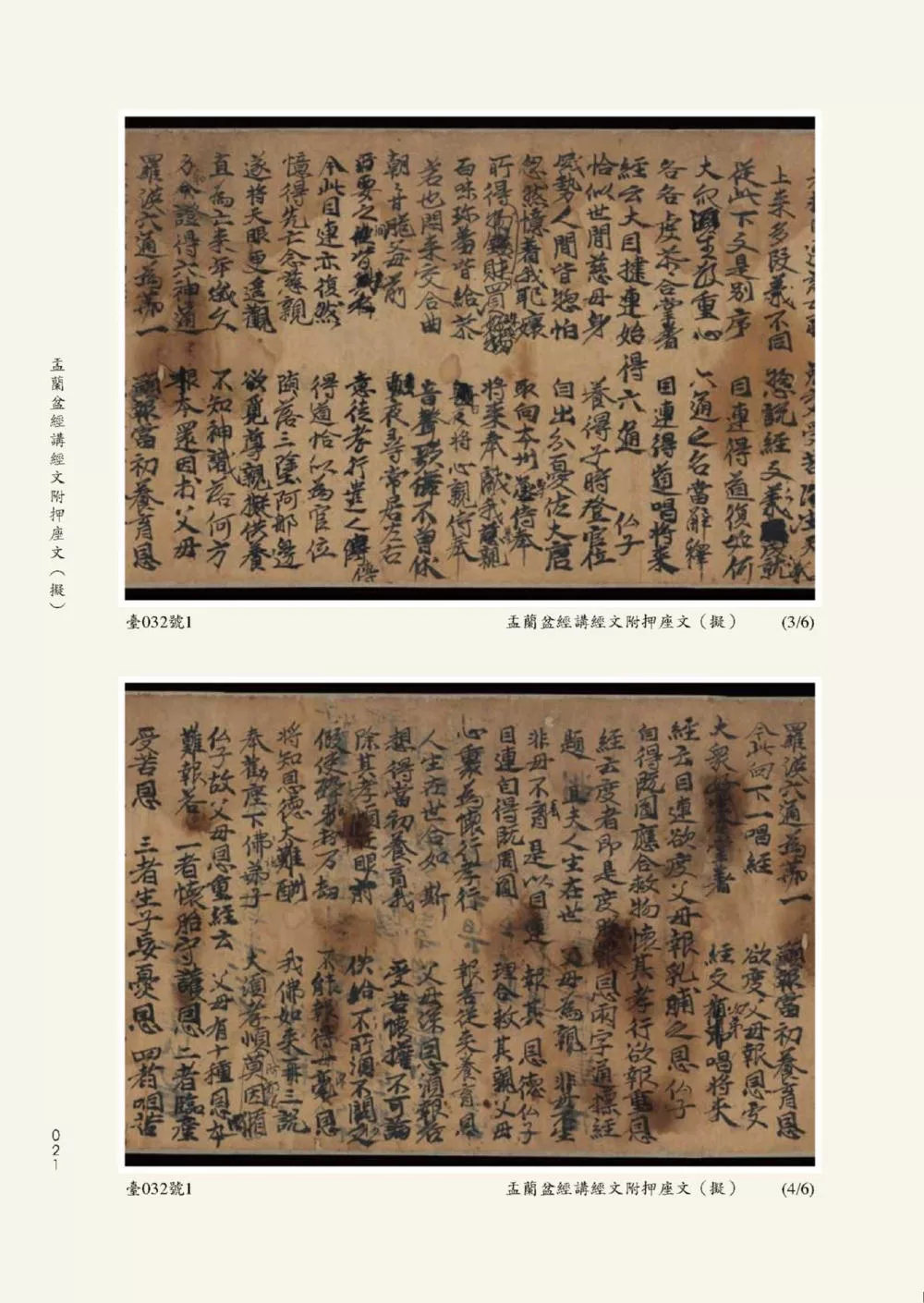序
曾淑賢/國家圖書館館長
國家圖書館職司國家文獻典藏,自一九三三年籌備伊始,即以集藏中文古籍善本為重要使命。本館草創時期即遇戰火,銜命西遷之際,亦克服萬難,於一九四○─一九四一年間籌組「文獻保存同志會」(以下簡稱同志會)搶購古籍。繼於復員時期及遷臺後,持續多方徵集,迄今以精緻豐美之一二九二二部(一三五四七八冊)善本典藏稱譽於世。其中典藏之敦煌卷子共百餘卷,該批文獻多為戰時及復員期間所購得,是臺灣收藏敦煌文獻最為豐富之公家機關典藏單位。
⠀
同志會成員由文化學者及版本學家所組成,於戰火最熾之際,化身書賈,巧避敵軍耳目,涉險於淪陷區搶購江南藏書家於戰亂中所拋售之累世庋藏,期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盡力存續文化命脈。期間屢仆屢起,在二年內計搶購善本四八六四部約四八○○○冊,為國家保存了重要之珍貴文獻,亦奠定了本館善本特藏之基礎。同志會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寫給蔣復璁館長之第六號工作報告書中,首次提及「李木齋所餘賸之敦煌卷子數十種(皆極精之品)有外流之虞。此批『國寶』,似當以全力保留之」。是年三月十九日再次函知蔣館長,提及李氏該批寫本實為精華所聚,時有境外大館表態問鼎之意,同志會正積極設法務使不歸異域,「為子孫百世留些讀書餘地」。目前可查得最早入館的敦煌文獻,是由同志會成員葉恭綽先生所經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購自香港;時葉先生暫居香港,負責廣東、香港兩地散佚古籍搶救之事。戰爭結束後的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間,本館陸續自北京、上海及南京等地購得敦煌文獻,主要是經由葉氏介紹購自李盛鐸(木齋)之女所收李氏舊藏,亦有部分為葉氏本人收藏,另有購自劉子昭等人者。至於與該批文獻時代相仿的日本寫卷,則分別於戰時及遷臺後購得。
⠀
本館館藏之敦煌文獻前身為名家所藏,繼由版本學者嚴選入館,數量雖不多,然皆為存世精品。其所屬年代上自東晉下迄歸義軍時期,除三卷道經及三卷藏文佛經外,其餘皆為漢文佛經,並有多件為無傳世本,彌足珍貴;另有經名家鑑賞、裝裱、題跋及鈐印者,充分展現其豐富之遞藏史。一九四九年,本館隨政府遷臺,這批敦煌文獻亦隨十餘萬冊善本運抵臺灣。如今,該批文獻有十種經文化部審定為國寶級及二種為重要古物級,實為中華文化與人類知識之精蘊淬鍊所在。
⠀
本館館藏敦煌文獻最早由潘重規教授整理著錄,於一九六八年發表〈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燉煌卷子題記〉一文刊於《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二期。一九七六年在潘教授積極倡導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一套六冊大開本付梓,首開敦煌館藏以照片圖錄方式全數編印出版風氣之先。近年來,隨著本館古籍數位化作業之推展,為方便研究者參考運用該批文獻,乃將其數位化影像公布於本館自建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供學界運用,並加入「國際敦煌項目」(http://idp.bl.uk),提供高階數位化影像檔於該平臺,以加強國際學術之研究與交流。
⠀
時光荏苒,歲月悠悠。本館館藏敦煌文獻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掀開研究新頁。二○一○年十一月,本館邀請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方廣錩教授蒞館,進行館藏敦煌文獻之鑑定研究。方教授此行對該批文獻進行全面研究及重新整理,除逐一檢視原件,就保存狀況、紙質特徵、紙數、字行數等進行記錄外,並析究文獻之內容原典,與《大藏經》內容進行比對,且依據文獻特性重新編目給號。感謝方教授之辛勤整理,為該批文獻撰寫敘錄,才有機會促成此次之重新編輯、出版刊布,提供研究者資料運用之便利性,在此特別向方教授致上最誠摯的感謝。
⠀
一九五七年十月,本館南海路舊館閱覽大廳落成,蔣復璁館長有感而發地自撰一副楹聯於門廳兩柱,上聯有云:「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皆嬛秘笈,歷劫不磨」。其所謂之唐鈔祕笈者,即今呈現於眾人眼前的這套煌煌巨著。嫏嬛福地藏祕笈,歷劫歸來志不磨。願藉由此次之出版,踵繼前輩志業,續寫傳布新頁。
後記
方廣錩/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就世界各敦煌遺書收藏單位的收藏而言,原中央圖書館收藏的這批遺書始終在人們的關注中。早在一九六○年代初,由王重民先生主持編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在其第四部分:「敦煌遺書散錄」中共收入散藏敦煌遺書目錄十九種,排在第一位的,赫然就是《前中央圖書館藏卷目》。該《前中央圖書館藏卷目》據「中央圖書館甲庫善本書目錄」,共著錄敦煌遺書六六號。因其中一號下有包含兩卷、三卷或者附有殘葉者,故實際共計著錄敦煌遺書七三號並附殘葉兩紙。
《中央圖書館甲庫善本書目錄》完成以後,該館所藏敦煌遺書續有增加。一九六七年,潘重規先生對館藏「敦煌寫本百五十餘卷」逐一審核、著錄、編目,發表在《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二期。接著,又於一九七五年對原目錄作了較大的修訂,即「依書目(指《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引者注)次第,重編〈題記〉,增載吳君(指吳其昱先生——引者注)之說,並采館方記錄,添注卷子幅度。寫定刊布」。潘重規先生把這一修訂稿命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發表在一九七五年《敦煌學》第二輯。該〈題記〉共計著錄館藏敦煌遺書一四四號(其中含日本古寫經三號四件)。與《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對每號遺書僅有寥寥數語之介紹不同,〈題記〉對每號遺書的經名、卷次、譯作者、抄寫時代、紙張、紙數、行款、界欄、框高、內容起訖及其與《大正藏》本的對照、避諱字與武周新字,乃至該遺書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的編號等各種相關信息,均作了較為詳盡的著錄。如前潘重規先生自述,該〈題記〉還著錄了館藏對某些遺書的一些信息(包括來源信息與庋藏信息),著錄了吳其昱先生對某些卷子的相關意見。長期以來,潘重規先生的〈題記〉成為人們了解館藏敦煌遺書的主要依據,成為敦煌學研究者利用這批敦煌遺書的導航。
《敦煌學》第二輯還刊登了吳其昱先生的〈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蕃文寫本佛經四卷考〉,石田幹之助先生撰、邱棨鐊先生譯的〈臺北圖書館所藏敦煌古鈔目錄〉,牧田諦亮先生著、楊鍾基譯〈臺北中央圖書館之敦煌經〉等,使《敦煌學》第二輯成為館藏敦煌遺書的研究專輯。此後,不少先生又在《敦煌學》及其他著作、刊物中,發表有關館藏敦煌遺書的新的研究成果,有關資料可以參見鄭阿財、朱鳳玉兩位先生,及其他諸位先生編著的各種敦煌遺書研究論著目錄,此不贅述。
我這次編目,不同程度地利用了王重民先生、潘重規先生以及其他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在此特向諸位先生的辛勤勞動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遺書編號與敘錄體例
此次承館方邀請,依據原件對館藏敦煌遺書及日本古寫經再次鑑定並重新編目,纂為敘錄。在此先介紹該敘錄的編號與體例:
(一)遺書編號
館藏敦煌遺書,除了前述《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給的「總目號」外,尚有館方所給的「登記號」與「索書號」,此外還有潘重規先生〈題記〉所給的「潘目號」,共計四種。
此次編目,為了既便於讀者查閱、又便於館方管理;同時考慮到原有四種編號中的「總目號」、「潘目號」、「登記號」等三種都未能將館藏敦煌遺書全部納入,唯有該館目前用來對館藏敦煌遺書重新給號,以與其他收藏單位的敦煌遺書及該館前此的四種編號相區別。
「臺號」從「臺○○一」起,到「臺一四二」止,將館藏敦煌遺書共編為一四二號。又,此次編目按照館方的意見,將館藏七件日本古寫經作為附錄一併納入。為與館藏敦煌遺書相區別,故以字頭「臺附」為標誌,從「臺附○一」到「臺附○七」,共計七號。本文把上述以「臺」、「臺附」為字頭的編號,稱為「主編號」。如上所述,此次共計著錄主編號一四九號。
為了體現敦煌遺書的文物特徵,也為了便於館方管理,著錄時需要把每件獨立的遺書單獨編為一號。但由於種種原因,收藏單位有時會在一個編號下納入幾件形態相互獨立的遺書,該館也不例外。遇到這種情況,編目時為了既不打亂館藏原編號次序,又能將各自獨立的遺書梳理清楚,一般採用在主編號後附加「A、B、C……」等字母的方式,為各獨立件分別給號。我把由此形成的編號稱為「文物號」。根據館藏遺書的不同情況,「文物號」有兩種表現形態:一種是館藏一個主編號中只有一件遺書,此時文物號形態與主編號相同;一種是館藏一個主編號中包含幾件形態各自獨立的遺書,此時在主編號後面附加「A、B、C……」等字母,故此時文物號的形態為「主編號A、主編號B、主編號C⋯⋯」等。如前所述,館藏敦煌遺書共有一四九個主編號,此次共編為一七○個文物號。亦即館藏的敦煌遺書與日本古寫經,共有一七○個獨立件。其中敦煌遺書的獨立件為一六二件,日本古寫經的獨立件為八件。
一件敦煌遺書上往往抄寫多個不同的文獻。這些文獻或分別抄寫在正、反面;或在正面、反面各抄寫若干個文獻。為了體現敦煌遺書的這一特徵,梳理清楚此批敦煌遺書共計抄寫了多少文獻,我採用「文獻號」來區別並著錄某遺書上抄寫的不同文獻。所謂「文獻號」,係在文物號後附加「1、2、3⋯⋯」或「背1、背2、背3⋯⋯」等,以表示該文獻抄寫在遺書的哪一面、及它在遺書正面或背面所抄諸文獻中的排列次序。故「文獻號」有三種表現形態:如果一件遺書上僅抄寫一種文獻,此時文獻號形態與主編號相同。如果一件遺書的正、背面各抄寫一個文獻,抄寫在正面的文獻號形態與主編號相同,抄寫在背面的文獻號形態則寫作「主編號背」。如果一件遺書正面、背面各抄寫若干個文獻,則按照這些文獻在遺書上的先後次序,依次把它們的文獻號編為「主編號1、主編號2、主編號3、⋯⋯」,乃至「主編號背1、主編號背2、主編號背3、⋯⋯」等,以此類推。館藏的一七○件敦煌遺書與日本古寫經,共抄有二一五個文獻。其中一六二件敦煌遺書共抄寫了二○七個文獻,八件日本古寫經共抄寫了八個文獻。故共計編為二一五個文獻號。
(二)敘錄體例
為便於把有關遺書的各項數據輸入「敦煌遺書數據庫」,此次編目的初稿,按照我設計的「條記目錄」格式編纂。有關「條記目錄」的著錄規則,可參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三月)或大型圖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九月)末尾所附「條記目錄」的有關說明。為避文繁,此不贅述。但本目錄正式定稿時,按照館方要求,將「條記目錄」改為「敘錄」體。兩種目錄的文體形式雖有不同,著錄內容基本對應。
按照館方要求,對每個文獻撰寫一條相應的敘錄。故本目錄共包括二一五條敘錄。諸敘錄按照主編號→文物號→文獻號這一次序排列。
二、學術價值
在〈談散藏敦煌遺書〉一文中,我依據敦煌遺書流散史及目前收藏形式的不同,把敦煌遺書分為三類:
第一類,從敦煌出土後,未經過中間環節,直接被收藏單位收藏。
第二類,從敦煌出土後,曾經過中間環節,其後被收藏單位收藏。
第三類,從敦煌出土後,在民間流傳,至今依然由私人收藏家收藏。
並將上述第二類、第三類稱為「散藏敦煌遺書」。本敘錄所著錄的無疑為第二類,屬於「散藏敦煌遺書」。
我認為,敦煌遺書包含文物、文獻、文字等三個方面的研究價值。因此,評價某一批敦煌遺書,包括散藏敦煌遺書時,應該從上述三個方面作綜合的討論。
(一)文物研究價值
如何評定敦煌遺書的文物價值,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觀點。我認為,「文物價值以敦煌遺書的斷代為主要依據,並考察其製作方式、品相、紙張(或其他載體)特點、保存數量、裝幀、裝潢、欄格、裱補、古代裱補紙、書寫主體、題記、印章、現代裝裱、收藏題跋印章、附加物,予以綜合評價。」以下參照上述標準,簡單談一下對館藏一四二號、一六二件敦煌遺書文物價值的看法。
1、抄寫年代分布及其占收藏單位總數的比例
中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是世界上收藏敦煌遺書最多的兩個單位,共計收藏敦煌遺書的文物號達三一四三四號,館藏則為一四二號、一六二件。我們可以把上述兩個單位所藏敦煌遺書之不同年代的寫本數量的分布及其占據總數的比例,與館藏同類寫本的相關數據作一個對比。
兩相對比,我們可以看到:東晉寫經,館藏占比約為○.六%,後兩個收藏單位同類寫經的占比約為○.三%;南北朝寫經,館藏占比約為一八.五%,後兩個單位同類寫經的占比約為八.六%;隋代寫經,館藏占比約為二.五%,後兩個館同類寫經的占比約為○.八%。亦即唐以前寫經,館藏約占據全部藏品的二一.六%,超過五分之一。而後兩個館同類寫經的占比約為九.七%,不足十分之一。亦即館藏高古寫經所占總數的比例要比後兩個單位高出一倍。
2、首尾殘況
敦煌遺書大部分殘破不全,其中有些甚小的殘片。編目實踐中,我一般對殘片不著錄其首尾的保存情況,僅著錄為「殘片」或「小殘片」。而對其他遺書則根據「全」(即保存完整)、「殘」(即已經不規則殘缺)、「脫」(從兩紙黏接處脫落)、「斷」(被後人剪斷)四種情況,著錄其首尾的保存情況。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英國國家圖書館的殘片、小殘片共達一萬多號,故下表僅統計其餘一九四四一號的首尾保存情況,而館藏的一六二件中,亦除去殘片、小殘片四件,故下表所列僅為一五八件。
從上述表格中數字的比較,我們可以了解館藏敦煌遺書的首尾存況也遠遠優於另外兩個單位收藏的敦煌遺書。
3、長度
據統計,不計八件日本古寫經,館藏的一六二件敦煌遺書中,包含大小紙張一五一八張,合計總長度約為六五一.八公尺,合計總面積約為一七○平方公尺,正反面總計抄寫三八三○○餘行,合計總字數約七二萬字。如將八件日本古寫經也加入,則上述統計數字為:總計古寫經一七○件,包含大小紙張一八六○張,合計總長度約為七三六.九公尺,合計總面積約為一九三平方公尺,正反面總計約抄寫四二○○○行,合計總字數約七七萬字。
如果僅計算每件敦煌遺書的平均長度,則因館藏一六二件敦煌遺書的總長度為六五一.八公尺。故其每件敦煌遺書的平均長度約為四.○二公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總長度為三四六○七.○九公尺,編為一七三三七個文物號。故其每件遺書的平均長度約為二公尺。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長度為二四○二一.四九公尺,目前編為一五一三四個文物號,故其每件遺書的平均長度約為一.五九公尺。
4、長度達八公尺(含八公尺)以上的遺書及其占總數的百分比
在編制敦煌遺書定級國家標準的過程中,通過調查研究,我們認為將每個獨立件的長度定為八公尺,作為敦煌遺書定級的參考指標之一,是比較適宜的。
按照這一指標,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七三三七件敦煌遺書中,八公尺以上寫卷共有一○三二件,約占寫卷總數的六.○%。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五一三四件敦煌遺書中,八公尺以上寫卷共有八三五件,約占寫卷的五.五%。館藏的一六二件敦煌遺書中,八公尺以上寫卷共有二四件,約占寫卷總數的一四.八%。
在〈談散藏敦煌遺書〉中,我總結了散藏敦煌遺書的若干特點,其中之一為:一般來說,散藏敦煌遺書的長度較長,保存狀態較好。館藏的敦煌遺書也符合這一特點。這主要是由於敦煌遺書是古代寺院的棄藏,絕大部分遺書斷頭殘尾。散藏敦煌遺書大都是人們從這些殘破遺書中挑選出來的。雖然這種挑選,實際不過是矮子裡拔將軍,所以絕大部分散藏敦煌遺書依然是殘破卷子。但散藏敦煌遺書畢竟是矮子裡拔出的將軍,它們的長度、保存狀態都要比第一類沒有經過中間環節直接進入收藏單位的遺書為好。
散藏敦煌遺書的另一特點是往往經過現代裝裱,有現代人收藏鑒賞題跋、印章等。館藏敦煌遺書,有的曾經袁克文、許承堯、魏忍槎等著名收藏家收藏,有的且有若干名人題跋,殊為珍貴。特別值得提出的是:
臺○二七號,為《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八。卷首下有一枚棗紅色方形陽文印章,二.五×二.五公分,印文難以辨認。但卷面有正方形陽文硃印共六枚:其中三枚七.五×七.五公分,印文為「覺皇寶/壇大法/司印/」。另三枚八×八公分,印文第一行上為星狀符印,下有「斬邪」二字;第二行為符印;第三行上為符印,下有「田田田」三字。這一印章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亦有發現,疑或曾被道士王園祿用來作為做法事之道具。
臺○九六號,為《十地經論》卷一。扉頁有六行題跋:「六朝人書《十地不動論》卷子。/敦煌莫高窟所出六朝隋唐人書夥矣。/古籍固罕,若經論、經疏亦鮮于寫經。/此《十地不動論》确為北朝人書。卷末有/『一姣(校)』二字,殆書者之名也。據此以校大/藏,勝于經典遠矣。乙丑(一九二五)冬月,克文。/」跋前上下有二枚印章:(1) 一.二×一.七公分,印文為「洹上寒雲」。(2)
一.○×一.○公分,印文為「雙爰庵」。故知該卷曾為袁克文珍藏。該卷現代已修整,接出綢面護首,特別是卷尾後配細長白玉軸。此種白玉軸因極易斷裂,故製作困難,極為珍稀。本人雖已經考察過數千號流散敦煌遺書,此類細白玉軸,至今僅此一見。
如前所述,敦煌遺書的文物特徵體現在諸多方面。雖然館藏敦煌遺書的數量不多,但年代涵蓋了從東晉到北宋初年,基本體現了敦煌遺書已有的各時代的主要紙張乃至題記、印章、雜寫的多種表現形態。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可以讓我們從小見大,大體把握敦煌遺書的總貌。其歷經文人墨客、社會名流珍藏的歷史,又為它們增色不少。限於篇幅,本文對這批遺書的文物特徵的進一步解說暫且從略。
需要指出的是,館藏敦煌遺書,除了臺一一九號尾部題記可疑外,未發現偽卷、偽題記。我們知道,散藏敦煌遺書中經常可以發現涉偽卷子,包括通卷作偽、部分作偽、在真卷子上添寫偽題跋、將真卷子截頭去尾相互拼接等等。從這一點講。館藏的敦煌遺書在諸散藏敦煌遺書特藏中可稱翹楚。據有關資料,當年收購這批敦煌遺書時,大多經過徐森玉、趙萬里兩位先生把關。從館藏遺書現狀可知,兩位先生的鑒定工作對這批遺書的質量保證起到極大的作用。
(二)文獻研究價值
所謂文獻價值,首先考察這些敦煌遺書上所抄寫的文獻,哪些有傳世本,哪些前此不為人們所知。其中,那些前此不為人們所知的文獻,自然具有更高的研究價值。但即使已有傳世本者,如果敦煌遺書寫本與傳世本文字有不同,則亦有一定的校勘價值。
館藏一四二號敦煌遺書,共抄寫二○七個文獻,今編為二○七個文獻號。大體情況如下:
1、一二○號文獻有傳世本,已經保存在古代大藏經中,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五八%。
2、二五號文獻雖未被古代大藏經收入,但敦煌出土後,被日本《大正藏》錄文,收入第一九卷、第二一卷、第八五卷等卷,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一二.一%。
以上兩類,共計文獻一四五號,現均可在《大正藏》中查到相應的文本,約占館藏敦煌遺書文獻號總數的七○%。經過初步考察,上述一四五號中,館藏文本有四六號均與《大正藏》本有差異,或為異卷、或為異本、或行文有差異,可供校勘。這部分文本約占《大正藏》所收文獻號總數的三一.七%。
3、雖無傳世文本,但前此研究者已有錄文、整理者,計四號,分別發表在《藏外佛教文獻》、《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中,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一.九%。
4、無傳世文本,前此亦從來無人錄文、整理,但被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推出的《電子佛典集成(二○一六版)》收入者,計二五號。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一二.一%。唯這一批錄文尚為初稿,還需修訂。
5、道教文獻三號,已收入《中華道藏》。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一.四%。
6、此次編目,共重新錄文三十號,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一四.五%。但其中《電子佛典集成(二○一六版)》已有錄文者一八號,《敦煌佛教經錄輯校》、《大正藏》已有錄文者各一號,完全屬於新錄文者僅一一號,新錄文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五.三%。
7、無傳世文本,至今仍未錄文、研究者,尚有一九號,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九.二%。
綜上所述,館藏二○七號敦煌文獻中,有傳世本者為一二○號,約占文獻號總數的五八%,無傳世本者為八七號,約占文獻號總數的四二%。如前所述,在有傳世本的一二○號文獻中,尚有四六號可據敦煌遺書校勘;而另外的八七號文獻,則全部是敦煌遺書提供給我們的新資料。這八七號文獻,不少已經有研究者注意並作了初步研究,亦有部分至今未為研究者所關注。已經作了初步研究的文獻,依然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所以,館藏敦煌遺書是值得研究者進一步發掘的寶藏。
此處僅就編目所及,介紹幾件重要的遺書。
臺一二七號,《遺教法律三昧經》卷下
該首殘尾全。現存一一紙,三八六行。有尾題「惟教三昧下卷」。因歷代經錄中並無與此對應的經名,故前此有研究者將尾題中的「教」字讀為「務」,認為該經或為歷代經錄著錄的《惟務三昧經》。
按:《惟務三昧經》,最早見錄於《出三藏記集》卷五,作:「《惟務三昧經》,一卷。(或作《惟無三昧》。)」屬於道安著錄的二六部偽經之一。後隋《法經錄》把它歸入真偽難辨的「疑經」。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則將它作為失譯經,直接收歸入藏。《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則繼承道安的著錄,將它判為偽經,故此經此後失傳。但館藏此文獻並非《惟務三昧經》,實為「《遺教法律三昧經》」,又稱「《遺教三昧經》」,臺一二七號尾題中之「惟」,實乃「遺」字之誤。後唐景霄纂《四分律鈔簡正記》卷十五稱:「《遺教法律經》等者,行古引經,許著五大色之失。亦名《遺教法律三昧經》。〈文〉此經明五部,各著一色。」宋允堪述《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輔要記》卷一稱:「⋯⋯《遺教法律三昧經》,古師引此經,便許著五大色衣。」臺一二七號正有五大部「著五大色衣」的內容。可證它實際是失傳已久的《遺教法律三昧經》。
《遺教法律三昧經》,最早見錄於隋《法經錄》,列為「眾律疑惑」。其後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六著錄,謂「見《始興錄》」。並稱:
西晉惠帝世,沙門釋法炬出。初炬共法立同出。立死,炬又自出。多出大部。與立所出,每相參合,廣略異耳。《僧祐錄》全不載。既見《舊》、《別》諸錄,依聚繼之。庶知有據,以考正偽焉。
隋彥琮《眾經目錄》亦仿照《法經錄》列為「疑惑」。但《大唐內典錄》接受費長房的觀點,把它作為法炬翻譯。《大周錄》繼承這一觀點。《開元釋教錄》在卷二「法炬譯經錄」中著錄了這部經典,但在卷十八的「偽妄亂真錄」中又稱:
《遺教法律三昧經》,二卷
右按長房等代錄及失譯錄,俱有此經。既並無本,詮定實難。且各存其目。(撰錄者曰:「此經余雖不者見全本,見所引者,多是人造。」)
也就是說,唐智昇當年已經未能見到該經的全本,他所見到的,只有其他典籍中的引文,他據那些引文對該經進行真偽判定,認為「多是人造」。但智昇的觀點,並未得到普遍的認同。如前所述,後唐、宋代的律宗僧人,均有繼續引用該經的。
今天,我們有幸看到館藏的該六世紀寫本,且下卷基本完整,甚為可貴。從內容看,該文獻雖然被命名為「經」,但論述的是戒律。所以《法經錄》把它列入「眾律」是正確的。按照《歷代三寶記》的記載,該文獻為西晉所譯。這也反映了中國早期佛典翻譯,未能正確辨析經律論的歷史事實。此外,我們現在看到的臺一二七號的文字,的確甚為質樸,呈現的也是早期譯經的形態;從其內容察看,該文獻的不少內容完全屬於對印度佛教的敘述,恐非初傳期中國佛教信徒所能杜撰。所以,智昇在沒有得到原本的情況下,僅依據引文便將本文獻判為「偽妄亂真」,恐怕有點草率。
不管怎樣,臺一二七號的出現,為我們研究印度部派佛教、部派佛教戒律、中國早期佛教戒律、早期譯經、中國人的疑偽經觀都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值得深入研究。
臺○九七號1,《論佛性如來藏義》(擬)
這是一件三階教經典殘卷。原卷雖首脫尾全,但無尾題,故該文獻原名不清,在古代三階教經典目錄《人集錄都目》中是否已有著錄,亦尚需考訂。敘錄所著錄為擬題。該文獻最早由日本學者西本照真發現,錄文後發表在他的《三階教の研究》中。此次依據原卷再次錄文。
三階教是隋信行創立的佛教宗派,歷史上曾經屢次遭到鎮壓,但屢踣屢起,最終約消亡在「會昌廢佛」的浪潮中,該教的典籍也由此損亡殆盡。所幸的是,敦煌遺書與日本古寫經中保存了一批三階教典籍,它們證明古代三階教曾在敦煌流傳,也為我們今天研究三階教這一已經消亡的佛教派別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臺○九七號1的主題是論佛性如來藏,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從竺道生之後,除了法相唯識等個別佛教派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理論可說已經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追究其原因,我認為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人之初、性本善」,以及中國儒家提倡的「人皆可為堯舜」不無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該文獻在論述佛性及其作用時,採用了「體」、「相」等範疇,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否有什麼內在的聯繫,似乎可以進一步探討。特別是在中國佛教主體性受到挑戰的今天,印度佛教到底是怎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逐步演化為中國佛教的?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有什麼相同,又有什麼不同?中國佛教有無自己獨立於印度佛教的主體性?如果有,我們應該如何定義與描述這種主體性?這種主體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如此等等,臺○九七號1都可以成為我們探討的對象。近些年,我比較關注禪宗研究。禪宗的源頭,固然追溯到達摩東來,但禪宗的發展與其他派別互有交流。其中禪宗在理論與行法兩方面,與三階教是否也存在一定的交流,就是一個頗有興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