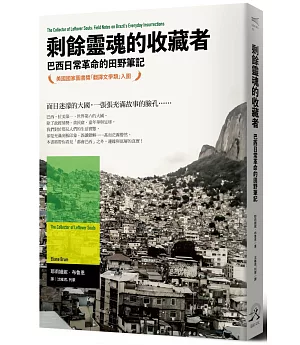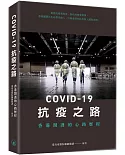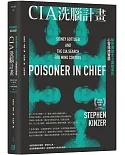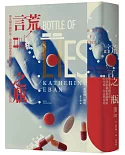前言
在不同的世界之間
身為記者,或者該說如我這般的記者,意味著得要成為一個雙面人;而對向的那一面便是母語的世界,那個人們初生而至的世界。這本書所描寫的人物,生來就都說著巴西語,這種語言源自殖民者的葡萄牙語,摻雜了過去巴西原住民的腔調,還有當年來到此地的各種非洲黑奴腔調;他們的發聲方式已不純正,提高聲調的眾多方式裡混雜了主人的母音與子音。他們的主體語言受到了影響,在葡萄牙殖民者脅迫下必須稜角分明、尖銳劃分之處,他們留下了婉轉的聲線。他們在過去鞭子抽打之處創造著音樂。我所說的「巴西語」(或「巴西葡萄牙語」)是一種反抗的語言。這是我的語言,也是書中所有巴西人的語言。
這些以不屈服的語言所述說的真實故事,於此首度以英文呈現。本書的夢想之一,是期望此番的交會不要成為某種帶有暴力意味的行為,而是帶來一種可能性。出版之際,有些國家正努力築起更高的圍牆,用以防止叛亂的語言入侵他們自認純粹的正統;他們害怕的,是受到其他現有體驗的汙染。如此說來,這本書將我那語言的革命性質帶進了英語中,而這也是書所應該做的——書應當對世人當頭棒喝,打破屏障。如果你翻開了它,翻開這本由一個巴西記者撰寫的書,那麼肯定你也不喜歡那些藩籬。
每當我造訪英語系國家都會發覺,巴西對於多數人而言並非真實存在;巴西只存在於嘉年華與足球的刻板印象中,還有貧民窟、光屁股與暴力,近年來則又多了政治腐敗。在本世紀的頭十年,巴西吸引了全球的注目,因為金屬加工工人出身的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不僅當選總統,更施展魔法,在不撼動富人特權的狀況下,成功減少了貧窮人口。所謂的「第一世界」特別喜歡這種魔法,因為它,地球上地緣政治中明顯的不平等,差異變小了,儘管這種不平等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此外,這種魔法人人滿意,因為沒有人必須為了達到最低社會公正標準而失去任何東西。但幾年之後還是證實了,世上不存在魔法。既然巴西沒能施展魔法,自然就回歸到了原先的處境,繼續存在於「富裕」世界想像的背景中。如果有人說財富必須重新分配,好讓那些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再死於飢餓與子彈,那他肯定不會是個受歡迎的人物。
二○一八年,巴西重回世界矚目的鎂光燈下,因為雅伊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當選了總統,他提倡酷刑並為施加酷刑的人辯護,他侮辱黑人、女性與同性戀,他宣稱少數族群必須消失,而他的政敵則注定要流亡或入獄。二○一○年代的尾聲,巴西加入了某些選民行為矛盾的國家陣營裡,人民藉由投票(選出獨裁者)反抗著民主。再一次,在字裡行間堅守與眾不同與獨特的反叛,以及日常的小小革命,成為在此文化淪喪之際得以讓生活堅定不移的必須。
巴西是個僅以複數存在的國家,即巴西人民。若只是單數,一切都將不可能。既然我們是複數的巴西人民而非單數,自然也就有許多巴西的聲音存在。我身為記者的挑戰是聆聽這些迥異的聲音,將之轉換成文字,並禁絕遺漏其中蘊含的訊息,盡量完整呈現他們訴說的世界。然而,這是一種我在嘗試的同時就已經失敗了的挑戰。
在全球最大的這片熱帶雨林,巴西占有其中最廣的一部分;在這個人為導致氣候變遷的世界,熱帶雨林成了一種策略財富。當人類不再害怕災難或擔心他們恐懼的災難成真,雨林就成了一種力量。自從一九九八年以來,我便頻繁探訪亞馬遜雨林,傾聽著關於人們、樹群與動物的故事。撰寫這篇前言時,我已經在阿爾塔米拉(Altamira)住了一年了,這座城市就位於亞馬遜雨林欣古河(Xingu
River)河畔。
這本書從一場雨林中的誕生開始寫起,結束於聖保羅都會區(Greater São Paulo)周邊的一場死亡。聖保羅是巴西最大的都會區,也是全球十大都會區之一,人口多於兩千萬,超過葡萄牙與荷蘭等國。我不住在亞馬遜雨林的時候,就會住在這座建築荒漠中;河流在這裡交會,覆蓋在混凝土墳墓之下,每當我們行經其上往往快步走過。我把自己的身體當成橋樑,置身於這些形形色色的巴西人民之間。
本書收錄的故事,來自我人生中的兩段記者生涯。較短的專題報導寫於一九九九年,當時的我任職於巴西南部的報紙媒體《零時刻》(Zero Hora),那裡也是我的出生地;我負責的是名為〈無人見著的生活〉(The Life No One
Sees)的專欄撰文,每週六刊出。在這個一整版的頁面中,我寫著那些一般被定義為「平常人」的生活。他們不是報紙上的那種新聞人物,他們的生與死被縮減寫成一小則短文,好比註腳一般,無足輕重到幾乎在頁面上一閃即過。我撰寫這個專欄的目的是為了告訴人們,世上沒有所謂平常的生活,只有受到馴化的眼睛,而這樣的眼睛無法洞見每個生活其實都是由不平凡轉化而來的。
若我們的眼睛不想被馴化,便要知曉每個個人生活所具有的獨特性,而這正是我將每一則小小的報導編織起來的原因。這些「未發生的事」(unhappenings,這是我造的詞,用以描述我所進行的報導工作)背後的政治意涵,就是沒人能被取代。因此,某些人的生活並不比其他人的還要有價值。累積了幾年,這些報導集結出版,並有幸獲得了巴西最大的報導文學獎。
本書後段收錄的八則短篇報導,則道盡了驅使我成為記者的動機。每個人赤裸裸出生,如何從擁有甚少,直至最終創造出一整個人生,這種種一切都令我著迷不已。這個動機也是帶領我們經歷這麼多世界與這麼多語言的關鍵。我想從這些執著的人身上學習如何賦予意義、創造人類的存在。生活就是我們創作的第一部小說。這部小說,我們稱為「現實」,就是我報導的實質內容。
一篇報導很短簡,卻需要大量的調查。我相信新聞報導,那是每日歷史的文字記錄,如實地記下生活傳述的訊息,就像是見證一般。我進行新聞工作時嚴謹以對、追求切實、重視用詞準確。但我也確信,現實的脈絡複雜不只由文字交織而成,其中還有質感、氣味、色彩、手勢。汙點、失落、暴行、各種細微差別,以及靜默、毀滅,也都錯綜融合成為現實。
我個人對新聞報導的看法是過去三十年建立起來的,我的人生幾乎每天都致力於接觸陌生的世界——不僅我看他們陌生,他們看我也很陌生。大家常說,你得上街踏破鐵鞋才找得到新聞,但新聞不只存在街上。一則報導還需要最原始的基進運動:跨越你自己這道鴻溝。或許這才是最深刻也最艱難的行動,它要求你跳脫自我,融入他人,融入那個他方的世界。唯有打開所有的感官去傾聽,才能做到這一點。那種傾聽裡,沒說的話與說出口的一樣重要,聲音和迴響也與寂靜一樣重要,家具的質感與選擇貼在牆上的畫一樣重要。氣味與缺席,否認、驚嚇與猶豫,咬指甲的痕跡、選擇或遺忘的機巧,分歧,還有被遺留的一切。
既是新聞報導,意味著我們得脫掉自己的衣服,套上他人的穿著。也就是說,我們得屏除自己的偏見、判斷、世界觀,這麼做是為了讓世人得知在這個星球上還有其他的存在經驗,且不僅只存在,而是那麼的獨一無二。然後,再走過漫長的路回來孕育文字,寫下這篇文章傳述的訊息,而這一切皆由這具從當地返回傳播新聞的身體交織而成。透過這一系列寫作報導的傳遞動作,他方成了彼與此。
透過這種姿態,我才能為那些報導沒有寫到的人們達到上述境界。身為記者,我發現自己常常遇上以口述方式創作文學的文盲;他們所給予我的滋養,重要性並不亞於圖書館架上的知名作家。拄著鋤頭靠在石頭上,或把釣魚竿放進獨木舟的男男女女,以充滿詩意的散文述說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均源自世上獨一無二的人生經驗。他們大方分享自己的故事,沒有意識到在述說的同時,他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宇宙。經過三十年,如今這些人成了一群對我影響深刻入骨的人。而這種與他人真實交集的過程是無害的。
書中收錄較長的九篇報導,其中七篇寫於本世紀頭十年,從二○○○年到二○○八年,我任職於聖保羅的新聞週刊《新時代》(Época);而這些篇章也收錄在另一本書《街頭之眼:尋找真實人生文學的記者》(Olho da Rua— uma repórter em busca da literatura da vida
real)裡。這些文章展現了我在新聞報導中絕不妥協的行事風格。在〈雨林裡的接生婆〉中,我試著放下自己的定見(過去的經驗積累而成的),在整個報導過程裡頭,我最主要的工具便是傾聽。
做為記者(以及身為一個人),我一直認為,知道如何聆聽,比知道如何提問更重要。如果可能,我甚至不希望自己開口去提出第一個問題。我總覺得所謂的第一個問題,其實與我自身比較有干係,遠勝於我想了解的對象。此外,第一個問題還會向受訪者洩漏了採訪者的期望。第一個問題相當於一種控制形式,而身為稱職的傾聽者,我必須放棄控制,所以我只會說:「告訴我……」。你永遠不知道人們訴說自己的故事會從哪裡切入。
一旦我們臣服於故事,任它由外而內澈底顛覆我們,記者這份工作帶來的就只有喜悅。如果我走一遭阿馬帕州(Amapá)或聖保羅地區,回來卻毫無改變的話,我就會放棄報導了。身為記者,意味著每篇報導都會帶來一次重生,以及自我的重新創造。當然,最好是透過自然分娩。
如果你是個像是聆聽音樂般的閱讀者,你將發現《剩餘靈魂的收藏者》收錄的每篇報導自有其詞彙、節奏與布局;要是並非如此,將對我產生重大的影響。即使我穿越整個巴西,穿梭於每個巴西人內在的巴西世界,我依然沒有真正離開自己的家。倘若我無法洞悉他人的語言,沒有聽懂不同地區蘊含的每一種人生所傳遞的訊息節奏,那麼,我寫的不過就是我自己,以及我那受限的語言。即使擁有其他人名或所謂的其他故事,我也只是個寫著新故事、觀點卻單一的寫作者而已。
我的挑戰在於必須維持局外人的立場,這麼做是為了保有好奇的雙眼,倘若我想看透奪目的表象,這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必須注意,絕不能讓觀光客的觀點汙染了自己,因為觀光客總是透過自己的偏見或想像來看待現實,他們只看自己想見的,只相信自己認定的真相——若是如此,你根本不需要離開家門。
記者相當於貼近隱私的外來者。每當進入他人的世界,我都必須搞清楚一件關鍵的事:別人向我引介自己的世界時,她會呈現什麼給我看,還有,她不讓我看見的又是什麼?她會引我踏上什麼樣的路?她會用什麼樣的詞彙來為自己的領土命名,包括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為什麼她選擇這些詞彙?
經過三十年的報導生涯,死者始終縈繞在我心中,他們的生命不會因為我的譴責而有所改變。我一直在尋找詞彙,試圖用最合適的文字描述他們的故事,好讓世人聽見;我尋思著究竟要怎麼做,才能讓這些已經入土的人成為回憶,不致連他們的聲音都被埋葬了。而我花了些時間才明白,欠缺的不是文字或聲音,而是耳朵。
我不太了解自己。每當我覺得稍微了解一點了,就又會揭露更多自己的另一面,然後逃離自己。或許,我唯一確定的是自己是個記者。靈魂進駐一具又一具的身體,將不同體驗轉化成文字,是構成我本質的決定性因素,而這已融入骨子裡了。我對無限荒謬的現實擁有不成比例的愛,而這份愛影響了我所有的世界觀。瓜拉尼蓋約瓦族(Guarani-Kaiowá)好幾個世紀以來遭到各式各樣的謀殺,儘管如此,他們依然抵抗不屈。我跟他們學到了另一個字:ñe’ẽ,這個字指的是「文字」與「靈魂」同時存在。正是在這他者的語言中(既非我的,亦非你的),我找到了足以定義自己這番追尋的詞彙。在兩個世界之間的漩渦裡,我想要成為能夠產生作用的文字。
在這本書中,一如在人生裡,我能獻上的唯有自己。我希望這樣就足夠了。
阿爾塔米拉,巴西,二○一八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