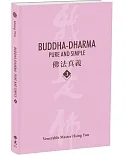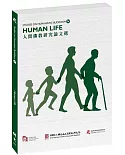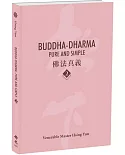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霧裡看花,能知大略。
佛教典故浩如煙海,本書僅僅選擇了其中習見、重要、內容豐富的一小部分。
佛教是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一,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影響所及,已經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佛教的用語,透過經典的不斷敷揚,更成為人們隨時脫口而出的典故;這不但表現在對事象的認識上,也是多數人人生觀的顯發。為免學人訛用,本書特拈出常用的典故,逐一釐清緣起,且以經典為據的詳加釋義。本書在分析佛教典故時,廣泛涉及了佛教的哲理、宗風、菩薩、人物、傳說、儀軌、器物、節日等有關知識。為了便於讀者進一步研究,更引用了佛經和許多文獻資料。
序
序
西元前六世紀左右,佛教在印度迦毗羅衛國誕生。經過兩、三百年,到了阿育王時代,開始向外發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傳入我國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包括中觀學派、瑜伽行派和密教等。通過魏晉六朝的譯經、弘傳和辯論,佛教迅速地深入了社會生活各領域,確立了在我國的地位。從此,佛教與固有的儒、道文化鼎足而三,互相交融,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一。隋、唐時期,除了深入研究印度的唯識學、律學外,還建立了許多我國特有的宗派,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形成了鼎盛的局面。當時的中國儼然是國際上大乘佛教的中心。隋、唐佛學上承魏、晉、六朝,下啓宋、元、明、清、民國,歷時之久,影響之大,超過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
經過多次「結集」,佛教經、律、論三藏逐漸完成。這是一個龐大的古代文獻寶庫。僅就漢文系統的大藏而言:《開元釋教錄》收入五○四八卷,清代《龍藏》收入七一六八卷,日本《大正藏》收入九○○六卷,新編《中華大藏經》將收入一萬多卷。巴利文、藏文系統的經藏也很可觀。《大藏經》中,除了佛教教理外,還涉及其他宗教、哲學、邏輯、語言、民俗、文藝、地理、天文、曆法、心理、醫方、生物、工藝等許多領域,有待進一步研究、發掘。
佛教認為現象世界都是思想和業力造成的,無盡的因果網絡構成了宇宙萬有。一切事物都處在成、住、壞、空,生、老、病、死的無常變遷之中。佛教的根本宗旨,就是修持戒、定、慧三學,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到達涅槃寂靜的「彼岸」。佛教最注重「覺」和「行」,主張以「覺」治「迷」,因「解」起「行」。佛教是「智慧」的宗教,然而不贊成單純的思辨;它認為,最圓滿的「智慧」是通過實踐驗證而完成的。佛教誕生伊始,就提出「一切眾生平等」的口號,對古印度種姓等級制度發起有力的挑戰,得到平民的支持。尤其是大乘佛教,還主張慈悲平等,捨己為人,救度眾生。讀過幾本佛經的人,對其中深刻而獨特的思惟往往會感到驚訝。佛經對思惟與存在、時間與空間、本體與現象等重大問題,都有精湛的論述;對宇宙的洞察,對生命的探索,對概念的分析,對理性的反省,……都閃爍著智慧的火花。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否認主宰一切的「造物主」,也否認永恆不變的「靈魂」。佛教對我國思想史的影響是巨大的。最明顯的事實是,程朱理學、陸王心理學都深受華嚴宗和禪宗的影響。清末,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均出入佛經,運用其中「平等無我」等思想去衝決封建羅網。
文學本是佛教的「餘事」,即副產品;但影響之大,可能是佛教本身始料所不及的。魏晉六朝,佛教化的文學已經趨於成熟。在《弘明集》、《廣弘明集》中收集了大量僧人文士的有關詩文。他們的哲理詩、山水詩善於發揮佛教的理趣和意境。其中謝靈運才大思精,尤為可觀。唐代佛教文學更加繁榮。僧人中有王梵志、寒山、皎然、齊己等,文士中有王維、白居易、柳宗元、斐休等,均擅長詩文,各有千秋。至於道世編纂的《諸經要集》、《法苑珠林》則是現存較早而且完整旳大型類書。宋代蘇軾、黃庭堅、張商英、王日休等作品,也深受禪、淨諸宗的影響。蘇軾同柳宗元一樣,善於寫作寓言小品。明代宋濂所作有關詩文,竟有幾十萬字。
高觀如居士指出:「漢譯各經典中,以羅什所譯《金剛》、《法華》、《彌陀》、《維摩》諸經於文學上最有影響。」事實的確如此。《維摩詰經》結構巧妙,想像奇麗,人物生物,對話酣暢,富有戲劇性。《法華經》譯注之多,流通之廣,在《大藏經》中首屈一指。兩經中的譬喻典故,如天女散花、不二法門、火宅、窮子、化城等,文人一再引用,世所熟知。此外,《金剛經》淋漓痛快的論說,《隬陀經》富麗堂皇的描述,均令人歎絕。
佛教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浪漫主義的想像力。佛經中展開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時空境界。在空間上,一毛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世界;從地獄的慘苦、天堂的富麗直到淨土的精妙、佛國的莊嚴,無奇不有。在時間上,從無始以來的過去,經剎那遷流的現在,直到無量的劫後的未來,包括小劫、中劫、大劫、芥子劫、磐石劫等,甚至說一念與百千萬劫平等。在變化上,既有宏觀上的成、住、壞、空,又有微觀上的生、住、異、滅;眾生有六道輪迴,佛、菩薩有千百億化身,……這些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的描繪,給中國文學開拓了許多嶄新的意境。
其次是新的體裁。眾所周知,在佛經的長行與偈頌相間,即韻白夾雜形式影響下,產生變文這種通俗文學。變文是中國俗文學的淵源,宋元話本、明清小說皆承襲其緒,寶卷更是其嫡系。《佛本行贊》用偈頌記述釋迦牟尼佛成佛的經歷,曲折生動,成為長篇敍事詩的嚆矢。王梵志、寒山、拾得以至邵雍的詩歌,都模仿了偈頌的的風格。《金光明經》等書中為法捨身的佛本生故事,感情激越,氣氛悲壯,對傳奇不無影響。至於早期的白話文正是記錄禪宗祖師言行的語錄和燈錄,如唐代的《神會和尚語錄》、五代的《祖堂集》。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就是效法禪宗語錄的。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一般不從經文中尋找正面答案,而往往在日常起居中即境點化,隨機開示;故而桃紅柳綠、風聲鶴唳乃至吃飯屙屎,都成了活潑潑的「妙用」。禪宗的公案能殺能活,隨說隨掃,機鋒畢露,妙趣橫生。禪師的開示或用當時的俗語,或用現成的詩句,或隨口而拈出,……本書中不少典故便是源於禪宗的。
再次是大量的譬喻。規模龐大的佛教術語及新辭彙隨著佛經譯傳而湧現,進入並豐富了漢語系統。在佛經中,譬喻運用廣泛,作用很大。佛理玄微,一般人難以理解,所以要「假近以喻遠,借彼而況此」,使人樂於聽聞,易於接受。《法華經˙譬喻品》謂佛陀「以無量喻為說法」。據說經中有「大喻八百,小喻三千」。其方式包括順喻、逆喻、現喻、非喻、先喻、後喻、先後喻、遍喻等(見《涅槃經》卷二十九)。為了說明「緣起性空」這一重要教義,就用了十個譬喻。佛陀的施教方式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其中所謂漸教、權教、半教、方便教等,最注重運用譬喻。《百喻經》說:「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智者取正義,戲笑便應棄。」佛家常說,譬喻如「指」,實義如「月」,要因「指」而觀「月」,由譬喻而見實義。正如用船渡入,到了「彼岸」,船就不需要了。對於經中的譬喻也應該作如是觀。具有文學性的佛教典故主要來源於經中的譬喻。印度民族富於相像力,創造了無數的譬喻、寓言,而佛經則是集大成者。佛教譬喻影響很大。如「盲人摸象」,中外盛傳:「水中撈月」,婦孺皆知。法國沙畹鈎稽的《佛經中五百故事》,都很著名。
佛教對我國文化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佛經的傳入掀起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翻譯的高潮,出現安世高、支謙、鳩摩羅什、玄奘等著名譯師,形成了質樸的的「古譯」、綺麗的「舊譯」和謹嚴的「新譯」等各種風格。當時,官辦了一些大型譯場,集中了一批學者專家。一部經的譯成,往往要經過口譯、筆受、校對、潤色等程序。歷代譯師總結出「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八備」、「六例」等寶貴經驗。佛教還帶來了古印度的聲明學,這對我國音韻學的發展很有影響。反切、字母、四聲應受了悉曇字母「以聲合韻」的啟發。創造三十六字母的守溫就是唐末僧人。經中「文、名、句三身」及「六離合釋」等,也是對語言現象的一種歸納。至於玄應等三部《一切經音義》、慧苑《新譯華嚴經音義》、法雲的《翻譯名義集》等,都是享有盛譽的語言學專著。
我國古建築中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五台山南禪寺、嵩山嵩岳寺磚塔、應縣木塔、泉州開元寺石塔,……都是建築藝術史上的瑰寶。敦煌、龍門、響堂山、麥積山等石窟及其石刻、壁畫,是舉世聞名的藝術寶庫。這些藝術珍品融合了印度、犍陀羅和我國各個民族的風格。壁畫多取材於本生(「捨身飼虎」等)和經變(「維摩變」、「淨土變」等),洋洋大觀。版畫源於唐代佛經中的佛像。顧愷之、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都是善於繪製佛經故事和人物的著名畫家。王維開創的南宗畫派側重寫意,以空靈見長,顯然受到了「六祖禪」的影響。宋、元時,還盛行觀音畫、羅漢畫和水陸畫。另外,唐代佛曲和舞蹈,多從盛行佛教的西域諸國傳入,如唐代樂府中有《普光佛曲》、《釋迦文佛曲》和《妙華佛曲》等;唐代舞蹈中有天竺舞、龜茲舞等。
雕板印刷的起源與佛經的流通大有關係。始於隋末唐初的佛像圖是最早的板刻。由於密宗的風行,刻印經咒蔚然成風。唐咸通九年的敦煌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雕板印刷書籍,技術嫻熟,書品精美。隨著佛經的廣泛流通,刻印、裝幀等技術日趨成熟和多樣化。佛教帶來的副產品還有天文、醫方等科學知識。隋、唐史書就記載了十餘種印度譯過來的醫書、方書。天文、醫方知識的傳入和密教的關係最為密切。創造《大衍曆》、測定子午線的一行就是一位著名的唐代密教僧人。至今西藏的佛教經典中,仍然保存著大量天文、曆數、醫方等文獻。
佛教典故浩如煙海,本書僅選擇了其中習見、重要、內容豐富的一小部份。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霧裡看花,能知大略。本書試圖揭示佛教典故的源頭,即典故在佛教中產生、發展和各種解釋的情況。同時,還儘可能指出它們在語詞中是如何運用的。本書在分析佛教典故時,廣泛涉及了佛教的哲理、宗風、佛、菩薩、人物、傳說、儀軌、器物、節日等有關知識。為了引起讀者進一步研究的興趣,便於文史工作者的利用,本書較多地引用了佛經和其他文獻資料。由於作者所知有限,成書倉促,書中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予以指正。
西元前六世紀左右,佛教在印度迦毗羅衛國誕生。經過兩、三百年,到了阿育王時代,開始向外發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傳入我國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包括中觀學派、瑜伽行派和密教等。通過魏晉六朝的譯經、弘傳和辯論,佛教迅速地深入了社會生活各領域,確立了在我國的地位。從此,佛教與固有的儒、道文化鼎足而三,互相交融,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一。隋、唐時期,除了深入研究印度的唯識學、律學外,還建立了許多我國特有的宗派,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形成了鼎盛的局面。當時的中國儼然是國際上大乘佛教的中心。隋、唐佛學上承魏、晉、六朝,下啓宋、元、明、清、民國,歷時之久,影響之大,超過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
經過多次「結集」,佛教經、律、論三藏逐漸完成。這是一個龐大的古代文獻寶庫。僅就漢文系統的大藏而言:《開元釋教錄》收入五○四八卷,清代《龍藏》收入七一六八卷,日本《大正藏》收入九○○六卷,新編《中華大藏經》將收入一萬多卷。巴利文、藏文系統的經藏也很可觀。《大藏經》中,除了佛教教理外,還涉及其他宗教、哲學、邏輯、語言、民俗、文藝、地理、天文、曆法、心理、醫方、生物、工藝等許多領域,有待進一步研究、發掘。
佛教認為現象世界都是思想和業力造成的,無盡的因果網絡構成了宇宙萬有。一切事物都處在成、住、壞、空,生、老、病、死的無常變遷之中。佛教的根本宗旨,就是修持戒、定、慧三學,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到達涅槃寂靜的「彼岸」。佛教最注重「覺」和「行」,主張以「覺」治「迷」,因「解」起「行」。佛教是「智慧」的宗教,然而不贊成單純的思辨;它認為,最圓滿的「智慧」是通過實踐驗證而完成的。佛教誕生伊始,就提出「一切眾生平等」的口號,對古印度種姓等級制度發起有力的挑戰,得到平民的支持。尤其是大乘佛教,還主張慈悲平等,捨己為人,救度眾生。讀過幾本佛經的人,對其中深刻而獨特的思惟往往會感到驚訝。佛經對思惟與存在、時間與空間、本體與現象等重大問題,都有精湛的論述;對宇宙的洞察,對生命的探索,對概念的分析,對理性的反省,……都閃爍著智慧的火花。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否認主宰一切的「造物主」,也否認永恆不變的「靈魂」。佛教對我國思想史的影響是巨大的。最明顯的事實是,程朱理學、陸王心理學都深受華嚴宗和禪宗的影響。清末,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均出入佛經,運用其中「平等無我」等思想去衝決封建羅網。
文學本是佛教的「餘事」,即副產品;但影響之大,可能是佛教本身始料所不及的。魏晉六朝,佛教化的文學已經趨於成熟。在《弘明集》、《廣弘明集》中收集了大量僧人文士的有關詩文。他們的哲理詩、山水詩善於發揮佛教的理趣和意境。其中謝靈運才大思精,尤為可觀。唐代佛教文學更加繁榮。僧人中有王梵志、寒山、皎然、齊己等,文士中有王維、白居易、柳宗元、斐休等,均擅長詩文,各有千秋。至於道世編纂的《諸經要集》、《法苑珠林》則是現存較早而且完整旳大型類書。宋代蘇軾、黃庭堅、張商英、王日休等作品,也深受禪、淨諸宗的影響。蘇軾同柳宗元一樣,善於寫作寓言小品。明代宋濂所作有關詩文,竟有幾十萬字。
高觀如居士指出:「漢譯各經典中,以羅什所譯《金剛》、《法華》、《彌陀》、《維摩》諸經於文學上最有影響。」事實的確如此。《維摩詰經》結構巧妙,想像奇麗,人物生物,對話酣暢,富有戲劇性。《法華經》譯注之多,流通之廣,在《大藏經》中首屈一指。兩經中的譬喻典故,如天女散花、不二法門、火宅、窮子、化城等,文人一再引用,世所熟知。此外,《金剛經》淋漓痛快的論說,《隬陀經》富麗堂皇的描述,均令人歎絕。
佛教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浪漫主義的想像力。佛經中展開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時空境界。在空間上,一毛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世界;從地獄的慘苦、天堂的富麗直到淨土的精妙、佛國的莊嚴,無奇不有。在時間上,從無始以來的過去,經剎那遷流的現在,直到無量的劫後的未來,包括小劫、中劫、大劫、芥子劫、磐石劫等,甚至說一念與百千萬劫平等。在變化上,既有宏觀上的成、住、壞、空,又有微觀上的生、住、異、滅;眾生有六道輪迴,佛、菩薩有千百億化身,……這些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的描繪,給中國文學開拓了許多嶄新的意境。
其次是新的體裁。眾所周知,在佛經的長行與偈頌相間,即韻白夾雜形式影響下,產生變文這種通俗文學。變文是中國俗文學的淵源,宋元話本、明清小說皆承襲其緒,寶卷更是其嫡系。《佛本行贊》用偈頌記述釋迦牟尼佛成佛的經歷,曲折生動,成為長篇敍事詩的嚆矢。王梵志、寒山、拾得以至邵雍的詩歌,都模仿了偈頌的的風格。《金光明經》等書中為法捨身的佛本生故事,感情激越,氣氛悲壯,對傳奇不無影響。至於早期的白話文正是記錄禪宗祖師言行的語錄和燈錄,如唐代的《神會和尚語錄》、五代的《祖堂集》。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就是效法禪宗語錄的。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一般不從經文中尋找正面答案,而往往在日常起居中即境點化,隨機開示;故而桃紅柳綠、風聲鶴唳乃至吃飯屙屎,都成了活潑潑的「妙用」。禪宗的公案能殺能活,隨說隨掃,機鋒畢露,妙趣橫生。禪師的開示或用當時的俗語,或用現成的詩句,或隨口而拈出,……本書中不少典故便是源於禪宗的。
再次是大量的譬喻。規模龐大的佛教術語及新辭彙隨著佛經譯傳而湧現,進入並豐富了漢語系統。在佛經中,譬喻運用廣泛,作用很大。佛理玄微,一般人難以理解,所以要「假近以喻遠,借彼而況此」,使人樂於聽聞,易於接受。《法華經˙譬喻品》謂佛陀「以無量喻為說法」。據說經中有「大喻八百,小喻三千」。其方式包括順喻、逆喻、現喻、非喻、先喻、後喻、先後喻、遍喻等(見《涅槃經》卷二十九)。為了說明「緣起性空」這一重要教義,就用了十個譬喻。佛陀的施教方式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其中所謂漸教、權教、半教、方便教等,最注重運用譬喻。《百喻經》說:「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智者取正義,戲笑便應棄。」佛家常說,譬喻如「指」,實義如「月」,要因「指」而觀「月」,由譬喻而見實義。正如用船渡入,到了「彼岸」,船就不需要了。對於經中的譬喻也應該作如是觀。具有文學性的佛教典故主要來源於經中的譬喻。印度民族富於相像力,創造了無數的譬喻、寓言,而佛經則是集大成者。佛教譬喻影響很大。如「盲人摸象」,中外盛傳:「水中撈月」,婦孺皆知。法國沙畹鈎稽的《佛經中五百故事》,都很著名。
佛教對我國文化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佛經的傳入掀起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翻譯的高潮,出現安世高、支謙、鳩摩羅什、玄奘等著名譯師,形成了質樸的的「古譯」、綺麗的「舊譯」和謹嚴的「新譯」等各種風格。當時,官辦了一些大型譯場,集中了一批學者專家。一部經的譯成,往往要經過口譯、筆受、校對、潤色等程序。歷代譯師總結出「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八備」、「六例」等寶貴經驗。佛教還帶來了古印度的聲明學,這對我國音韻學的發展很有影響。反切、字母、四聲應受了悉曇字母「以聲合韻」的啟發。創造三十六字母的守溫就是唐末僧人。經中「文、名、句三身」及「六離合釋」等,也是對語言現象的一種歸納。至於玄應等三部《一切經音義》、慧苑《新譯華嚴經音義》、法雲的《翻譯名義集》等,都是享有盛譽的語言學專著。
我國古建築中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五台山南禪寺、嵩山嵩岳寺磚塔、應縣木塔、泉州開元寺石塔,……都是建築藝術史上的瑰寶。敦煌、龍門、響堂山、麥積山等石窟及其石刻、壁畫,是舉世聞名的藝術寶庫。這些藝術珍品融合了印度、犍陀羅和我國各個民族的風格。壁畫多取材於本生(「捨身飼虎」等)和經變(「維摩變」、「淨土變」等),洋洋大觀。版畫源於唐代佛經中的佛像。顧愷之、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都是善於繪製佛經故事和人物的著名畫家。王維開創的南宗畫派側重寫意,以空靈見長,顯然受到了「六祖禪」的影響。宋、元時,還盛行觀音畫、羅漢畫和水陸畫。另外,唐代佛曲和舞蹈,多從盛行佛教的西域諸國傳入,如唐代樂府中有《普光佛曲》、《釋迦文佛曲》和《妙華佛曲》等;唐代舞蹈中有天竺舞、龜茲舞等。
雕板印刷的起源與佛經的流通大有關係。始於隋末唐初的佛像圖是最早的板刻。由於密宗的風行,刻印經咒蔚然成風。唐咸通九年的敦煌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雕板印刷書籍,技術嫻熟,書品精美。隨著佛經的廣泛流通,刻印、裝幀等技術日趨成熟和多樣化。佛教帶來的副產品還有天文、醫方等科學知識。隋、唐史書就記載了十餘種印度譯過來的醫書、方書。天文、醫方知識的傳入和密教的關係最為密切。創造《大衍曆》、測定子午線的一行就是一位著名的唐代密教僧人。至今西藏的佛教經典中,仍然保存著大量天文、曆數、醫方等文獻。
佛教典故浩如煙海,本書僅選擇了其中習見、重要、內容豐富的一小部份。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霧裡看花,能知大略。本書試圖揭示佛教典故的源頭,即典故在佛教中產生、發展和各種解釋的情況。同時,還儘可能指出它們在語詞中是如何運用的。本書在分析佛教典故時,廣泛涉及了佛教的哲理、宗風、佛、菩薩、人物、傳說、儀軌、器物、節日等有關知識。為了引起讀者進一步研究的興趣,便於文史工作者的利用,本書較多地引用了佛經和其他文獻資料。由於作者所知有限,成書倉促,書中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予以指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滬上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9折$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