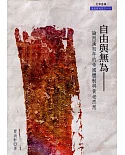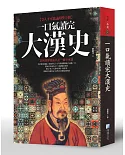導讀
永恆的漢武帝製造工程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楊生民教授的《漢武帝傳》,二○○一年於中國大陸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繁體版第一版,從學術思想、社會、財政、政治體制、對外關係、宗教祭祀、君臣關係、後宮等角度切入,全面探討漢武帝自少年而盛年、從中年到老年波瀾起伏的一生,至今仍為中文學界裡較新的漢武帝傳記。此次再版,值得推薦。
然而這二十年來,秦漢史學界對漢武帝的研究並非全無進展。史學家對漢武帝究竟有何新認識,不能不為閱讀本書的讀者關心。限於篇幅,本文只介紹北京大學歷史系辛德勇教授於二○一五年出版的《製造漢武帝》一書。
歷史書寫的研究取徑,近年在海峽兩岸史學界大行其道。其緣由固然有著西方後現代學術氛圍的浸染,但乾嘉考據、史料學派等深厚史學傳統的基礎,亦不容小覷。無論如何,充分關注史料的形成過程、對史料進行層層拷問,已成為當代史學工作者的特色。帝王傳記的寫作,亦難自外於此風潮。帝王歷史形象的書寫蔚為主流,犖犖大者,先有英國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製作路易十四》,後有中國史家辛德勇的《製造漢武帝》。
二○一五年辛德勇出版《製造漢武帝》一書,不僅秦漢史圈內人盡皆知,更引發海內外中國史學者高度關注。原因不僅是漢武帝形象的歷史書寫這一重要課題,還因為此書挑戰了近三十年來大陸史學界對漢武帝晚年政策方向的主流觀點。一切要從一九八四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田餘慶教授發表〈論輪臺詔〉一文說起。
漢武帝在位期間完成了東征朝鮮、南平南越、北伐匈奴、西服西域等一系列對外擴張的驚人武功,打下了當代中國的大半疆域。如此豐功偉業的代價卻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影響不可謂不鉅大。田餘慶根據漢武帝晚年頒布的輪臺詔書,指出武帝晚年追悔過去四十多年的對外擴張政策,國策方向從擴張轉變為守文,為身後的昭宣之治奠定基礎。楊生民《漢武帝傳》完全採納此說,至今仍為人普遍信從。
然而辛德勇從史源學的角度切入,指出田餘慶的分析來自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但司馬光是北宋人,撰寫千年前的漢代史事自然有所憑依,《資治通鑑》的依據分別來自南朝王儉的《漢武故事》與《漢書.西域傳》的輪臺詔書。《漢武故事》成書既晚,又是小說家言,不可信據。《漢書.西域傳》雖為班固所作,但考慮到班固撰述《漢書.武帝紀》時未載輪臺詔書,辛德勇認為輪臺詔書記載漢武帝晚年罪己悔過的範圍,應僅限於李廣利伐匈奴一事。今人論漢武帝晚年政治,應以《漢書.武帝紀》為準,其內容根本看不出漢武帝晚年政治的重大轉向。因此司馬光《資治通鑑》敘述漢武帝晚年形象時,偏離了一般的史料運用原則,顯然有獨特用心。在辛德勇看來,司馬光是為了現實政治目的,輕信不可靠的史料,藉此塑造漢武帝晚年追悔的明君形象。
上述辛德勇對《漢書.武帝紀》、《漢書.西域傳》、《漢武故事》與《資治通鑑》諸種歷史書寫的評析,已發展成對班固、王儉、司馬光等作者心思的推求,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可以言說、不可論證的「心知其意」範疇,在史料寡少的情況下,尤其難以排除其他解釋。例如:《漢書.武帝紀》與〈西域傳〉有無輪臺詔書的原因,固然可能如辛德勇所理解;但也可能是單純的「互文見意」,輪臺詔書不見於〈武帝紀〉,不一定等於它不具有整體國策的意義;再考慮到班固在〈武帝紀〉論贊裡委婉陳詞,卻在〈昭帝紀〉論贊直率批評武帝「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班固不將武帝追悔的輪臺詔書寫在〈武帝紀〉,而寫在〈西域傳〉裡,亦可理解成為尊者諱的史筆,田餘慶正主此說。其高足李開元先生更認為〈武帝紀〉與〈西域傳〉的差異,反映班固的《漢書》「無力也不能將這一段歷史清理出合理的脈絡來。」
《漢書》的歷史書寫既然有這麼多可能的解釋存在,探討「製造漢武帝」的同時,就不能不將「製造班固」一併納入視野,但辛德勇卻沒有在《製造漢武帝》一書裡,著重探討班固《漢書》的歷史書寫問題。因為對辛德勇來說,「製造漢武帝」並非他著書的終極目標,他的終極目標是想證明研究秦漢史,《通鑑》的記載絕不可以取代《史記》、《漢書》,《通鑑》絕不可被視為秦漢史的史料。既然辛德勇想證明《漢書》是比《通鑑》更可信的史料,《製造漢武帝》一書便不得不強調司馬光的歷史書寫,進而忽略班固的歷史書寫,也就難以將《漢書》與《通鑑》並觀,用同樣嚴格的史料批判精神去檢討。這就是辛德勇不曾探討「製造班固」的主因。
《漢書》是研究西漢史的基礎史料,這確實是顛撲不破的史料學常識。但《漢書》的歷史書寫既然有這麼多可能的解釋存在,西漢史研究便非「常識」可以完全規範。面對變化萬千的歷史書寫,史家不能被「常識」拘泥,必須努力「別出心裁」地對各種史料加以取捨,方可能不人云亦云,提出自己的新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歷史書寫以歷史事實的存在為基礎,千變萬化的歷史事實導致歷史書寫難有一定的準則。異人異地異時,歷史書寫便可能有所改變。要想了解「製造漢武帝」的歷史書寫,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探索更根本的「製造漢武帝」的歷史事實。
涉及「製造漢武帝」的歷史事實又可析分為「漢武帝的政策」與「漢武帝之心」。班固、司馬光等歷史書寫者的心思不易把握,歷史事實的主角漢武帝的心思也同樣難以掌握,甚至更難,因為他的心思隱藏於歷史書寫者的心思之後。在午夜夢迴之際,漢武帝究竟是追悔於他的全盤政策?還是只對李廣利伐匈奴一事感到後悔?見仁見智。考慮到人心的複雜與善變,答案也可能是以上皆是——隨著不同時候的漢武帝心思而定。
漢武帝之心難覓、難證,歷史事實的研究理應致力於探討相對客觀、可供驗證的漢武帝政策。然而在「製造漢武帝」的論爭中,就連漢武帝政策究竟為何的歷史事實都難有定論,這是因為史家往往不願意停留於表面的歷史事實,更願意去追究深層的歷史事實。田餘慶將輪臺詔書、巫蠱之禍、鹽鐵會議等政治事件全部綁在一起,企圖從政策的角度論證漢武帝晚年及過世之後,政壇上存在兩條不同的政治路線,政治路線的背後則是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換言之,政策的出台與政治事件的出現,並非純憑政治人物的個人意志決定,更須考慮背後政治結構的影響。然而田餘慶真正關注的政治集團與政治結構等深層歷史,實非政治事件與政治路線等表層歷史之有無可以直接證明。換言之,不管漢武帝晚年及過世之後政治上是否發生重大轉向,當時政壇都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集團,而政治結構也必然發揮其自身的作用。受限於史料,深層歷史在此幾乎不可能實證。辛德勇從實證的角度出發,致力於政治重大轉向之辯,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田說,但未能在理論框架上提供另一套新的理解方式,終究著於皮相,遂導致田餘慶的政治史觀並未被真正駁倒。從深層歷史來說,漢武帝政策究竟為何的歷史事實仍難以定論,
上文盡力呈現班固、司馬光、田餘慶、辛德勇等歷史學者前仆後繼地「製造漢武帝」,其間牽涉的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情況高度複雜,因而創造了波瀾壯闊、延續兩千年之久的史學論戰。在這裡面,並無簡單的歷史圖象可以提供。
歷史研究雖須以史料學常識為基礎,卻又不能被史料學常識所拘泥。史料學常識可以從歷史研究之中提煉,卻不應是歷史研究的目的。西方史家曾經指出:
確定一種記載優於另外一種的危險在於,它是為了把「歷史」澆鑄成一個單一的真實故事。這也是尋求一種「客觀的」或「科學的」歷史所遵循的邏輯──就其意欲實現的目標而言,它們都是不可能的。
本此立場,我希望「製造漢武帝」的議題可以繼續討論下去,直至永遠。上述諸家之說看似紛紛擾擾、各說各話,實則引領讀者進一步思考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的關係,思考歷史的真相應如何探求,深具學術意義。如果《漢書》、《漢武故事》、《資治通鑑》的史料價值被確定下來,如果班固、司馬光、田餘慶、辛德勇的是非對錯已成定論。不管是漢武帝的歷史,還是現代史家的論著,便只剩下記誦的價值,失去重新理解、重新構建的可能性,歷史學的意義也就蕩然無存。行文至此,本文似乎成為破而不立的騎牆之論。但只要能欣賞各種推陳出新的精彩史論,浸淫於知識的饗宴之中,「心無定見」又有什麼關係呢?
綜上所述,辛德勇《製造漢武帝》涉及的重要概念關係可製表如下:
此表格雖然只涉及漢武帝晚年是否悔過一事,但讀者閱讀《漢武帝傳》本書時,自可將此表格套用在其他漢武帝的史事,甚至應用於其他歷史書籍,進一步思考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歷史人物的心思與行動等錯綜複雜的關係。更有甚者,讀者若能跳脫「歷史」二字,回到現實人生思考事實與書寫、人們的心思與行動,才是真正讀懂史書、知古鑑今。舉例為證,上述「製造漢武帝」、「製造班固」、「製造司馬光」等層層遞進的歷史書寫鏈條,尚有最後一環需要扣上,那就是「製造辛德勇」。
上文已指出「製造漢武帝」並非辛德勇的著書目的,他的著書目的是想證明《漢書》是比《通鑑》更可信的秦漢史史料。然而《漢書》比《通鑑》更可信,是一個稍涉秦漢史便知的常識。辛德勇為何會想用一本書去證明一個看似無懈可擊的史料學常識?這又得回到田餘慶與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關係。
原來北京大學歷史系至今仍存在一個源遠流長的《資治通鑑》讀書會,據說上承民初陳寅恪帶學生讀《通鑑》的傳統。直到今天,北大歷史系教授仍輪流主持《通鑑》讀書會,引領北大歷史系的中古史研究生進入學術的殿堂。《資治通鑑》的史學特色無疑是通貫,打通秦漢晉唐的歷史書寫,適足打破當代史學囿於斷代的缺陷。故《通鑑》讀書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北大中古史發展出「立足魏晉,放眼秦漢」的研究取徑。
「立足魏晉,放眼秦漢」的研究者確實與一般秦漢史學者有別,為秦漢史研究帶來了新鮮的洞見與活力。但回溯前朝的「後見之明」未必全無弊端,受《通鑑》影響的秦漢史研究,也難免被司馬光的歷史書寫遮蔽,反而忽視了更原始的史料《史記》與《漢書》。在北大歷史系授課的辛德勇,面對浸淫於《通鑑》讀書會傳統的中古史研究生,自然深感有必要強調上述的史料學常識——《漢書》比《通鑑》更可信。
分析辛德勇自身的歷史書寫,不僅有助於讀者理解《製造漢武帝》一書的寫作用心,還可提醒讀者不只是古代史家的歷史書寫需要留意,現代史家的歷史書寫同樣值得關心。如果不具備分析歷史書寫的能力,那閱讀再多史著,也只會被史家牽著鼻子走,「人人都是歷史學家」不啻是一句空話。
回到楊生民教授《漢武帝傳》本書,歷史研究並不容易,此書並非漢武帝的故事集,而是漢武帝的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之綜合體,無論是學術思想、社會、財政、政治體制、對外關係、宗教祭祀、君臣關係、後宮等領域,還是漢武帝自少年而盛年、從中年到老年波瀾起伏的一生,均值得讀者從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的關係切入,細細品味。
游逸飛/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