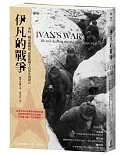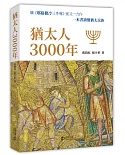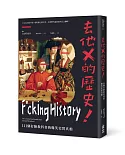序 Prologue
上次到英國已經像是上輩子的事了,那時我才二十歲,年輕得很。
英國曾經有一段短暫而炫麗的時光,產出了全世界最受矚目的一切。披頭四(The Beatles)、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瑪麗.奎恩特(Mary Quant)和迷你裙、崔姬(Twiggy)與賈斯汀.維倫紐夫(Justin de Villeneuve)、理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與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
的愛情生活、瑪格麗特公主(Pincess Magaret) 的愛情生活、滾石樂團(The Rolling Stones)、奇想樂團(The Kinks)、無領西裝外套、電視節目《復仇者》(The Avengers)與《密諜》(The Prisoner)、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連.戴登(Len Deighton)、瑪麗安娜.斯福爾(Marianne
Faithfull)和達斯蒂.斯普林菲爾德(Dusty Springfield)的間諜小說。大衛.海明斯(David Hemmings)與泰倫斯.史坦普(Terence Stamp)主演的愛荷華州不會上映的奇怪電影,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導演的不可能在全美任何地方演出的戲劇、《每週綜述》(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普羅富莫(Profumo)的醜聞,基本上,根本就是全部的全部,一切的一切。
當時英國產品完全擄獲《紐約客》(New Yorker)與《君子雜誌》(Esquire)編輯的心—吉利蓓(Gilbey)和坦奎利(Tanqueray)的琴酒、哈里斯(Harris)毛料、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OAC airliners)、雅格獅丹(Aquascutum)西裝、維耶勒法蘭絨(Viyella)裙子、傳統手工絨帽、雅倫潘恩(Alan
Paine)毛衣、達克斯(Daks)長褲、名爵(MG)與奧斯汀.希雷(Austin
Healey)跑車以及種類多達數百種的蘇格蘭威士忌。當時「英國製造」即是優雅與品味的勳章,更是所有品味名家的夢幻逸品。不過我必須說,即便在當時,英國製造也有凸鎚的時候,好比那時相當熱門的「酒吧」(Pub)古龍水,我不確定此款香水的命名有何深意,我只知道身為一個在英國酒吧喝了四十年啤酒的傢伙,我絕對不會想把酒吧味抹在臉上。
可能當時全世界都在關注英國,因此我誤以為自己也對英國略知一二,沒想到一到倫敦我就被打臉了。我連說英文都打結。一開始,我分不清楚領子(collar)和顏色(colour)、卡其色(khaki)與車鑰匙(car key)、信件(letters)與生菜(lettuce)、床(bed)與裸露(bared),以及業力(karma)與平靜(calmer),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到牛津一間不分性別的理髮院剪頭髮,體型碩大表情陰森的老闆娘引領我到理髮椅前,並告知我:「等等獸醫(vet)會來幫你看看。」
我嚇了一跳,「妳是說專門處理狗狗貓貓的獸醫?」我用受驚的語氣問。
「不是,她的名字是伊維特(Yvette)。」她邊說邊用眼神窺探我,打從心裡認為和我這愚蠢生物打交道滿耗體力的。
我在酒吧問服務生店裡有什麼三明治?
「火腿與起士。」一位男士回答道。
「好,來一份。」我說。
「什麼來一份?」他回我。
「請給我一份火腿與起士。」我很狐疑地回答。
「不是,是火腿或起士。」他向我解釋。
「所以不是兩種都加?」
「不是。」
「哇,」我很驚訝地回應,然後把身子靠近他並用自信低沉的語氣問:「為什麼?味道太重嗎?」
他瞪著我。
「好吧,我要一份起士三明治。」我懊惱地說。
當三明治端上桌時,起士被削得碎碎的,我從來沒看過有人如此用力地處理乳製品,三明治旁還有幾條我以為是從污水池打撈上來的不明物體,別稱布萊斯頓(Branston)酸黃瓜。
我小心翼翼啃食面前食物,原來味道還不錯。我慢慢發現,英國實在是個令人感到無比怪異卻又顯露耀眼光芒的國家。這就是我對英國的第一印象,記憶猶新。
我對英國的印象以鐘型曲線發展,一開始我從最左邊的「一無所知」出發,一直往上攀爬至「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境界。當我抵達英國知識巔峰時,我以為自己會一直滯留在舒適圈內,沒想到一轉眼,我就快速地往「無知」的一方墜落崩塌,等我清醒過來時,我發現英國又以極其陌生的面貌矗立在眼前。轉眼間,新生代人才輩出,我不知道的名人與新秀滿地都是,我只能仰賴其他來自新世界的人類向我介紹那些奇怪的拼音組合,像是BFF、TMI
和TOWIE。
我對新世界根本沒轍。前幾天我才讓抄錶員吃了閉門羹,他的要求實在讓我無法招架。他是抄錶員啊,那根本是只存留在遙遠的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首相時期的產物吧。我熱烈地迎接他,甚至搬來梯子好讓他能仔細研究我的水電錶。當他離開後,不到一分鐘又立刻折回,很快地,他讓我備感困擾。
「不好意思,我想再看看『男廁』內的水電錶。」他跟我說。
「啥?」
「嗯,在我們的紀錄裡男廁還有另一個水電錶。」
「呃,這是我家啊,我們根本沒有男廁這種東西。」
「但紀錄顯示這裡是學校。」
「呃,這裡不是學校啊,這是住宅,你剛不是進來過了嗎?你有看到年輕人在上課嗎?」
他很用力地思考了一分鐘。
「你介意我再進去看看嗎?」
「啥?為什麼啊?」
「一下下就好,不到五分鐘。」
「你覺得這裡藏了一間我們從來沒發現的男廁嗎?」
「天下無奇不有啊。」他好像滿正面的。
「我真的沒辦法讓你進來,這真的很怪。」我拋下這句話,轉身關上門。我聽見門外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不好意思,我還有事情要忙。」我隔著木門大聲回應。我沒騙人,我真的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忙,這和本書接下來的內容有極大的關係。
我正準備前往伊斯特利(Eastleigh)參加英國公民考試。
這件事真是徹頭徹尾地諷刺。當我開始對當代英國生活熟稔時,官方卻召喚我,要我提出自己對英國生活確實有所認識的證據。
以本人淺見,你只有兩種方法能夠成為英國公民。第一種方法很詭異,但卻是相較之下較為可行的方法,那就是找到一個英國的子宮並躲在裡面九個月。第二種方法則是填寫一堆表格並在眾人面前大聲宣誓。然而,自二○○五年開始,選擇第二種路徑的人還需證明自己的英語能力,並參與英國知識測驗。
因為英文是本人的第一母語,所以得以免除語言鑑定的麻煩,但是沒有人躲得過嚴苛的知識測驗。不管你多有自信通曉英國的一切,但是你絕對不可能能掌握詭譎的「英國生活知識測驗」(Life in Britain Knowledge Test)。舉個例子,你知道誰是沙克.狄恩.穆罕穆德(Sake Dean
Mahomet)嗎?(好吧,他是把洗髮精引進英國的人)。你知道一九四四教育法案的別名是什麼嗎?(《布特勒法案》〔he Butler Act〕)。你知道終身貴族爵位是從哪一年開始授勳的嗎?(一九五八年)。你知道從哪一年開始女性與兒童的每日工作時數上限是十小時嗎?(一八四七年)。你必須能認得出傑森.巴頓(Jenson
Button)(不要問我為什麼)。如果你答不出大英國協的會員國數目,或是克里米亞戰爭時期誰是英國的仇人,又或者你不知道錫克教、回教、印度教與基督教分別於英國所占的人口比例,或說不出大笨鐘的本名(伊麗莎白塔),你就可能無法取得英國公民權。事實上,測驗中還包括了幾題沒有正確答案的題目,例如「英國大陸距離最遙遠的兩端是?」你必須回答從地角(Land’s End)到約翰奧格羅茨(John
O’Groats),但這根本不是事實啊。這測驗真的是恐怖到了極點。
為了準備考試,我買了整套的教科書,其中還包括有著閃亮亮封皮的《英國生活:給新住民的建議》(Lif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Guide for New Residents)以及兩套輔助教材:一本是《官方版學習指南》(Official Study
Guide),此書主要功能在於教導你如何使用那本有著閃亮亮封皮的教材(兩書的編排內容完全相輔相成);第二冊則是《官方版練答題》(Official Practice Questions and Answers),其中包含了十七回的題庫大全。我當然二話不說先做了幾回測驗,結果淒慘無比;試問如何稱呼威爾斯議員(Welsh
MPs)?答案顯然和葛爾士(Gareth)與戴芬德(Dafydd)無關。
《官方版學習指南》還滿好讀的,內容平鋪直敘,時而稍嫌空洞,但總不至於太過荒腔走板。
藉由此書你理解到英國社會重視公平價值,並展現出文學與藝術相關的豐富底蘊;英國社會講究禮儀,並開啟了與蒸汽相關的科技大時代。基本上英國佬喜歡在花園裡摸摸弄弄、散步、用大火炙燒牛肉,並在星期天大吃約克郡鹹派(如果是蘇格蘭人的話,則會選擇羊雜碎)。英國人喜歡到海邊度假,他們遵守《行人交通規則》(Green Cross
Code),對排隊一事極富耐心,他們投票理智並且尊重警察這門職業,而皇室更是英國社會欽仰的對象,基本上來講,英國社會特重中庸之道。三不五時,他們會到酒吧喝兩杯英國黑啤酒,或玩幾局九柱戲或撞球;事實上《官方版學習指南》的撰寫者應該都是足不出戶的宅宅吧。
有時候,《官方版學習指南》太求政治正確以至於語意含混到什麼都沒說,例如該書如此形容英國的音樂場景:「在英國,你可以在不同的音樂場地與音樂祭,聽見各式各樣的音樂。」(我不是喜歡狡辯,但是音樂場所本來就是聽見各式各樣音樂的地方啊。)有時候你不免覺得《學習指南》根本就錯誤百出,別再提地角與約翰奧格羅茨了,那根本不是英國領土上最遙遠的兩點呀。該書還認為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正是該國國人最引以為豪的男性代表,但是霍普金斯早已歸化為美國籍並定居於加州好久了。重點是,《官方版學習指南》還把安東尼的名字拼錯了。此書將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的「詩人之角」(Poets’ Corner)誤植為單數的詩人之角(Poet’s
Corner),難道那裡只夠平躺一位已故詩人嗎?我試圖平心靜氣地翻閱《官方版學習指南》,不過如果官方要求人們熟知英國相關知識,難道出題者們不該展現出應有的學養嗎?
總之,歷經了一整個月的苦讀後,大考日終於到來。依照指示,我必須於指定時間出現在漢普郡(Hampshire)伊斯特利的韋塞克斯大樓,這是距離我家最近的考場。伊斯特利為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衛星城鎮,並於二次大戰時遭受砲火無情攻擊,好吧,或許也沒那麼戲劇性。
總之伊斯特利是個不會讓你留下任何印象的地方—它並沒有醜到離奇,但也毫無吸引力可言;市況絕非繁榮,但也不至於蕭索死寂;市中心看得見若干商業活動,可說是一息猶存。聖貝里超市外牆更直接加裝玻璃頂棚權充巴士站,讓鴿子能有個乾燥之處排泄。
伊斯特利和其他英國城鎮一樣,工廠與小商店相應倒閉,唯一僅存的經濟活動則是販賣咖啡,場域則為咖啡店。該城商店可約莫劃歸為兩類:沒人的商店和咖啡店,而且還有很多空無一人的商店正轉型成咖啡店,你可以從招牌看出發展脈絡,當然,也有很多乏味的咖啡店正致力於將自己變成一間完全沒人會光顧的店,看起來,他們的努力很快就會獲得回報。本人對經濟學毫無所知,不過這看起來就是所謂的惡性循環吧。雖然有一、兩位豪氣凌雲的企業家在此開了一元商店或投注站,也有幾所慈善機構企圖挖掘出廢棄空間的潛力,不過伊斯特利真是個適合坐下來喝杯咖啡觀賞鴿子排泄的好地方。為了拯救該地經濟危機,我買了杯咖啡,觀看鴿子沿路大便,接著,親赴考場。
該日清晨,有五名考生報到,迎接我們的是整間的桌椅、電腦螢幕、滑鼠與滑鼠墊,我們無法看見其他考生的螢幕。當我們入座後,電腦螢幕出現了四道練習題,讓我們確定滑鼠與滑鼠墊的功能完好。既然是練習題,題目想當然耳非常簡單,考題如下:
「曼聯」(Manchester United)為:
(a)政黨
(b)舞團
(c)英國足球隊
包含我在內的四名考生只花了十五秒就答題完畢,獨獨一名優雅、豐腴的中年女性例外。我猜她或許來自某些嗜吃甜食的中東國家吧,總之她實在花了很久的時間。主考官兩度過來查看她的狀況,我只好翻看抽屜打發時間,雖然抽屜沒有上鎖不過也沒有任何東西,我試著玩了一下滑鼠,看看是否能與空白畫面互動。很好,瞭解了。
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時間,那名女士表示作答完畢,主考官過來檢視她的答案。他彎腰將身子傾向螢幕,以訝異但相當低調的語氣說道:「妳沒有答對啊。」
她尷尬地笑了笑,不確定主考官是否在稱讚她。
「妳要不要再試一次?」主考官相當親切地詢問。「妳有權再作答一次。」
很明顯地,那名女士根本不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她豪氣地決定放手一搏,考試正式開始。
第一道考題是:「看過伊斯特利後,你還想待在英國嗎?」好吧,其實我根本記不得第一道考題或是其他任何考題。應試者不能攜帶紙筆,所以我既不能抄寫筆記,也不能用鉛筆計算自己的牙齒數目。總共有二十四道複選題,你只有三分鐘可以應答。基本上來講,你要麼就是非常確定答案,要不然就是根本毫無頭緒。答題完畢後,我走到主考官座位旁,等待電腦計算成績,嗚,電腦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計算,不過好在主考官笑容滿面地通知我好消息,雖然他也不知道究竟我答對多少題,因為電腦只顯示測驗通過了。
「我會把測驗結果列印出來。」他說。我們又花了一段時間等待。我以為他會給我一張用羊皮紙謄寫的精美證書,堪比攀登雪梨港灣大橋或維特羅斯連鎖超市(Waitrose)烹飪班提供的那種,但他只給了我一張薄薄軟軟的列印紙,上面註明我的知識程度足以應付現代英國生活。
我笑容燦爛得不輸那名中東女士(我最後一眼看見她時,她似乎正在和鍵盤搏鬥),本人心情愉悅地離開韋塞克斯大樓,一股興奮之情熊熊竄起。太陽耀眼如常。對面的巴士站裡有兩個穿厚夾克的男人正在喝早餐的黑啤酒。一隻鴿子一邊啄食菸屁股一邊排泄。現代英國生活看起來,還滿不錯的。
約莫是隔日,我和可愛又仁慈的出版商拉瑞.芬雷(Larry Finlay)在倫敦共進午餐,討論我的下一本書。拉瑞這人一點都不無聊,也因此我提議了許多無聊到有點誇張的主題──瑪米.艾森豪威爾(Mamie Eisenhower)的傳記、關於加拿大的散文等,看看他會用什麼怪點子來否決我。
「你知道嗎?」他說,「《哈!小不列顛》出版已經二十年了!」
「是喔?」我回答道,原來時間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逝了。
「你從來沒想過要寫續集嗎?」他語氣很輕鬆,但我從他的虹膜中看見一絲不尋常的閃爍光芒。
我想了一會兒,「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滿巧妙的,」我回答,「你知道嗎?我正好要參加英國公民考試。」
「真的?」他回答。他的眼神越來越明顯開始閃閃發亮。「你要放棄美國公民了?」
「沒有,我會保留美國身分,但是要拿雙重國籍。」
拉瑞的腦袋開始快速飛轉,他開始思考市場計畫,要張貼在地下鐵的海報已經展開,不要太大的,可以用小一點的尺寸……「你可以好好利用新的英國身分。」他說。
「呃,我不想再去那些老地方,寫一堆一模一樣的事。」
「那就去沒去過的地方啊,」拉瑞附和我說,「可以去……」他快速地思考了一下有什麼根本沒人會去的怪地方,「博格諾禮吉斯啊。」
我興味盎然地看著他,「我這個星期已經第二次聽見這個地名了。」
「這就是徵兆。」拉瑞。
當天下午,我回到家從抽屜拿出那本老舊到快要鬆散開來的《不列顛地圖集》(AA Complete Atlas of
Britain)(這地圖集真夠舊了,裡面連M25公路都還沒蓋好),隨手翻了一下。我非常想知道英國大陸最遙遠的兩點距離為何?很明顯地,那絕對不會是《學習指南》說的從地角到約翰奧格羅茨(依據《官方學習指南》提供的答案,英國大陸最遙遠的兩點距離為蘇格蘭北海岸的約翰奧格羅茨到英格蘭西南方的地角,兩地相距一四○○公里。事實上,以地圖看來英國的最北端並非約翰奧格羅茨,而是往西十三公里左右的鄧尼特角(Dunnet
Head),兩者位在同個海岸線,但鄧尼特角往北延伸了至少六塊地。不過麻煩的是,若你想從地角旅行至約翰奧格羅茨,取道必得蜿蜒曲折。但是若非直線進行的話,那麼任何地圖上的兩點都有可能成為英國大陸最遙遠的距離不是嗎?
我想知道的是不涉險海道的直線最遠兩處。我拿出一把尺丈量地圖,赫然發現最遠的直線兩點並非地角至約翰奧格羅茨,而是地圖左方少有人跡的蘇格蘭憤怒角(Cape Wrath)至博格諾禮吉斯,想不到吧。
拉瑞說得沒錯。這就是上天給我的徵兆。
我用大約一秒鐘的時間思考以布萊森線(The Bryson
Line)為主軸穿越不列顛的可能性(我以本人之名為此線命名,畢竟我是該線的發明者),但是我很快就發現這條路徑不但不可行也毫無吸引人之處。沿著布萊森線旅行意味著我必須穿越民宅、踩踏他人花園、以身涉水、橫跨草原,聽起來滿瘋的。假使我想要稍微文明點,那表示我必須不斷地在麥克爾斯菲爾德(Maccles_eld)或伍爾弗漢普頓(Wolverhampton)這類的郊區穿梭,這似乎是相當倒胃的旅行。不過,我決定讓布萊森線作為此行的精神指引,並由兩點進出英國,若在方便我也沒忘記的情況下,我也可能實際探查布萊森線,但一切隨緣。就當作這是「私人通行權」(terminus
ad quem)的起點好了,管它這是什麼意思。我會盡其可能地避開上次旅行時造訪過的地點(我可不想氣喘吁吁地站在某個定點唏噓過往,這對老人來說太淒涼了),我希望造訪新的城鎮,並以沒有偏見的全新眼光觀看不列顛。
我對憤怒角很有興趣。我對該地一無所知,只知道那裡八成可以停放大型休旅車,聽起來那是個粗獷、艱險、有著巨浪拍岸,極度適合勇者的地方。當偶遇的人問起我旅行的目的地時,我可以遙望北方以堅定的神情回應:「天意要我去憤怒角。」可想而知,對方會以仰慕的語氣回應:「噢,好遠呀。」我會面帶滄桑地說道:「嗯,希望那裡至少有可以喝茶的地方。」
不過在展開遙遠的冒險之前,我還要穿越數百哩造訪英國歷史小鎮和鄉村美景,而且我必須先前往位於英國海岸的博格諾禮吉斯,這美妙的地方。
導讀 Introduction
小而美──享讀碎碎唸
二十年前,旅遊文學名家布萊森推出《哈!小不列顛》(Notes From a Small
Island),名噪一時。《哈!小不列顛》洛陽紙貴,成為書市寵兒,一部分是因為「知識分配不均」:英國「知識」(我是指知識,而不是指英國實體)像是一座寶庫,布萊森可以登堂入室,可是大部分民眾找不到入口。但是,二十年之後,多虧電腦網路,「知識分配不均」的情況大幅改善。誠然世界上許多人口仍然陷於赤貧,不能享用網路,但是國內無數青年卻早就將網路、手機帶來的方便視為理所當然。那麼布萊森現在推出《比爾.布萊森大不列顛碎碎唸》,還有什麼賣點呢?
布萊森的強處,絕對不僅僅在於陳列旅遊資訊,更在於勇於提出個人觀點。《比爾.布萊森大不列顛碎碎唸》可以提醒各種仰賴「網路養分」的寫手、文青、背包客:在這個時代,光是整理資訊並不足以讓自己在茫茫人海勝出(誰不會靠GOOGLE 找地圖呢?),只有大膽提出「與眾不同的見解」才可能鶴立雞群。自助旅行者只要手機在手,就以為自己變成旅遊達人,結果每個人都交出來大同小異的FB照片:
「這是莎士比亞的家鄉,好棒,順便轉貼一首莎翁的十四行詩。」或,「我在巨石陣現場,好棒,謝謝某某部落格推薦。」這些看圖說話的FB貼文,只有別人早就陳列過的情報,卻沒有個人意見。但是,這種貼文竟然偶爾可以結集出書,還賣得不錯。
《比爾.布萊森大不列顛碎碎唸》持續強調一個觀點:英國「小而美」。小,但是美好。我看得出來布萊森憐惜英國的情感。不過,我想要提出另一種詮釋「小而美」的說法:小,而且美國。對來自美國的布萊森來說,英國之所以可愛,正因為英國就是迷你版本的美國化身,美英兩國是表兄弟:英國的人事物顯得比美國優雅(例如「新福爾摩斯」),卻也比美國古怪(例如「豆豆先生」);比美國時尚(例如「007」),卻又比美國蠢(例如「天線寶寶」)。在感嘆英國衰亡的時候,美國人心裡想著美國的茁壯。這種表兄弟的情感不會延伸到法國、德國等等其他第一世界國家。
布萊森的新書勇於陳述個人意見─並不是毫無組織的嘮叨,而是經過整合的主張。我認為,此書主張「正在消逝的前一世紀英國(二十世紀英國)需要被哀悼」(至於書中陳列的各種資訊,只是配菜,不是主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國已經快速「廢墟化」。被淘汰的港口、被廢棄的鐵道、被垃圾吞沒的街道(布萊森很迷戀街道垃圾,一直在碎碎唸垃圾!),都是廢墟英國的實景切片。布萊森這一回遊遍英國,意在跟一個個「老朋友」(舊景點)道別:走到曾經風光的廢墟,便送上憑弔的花束;遇到即將成為廢墟的舊址,就看這個老朋友倖存於世的最後一面。抓住作者「哀悼英國」的微言大義,才比較容易理解為何作者總是不小心踏入報廢的景點(其實不是不小心,而是故意),裝瘋賣傻,苦中作樂。作者披著鬧事的外皮,行致哀之實─人在悲傷的時候,偏要強顏歡笑。布萊森是觀光客的相反:觀光客專門找光(光鮮體面的人事物),但是布萊森偏要深入無光的所在。
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