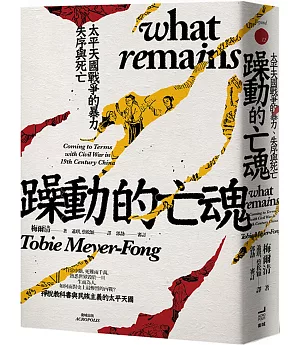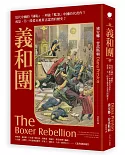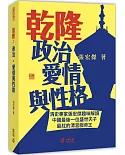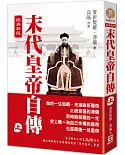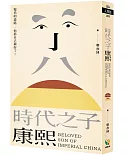作者序
本書英文版的受眾主要是英語世界裡對中國史感興趣的學者和學生;他們堪稱小眾。儘管如此,我卻也希望這本書能突破這個既有的小眾讀者圈,希望它也能吸引研究內戰、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學者,或是吸引那些有興趣了解不同文化脈絡下的人群如何處理災難的讀者。但最終,我期望這本書能譯成中文,介紹給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讀者。這些讀者熟悉太平天國的歷史,因而對本書的特殊視角可能會產生更直接的反響。
我首先要感謝蔣竹山教授把本書收入他主編的「新史學譯叢」,並擔負起為本書在臺灣找到出版社的責任。感謝衛城的編輯們在本書中譯本無法在中國大陸方出版時,慨然接手出版事宜。感謝蕭琪和蔡松穎仔細、詳盡地翻譯原著,並感謝郭劼確保譯稿的精準、雅馴。他們三人都不吝付出自己的時間和專業,能和他們一起合力完成這項工作,我感到非常愉快並深受啟發。
歸根究底,本書所書寫的,是大規模的暴力以及歷史記憶如何為政治所用。本書講述了人們所沉痛經歷的家破人亡,講述了那些受影響最深的人──包括父母子女、夫妻,以及地方社群──如何努力理解、承受這樣的家破人亡。本書也解釋了清政府是如何在各個層面上,設法從這樁暴露了它自身軍事和政治弱點的事件中,汲取出正面的訊息。本書展示了國家祀典如何將普通人所經歷的痛苦和死亡,轉化成盡忠犧牲的英勇姿態;同時亦展現了這些表面上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國家封賞,如何成了當地重建工作的一部分,從而具有新的、時而矛盾的含義。我希望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讀者,可以藉由閱讀本書,對太平天國之後的其他事件以及人們對這些過往暴力的應對(或不應對),會有更好的理解。
在這個書寫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我試著說一個無關中國堅定走向革命現代性的故事,並盡量不討論名人及其理念。我希望身處於現下的我們,來思考暴力、動亂和死亡對遭逢這一切的人們而言,意味著什麼。我寫這本書,是為了重申我們有著共通的人性。當災難降臨時,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家庭的一分子,我們都會盡力求生。不同時空的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差別,但到頭來,人們對災難的應對方式在某些部分上是相似、甚至是舉世皆然的。對災難相似的反應,提醒著我們要對戰爭與苦難戒慎恐懼,並且珍惜我們深愛的人、深愛的地方。也許本書的中文書名《躁動的亡魂》有助於我們記住這點。
有些讀者認為本書對清朝抱有同情,因為書中採用的部分材料常常被史料編纂者歸為代表清朝立場的一方。但這畢竟不是一本關於英雄和反派的書。而且,我認為,如果我們將太平天國戰爭視為壁壘森嚴的兩方之間的鬥爭,就會對過去作出錯誤描述。在當時,即便人們謹慎地、大張旗鼓地維繫忠臣和叛軍間的界線,這界線也可以是模糊的。無論他們聲稱為誰而戰,1860至1864年間江南一帶軍士們的殘忍行徑,在個人身體與社會機體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傷疤。這在當時許多目擊者的作品中都有清楚的記載。因此,本書所講述的故事是:在中國十九世紀中葉的背景脈絡下,歷史書寫和紀念活動是如何從模棱兩可、機會主義以及人們所經歷的憤怒中,建構起清晰的道德與政治意涵的。我並沒有特別為清朝方或太平天國方說話的意思。
另一些讀者則問我,為什麼堅持把太平天國戰爭與二十世紀的暴力事件相聯繫?為什麼不把它當作是黃巾軍、赤眉軍或五斗米道一類的朝代末叛亂?我的回應是:為何不能把它與二十世紀的暴力事件相聯繫呢?事實上,至少從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就一直被當成是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序幕。我們不該把「現代」這個詞的意涵侷限於進步、烏托邦和發展。「現代」這個詞不該只有正面的意涵。另有人曾經問我:如果戰爭能促進國家發展而給國家帶來好處,這場戰爭是否終究是值得的呢?對此,我的回答是:對誰而言是值得的呢?且這又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呢?也有些人問我如何評價洪秀全。我的答案是:
我不會去評價他,那不是我要做的事。
在2020年4月寫作這篇序的當下,世界正面臨著全球疫情和一場規模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未曾有過的經濟危機。大難當頭,我為能和親愛的家人一起待在家裡而深感慶幸。我希望我是錯的,但我感到我們正走向動盪的時代。我無法預測這樣的艱難時刻會以怎樣的面目呈現。我的想法有一些自私、現實且稍顯偏狹。我想和朋友們暢談、想見到我的學生們。我覺得有些無助,並感懷昨日不再。我想要回到去年夏天,那時本城的棒球隊節節勝利,河邊的酒吧與餐廳被歡笑的客人擠得水洩不通,而我尚能毫無困難地出國拜訪摯親好友。我想要看見一個熟悉的未來,卻只看到構築起過去美好時光的基石搖搖欲墜。也許這本關於苦難的書,今日讀來,能教我們如何堅韌地面對這一切?
梅爾清,2020年4月17日
華盛頓特區
推薦序
傾聽亡魂的聲音
涂豐恩(「故事」網站創辦人暨執行長)
西元1861年,太平軍與清軍之間陷入激戰。
前一年,太平軍剛剛擊潰了清軍的江南大營,再次讓清政府大為震動。他們攻佔了蘇州、杭州等城市,而後又發起西征,目標位於長江中游的武漢,政府軍也隨即展開反擊。那年4月,雙方在另一座長江沿岸城市安慶短兵相接,由曾國荃率領的湘軍,將太平軍佔領的安慶團團包圍,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率眾前往馳援,卻沒能成功。幾個月後,太平軍宣告彈盡援絕,大勢已去,清軍攻破了安慶,整座城市重回清政府掌握之中。
就在這場安慶保衛戰正酣的同時,有另一場戰事在太平洋彼岸爆發。1860年的11月,美國舉辦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代表共和黨的林肯當選美國第十六任總統。這個結果卻引起南方各州的不滿,由南卡羅來納州為首,前後共有七個州陸續宣布脫離聯邦。隔年3月,林肯在就職典禮上仍在呼籲統一團結,卻沒能挽回分裂的局勢。到了1861年4月,南方與北方的軍隊在薩姆特堡第一次交火,南北戰爭就此拉開序幕。
這場兄弟鬩牆的內戰,一共打了四年多,造成前所未有的慘烈傷亡。到1865年南方軍全數宣告投降為止,估計至少六十二萬名士兵命喪戰場──這數字比美軍在兩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中犧牲的人數全部加起來還要多。以當時美國人口來計算,平均每一百人中,就有兩人死於戰爭。而這還沒有計入遭到波及的平民。
毀滅性的內戰,迫使美國民眾必須逼視死亡。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歷史學者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寫過一本《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在書中,她把南北戰爭的焦點,從征戰沙場的英雄與將軍,轉移到那些大量的、無名的死者身上。
生命大規模地消逝,改變了「死亡」本身的意義,比如人們開始追問,遠赴戰場的士兵們,在沒有家人陪伴的情況下,如何還能獲得「善終」(Good Death)?在戰爭情境下,殺戮如何不與宗教信仰產生衝突?還有那些活著的人呢?福斯特寫到:
人們發現,自己處在了一個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道德宇宙中──在這一道德宇宙中,超乎想像的浩劫已成為了日常的經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上帝在哪裡?一個仁慈的神,怎能允許這樣的殘忍與這樣的苦難存在?懷疑快要壓倒了信仰──這是對上帝仁慈與靈魂不朽的基督教敘述之信仰,是對世俗生命的可理解性與目的之信仰。語言似乎無力解釋;人們似乎無法理解他們的死亡──以及他們的生命──的意義。
逝者已矣,而生者才剛要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
同一時間在太平洋此岸,太平天國為中國社會帶來的衝擊不遑多讓,上千萬人的死亡,大規模的破壞與屠殺。對於失序的恐懼,在在挑動著人們的情緒,刺激著人們的想像。死亡不只是肉體的消逝,它需要悼念,也需要詮釋。它需要意義。這是歷史學者梅爾清在《躁動的亡魂》一書中要探索的主題。
梅爾清教授並未著墨太多在我們熟悉的人物,如洪秀全或曾國藩,反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較不知名的地方文人,或是犧牲性命的無名將士。對他們而言,死亡有何意義?他們用筆墨與身體,寫下了太平天國的另一種歷史。這不是一項容易的研究工作,卻改變了我們理解這段歷史的視野。
歷史是關於記憶的學問,關乎我們記住哪些事情,又如何記憶。一旦我們拉長時間,記憶本身也成了歷史,層層疊疊。比如關於太平天國的歷史記述,在臺灣受教育的讀者,可能已經十分習慣將它視為一場叛亂,是在那內憂外患不斷的晚清末年,另一場荒唐亂事;但在海峽彼岸的中國,有段時間卻將太平天國視為英雄豪傑,農民起義典範,例如1973年一本由「『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所編纂的《太平天國革命》,講到清軍策劃戰略,便說他們「用心十分險惡」,還與歐洲國家等「外國侵略者」聯手,至於講到太平軍的人物,則說他們「堅貞不屈」、「可歌可泣」,不時有著「輝煌勝利」。
而今農民起義已經不再被歌頌,中國轉而渴望和諧社會、和平崛起,要的是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歷史上人們的情緒、傷痛、失落,與夢靨般的記憶,難道就一筆勾銷,通通都不算數了嗎?在每一場災禍過後,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哪些人與事應該被記得,又有哪些不該被遺忘的卻遭到埋葬?《躁動的亡魂》以太平天國為例,對這些議題進行了一場嚴肅的追問。
歷史是關於死者,也是關於生者。或者說,是生與死之間的對話和交流:歷史學者不也一向都是招魂者嗎?我們總是在傾聽亡魂的聲音,不論那是躁動的,還是幽微的。
《躁動的亡魂》一書雖然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內容卻充滿情感,甚至有個十分感性的結尾,在兩位譯者的精心翻譯下,這些文字更是顯得格外動人。「戰爭結束後,留下了什麼?」作者問。而這本書是她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