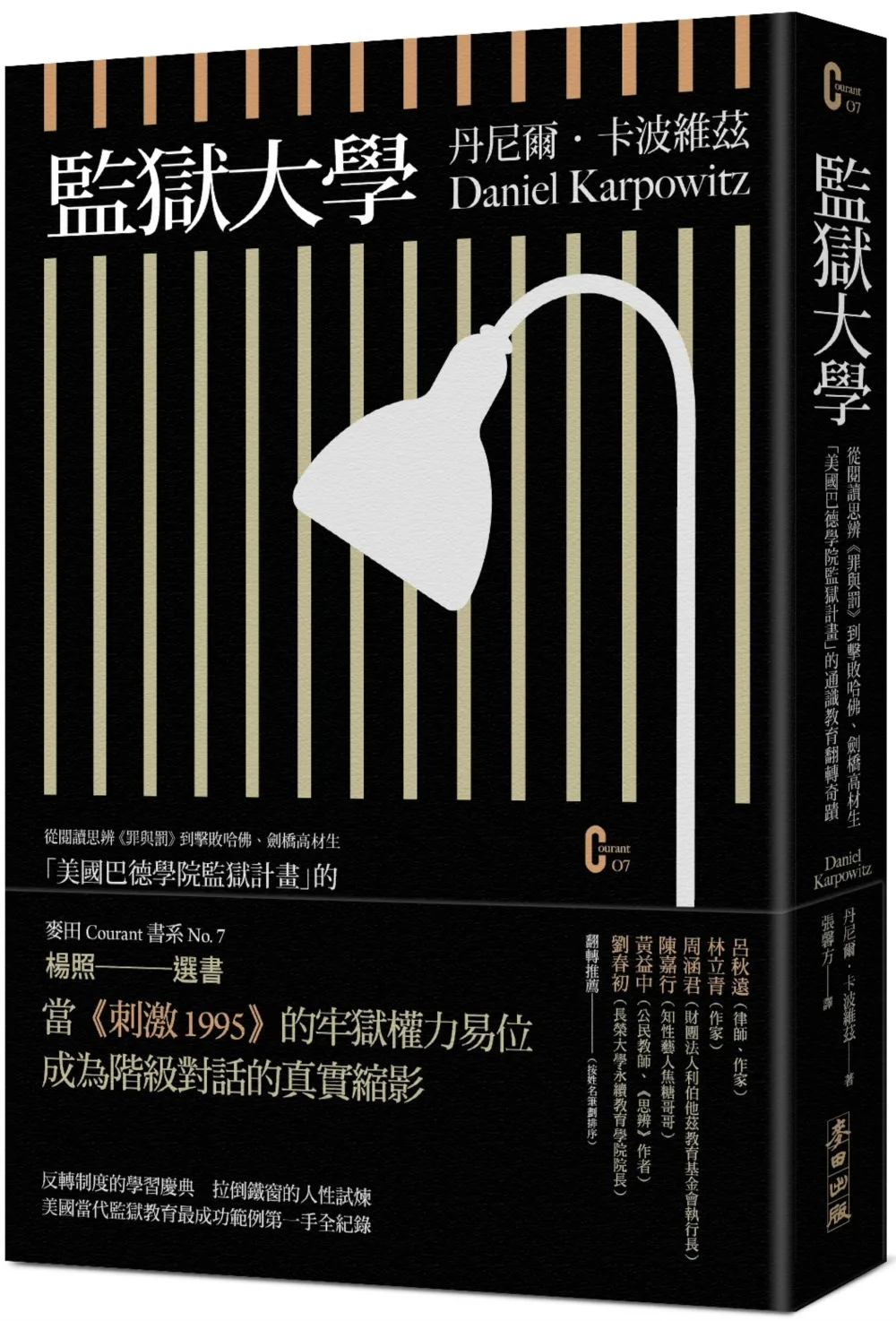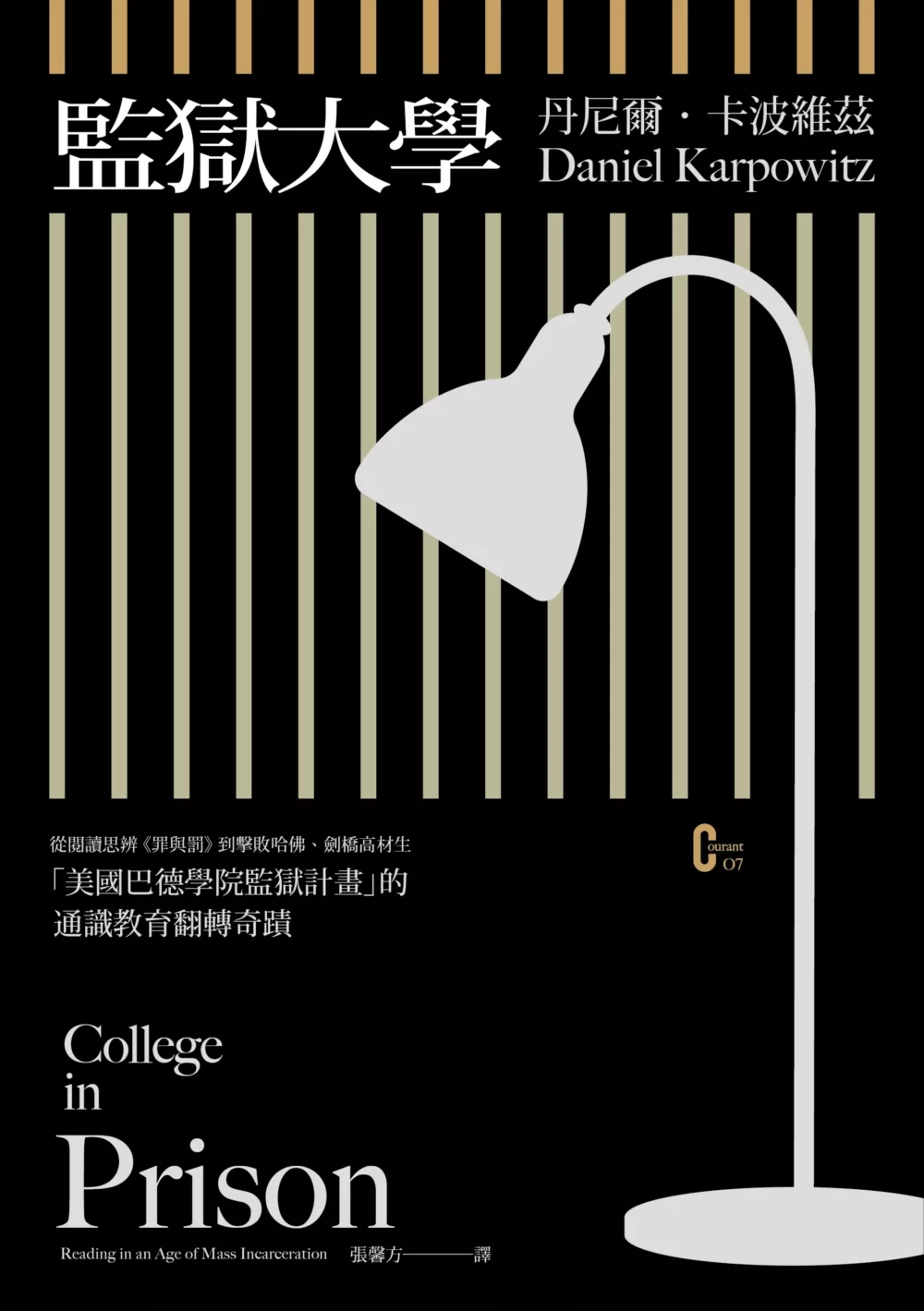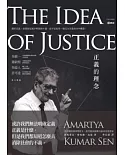監獄大學:從閱讀思辨《罪與罰》到擊敗哈佛、劍橋高材生,「美國巴德學院監獄計畫」的通識教育翻轉奇蹟
定價:360 元
NT $ 252 ~ 332
- 作者:丹尼爾•卡波維茲
- 原文作者:Daniel Karpowitz
- 譯者:張馨方
- 出版社:麥田
- 出版日期:2020-05-30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863447692
- ISBN13:9789863447696
- 裝訂:平裝 / 288頁 / 21 x 14.8 x 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