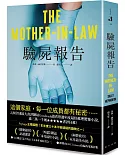序
塞拉哈汀・德米塔斯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入獄至今,官方對他的指控是恐怖主義。這個罪名近年來在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的主導下,擴大適用於任何他眼中的政治威脅。而德米塔斯確實是個嚴重威脅。他致力倡導和平,不僅代表庫德族,也為所有在土耳其希望透過民主途徑尋求社會正義的人發聲。儘管國會席次遭到剝奪,他仍藉由寫小說與外界持續保持對話。
德米塔斯在鄰近土耳其西界的牢房裡決定提筆時,想必明白他正追隨一個輝煌的傳統。首先,他肯定會憶起土耳其最偉大的詩人希克梅特(Nâzım Hikmet,
1902-1963,土耳其詩人、劇作家、小說家,被稱為「浪漫共產主義者」及「浪漫文藝復興人」,因讚賞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多次遭土耳其政府逮捕,後流亡蘇聯並於莫斯科郊外因心臟病發逝世),正是在獄中寫下最撼動人心、歷久不衰的詩句。他也會想到奧爾罕・凱末爾(Orhan Kemal,
1914-1970),這位紀錄被剝奪者故事的作家,與希克梅特關押在同一間牢房,並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第一篇小說。索伊莎(Sevgi Soysal, 1936-1976)以幽默而溫暖的筆調,寫下關押在女性政治監獄裡的日子,想必也為德米塔斯帶來啟發。此外還有現代史詩大師亞沙爾・凱末爾(Yaşar Kemal,
1923-2015),不論在書裡或書外(獄中或出獄),都將生命奉獻給能夠想像一個沒有不公義、沒有獨裁專制的世界的人。
這些文學道路的先行者除了賦予德米塔斯勇氣,也為他帶來讀者。土耳其擁有偉大的抵抗書寫傳統,與之攜手並進的,是閱讀此類作品的偉大傳統。因為在你手中的不是一份政治傳單,而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故事訴說普通百姓的普通生活,並透過同理心與溫柔的機智,從中映現人民的希望與恐懼。
德米塔斯出生、成長於東南部城市埃拉澤(Elazığ)。五歲時,新興的庫德工人黨(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 PKK)開始推動庫德獨立運動。十一歲時,庫德工人黨試圖發起全面性的庫德族叛變。整個青少年時期,德米塔斯默默見證了隨後的國內衝突——庫德工人黨襲擊警察與軍隊,國家則發動大規模逮捕、濫用刑求、滅村行動及法外處決。
暴力衍生暴力。一九九一年,德米塔斯十七歲,著名的庫德族運動者艾登(Vedat Aydın,
1953-1991)在安卡拉一場人權會議上以全母語發言,此舉引發激烈公憤,亦違反實施十餘年的語言禁令。總算有人來到權力中心為庫德族人發聲。只是好景不常。艾登遭到肢解的屍體在鄉下田間被發現,土耳其維安部隊向參加葬禮的數千人開火之後,德米塔斯決心投身為庫德族使命奮鬥。德米塔斯自安卡拉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擔任人權律師,並成為人權協會迪亞巴克爾分會的執行董事會一員,艾登先前也曾擔任此會會長。德米塔斯很快就博得「骨頭」的暱稱,因為他總是鍥而不捨地尋找PKK戰士的遺骨,將之送還遺屬安葬。不宣而戰的戰火持續肆虐,眼前仍不見終點。
二○○七年,德米塔斯以無黨籍身分首度贏得大國民議會的席次。當時艾爾段已擔任總理四年,其主要盟友為伊斯蘭教士葛蘭(Fethullah Gülen,
1941-)。葛蘭雖流亡美國賓州鄉間,實則主掌了一個帝國般的龐大組織,旗下涵蓋學校、銀行、報社,據信土耳其各級機關都遍布其支持者。艾爾段的最大政敵,則是死硬世俗派的軍方勢力,兩者之間長期的權力鬥爭,最後在艾爾段指控三軍高階將領犯下叛國罪告終。多數被訴軍官仍囚於獄中時,庫德工人黨也遭監禁的領袖表態願意協商停戰。隨著談判進展,德米塔斯的聲音越來越有分量,不僅在談判桌,在公開場合亦然。他倡導和平,致力推動一個土耳其人與庫德人能合作並存的國家,以他的話來說——「共同攜手,拯救土耳其癱瘓的民主體制」。
二○一二年,德米塔斯參與創建人民民主黨(Halkların Demokratik Partisi,
HDP),支持者很快擴及庫德族基本盤以外的選民。教育程度較高的土耳其人,尤其年輕族群,對於該黨擁抱多元文化政治、主張和平和解、性別平等理念感到認同。性別平等的實踐亦反映於政黨的組織架構,他們效法德國綠黨的共同領導制度,各層級的領導職皆由一位男性及一位女性共同擔任。二○一四年,德米塔斯站上黨內最高位置,與女性同僚尤賽達(Figen Yüksekdağ,
1971-)共同擔任黨魁。其黨內規章亦要求成立具自主權的女性議會,肩負將女性議題全面融入政黨運作的任務。女性議會在提名參選人階段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為鼓勵女性挺身參與,將女性登記參選的費用設定為男性的一半。
二○一五年六月,人民民主黨投入第一次普選選戰,最後贏得百分之十三的總票數,在大國民議會五百五十席中拿下八十席,排名第四。若非受阻於當時政局的其他權謀角力,這項空前的勝利無疑會為土耳其的全國政治開啟新頁。艾爾段在肅清軍方敵對者、以自家人馬代替後,控制了軍隊勢力,越來越走向專制獨裁。他拋棄先前的多元化論調,重回舊時的單一民族主義,越加強化了庫德理念支持者的不信任感。鄰國敘利亞的內戰,尤其庫德族戰士(在西方因壓制伊斯蘭國而備受欽佩)的處境,即是危險的例證。再一次,坦克駛入東南部庫德族區的城市,宵禁頒布,且往往長達數日,迫使居民在烽火肆虐、糧食飲水有限的情況下受困家中。家園在戰火中化為斷垣殘壁時,甚至無法為死者安葬。
與此同時,安卡拉當局的伊斯蘭主義勢力結盟瓦解了。親葛蘭的司法界及警界,針對艾爾段的正義發展黨(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AKP)發起一連串大動作的貪腐指控。土耳其最大的兩個伊斯蘭主義組織至此反目為敵。
其後,二○一六年七月十五日,爆發了一場極其詭譎、血腥的政變,儘管土耳其過去不乏不尋常的政變,此次仍屬史上少有。政變從一開始就在網路上即時轉播,短短數小時內遭到弭平。震怒的艾爾段旋即大舉整肅異己,不論是實際的反對者或他認定的潛在敵人,皆在其列。他對庫德族區重新主張國家控制,遭遇任何反抗,都以不成比例的武力進行殘酷鎮壓。到了該年十一月,德米塔斯與其他同黨領袖遭到逮捕,被控為庫德工人黨散播宣傳,德米塔斯對此罪名斷然否認。
政變未遂後三年,土耳其成為全世界監禁最多記者的國家。成千上萬的公務員、教師、學者失業或面臨刑事調查,公部門以外也有許多人僅僅因為小孩就讀的學校或使用的銀行服務有問題,而遭受同樣命運。
有少部分艾爾段的批判者成功逃出國,許多人則是護照遭到撤銷或限制出境。凡被扣上「叛國者」或「恐怖分子」帽子的人便難以再找到工作,估計現在有超過一百萬土耳其公民陷入人稱「民事死亡」的處境。鄰居迴避、就業碰壁,也無法到國外重新生活,就此墮入貧困,孤立無援。
其中庫德族區域受創最為慘重。作家暨藝術家拜莎(Nurcan
Baysal)寫道:「今天,如果你去到庫德族區域的城市,你會看到市政大樓、警察局及公家機關前方架設著拒馬;你會在街上看見坦克、武裝車、警察與身負重裝的士兵;你會目睹城市殘破傾頹,人民流離失所;你會在錫爾納克(Şırnak)與哈卡里(Hakkâri)的外郊看見人們棲居帳篷;你會發現成千上萬的教師、醫生、學者、作家、記者沒有工作。路上到處都是檢查站。監獄裡,四到六人同擠一張床,因為監獄人滿為患。」然而,正如她繼續指出的,國際上仍難以獲知這些情況。幾次大動作拘捕外籍記者的事件之後,已經很難在這些地區發現國際媒體記者的蹤影。
艾爾段掌控了所有國內主要媒體,大量運用監控科技,意味著沒有人能冀望使用社群媒體而不被察覺。然而,《黎明》於二○一八年春天在土耳其出版,至今已銷售二十二萬本。最近一次書展,有二十位作家挺身代替無法出席的德米塔斯簽書,排隊簽名的隊伍延續了六個小時。
對土耳其的讀者而言,作家德米塔斯的魅力,也同樣是德米塔斯作為政治人物所展現的特質:幽默感、對平凡人的惻隱之心、長期支持女權,以及與土耳其年輕世代的連結——熟稔網路、貼近世事、追求更大的個人與政治自由。不過最重要的,讀者珍愛這位作者,因為選集的每一篇故事都透出可貴的希望之光,不論處境多麼黑暗,儘管近年來遭受種種倒退挫敗,土耳其殘破不堪的民主仍有一線希望,只要土耳其人與庫德人能夠學習攜手合作。
故事裡,生命的嚴酷總是隨時逼近。然而不管他的角色身在何處——在獄中或在巴士後排、在墓園緬懷死者,或在廚房向母親道歉——都是想像力豐富、聰明巧妙的說故事人,敘事間充滿日常語言的音樂性,並且無論如何都會找到力量,繼續前進。「只要懷抱勇氣與決心邁步向前,有時候你可以比車子還快。」其中一個角色說:「艱苦的日子總會結束,老媽,一定會的。」另一個角色坦承兒時頑皮行徑之後說:「我滿懷感激親吻妳的手,」他繼續說,「以及天下所有母親的手。」
不熟悉德米塔斯的讀者,恐怕會認為這些文字不夠誠懇。事實上,德米塔斯從一開始就將女性——無論是母親或女兒,勞工或專業人士,社運者或選民——視為促成改革的強大力量。他也深知女性在土耳其面臨的危險,這在本書的同名篇章裡反映得再清楚不過,那是一篇關於「榮譽處刑」的故事。
受害者的名字叫雪荷(Seher),在土耳其語裡就是「黎明」的意思。但是故事裡沒有光,只有被迫殺死親姊姊的男孩的悲痛。男人中只有他要獨自承擔良心的苦責,這似乎不會為他的母親與妹妹帶來多少希望。但是德米塔斯,這位作家暨政治家,拒絕喪失信心。「黎明是光明自黑暗中乍現的時刻。」他被問到為何選擇這個名字及書名時回答。「黎明代表希望,每一天都重新復甦、重燃新生。黑暗自認為永恆不朽,在黑暗以為將光明澈底熄滅的時候,黎明便發出重重的第一擊。黎明是為黑暗劃下句點,宣告光明開展的時刻。」
二○一八年六月的最近一次總統大選,便給了德米塔斯這樣的時刻,儘管選舉最後由艾爾段勝出,或許還涉及不正當操縱。德米塔斯的政黨推舉他為候選人後,由他的家人和律師透過推特傳播訊息,經營線上選戰。選戰的最高峰莫過於德米塔斯從獄中發表演說的時候。他在撥給妻子的電話中演說,妻子再上傳網路,旋即在社群媒體造成瘋傳。德米塔斯最後僅獲得全國百分之八點多的票數。
德米塔斯目前面臨一百八十三年的總刑期,這或許反映了他在土耳其總統眼中是多麼危險的威脅。然而他能在獄中安頓身心,以詼諧的口吻,書寫那些他被排拒無法觸及的日常世界,則在在印證了他的精神。我們不知道他還必須忍受不公義多久。在此期間,我們有他的文字,以及他的承諾:持續寫作;頌揚我們共有的人性價值;透過翻譯,與世界各地同樣在對抗專制者與極端分子的讀者建立連結;並且提醒我們,黎明會在地平線的另一端,等待著。
莫琳・弗瑞莉(Maureen Freely)
二○一八年十一月,倫敦
作者序
我是一名政治犯,寫下這篇文字的時候,正關押在土耳其艾迪尼市一所高安全級別監獄裡。我猜想,你們大多數都不曾收到從監獄寄出的信,所以我希望你們就這樣看待這篇序文:一封從獄中寫給你的信。
我在一年十個月前遭到逮捕,當時我是土耳其的國會議員,也是簡稱為HDP的人民民主黨的共同黨主席,這個政黨在土耳其的前一次選舉中,獲得近六百萬人投票支持。我與成千上萬的異議者成為政府的清肅目標,以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為由,將懲罰性措施正常化。政府迄今對我發動了一百零二次調查,提出三十四項不同控告。總和起來,我目前面臨一百八十三年的總刑期。
在西方國家,監獄一般而言是犯罪受罰之處,在土耳其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監獄的高牆之內,現在正囚禁著大量有能力、受過教育的人民,足以滿足任何一個中型現代國家的需求。我身為人權律師,曾經數年堅持不懈舉報土耳其監獄的人權侵犯案例,因此我可以完全肯定,並帶著極大的沉痛告訴各位,自一九九八年成為律師以來,我從未目睹人權像現在一樣,如此頻繁而持續地遭到踐踏。現在的土耳其,有人挺身反對政府高漲的獨裁主義,就會迅速被監禁。他們可能是推特發文被視為批判當今政權的異議者、揮舞反抗標語的大學生、忠實報導的記者、參與和平請願簽署的學者,或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國會議員。政府相信連坐懲罰政策將能有效壓制「外面的」數百萬異議分子,他們所處的世界無異於半開放的監牢。於是入獄近兩年期間,我不曾疑問自己為何淪落至此。如同其他許許多多關押在土耳其監獄中的異見者,我也同樣在為和平與民主化付出必要的代價。即使被迫在獄中度過終生,我對於捍衛和平、民主與人權之權利的信念堅定不移。
今日世界普遍認為文學與政治是兩個獨立的領域,我從不認同這樣的觀點。讀者或選民對於作家或政治人物的期待,本質上並無二致,都是希望獲得啟發。兩者都被期待能夠創造意義、仔細觀察所處的社會,並且反省社會面臨的議題。最終,尤其在壓迫政體之下,政治人物背負的責任,與以社會福祉為優先的知識分子所背負的責任,不會有太大差異。
事實上,同時身為政治家與作家,我始終相信我們的鬥爭行動必須在兩個層面實踐。首先是在語言領域裡進行的智識鬥爭,這個領域自然包含文學。而目標在於重新奪回和平、民主、人權這些日復一日被侵蝕殆盡的概念,讓它們脫離政府與制度性政治設下的虛假界線的限制。一般常言,這些價值是已開發國家與壓迫政權,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區別,然而在西方國家政府,它們卻經常被送上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祭壇,成為犧牲品,情況屢見不鮮。寫作當前,政治危機在世界各地爆發,而這正是關鍵核心。
今天,我們必須設法對付一個扭曲至面目全非的政治論述,必須解決政治訴求遭到以和平穩定之名強制噤聲的處境,以及名為「發展中民主政體」的政權卻不正當操縱選舉、踐踏公民自由的事實。有些人會認為,在動亂困境中訴諸文學的角色不免過於天真。我難以苟同。文學,這個無疑構成了任何文化骨幹的藝術形式,不僅仍居於批判思考的先鋒,其催化出的想法與情思更可以反過來創造政治改革。切莫忘記,只要我們繼續為文字注入活力,文字便不會離棄。
我們必須恢復文學的轉化角色。我們有能力以和平、民主、人權概念,以及其中固有的價值為核心,創造一種新的語言。為了達成目標,只有政治運動是不夠的,必須也在智識和藝術層面投入。亦即,找到一種新的發聲方式,來對抗已發展國家的民粹主義崛起,來迎擊世界各地不斷增加、嚴重程度更勝以往的專制政權。假如我們認真看待使命,就必須先誠實自我檢視。因為民主危機不僅該歸咎於政府政策,社會本身組織力不足、無法制衡政府權力也有責任。
今日許多國家,尤其中東,對性別、宗教、族群認同的箝制令人極為擔憂。為了生存,我們變得退縮沉默。在社會束縛之下,我們開始自我孤立。我們需要的是新的鬥爭形式,使我們得以拆除禁制的高牆。不過新的反抗手段究竟該如何成形,絕不可能僅由我們決定。
創新與創造是一種合作的過程。自古以來,推動公平與正義的奮鬥,其創新變革都源於各種想法、情感與集體行動的交會。換言之,是那些不怕為進步政治而犧牲、勇於接受新觀念的男男女女的作為改變了世界。儘管我們今日面臨嚴峻的挑戰,民主體制在許多國家依然蓬勃發展。然而,那些確保民主正常運作、促進和平、保護人權的制度並非自動產生,而是過去長期的社會抗爭奠定的基礎,歷程充滿了犧牲與協商。如同女權運動一路以來承受無以計數的壓力,從一波轉進到下一波,又如民權運動為了廢除種族歧視政策付出極大的代價,今日專制政權之下的人民,也在為自由、為民主付出高昂的代價。現在端視我們如何以非暴力公民反抗的信念為基礎,在這之上開闢新徑。而所謂非暴力抗爭,在對抗壓迫性的措施時,會毫不猶豫做出犧牲。此外,我們也必須開創一種普世的政治語言,不論在先進國家或專制政權之下,這種語言都能讓人們的心靈產生共鳴。我衷心相信,領導這場終結不公義與不平等的戰鬥,並開創新政治語彙的,會是女性、年輕人及被壓迫者,東西方皆然。
本書輯錄的故事皆以平凡人物為主角,由一位爭取自由平等的政治家,在遭到專制政府不正當監禁後寫就。書中有一些片斷是我的親身經歷,這些過去,在入獄期間從記憶深處重新浮現。多數政治家都相信洋洋灑灑、華麗恢宏的論述能傳達偉大的真理。我不一樣,我始終相信人類故事的力量。雖然身陷囹圄,但我知道有千千萬萬個德米塔斯在外面奮戰。德米塔斯在地底礦坑,在工廠。他在演講廳,在廣場,在參加集會。他在工地,在罷工,在抗爭。他剛被解僱。德米塔斯失業而貧困,他年紀很輕,他是女性,他是小孩。他是土耳其人,他是庫德人,切爾克斯人。他是阿拉維派,是遜尼派。不管他是誰,他鬥志高昂,信念堅不可摧。我的政治參與圍繞的核心,並非崇高理想或抽象符號,而是一般人能夠改變世界的一般人。
塞拉哈汀・德米塔斯
土耳其艾迪尼高安全級別監獄
二○一八年八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