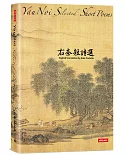推薦序
宇文正為何寫詩?
陳義芝(詩人)
宇文正為何寫詩?我未聽她說起,也尚未見其自序,並不確知。據說早年她就寫詩,但在我與她相識的這二十年間,熟知的是她的小說和散文。
──也許是時光催迫,感慨加深了。
〈那時我是你的如花美眷〉一詩,她以一隻在烘衣機烘烤落單的毛襪,抬頭望著高掛曬衣夾上的另一半,喻示人生境遇:相知與分離。〈風吹落的〉,以荒野小徑的枯葉被腳踩得「玉濺瓦裂」,揭示生命中也有心碎時,也有歡愉時,從前不曾留神而今始感知的空無。
──也許是回憶堆疊而歷歷難忘。
〈回憶是這樣一種生物〉即描寫往事如殘骸,在腦海這座巨大墳場,幻化成美麗珊瑚,不斷地召喚她。另一首〈無題〉,說初秋時光「天不藍了/知了已瘖啞」,鉛筆卻是發燙,渴望向人吐露,每個字都帶了秋意。
──也許生具一顆詩心,為了禮讚生命。
〈有一天〉描寫即使身體衰老了,思緒零亂了,心靈那一隻蝴蝶仍隨風飛舞:「蝴蝶永遠聽懂風的召喚/它翅膀的形狀將是所有形狀的翅膀」。〈請在早晨遇見我〉強調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刻是早晨,生命每一天都有新鮮的早晨,不因年齡改變,但看是否有一雙翅膀翱翔、詠嘆星光滿天。
──也許宇文正要說出對社會發展最深的憂傷。
〈海王星書簡〉說:「有人綁架孩子/有人綁架真理/有人綁架了/人民……夏天綁架春天/黑煙綁架天空」,即使最強大的風也「吹不散可疑的霧霾」,以悲哀的無力感,引發讀者進一步思索,台灣是被什麼政治騙術、什麼刻薄語言所綁架。〈2018晚秋的晨禱〉說:「誰來阻攔那雙手?/不要任其撕開鳳蝶的翅翼/不要任其敲裂細薄的蛋殼/不要任其摜碎古老的瓷瓶/不要任其塗沒那天雨粟鬼夜哭的字/不要任其絞斷那行雲高山流水的琴弦/誰來攔阻?/不要任其吹散那藍田細瘦一縷/煙」,九行連用六個「不要任其……」的複沓句,顯見是對教育政策的黑手伸入文學、文化的控訴。
上述係就宇文正詩作之詩情與言旨而言。若論其詩法,無疑地寄深情於淡筆,所謂「沖和澹蕩,似即似離,在可覺與不可覺之間」。例如,〈節奏不明〉一詩,「春天模仿著冬天/就被冷雨溶化了」,「冬天模仿著秋天/風吹皺了過往」,敘述者頻頻回顧歲月經歷卻不直說悲歡;〈失眠者〉:「不要開開關關那扇門/它總是意義──意義──」,「但也不要掛那串貝殼/最怕海呵海呵把心搖到了遠方」,構思悠遠,不寫形而寫神。
迷離惝怳的表現,當然也是嫻熟中文詩學的她所擅長,〈光之瀑布〉詩中的是與不是的筆觸,究竟是今生的抽痛還是來世的驚夢?〈在江湖〉詩中的情與不情的吞咽,愛要說出口嗎?白鵰的嘆息又是為了什麼?卷二的〈剎那〉,描寫宿世波折的情緣,終將相會,也是一首感人之作:
那時你從若干光年之遠而來
我從大雨中走進人叢走向你
雨水順傘沿一路跌落
我不知道自己認識過你
前世的前世我不知道
你的話語凍結
眼神說著妳來了妳來了妳來了妳來了
詩意連貫,確實可見詩的藝術。下一節,以星光、海濤、燦亮的水光、轟然照面的花開一瞬、一滴冰涼墜地的水珠,與詩中的「你」相指認,從「我不知道」到「我知道」,行氣如虹,餘波蕩漾。
早年新月派名家梁實秋曾說:「沒有情感的不是詩,不富情感的不是好詩,沒有情感的不是人,不富情感的不是詩人。」借這幾句話探察宇文正為何寫詩?終於可知:因為有敏銳的愛恨悲歡,有誠摯地面對萬物與人生的態度。她是「新生」的詩人!
(二○二○年一月六日寫於紅樹林)
推薦序
跳音與異音
楊佳嫻(詩人)
宇文正具多重身分──小說家、散文家、副刊主編、記者(還有貓奴)──無法率爾將她歸入「小說家寫詩」的行列中。一談到「小說家寫詩」,心頭浮現七等生、駱以軍、伊格言、王聰威,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哈金……,這些人小說風格差異很大,圈在一起還是有些粗暴的,即使他們不少詩作確實展現出環繞著情節來展開的傾向。然而,這並非兼具小說家身分的詩人專屬,漢語詩中稱之為「散文詩」的類別裡,如商禽、秀陶等,或者在思維色彩發達的詩人比如羅智成筆下,也曾展示過類似的組織詩的方式。
因此,對於多元創作者,與其說詩怎麼寫會與其「第一創作類別」有關,倒不如說還是和這個文類在這名寫作者生活與精神上占有的位置有關。我以為詩對於宇文正來說,是神思與日常的接縫處,讓普通日常得到翅膀,比如從襪子落單而寫出的〈那時我是你的如花美眷〉,神思則降落人身人心得到形狀,比如〈所以我要撐把傘〉中從雨點打落聯繫到母親在鐵罐裡找釦子。在第一本詩集《我是最纖巧的容器承載今天的雲》裡,宇文正大多數詩作並不朝情節性來發展,而以即景生情、抒情時刻驀然閃現為主,且短製居多,簡潔與靈巧取勝。短,並不保證簡潔與靈巧,這還得依賴節制,必要時躍接、跳開、瞬止,詩意在斷口處自湧自生。
〈飼養〉,只有三行,「向天空釣一片雲/向大海釣一朵浮浪/餵給我饑餓的透明的鷹」,前兩句以「釣」來提亮,不過,在鮮詭意象如家常便飯的台灣現代詩裡並不讓人驚奇,第三句卻突然盪開去,饑餓的透明之鷹是「我」真正的渴望嗎?「透明」與「饑餓」的關係又是什麼?逗引讀者,釣出困惑,比給予一個想當然耳的平庸想像更符合詩的任務。〈風吹落的〉這首詩長一些,便有餘裕做時空或感覺的鋪展:一開頭就把一球薄脆落葉比喻成剛烤好的可頌,取消落葉在文學中長年被賦予的蕭瑟慣性,反而拿來「一腳扣住」、餵養「心碎」之感──因為十七歲時追求絕對、追求破裂;甚至,到了三十歲,也還態度從容,能與落葉「惡戲」,不怕「一路踩出玉濺瓦裂」。但是,那滿地落葉不正是時間早一步給出的預告?挫出灰來,裹住「這一生的/空無」。全詩情緒急轉直下,又不致滿濫,退潮露出的沙灘最惆悵。
最後,想提一提〈懺悔〉。這首詩寫女子到醫院回診乳癌康復情形,照完超音波,等候醫生來說明的空白裡,女子心懸未下,開出許多「戒〇〇」的支票,期望換來命運垂憫,聽醫生吐露安慰的答案。那些「戒」反寫出生活中的「癮」,而「癮」又往往是「活著」的證明,在疾病面前、在已傷損過的身體面前,究竟「癮」和「戒」,哪個才奢侈呢?當醫生宣布無異狀,女子拿出手機,彷彿要重訪這個世界似的「迅速滑過今日大事」,且強烈感受到「真的好多大事」,最重要的,不就是「我健康」、「我還好好的」這件大事嗎!《我是最纖巧的容器承載今天的雲》的柔美中,〈懺悔〉像一段異音,嘈嘈切切,卻使整部詩集更為豐富。
自序
一切都將枯竭的時候
那個早晨走出家門,初夏的陽光輕刺手臂,有一種異樣的觸感。走向社區巴士停靠處,司機先生拉著水管正在洗車,小水窪在我的腳下凝聚成形。我低頭看那一灘水窪,波紋,如外星人盯著一顆新鮮的星球,聆聽細細唆唆的水流。司機抽走水管,起動了引擎,清淺水窪在我眼下迅速乾涸。我快步趕上了車。
車上,拿出手機,在備忘錄裡迅速寫下一首小詩:
我錯過了世界末日
對大廈管理員的招呼不知所措
我就這樣開始了寫詩。寫詩忽然成為我這段時光裡最重要的心智活動。我一樣地每天在同一時間走出家門,走到社區巴士停靠處,不遠的樹叢,曾有人告訴過我,那裡有老鷹的巢穴。我習慣目光搜尋樹叢、天空,尋找老鷹的蹤跡,看到的,多半是雲,每天不一樣的雲。開始寫詩之後,眺望的世界有一種離奇的新鮮感。
但我其實不是第一次寫詩,二十多年前,有段時間我在家帶孩子、寫小說,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短篇小說一篇一篇發表,很快地在遠流小說館出了兩本小說集,也很快地就覺得好像把鬱積著想寫的東西寫完了,搖著身邊的小嬰兒床,也許我的寫作生命就要結束了,而我已離群索居。我留意到有隻螞蟻繞著眼前的杯子打轉,白開水也會招螞蟻?我攤開稿紙,寫了一首短詩〈靜謐〉,捕捉此時此刻,我寧靜無波的生活。
我陸續寫了一些詩,直到重回職場,在工作、家事的夾縫間,一點一點地繼續紡織我的小說,我又結了新歡寫起散文,幾乎忘了寫詩這件事。
這兩年,在忙碌裡,在煩亂裡,在對這個世界、所處的社會感到悲傷的心情裡,而自己創作的慾望像荷爾蒙般恐怖地流失,我想著,也許我的寫作生命就要結束了。
深秋,我到京都賞楓,吸引我目光的,卻是滿樹金黃的銀杏。銀杏這樣美啊。看著銀杏,如見一位久別的知己。從很早以前,我便察覺自己對於美的觸動,多來自靈魂很深很深某個屏幕被揭起的一瞬。我聽二胡、巴烏,總有前世要被召喚出來的幻覺。對於喜歡的人,朦朦朧朧都會有早已識得的困惑,歡喜,也因此讀《紅樓夢》時,寶玉說:「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我懂,我國三時第一次讀就懂。今秋第一次見到整樹燦然的銀杏,又像不是第一次見。
我想起從前陪小孩讀植物百科時曾讀到,日本二次大戰廣島原爆後一段時日,萬物枯竭的死城裡,最先長出新芽的生命,便是銀杏。從地上拾起一葉完整的小扇子,我想到了詩,詩對於我,也許就是這樣的東西吧。在我覺得一切都將枯竭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