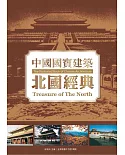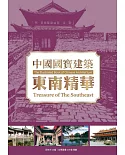序
作為圖像的紫禁城
紫禁城北面的景山,雖說是建造紫禁城的時候,由人工專門為皇宮堆砌出來的一座「靠山」,既不高,也不大,卻是欣賞紫禁城的最佳位置。
人們從景山最高處的萬春亭望下去,大概都會驚訝發現:紫禁城原來是這麼一幅大畫卷啊!
凝視著鋪展於眼底那鮮豔奪目的紫禁城大畫像,相信任何人心中都會湧出特別的感受。
是啊!當皇宮—紫禁城—作為帝制時代統治核心的功能終結之後;當故宮—紫禁城—轉型為博物館公共文化空間之後;當紫禁城—現在的故宮博物院—僅僅成為大眾自由「觀看」的對象之時,紫禁城便只留下了「圖像」的意義。
誰都知道,紫禁城是皇帝建造的,是為皇帝建造的。
按照帝王的意志以及為帝王服務的意志建造的紫禁城,如其他皇宮一樣,一定是當時當地最好、最輝煌的建築。並且,由於紫禁城是最後的皇宮,因至少有十幾個世紀之久可繼承的傳統和可吸取的經驗,所以與以往的皇宮相比,紫禁城得以建造得無比恢弘、無比壯美、無比豔麗,同時也無比規範、無比標準。
紫禁城,這座中國最後的皇宮,是傳統文化中,皇權文化在建築形態上的集中呈現,是帝制文化的立體化、符號化、圖像化,也是帝制文化與古代建築文化的高度統一,甚至是最完美的統一。由此,把已經成為大眾視野中「圖像」的紫禁城,置於圖像學領域中觀看、欣賞、解讀時,紫禁城便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傳統文化中皇權文化、古代建築文化的標本特性,從而為所有觀看者與解讀者,提供欣賞角度和解讀通道的種種可能。
2017年,紫禁城落成590餘年之後,當年走進紫禁城的人數創造了歷史紀錄:1700萬!在全世界,絕對沒有哪一座皇宮遺址、哪一處公共文化空間,在一年之內能夠做到這麼多人進出的成就。
就如所有的帝王一樣,建造紫禁城的明朝永樂皇帝朱棣,希望朱家的帝業承傳萬世。但他絕對想像不到,幾百年之後,他的宮殿已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並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中國皇宮建築群,成了全世界參觀人數最多的遊覽勝地。
當這麼多人湧進昔日的皇家禁地隨意參觀「博物館」的時候,有多少人是在現代理念下,理性地解讀,又或感性地領悟眼前古老的紫禁城?又有多少人在思索、探尋理性解讀與感性領悟之間的碰撞與糾結?包括它的保護者、管理者、傳播者。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紫禁城作為帝制統治核心功能的終結,是民主革命的結果;皇帝的舊宮殿轉型為人民的博物館,是民國時代的文化革新與文化建設的結果。在紫禁城這樣一個空間不曾改動的圖像中,隨著時間的流動,演繹和累積著皇朝與民國、君主與民主、集權與公權的對峙跟交替。
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我所指的理性解讀,是以民主的科學價值觀,還原、認識、評價紫禁城的歷史,即透過紫禁城的顯性圖像,身臨其境地認識紫禁城與帝制時代的體制制度、禮儀規範、皇帝的執政行政、皇家的宮廷生活,及其與歷史發展、國家命運、民眾生活的關係。
我所指的感性領悟,是在感受著紫禁城強烈的視覺衝擊與心靈震撼時,仔細體會紫禁城建築的美不勝收。
我所指的思索、探尋理性解讀與感性領悟之間的關係,是進一步追問政治文化與建築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與古代建築藝術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如我在正文中所論:紫禁城其實是一個「主題先行」的藝術結晶,即中國帝王意志、統治思想、傳統文化的藝術結晶。紫禁城不是在建築美學的指引下完成的,而是在帝制、宗法、禮教理念的指引下完成的,或者說,古老文化、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禮制理念左右了建築審美取向。
這正是中國古代宮廷建築審美的獨特性、根本性所在。
宏大的建築源於深厚的文化,找到了這個文化之本、文化之根,也就能明白面對紫禁城宏大建築群之時,我們為什麼總是為建築理念與藝術審美二者的完美統一而一再震驚。
對紫禁城的理性解讀與感性領悟的最大特徵,是以實體為對象、仲介,以可視的,可走進去的「圖像」為對象、仲介。與平面圖像(印刷品)、影視圖像不同,作為「建築」的圖像是可以走進去的多維圖像。走進紫禁城,即走進紫禁城圖像之中─在「圖像」中行走,在行走中解讀,在行走中領悟。
規模無比宏大、迷宮般的紫禁城,形成多維而連綿鋪排的紫禁城圖像,其相應的、明確又複雜豐富的資訊,足以使活動在圖像中的人,成為圖像中一個移動的「圖像分子」,成為被圖像化的「圖像」,被符號化的「符號」──包括封建時代主宰紫禁城的皇帝本人。
如皇帝的登基、早朝、經筵;皇帝的坐姿、站態、行走路線,統統被紫禁城空間嚴格限定,對臣子與奴僕的限定就更不必說了。可以說,紫禁城圖像是使皇帝成為皇帝、奴才成為奴才、臣民成為臣民的堅固牢籠。
雖然皇宮的功能早已消逝,現在的人們可以大搖大擺地以主人公的姿態,以審視者的身分行走在紫禁城圖像中,但仍然需要警惕紫禁城圖像的隱性綁架,警惕被其圖像化為紫禁城圖像中的一個移動的「新圖像」。
時世雖大變,但曾經瀰漫著帝制文化、皇權文化的那個實體沒有任何改變;曾經散發著固化帝制、固化皇權的強大而奇異的「氣場」力量之空間仍然原樣存在。
況且,那種長時期固定化的力量太強大,行走在這樣的氣場中,此時此刻「這一個」的視覺與感覺,很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被感化、被置換為彼時彼刻「那一個」的視覺與感覺,亦即成為被圖像圖像化的「圖像」,被符號符號化的「符號」。
於是,「這一個」移動的圖像或符號,會隨時隨地不由自主地認同帝制文化、皇權文化,或它們的某一方面。於是,現在的「這一個」便成了原來紫禁城的附屬與俘虜,即皇帝的附屬與俘虜。
這樣的事實其實屢見不鮮。
這是我反覆強調行走在紫禁城「圖像」中的人,必須自覺堅守現代理念理性的理由。不只是成百萬、上千萬的參觀者,也包括紫禁城的保護者、管理者、傳播者,而後者尤其重要。
一方面存在紫禁城圖像對於「我」的綁架與俘虜,即對「我」的負面影響與改造的危險;另一方面,在對紫禁城圖像的解讀與感悟中,「我」對於紫禁城圖像的選擇、置換與再造的空間無限寬廣。
一切基於紫禁城建成之後,特別是紫禁城成為現在人們視野中的圖像之後產生的多義性。
紫禁城既是一個實體,也是一個象徵體,更是一個成為圖像之後能夠激發無限想像的空間。
紫禁城的建造理念,幾百年來的實際使用,尤其是近百年的功能轉換,使得這一形態未改的建築實體,在圖像意義上一直處於「生長」狀態。
由建造理念決定,建造之時就賦予建築本體多重意義,包括明顯的、隱含的、象徵的,在後來的使用與轉換中,更衍生出真實的、虛擬的、視覺的、心理的、潛在的多重圖像。也就是說,紫禁城圖像是一個動態的「成長」過程,這個過程將會隨時間而繼續。
紫禁城建造者的初衷,紫禁城「需要」和「想要」的理解,與後人的理解和可能的解讀,永遠不可能對等。所以,理解和解讀的過程,即創造的過程。不斷「生產」出來的圖像,可以透過「我」的解讀不斷地「再生產」。
參觀紫禁城,把紫禁城作為圖像,首先是視覺行為。紫禁城是看的,不是讀的,但看也是讀,要讓走馬看花、浮光掠影的看,深化為認真的解讀。
「讀」屬於帝王的紫禁城之圖,「讀」屬於自己眼睛、自己心靈的紫禁城之圖。
當參觀者用自己的眼睛與心靈,把紫禁城作為完整或分解的圖像來讀時,事實上已進入重構的創造狀態。此時參觀的對象已不再是建築客體,而成為參觀者的主體創造了。這樣,參觀者就可以進入讀懂原本屬於建造者的帝王之圖,以及屬於自己眼睛與心靈之圖的境界了。
前面說過,紫禁城是皇帝為自己建造的。然而,中國的帝制一去不復返,建造紫禁城的實際目的與使用功能也一樣,誰都不會有再建一座紫禁城的白日夢,紫禁城的原創意圖就此終結。
前面也說過,紫禁城並不是在建築美學指導下設計建構,但基於文化原因,作為「主產品」的意義與作用雖然隨風而逝,作為「附產品」如紫禁城圖像的美學價值、美學意義等反倒可能成為永恆。
本書中,我所關注和集中討論的,就是紫禁城的「圖像」之美。
紫禁城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皇權宗法禮教,亦是古老哲學詩學的形體化、格式化、標準化、圖像化,因而作為東方古代建築的集大成之作,紫禁城建築留給人們的是無與倫比的東方建築之美。
紫禁城之美顯現在其選址、規劃、格局、結構、造型、著色中;顯現在其高低錯落、疏密協調、寬窄相間、空間節奏、光影變幻中;顯現在其整體的統一、完備、端莊,和變化差異下的對應、和諧、均衡、靈動中。
一句話:紫禁城整體的浪漫想像與細節的靈感閃爍,鑲嵌在高遠、博大、深厚、精緻的文化背景上。
紫禁城就這樣凝結為經典圖像。
這樣的經典圖像經得起歷史的篩選,經得起歷史的挑剔,經得起現在與未來的想像,不論是它的整體,還是局部,甚至是那些最細枝末節之處,最不為人們注意的角落。
既古老又變幻的紫禁城圖像屬於它的創造者,屬於近600年來所有見到和想到它的人們,更屬於今後見到和想到它的每個人的眼睛和心靈。
不只是從事城市規劃、建築設計的人們,也不只是從事造型藝術、工藝美術的人們,所有從事藝術創造、藝術設計的人們,都能夠隨時隨地從偉大的紫禁城中汲取藝術創造的靈感。任何一個人,只要有屬於自己的眼睛和心靈,都能從紫禁城圖像中,直觀地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多方面的表達,和東方建築美學的強烈感染力,並受到無限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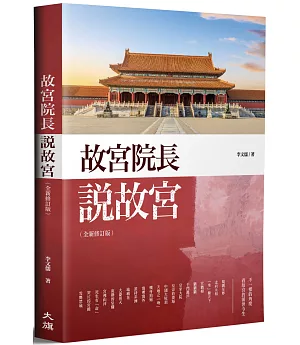




![高雄市左營區鳳山縣舊城(城內空間)考古調查發掘暨展示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共2冊)[盒裝]](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90%2F34%2F0010903494.jpg&width=125&height=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