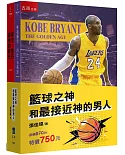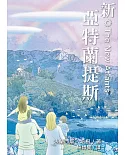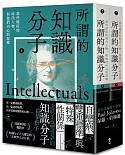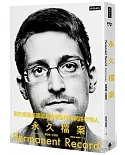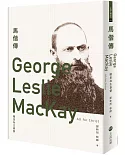推薦序1
珍‧雅各,與你我並肩而行的城市改革者
請給我一個閱讀厚達六百頁傳記的理由。理由無他,因為她是珍‧雅各(Jane Jacobs)啊!
珍‧雅各是何許人也?基於她在城市與經濟思想上的巨大貢獻,在她死後,美國與加拿大都明定了「珍‧雅各日」(Jane Jacobs Day)、幾十個國家的城市定期舉辦「珍散步」(Jane’s Walks)的活動(以徒步或騎腳踏車的方式來探索地方鄰里)、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珍‧雅各獎章(Jane Jacobs
Medal)(以表彰對都市設計有卓越貢獻的人士)、谷歌(Google)在她百年誕辰當天以她做為搜尋引擎頁面的主圖像。
如果你讀過由誠品書店選為百大經典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你會好奇,是怎樣的人生經歷與學術訓練,讓她可以寫出這樣的經典?如果你不認識她,你會好奇這位成長在美國長春藤盟校還拒絕招收女學生的年代,只有高中畢業,卻能夠與撰寫《寂靜的春天》的瑞秋‧卡森以及《女性迷思》的作者(也是婦女運動的推手)貝蒂‧傅瑞丹齊名的偉大女性,究竟是怎樣的一號人物?
珍‧雅各的父親是醫師,母親曾經擔任小學老師與護士。她從小受到父親很深遠的影響,喜歡查閱百科全書。父親告訴她,不要輕易許下自己無法實現的諾言,尤其是「我這一輩子(the rest of my
life)都……」這種要賭上一生的。小學時,有次老師要同學們承諾從今以後每天都要刷牙,珍‧雅各就不舉手,還說服同學不要舉手,結果被老師趕出教室。她痛恨學校教育,高中畢業就急著去工作,想要寫作或當記者。父親認為應該先學習一技之長再上班,於是她便去學了速記(那年代還沒有錄音機)。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某小報婦女版編輯的無薪助理。
十八歲時,珍‧雅各到紐約尋找工作機會,住在姊姊家(位於布魯克林皇冠高地)。有天,她在曼哈頓搭公車,受到站名克里斯多福街(Christopher
Street)吸引,下了車,自此愛上格林威治村。這裡有吸引人的建築、蜿蜒的馬路,有市場、書店、咖啡館、劇院、修鞋店,是很有創造力的鄰里。她覺得這才是適合定居的場所。後來她憑著速記能力在一家公司擔任秘書,便搬到格林威治村居住。那幾年她經常探索、觀察、描繪紐約的鄰里。《時尚》雜誌還刊載過一些她的文章,當時一篇文章的稿費相當於她一個月的薪水。她從觀察人孔蓋(上面的文字)進而研究其下(紐約地下世界)管線的運作。
當時哥倫比亞大學還沒有招收女生,想要回到學校進修的珍‧雅各只能選讀推廣課程。她修了地質學、化學、動物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成績很好,然而她並沒有取得大學文憑。她二十五歲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書:《制憲遺緒》(Constitutional chaff: Rejected sugges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後來,她到《鋼鐵紀元》(The Iron
Age)雜誌工作,撰寫文章。有鑑於自己的家鄉史卡蘭頓的礦產關門,二萬多人失業,數千家庭外移尋找其他工作機會,家鄉有可能成為鬼城,她撰文討論這個問題,引來各方關注,政府也因此將(服飾、背包)工廠設置在此,增加許多工作機會。但即便珍‧雅各如此有能力,雜誌社老闆卻認為她是麻煩製造者。在性別歧視嚴重的當時,她曾因為女性薪水只有男人的一半,組工會爭取工人的權益。一九四三年,珍‧雅各轉換跑道,進入政府單位(戰時情報局)工作,這單位成立的目的是鼓勵愛國心、說服美國人參與二次大戰。此辦公室於一九四五年收攤後,她轉往另一政府部門發行的《亞美利堅》(Amerika)雜誌工作,宣揚美國的民主來對抗共產獨裁,寫的文章被翻譯成俄文,以對俄宣傳。
二十八歲時,她與建築師鮑伯‧雅各結婚,在格林威治村買房。這地方有各種族、不同背景的居民。有了兩個兒子後,母親的角色又讓珍‧雅各有了不同的觀看城市的觀點。這座城市會是一個有活力而安全的地方嗎?一九五二年,她轉到《建築論壇》(The Architectural
Forum)雜誌任職,開始撰寫有關建築、都市計畫的文章。戰後,大量少數族裔搬遷進都市中心來找工作機會,居住在擁擠、條件很差的環境裡。政府開始大規模都市更新,清除舊房,興建高級華廈、劇院、政府辦公大樓,也為貧窮者興建國民住宅(現代主義風格的高樓)。當時《建築論壇》雜誌非常關心以下諸問題:什麼是都市更新與重建美國城市的好方法?人們應該住在高層還是低層的建物?都市空間要如何安排,讓小汽車得以通行?商業與住宅空間的關係為何?珍‧雅各後來到費城、波士頓參訪,看到了舊社區的活絡與多樣,以及新高層國宅的單調與危險。當時超大街廓的國宅,缺少轉角的報攤與雜貨店(這些商店可以聯絡社區感情),高樓層則阻礙了家長關照遊戲的兒童,犯罪的危險讓人更不敢出門。
一九五六年,《建築論壇》雜誌編輯臨時無法到哈佛大學演講,請她代打,她勉強答應,結果演講空前成功。她批評都市規劃師偏愛單調無聊的超大街廓高層國宅,卻不喜歡沿街的低矮建築,認為如果沒有糖果店、小飯館、洗衣店這些居民可以碰面的地點,居民就更難有機會相遇。都市計畫將傳統物理社區剷除的同時,也會將社會社區一併剷除。當時《財星》雜誌的編輯懷特(William F.
Whyte)就坐在台下,深受她原創的想法吸引,便邀請她為《財星》寫一篇專文。然而雜誌社的其他工作人員卻抱持保留態度,認為一個騎腳踏車上班的女人,沒事的時候在鄰里搞社會運動,從沒寫過一篇偉大的文章,恐怕無法擔當此大任。一番波折後,她寫就了名為〈市區是為人民而存在〉(Downtown is for
people)的文章,強調都市之所以有趣就在於豐富的街道生活。她宣稱都市規劃師所推動的開闊、公園式的、不擁擠的、對稱、有秩序的空間計畫,其實就跟墓園一樣。舊都市中心也許有些髒、有些醜,但是大規模的空間計畫會摧毀街道。洛克菲勒基金會希望她可以將此文擴大成為一本書,給她經費,可以暫時不用工作來寫書,而藍燈書屋(Random House)的著名編輯也承諾幫她出書。
正當珍‧雅各寫書時,摩西斯(Robert Moses)規劃了一條四線道快速道路,將會穿過格林威治村,毀了華盛頓廣場。此廣場是社區各族群非常重要的活動地點。珍‧雅各於是組織當地居民,起來反對此道路計畫。
摩西斯擁有權力且傲慢,持續開闢快速道路、橋樑、公園,興建聯合國總部,讓汽車族可以住在郊區,到市中心上班。任何擋在他計畫前面的,都將遭他摧毀。他認為讓不斷增加的汽車的快速移動,值得付出摧毀舊有社區當作代價。摩西斯認為要解決汽車的問題就要拓寬馬路,但珍‧雅各認為道路愈寬汽車就愈多,雙方各持己見,而面對珍‧雅各率領的抗議人士,摩西斯甚至在一次在會議上大吼:「其實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反對這個計畫,除了一堆媽媽們!」快速道路的興建案被成功擋下來了,珍‧雅各也成為著名的社區領導人與公眾人物。後來,她又成功阻擋了哈德遜街削減人行道寬度以拓寬車道的計畫(她就住在那條街上)。
一九六八年,珍‧雅各因參與反越戰示威而入獄,之後為避免兒子遭徵兵到越南打仗,舉家搬到加拿大多倫多。在那裡,她又遇到興建快速道路計畫,再度聯合市民將其擋下。在加拿大,她一方面持續參與社區運動,一方面寫作不輟,出版了好幾本重要書籍。
如果摩西斯是從鳥瞰的角度觀看都市,把都市當作一張平面圖在其上任意揮灑;那麼珍‧雅各就是站在地面,從人群之中體驗都市。她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提出「街道芭蕾」與「街道之眼」的概念,經紐曼(Oscar Newman)的《防禦空間》(Defensible Space, 1973)發揚光大,隨即開啟了「以環境設計防治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這門學科領域。她主張土地混合使用、高密度、新舊建築並存,幾乎與當時的主流都市計畫理論背道而馳。多數讀者稱讚她的想法原創、深具啟發、挑戰性。當然也有批評者認為,她只是想要複製格林威治村、太過羅曼蒂克、缺少對於權力結構的分析。她在另一本著作《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城市,是經濟發展的溫床》則大膽提出城市先於農村的論點,她所強調的創新,在知識經濟盛行的當代,仍有相當啟發。
珍‧雅各著作的中文出版,臺灣目前共有三本,包括《經濟就是這麼自然:聰明婆婆的經濟學講義》(先覺,二○○一)、《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聯經,二○○七),以及《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早安財經,二○一六)。事實上,早在「六一二大限」1之前的年代,建築學者漢寶德在一九七三年編輯的《環境心理學:建築之行為因素》(境與象出版),就選了兩篇珍‧雅各的文章,分別是〈人行道的利用:安全〉與〈人行道的效用:吸收兒童〉。四年級世代的建築系學生都深受其影響。
珍‧雅各傳奇的一生,值得人們細細品味。有人將之寫成歌劇、拍了紀錄片、繪寫兒童繪本、出版有聲書,更不用說還有很多人爭相為她作傳。
這本《凝視珍‧雅各》,有何特殊之處?珍‧雅各生前拒絕過很多記者為她出版傳記,但《凝視珍‧雅各》獲得雅各家族授權,作者得以訪問她的家人,獲得許多私密資料,還調閱了美國聯邦調查局二百多頁的相關檔案,得以近距離描繪這位奇特人物的家族史、在家中餐廳的談話,以及周遭人士對她的感受與評價。
想親炙這位思想家與社會運動者的精彩人生,這本書值得閱讀與珍藏。
畢恆達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推薦序2(節錄)
街道之眼,城市之心:洞察庶民經濟的小市民傳奇
蛤!「珍‧雅各傳」?今年暑假聯經編輯黃淑真來信,要我幫即將出版中譯本的珍‧雅各傳記《凝視珍‧雅各》(Eyes on the Street: The Life of Jane
Jacobs)寫推薦序。當時我正在徒步環島,走在新竹、苗栗之間的西濱快速道路上。剛剛下了場雷陣雨,全身溼答答的,晚上準備落腳在白沙屯拱天宮的香客大樓。不知道是被太陽曬昏了頭,還是淋雨腦袋進了水,我納悶著,珍‧雅各既不是偉人,又稱不上名流,而且還為了幫兒子躲避兵役,舉家從美國「落跑」到加拿大,臺灣讀者會有興趣了解雅各媽媽的生平種種嗎?
珍‧雅各,您哪位?
記得二○○六年四月底珍‧雅各過世時,北美各大媒體皆以顯著篇幅報導這位街道守護者的死訊。曾於紐約居住過的文化評論者胡晴舫也在《中國時報》寫了一篇〈都市之母〉的悼念文。我猜想,除了少數景觀建築與都市計畫的學者專家外,而且還得是人文掛的,在臺灣應該沒有太多人知道珍‧雅各是哪一號人物。畢竟她的著作一直以來都沒有繁體中文譯本,不會廣為人知。剛好我在二○○五年七月底完成珍‧雅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一書的經典譯注計畫。於是我趕緊聯絡出版社,建議他們把握時機推出中譯本。但礙於作業順序,《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還是遲至二○七年暑假才正式出版,距離原著初版的一九六一年,整整晚了四十六年。
儘管《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書中談論的內容盡是一九五○年代美國都市的更新課題,但是經典就是經典,不會因為時空距離而遮掩其智慧光芒。慧眼獨具的誠品,甚至主動簽下《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的獨家首發,上市不到兩個禮拜就銷售一空。截至二○一七年止,《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繁體中譯本前前後後刷了九刷,長銷萬本。加上這十年間,臺灣先後發生苗栗大埔區段徵收強拆案、師大夜市住商混合衝突,以及臺北士林文林苑都更案等相關課題的喧騰延燒,也順勢帶起一股小小的珍‧雅各風潮。
二○一七年華人新世代(CNEX)紀實影像主題紀錄片影展,推出《紐約大國民:珍‧雅各》(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的紀錄片,片中描述珍‧雅各如何與社區居民合力對抗紐約市政府的下城區拆遷計畫及穿城而過的快速道路興建計畫。除了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外,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還為此片舉辦了一系列的大學校園巡迴講座,希望臺灣年輕世代了解珍‧雅各極力捍衛的街道生活與熱情擁抱的活力城市。《紐約大國民:珍‧雅各》首映時,以深度報導著稱的網路媒體《報導者》請我撰寫一篇觀影評論,但礙於當時我正為住家大樓法定空地遭一樓住戶侵佔等社區問題,主動請纓擔任管委會主委,並為訴訟官司(一案原告,三案被告)及各項興利除弊的大小事務,忙得焦頭爛額,難以抽身,只好婉拒邀稿。
又過了兩年,聯經竟然準備翻譯出版二○一六年才問世的《凝視珍‧雅各》,而且要同步改版《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其間的轉折,不可謂不大。我很樂見在臺灣有更多人認識及了解珍‧雅各的生平事蹟及其城市洞見,也期待有更多讀者因此將珍‧雅各守護街道生活與關注城市經濟的庶民主張,以市民參與的具體行動和縝密周延的專業規劃,加以發揚光大。
究竟珍‧雅各有哪些事蹟值得傳頌作傳?又有哪些城市洞見歷久彌新?這恐怕不是三言兩語可說得清的,我也不想在此「爆雷」或「破哏」,就留待讀者自己從書中細細體會。然而,其中有幾件不足為奇的小事,包括對她的一些誤解,值得一提。或許這正是珍‧雅各魅力之所在,讓她稱不上傳奇的一生,及其屢被主流學者嗤之以鼻卻無力反擊的精彩著作,特別是《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得以名留青史。
微隱於市、現身發聲的理念之人
首先,珍‧雅各並非刻板印象所認知的家庭主婦或社區婦女,而是用具體行動和著書立論來體現日常經驗與生活常識的小市民∕大國民典範。而且,這兩件事─守護社區的具體行動和將其理念轉化為著作論述─互為表裡、相輔相成。表面上看來,珍‧雅各是一個僅有高中文憑,速記員出身的刊物編輯及自由撰稿人。但實際上她從學生時代起就投稿校刊,高中畢業後擔任地方報社實習記者,以及來到紐約闖蕩,先後歷練過各種雜誌的編輯工作,包括貿易雜誌《鋼鐵紀元》(Iron
Age)、政府文宣雜誌《亞美利堅》(Amerika)、專業雜誌《建築論壇》(The Architectural Forum)等等,而且一路從祕書、編輯助理、編輯做到副主編,也為《時尚》(Vogue)、《財星》(Fortune)等知名雜誌撰寫文章,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關於都市更新課題的演說,後來甚至得到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寫作獎助,以兩年的時間專職撰寫《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將她長期穿梭於大街小巷觀察城市的心得,整理成一系列關於街道、公園、社區、市區、更新的都市論述。這些瑣碎的事蹟稱不上醜小鴨變成美天鵝的勵志故事,也不是《紐約大國民珍‧雅各》紀錄片中剪輯出來的開發∕保存、權勢∕庶民,或是族裔、階級、性別等二元對立的社會鬥爭,卻是一個關心社區與熱愛城市的知識分子,或是社會學家柯塞(Lewis
A. Coser)所稱的「理念人」(men of ideas),終其一生生活實踐的點點滴滴。
珍‧雅各缺乏景觀建築、都市計畫,乃至於經濟學、社會學等學術訓練是不爭的事實,但這樣的學術欠缺反而造就出她的專業優勢,而非罩門。因為她切身、直觀地以城市居民的使用者角度,而非景觀建築或規劃者的生產者觀點,來理解與看待都市更新的種種課題,包括街道生活的基本特性、都市經濟的原理原則、貧民窟的新舊迷思,以及更新重建的戰術運用等等,都為當時作為學術與專業主流的藍圖式規劃及夷平式都市更新,拉扯出有待修補的理論破綻及經驗缺口。換言之,珍‧雅各是用由下而上的庶民語言,而且是許多高高在上的專業規劃者疏於關注的生活常識,來理解與闡述深刻、複雜的城市運作。有別於畫地自限的民粹反動,這種源自實踐檢驗的生活智慧,以及由此歸納而來的城市洞見,高舉的正是挑戰學術權威的「庶民觀點」。
珍‧雅各伶牙俐齒、咄咄逼人的論述能力,配上她那有點兒怪異的容貌─乾如稻草般的俐落髮型、突出於厚框眼鏡的尖鼻子、深度近視也遮掩不住的銳利眼神,還有看不出年代與造型的寬鬆服裝等等(是不是只差一頂高帽子,就像極了童話故事裡的老巫婆?)─讓許多不曾受過民眾質疑與挑戰的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特別是建築規劃界的男性權威,招架不住。總之,她絕非才貌出眾的美女,甚至連親切順眼也稱不上,但卻是那種你在人群中能夠迅速辨識,而且留下印象深刻的人。這群在產官學界闖蕩多年的「大國民肯恩」(Citizen
Kane)1,只好將這個聰明、難搞的「小市民珍」(citizen Jane),妖魔化為路上大嬸或市場歐巴桑的「婦人之見」。其實,像珍‧雅各這種愛管閒事,但不僅止於私下議論,而是敢「踹共」的婆婆媽媽,甚至有本事著書立論,將「婦人之見」提升為具有理論洞見的「庶民經濟」,才是現代社會最「慫夠有力」的基進力量。
吳鄭重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序
想想你會想聊聊哪些關於珍‧雅各的事,而於此同時,你很難讓自己不去好奇她究竟會快人快嘴地回你什麼話。
你可能不會想和珍辯論,因為她肯定會贏。在口頭爭論一事上,她可是所向披靡。在尚未寫就《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三十多歲時,她為一本重要雜誌寫了篇火藥味濃重的文章,但雜誌發行人對此報導提出了質疑。珍跟發行人見面時,只用一項說明來為她的報導辯護,她說這是:「事實和第一手觀察構成的長篇文章。」後來,她問一個投合的同事為何剛才不多為她挺身而出說點什麼?對方回答:「我沒必要出場呀,因為那個可憐人(發行人)已經踢到了塊鐵板。」
你可以說珍‧雅各這人不會欣然容忍他人的愚蠢。這是事實,但你不會想指出這一點,因為這是糟透了的陳腔濫調,你不會想在珍的面前重彈老調。在她面前,你會想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現,不過如果你的論點有缺陷、缺少中肯的例子、洞見有失清晰,那麼你很可能不會想自暴其短。因為如果你暴露這些缺失,不管是在她位於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家裡的廚房餐桌旁,或是之後在多倫多、公開的聚會,又或是在一群學者之間,她都會毫無顧忌地把矛頭指向你。羅傑‧塞勒(Roger Sale)在一九七○年的《哈德遜評論》(The Hudson Review)中如此寫到她:「是有辦法和珍‧雅各爭論,但這些辦法不若你以為的那麼多。因為依照她的主張,她幾乎總是有道理,而真正的問題要到你開始思考她遺漏的部分時才會浮現。」
珍(所有人,包括她的三個小孩都這麼叫她)寫了七本書、拯救了鄰居、阻止了快速道路的興建、曾經被逮捕兩次、沉浸在大批仰慕者的極度崇拜中,還在廚房餐桌旁進行過無數次的討論和辯論,而她總是講贏。至少在晚年(儘管有理由認為早在她小學時期就如此了),她總是主導談話。她傾聽、她回應、她挑戰。她思考自己想說什麼,然後說出來;沒裹上任何糖衣,也不刻意圓滑,就這麼直白地脫口而出。你可以說她冷酷,也可以說她誠實。曾有人這麼說過她:「她完全不是那種親愛、和藹的奶奶。」
珍是個再正常不過的人,在所有大方面都健康快樂。她有愛她的朋友,也善待他們,態度親切、充滿愛。她這人可以很有玩心,甚至傻呼呼的;至少她曾把臉擠壓成好笑的形狀讓別人拍過一次照。當你和她打招呼,她會用雙臂緊緊環抱你。對她來說,書寫幾乎是世界上頭等大事,書寫令她得以幫助自己的孩子、朋友和鄰居。她總是直言不諱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不曉得如何拐彎抹角。有一次,和她合作的一位雜誌編輯,在她向《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吐露自己的想法時對她說:「我認為妳真的不該這樣大談自己的意見」
現在,在看過上述諸多描述後,我們有理由提問:她這人總是這樣嗎?或者那是隨時間發展出的一種個人特質?因為第一本書出名之後才變成這樣?也或許是在她遷居多倫多,成為該市一位備受尊敬的代表人物之後才如此?這些是不是一名卓越人士有時經年累月地養成,融入成為自己一部分「個性」的造作?還是她向來如此?
珍‧雅各寫了七本書,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下稱《誕生與衰亡》),這本書在一九六一年初版後不斷再版,並且被奉為重新形塑人們對城市的看法和附加期許的巨作,影響卓著更勝其他。談到《誕生與衰亡》,讀者們有時會表現出與這本書相遇對他們來說幾乎像是一次宗教經驗。讀這本書之前,他們還是原來的自己,讀過之後竟幡然改變。此後他們的視野截然不同。他們的芝加哥、紐約或波士頓被重新形塑,當中重要與不眾要的事物達到嶄新的平衡。今日,對許多人而言,珍‧雅各是令人狂熱崇拜的偶像,以《誕生與衰亡》作為某種信條,就像毛主席的小紅書(指《毛語錄》)在其年代的地位,或是《聖經》、美國憲法,是一座「真理」的寶庫。我是在一九七○年代初讀到《誕生與衰亡》這本書的,是在早期透過本書受雅各吸引的那批人。這本書堅決主張每一座都市都可能達致絕佳樣貌的大無畏;它對都市感性的肯定,就像我成長時期在紐約及之後在巴黎和舊金山領會到的那些,帶來莫大的啟發。
不過這麼些年過後,你正在讀的這本書的主題並非城市、都市規劃或都市設計。這並不是透過從城市前線收集關於活化(rejuvenation)和再生(revitalization)之類振奮人心的故事的一本書,它並不手把手拉著讀者,帶領大夥走過巴爾的摩(Baltimore)復甦的站北區(Station
North)或是布魯克林仕紳化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漫步過改建為住宅的舊倉庫和辦公大樓,或重新活絡起來的商業區;或是為紐約或其他都市的犯罪減少和安定而欣喜;或是欣賞打亂都市的城市公路被拆除後的波士頓和舊金山的景象。從適切觀點來看,上述的每一項都可能是珍‧雅各應該負責解決的問題。你的確會在這本書中讀到這樣的美好故事,但它們並非本書主題。
確切地說,這本書是促使這類美好故事成為可能的這位傑出女性的傳記。這本書回頭凝望某段時期;當時,為數不多的都市生活正面報導被掩埋在介紹新郊區發展、以苜蓿葉形交叉口連結的新州際公路、新一波公司往郊區辦公園區大遷移的成堆新聞稿底下。本書凝望舊的城市鄰里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是高樓住宅計畫;當貧民窟就是貧民窟,而所有的人都知道,或自以為了解它們是什麼;人們只要有意願住在城市就會被認為有些奇怪的時期。凝視珍‧雅各邁步環顧她的周遭,並促使其他人透過嶄新角度觀看這一切的時期。
在珍的後半生,以及自從她在二○○六年以八十九歲之齡辭世以來,她持續激起人們的熱忱,其強度教人刮目相看。人們稱她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城市思想家」,排名超越了美國景觀設計大師奧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美國城市建築學家孟福(Lewis Mumford)、紐約建築大師摩西斯(Robert Moses)以及美國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人們將她譽為「常理的天才」(common sense)、「美國城市教母」、「城市梭羅」(Thoreau)以及「經濟界的芮秋‧卡森」(Rachel Carson);評論她的著作之一《生存系統》(Systems of
Survival)為:「具有像伍迪‧艾倫電影一般毒辣的敏銳觀察。」有一部伍迪‧艾倫的電影甚至反過來被形容成:「傳達出珍‧雅各和她的抱怨關於現代建築和戰後都市生活的疏離縮影。」人們將《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和「馬丁‧路德四個世紀前釘在威登堡城堡教堂的文件」1相提並論。曾有個自稱珍‧雅各粉絲的男人造訪她在紐約和多倫多的住處,並表示對他這個「城市迷」而言,「這就像是到密西西比州的優雅園(Graceland)和圖珀洛(Tupelo)2旅行一樣」。瑪莉安娜‧莫利列維奇(Mariana
Mogilevich)在一篇標題為〈聖珍的社群〉(The Society of Saint Jane)的專文中寫道,珍過世之後:「不出所料,人們毫不遲疑地立刻開始神聖化她。」在「占領華爾街」運動期間,經濟學家珊蒂‧池田(Sandy Ikeda)問道:「這時候珍‧雅各會怎麼做?」而當一九六○年代的反文化聖經《全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雜誌創辦人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被問到如果可以成為其他人,他想變成誰時,他選了珍‧雅各,一個「十五世紀威尼斯的首席女性。棒極了」。
個別而言,上述這些例證可能激起人們高度的好奇和興趣,但是總的來看,它們令人心生疑惑:你可以景仰珍‧雅各─像我這樣,然而卻逐漸厭倦或懷疑人們對她的吹捧有加;此般誇大的言論並不會增進我們對任何活生生人物的了解。目前,我們不需要判定珍‧雅各是否真的確實與她「明眼女士」(Mrs.
Insight)的美譽相稱,或者是否真的足以躋身「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都會思想家」之列,或是僅僅達到較低的凡人水平而已。的確,一如我們所知,有許多修正主義者對珍‧雅各留給世人的遺產提出多面向的質疑。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這類對她的讚揚察覺一項鐵的事實:幾千位建築師、都市社運分子、都市規劃師、經濟學家、無數的都市居民,以及提倡獨立思考的人,就是以這種非凡的角度看待珍‧雅各;和冷靜、充滿敬意的讚美相較,她所說的事或她訴說一件事的方式之中,有某種更能引發人們熱忱和敬畏的存在;許多人透過閱讀她的著作或聽她的公開演說,成為她的追隨者或助手。
這個現象令人不解的地方在於:珍‧雅各並沒有那些令人引以為傲、足以提高公眾聲望的表面優勢。比如說,她不是男的;她不富有;她直到將近五十歲以前,都沒有獲致任何重大的公眾肯定;她從來都不是美女,而她的不美甚至也沒有讓人留下印象;在漫長的公眾人物生涯中,她一直是個臉圓圓大大、穿著不合身背心裙裝和運動鞋的年長女士。她有時近乎短促而尖聲的音色,絲毫沒有令人舒心欲睡的莊嚴感。為了介紹她自己的著作或極力呼籲的社會議題,她不會全然迴避電視訪問或公開曝光,但通常也不主動爭取。她的第一本著作大獲成功後,在必須要做個名人還是寫書的抉擇上,她選擇了後者。於是,這一切都令人納悶:怎麼會有這麼多人為她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