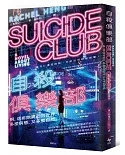導讀
作品解析:《一百個影子》的五個註釋
去年秋天閱讀完《世界文學》(二○○九年秋季號)刊載的黃貞殷的首部長篇小說《一百個影子》之後,深深感覺到我必須為這部小說寫點什麼才行,或許是認為必須守護這部小說,不至於被誤讀,可能的話,要讓更多人能閱讀到這部小說,因此我義務感發作地請求出版社一定要讓我撰文推薦,因此寫下這一篇文章。雖然在黃貞殷的小說中,許多很罕見的事情,卻能夠發生得很自然、不意外、不唐突,但對於以閱讀、撰文維生的作者來說,到達這種情況的日常生活,已經是一種事件,作者的第一部小說集《七點三十分、大象列車》(二○○八年)也是一部好作品(若能依據發表順序閱讀她的作品,就能夠發現她的小說內容,越來越豐富)、爾後的〈夜行〉(《changbi》二○○八年春季號),或是〈Danny
DeVito〉(《子音與母音》二○○八年冬季號)一類的作品,他的小說越來越漸入佳境,而《一百個影子》這部作品是讓我給予小說家黃貞殷最高評價的重要關鍵。
這部小說的內容整理如下,都市中有一棟四十年來人潮來往的電子商城,在這座商城即將面臨拆遷的情況下,一一介紹在這個地方生活的人的情況。同時小說內文也以社會體制的無情與登場人物的善良作出強烈的對比,同時也詢問著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真的是值得居住的世界嗎?這一類的問題。如果用兩句話來說明這部小說,就是這可以視為恩喬與伍宰的愛情故事,不過這一段愛情,是基於善良人們的善良所孕育的愛情,而可以守護善良的希望,就是愛,所以這本小說是倫理之愛的敘事手法。若要用一句話說明這部小說的話,就是深思熟慮的象徵與無法遺忘的文句所組成的長詩。若要用一個詞彙形容這部小說的話,就是謝謝,這本小說能出版,我只想到謝謝一詞,然而短短的文字可以道出一切嗎?我嘗試著用五個觀點去解析這一部小說。
一、現實——顯而易見的解體
「最終,甲棟就這樣被推平,剩下的地方以飛快的速度變成一座公園。」
首先是現實,我們所謂的「現實」是由空間與人們組成,而哪裡都有人居住,這是完全不需證明的事實。只是這其實相當愚蠢,因為只要證明過一次,就再也不會進行再次思考了嗎?人們在話語與文字之中,完整顯示出對於「現實」這一詞彙的使用方式,是毫無邏輯思考可言,在用這一詞彙的那一瞬間,就是冷漠,人們為了不與現實打照面,所以常用「現實」這個詞。在文學工作中,我們對於現實的思索容易被妨礙、對於不證自明帶有錯誤的想法,因而出現種種瓦解的情況。這樣的空間,有這樣的人們居住著的這個想法,是很簡單的能夠感受到現實,而我的空間與我的生活,與所謂的現實並不是分開的,是真切的事實;此為這部作品是部好小說的第一原因。黃作家將我們普遍誤認為是簡單空間的例外之處,以及讓我們熟悉的信任,轉為陌生的方式,迴避使用現實一類的話語,而是用真實的事實做突破口。
是什麼樣的空間?「我在市中心的電子商場工作,甲棟、乙棟、丙棟、丁棟、戊棟的商場建物,原本是分開的五棟建物,經歷四十幾年的歲月,到處都有翻修改建,連來連去的就變成如今這樣的相連建築構造」,此處原本只需要以「五棟建物」說明即可,不需要這樣一一唱名,但為了尊重過往四十多年歲月中,以不同方式生存的各棟商家,這樣做是對的選擇,而電子商城確實也是依這樣的順序進行拆遷。再者,對於決議拆遷電子商城的人來說,缺乏的就是對過往時間的尊重,或者可以說政策負責人有拆遷電子商城,或可以闢建公園的數十個理由,但不論理由為何,對於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生命共同體,或是一個文明長久累積的歲月來說,都是一種不被重視、被隨意丟棄棄置,就這一點來說,確實無法擁有正當性。
如果這位老爺爺去世的話,那這些燈泡又該怎麼辦呢?沒有他的話,有誰會站在這裡呢?長久以來累積的那些珍貴的物件,全部都丟棄嗎?每去一趟Omusa,我都會被這樣的想法困擾著,一些來到修理店的客人,也會提出類似的問題,談著修理店跟呂姓大叔,每當這個時候我都會思索這間修理店的來歷。
為了抗拒這個無力感,所以作者選擇一一介紹在這個空間生活的人的生命「歷程」,以沉默的方式傳遞禮節,若要計較的話,就是話者「恩喬」與她的戀人「伍宰」身為這部小說主角的這件事情,因為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比其他人更有價值,所以這本小說應該沒有主角,或者該說是全部的人都是主角。不過這部小說(包含恩喬工作的呂姓大叔的修理店)還特別花心思描繪燈具店家「Omusa」,在作者富有情感的描述下,彷彿讓人想起一九七〇年代以來,那些歲月累積而成的空間的主人、或是生命共同體,讓人不禁肅然起敬,而這與那些深信拆掉過去就是發展進步的人們,以及這個有著完全不同基準、不同速度支配的地方,讓這些商店因為拆遷而消失殆盡,「長久以來累積的那些珍貴的物件,全部都丟棄」的時代,這就是我們今日稱為現實的複雜真相。
二、幻想——不幸的孤獨
「……我的影子也這樣具有威脅嗎?」
這追根究底就是幻想,所以將其設定為影子分離後,就像獨立的氣體一般,昂首闊步。影子分離現象,在這部小說中登場時,幾乎都是與所有人物混合、或是與事件混合,可以說是這部小說的核心動機,若真要問是何種的話,我認為這部小說是以面臨拆遷的電子商城為背景,恩喬與伍宰為共同觀察者,有時會混合一些影子,或是混合當今的人們(也就是目前韓國社會中的弱勢少數),看到他們不幸的遭遇,也就是這部小說是為這些人所寫。作者尊重既有批評的論述,而採用「幻想」一詞,但其實這真的難以找到一個適當的詞彙,即使能夠突破複雜文學理論的問題,若這部小說中,是認為影子分離的現象,在現實暴力之前,在主角們的韌性到達某一界線時,而發生事情的話,採用帶有「非現實」幻想之意的「幻想」一詞,就是明白地指稱這個社會體制,多會讓人覺得不道德,這還不如說是比較接近「極的現象」。
我們必須從這樣的脈絡,去理解黃貞殷(不僅是這本小說,還有她過往的作品)動員幻想的領悟,如同剛剛所述,書中人物承受的不幸,是在現實當中,無法以現實的手段對面的種類時,小說家該如何將那極度的不幸小說文字化呢?這不是美學(技巧)問題,而是倫理道德(姿態)的問題,若稍稍改變一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說明「說故事的人與小說家」中說的話時,今日我們從各大媒體媒介所聽到的許多不幸,而那些不幸多半都經過加工、採用較為老套的表現方式,使得這些「不幸」失去主體性而降為一般的流量資訊,這世界不幸很多,而我們早已因習慣而遲鈍。也就是前文所提及,小說家必須與現實這個概念式的不需自證奮戰,同樣的,小說家還必須與「不幸平凡化」對抗,守護「不幸的特性」,此時,幻想就變成一個方便的裝置。就像卡夫卡(Franz
Kafka)於《蛻變》一作品中,將一位銀行員變成一隻甲蟲,但他依然記得自己的不幸一樣,黃貞殷在〈帽子〉中,將父親變成帽子,而父親的不幸並沒有因此消失,反而是保留下來,這不是什麼朝氣蓬勃的現實偏離,而是一位小說家對每一個獨一無二的不幸的禮遇。
因此,電子商場的不幸也是一樣,托作者福,讓電子商城這一案例,不會成為無數拆遷「們」的集合體之一,作者不是選擇用直接傳遞心情的方式,而是選擇採用影子,也就是透過「幻想對應物(變更艾略特「客觀對應物(Objective
Correlative)」來間接描繪,不論是要負責一家九口生計,最終放棄希望的伍宰的父親的死亡、還是為家人奉獻卻漸漸被家人冷落,失去生活意義(或說差點失去)的呂姓大叔與他的工廠朋友、或十二歲時因為悲劇的產業災害失去父親的劉坤先生、或因為店面遭拆遷而銷聲匿跡的Omusa老爺爺。不過雖說是間接化,卻也比採用直接的敘事手法,這更能強化這些不幸的特性,這就是幻想逆轉的威力。然而,作者的幻想,對於他人的不幸,是不是用過於老套的表現、或是誇張過頭的美麗詞彙,會不會產生非倫理性的潔癖呢?
三、語言——一般化的暴力
「恩喬小姐知道貧民窟是什麼意思嗎?」
相信各位不時也會觀察到這一類神奇的事實對吧?也就是說,各位在慣用語之中,聽到的、用到的明確的用語,以及快速說話時,那些突然插入卻不會引起爭端的話語,然而一旦那些用語進入檢視程序,脫離那一次性的情況,要找出他的意義時,就會非常繁瑣、令人厭煩,以及出現奇妙地抵抗,所有的努力都會成為挫折。——摘自保羅‧瓦樂希(Paul Valéry),〈詩與抽象事由〉
所有的話語,都會有沉寂的時候,所以詩人總是會從頭開始,也就是會出現「語言情境的整理」,才可將一個用語做連結,成為可引用的句子,而這個過程就必須經歷上述無數次的轉換,就算不是詩人的我們,也偶爾會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這一情況。而在黃貞殷的小說中也常出現這樣的場面,經過她手中的「客觀」一詞,突然變成會引起「衝突」(〈不倒翁與斑鶇〉)、「毀滅」一詞,讓人覺得怪異(〈夜行〉),然而若說那象徵主義詩人的宗旨,是意識論的話(已被汙染的話如何感受到真理),那我們黃貞殷小說家所做的相似的工作,其宗旨就相對具有倫理。如何將各個不幸,從平凡化的現象中拯救拉出,在問題意識的延長線上,黃作家採行「語言與陌生」的方法,拆解語言無意識的暴力。
試試看,髮旋。
髮旋。
髮旋。
髮旋。
髮旋。
好奇怪喔。
髮旋。
髮旋,說著說著好像髮旋已經不是髮旋的樣子。
就是說啊,髮旋。
髮旋。
說起髮旋啊,伍宰先生說道,
每個都不一樣,我記得在書上有看到,每個人的髮旋都不一樣。
真的嗎?
但是通通都稱為髮旋,可能是方便稱呼的關係,看著髮旋的處境,突然覺得很暴力。
「髮旋」一詞不斷重覆地出現,而當這一詞自動重覆循環時,正是作者所謂的「暴力」表現,伍宰對恩喬說妳的髮旋「模樣挺有趣」,而恩喬回說:「伍宰先生,我也只是知道自己有髮旋,從來沒有想到髮旋是什麼樣子。」作者透過這段話,告訴我們這樣常見的想法,有多暴力,應該也是對現代哲學所稱的「一致性」表現出最謙卑的抗議,所謂「一致性」,是忽略個別的特性,將應為多樣化的個體進行統一。許多人指控二十世紀許多歷史災難的背後,都有一致性的問題,而作者藉由「髮旋的處境」謙遜地表達她的指控。前述提及小說家必須與現實對抗、也需要與不幸的平凡對抗,現在還要再追加一樣,小說家也要與語言的一般性對抗。
許多的案例,都可以表現出作家這個工作,會讓我們在常見、熟悉的用語前,好似初次、一般站立著的感覺,伍宰跟恩喬說其幼年故事時,說出「少年伍宰的父母可能,可能有欠債。」是要傳遞這個社會可能、或說必然會欠債的情況,而恩喬卻反問這世界不是也有不欠債的人嗎?此時的伍宰說,除非有一天人們都是從叢林冒出來,要不然所有的人類都會很自然的欠債,都需要償還債務,這時我們所謂的「債務」(不是經濟類債務),是需要理解成倫理性的債務。再者,對於將電子商城稱為「貧民窟」這一情況,伍宰尖銳地指出:「這個地方總有一天會被全數夷平,若要說是誰的生計、誰的生活圈一類的話,會讓人想太多,所以乾脆就說是貧民窟會簡單許多,不是嗎?」時,我們才深深感受到「貧民窟」這一詞的暴力性,以及感覺到罪惡。所以作者也對語言的倫理性相當敏銳,只是這樣的態度,對於基本上屬於社會弱勢的一方,真的是必要的嗎?
四、對話——倫理的無知
「伍宰先生,我這樣喊到。
是的,伍宰先生回應。」
該如何從這樣的語言暴力中逃出呢?身兼評論家與作家的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就曾經在與其好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進行交流時,就針對倫理提出更尖銳的問題,布朗肖特別之處在於他著眼於虛偽「寫作」中,所衍生的普遍性倫理問題。他對於寫作的語言,成為這世界暴力的這一點,有著深深的疑惑(如先前描述,小說家也發現這個問題,也同樣很苦惱),然而他卻認為在口說時,最少有兩位對話的情況下,會有不同的情況。「想與未知的對象締結一段關係的話,必須注意可還原距離,才是口語最特別的禮物。」雖然不見得一定具一致性,但仔細閱讀黃貞殷小說中的人物對話時,隱約可見這樣的脈絡,有人說黃貞殷小說中的對話看起來毫無意義,但反而黃貞殷的小說是更接近事實真相,他們的對話,可能在「某種」分類下毫無意義,卻在「其他」種類中更加深具意涵。
恩喬小姐想要變成什麼?行星還是衛星?
我不喜歡軌道。
那彗星呢?
彗星也會轉不是嗎?哈雷一類的。
哈雷啊……思緒暫時止住,那流呢?伍宰先生這樣問到
那流星的話,是不是剛剛好嗎?
轉眼間就消失了不是嗎?虛無飄渺。
虛無飄渺啊。
A是B嗎?嗯……不是嗎?是吧,就是對吧?若覺得這樣的對話很奇怪,會是什麼原因呢?此處並沒有獨斷式的判斷,而所下的那個判斷也沒有強迫,沒有為了效率而加速,取而代之的是某種倫理的「距離」,而「距離」,會使得對話會緩慢、小心且謙遜地進行,所以逆轉部分也可以這樣說嗎?乍看之下是天真浪漫的對話,事實上確是用盡策略的對話。目前為止我們在現實的抵抗中、不幸的平凡中、語言的一般化之中,依循特定規則、使用某種要素,努力進行對話,這樣的對話該如何命名為佳呢?我想這可以稱為「倫理的無知」。世俗的利害算計太多,影響我們的對話,讓我們的對話顯得又聰明、又悲傷,而這就是那些無知人物的倫理對話,之所以看起來毫無意義,卻又美妙之處。
然而,對於這本小說的人物來說,他們毫無自我意識,我們對話範圍中,會出現許多錯誤與暴力,而這或許是他們比較接近沒有本能的人。因此他們的對話,是在世俗利害算計的支配下,在這世界所有話語之中,清楚表達無言的抗議,或是成為溫暖的安慰。本書第三章的對話就是典型的狀況,無害卻被當成害蟲,被當成是社會弱勢象徵的老鼠新娘,卻是同為社會弱勢的劉坤先生極度厭惡的害蟲,這卻也讓我們能夠理解並接納劉坤先生悲傷家族歷史的原因。小說中最痛苦的這一段對話,或許可以當成是對這世界無言的抗議,當劉坤先生話語中所流露出的執著,勉強支撐著在藤樹亭中,並排而坐的伍宰與恩喬的對話時,這對話就是這部小說最美麗的瞬間,讓被這個庸俗欲望掛帥、熙熙攘攘的世界排除在外,需要慰藉的讀者能夠獲得些許安慰;最後就是要提及恩喬與伍宰的愛情。
五、愛情——戀人們的共同體
「跟著我們的影子其實一點都不可怕……」
從他們的口中未曾出現「愛情」二字,他倆的相遇、與他們的苦痛令人難以聯想到愛情,而若我們看不出來他倆的關係是愛情的話,那應該是我們不懂愛情之故。究竟愛情是什麼呢?認真看著戀人的髮旋模樣,而那是獨一無二的事情,就像我喜歡鎖骨漂亮的人,卻會對鎖骨不漂亮的戀人說「不漂亮我也喜歡,就是喜歡」,將單獨性用不可能的事轉化成絕對化的事情。緊接著再一次的問愛情是什麼?那是守護戀人免於絕望、當戀人無心說出「死定了」之際,他會說「如果不是真心想要死的話,不論如何都不要說死」。當停電的時候,原本就會打給戀人的行為,想告訴對方我與你同在黑暗的空間裡、當戀人於夜晚無法入眠時,會跑去找他,一同打羽毛球。
然而,若是讀者能夠充分理解這樣的愛情,也就是在這部小說所帶有的意義時,肯定會反對將這部小說分類為「戀愛小說」,布朗肖曾經說過:「當戀人之間的共同體,具有正向目標時,有時會瓦解這個社會。」若這句話是事實,則優秀的戀愛小說,也可以說是描繪這備受壓抑的社會體制,然而這部小說(不過或許這一點也會讓部分讀者認為,這小說太善良,讓人徒生不滿)不是用間接的方式,而是採用直接的方式,所以透過這對戀人展現出的某種倫理關係,向系統性的非倫理的悲壯表達抗議。說得更清晰一點,恩喬與伍宰所形成的戀人共同體,向我們傳遞出這世界的一種表象,舉例來說,因為體貼遠道而來的客人,深怕他們因為不小心而必須再跑一趟,所以會多放一個燈具的Omusa的老爺爺,因為他的慈悲所建構的世界。而今,那樣的世界卻一一被我們忽略、拆除,不是嗎?如同前述,這就是我們說「這一段愛情,是基於善良人們的善良所孕育的愛情,而可以守護善良的希望,是愛」的原因。
(……)藤樹的葉片燙過之後,伍宰先生突然說道。
燙過之後,喝那水,有人這樣說,說喝那水之後夫妻之間就會再度琴瑟和鳴。
真的有那種說法?
哪時候我們之間琴遠離的話,就來燙過喝喝看?
這句話讓我慌張失措,支支吾吾地說我們連夫婦都不是,伍宰先生在雨傘下微微地笑了起來,我咳了幾聲,清了清喉嚨。
琴瑟如何我不清楚,不過伍宰先生,這樣坐了一下覺得肚子溫暖許多,真好。
什麼?
單純覺得很好,
我看著這個夜色,坐著。
所以守護這份愛的同時,我們所感受的懇切,是我們始終無法拋棄為希望而激動的心,當然這兩人也會毫無理由的動搖,「早已是黑暗的關係,所以黑暗的地方就是黑暗的,難道就不會有可怕的事情嗎?還是根本不會有這種事情?黑暗無心的話該怎麼辦?」,為了守護這樣的恩喬,伍宰也是使用俄羅斯娃娃,而這一行為確實也毫無道理,同樣都稍稍透露些許情緒,「那裡面本來什麼東西都沒有,也沒有那個核心,(……)可能是因為很空虛的關係,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可能跟人生在世差不多吧。」但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希望。作者讓這部小說從開始(〈森林〉)到結束(〈島〉),是刻意塑造戀人迷失方向,但作者將整體氣氛調整得相當美好。最初章節面對恩喬的呼喊,伍宰沒有回應,然而時序走到最末章節時,伍宰在恩喬呼喚之前說:「恩喬小姐,伍宰先生呼喚著我說道,唱歌好嗎?」我想這可以當成是一美好明確的結尾。
※※※
閱讀這部小說,看到現實的對抗、不幸的平凡、語言的一般性、倫理的無知、戀人的共同體……每一部分都可以分開說明,但所有優異的小說都是這樣,黃貞殷作者的這部小說也包含、混合著所有必要要素,因此我們說這充滿黃貞殷特有的風格與特色,這些風格與特色不是一次性,畢竟一部作品的藝術性,若只由個別的架構負責,如同部件一樣形成一部小說,就會感受到空虛,不是嗎?那種相較於故事,沒有留下一句話、一個象徵、一份對話的那種一次性小說。然而這部小說不同,這部作品能引導人再讀一次、再一次衝擊承受,這部小說的文字描繪出將一群人步履蹣跚地拉出他們賴以為生的基地、這部小說的所有象徵有大半都是頹廢建物,如碎片一般凋零、這部小說的對話,是人們在無意間展現出最真實的表情,沒有吶喊、沒有歡呼、沒有訓誡、沒有勢力派別,黃貞殷完成一部僅有一百七十頁(譯註:此指韓文版)的小說,一部既短、又具有深意的小說,在近來韓國小說到達最具倫理絕望與希望的當下,我無法哭、也無法笑。
申行哲
後記
因為在這個依然粗暴的世界
有幾個可以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想著
若這世界可以
不這麼暴力地對待他們的話
那該有多好
這個世界從一開始
可以不要那樣
礙手礙腳的話
希望,
在身旁就能帶來
一絲安慰的心願
不是自戀
是希望可以動員到溫暖
讓走在夜晚道路上的
兩個人,可以有希望
遇到某個人
願各位平安
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