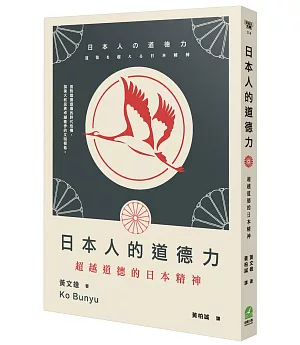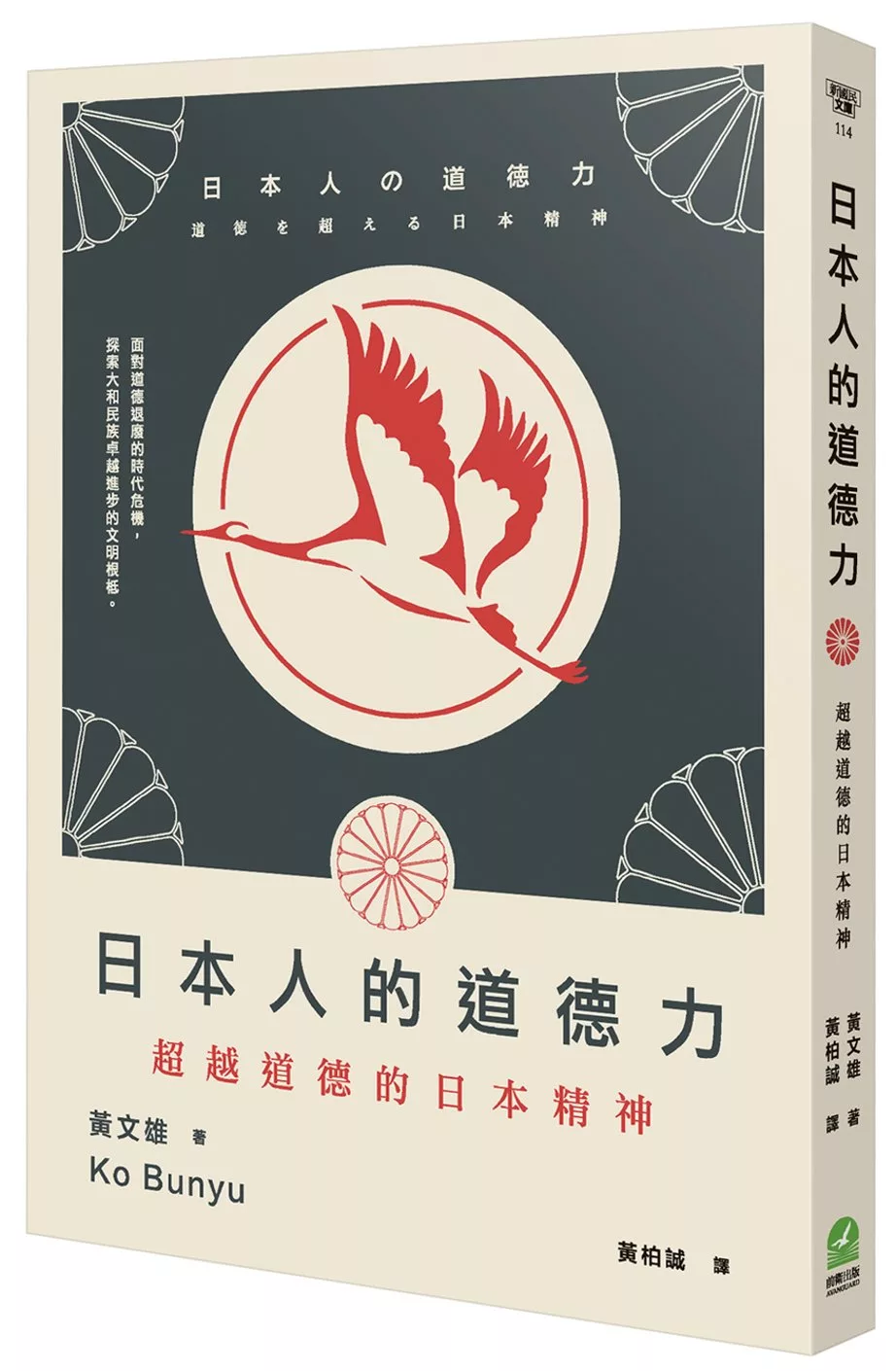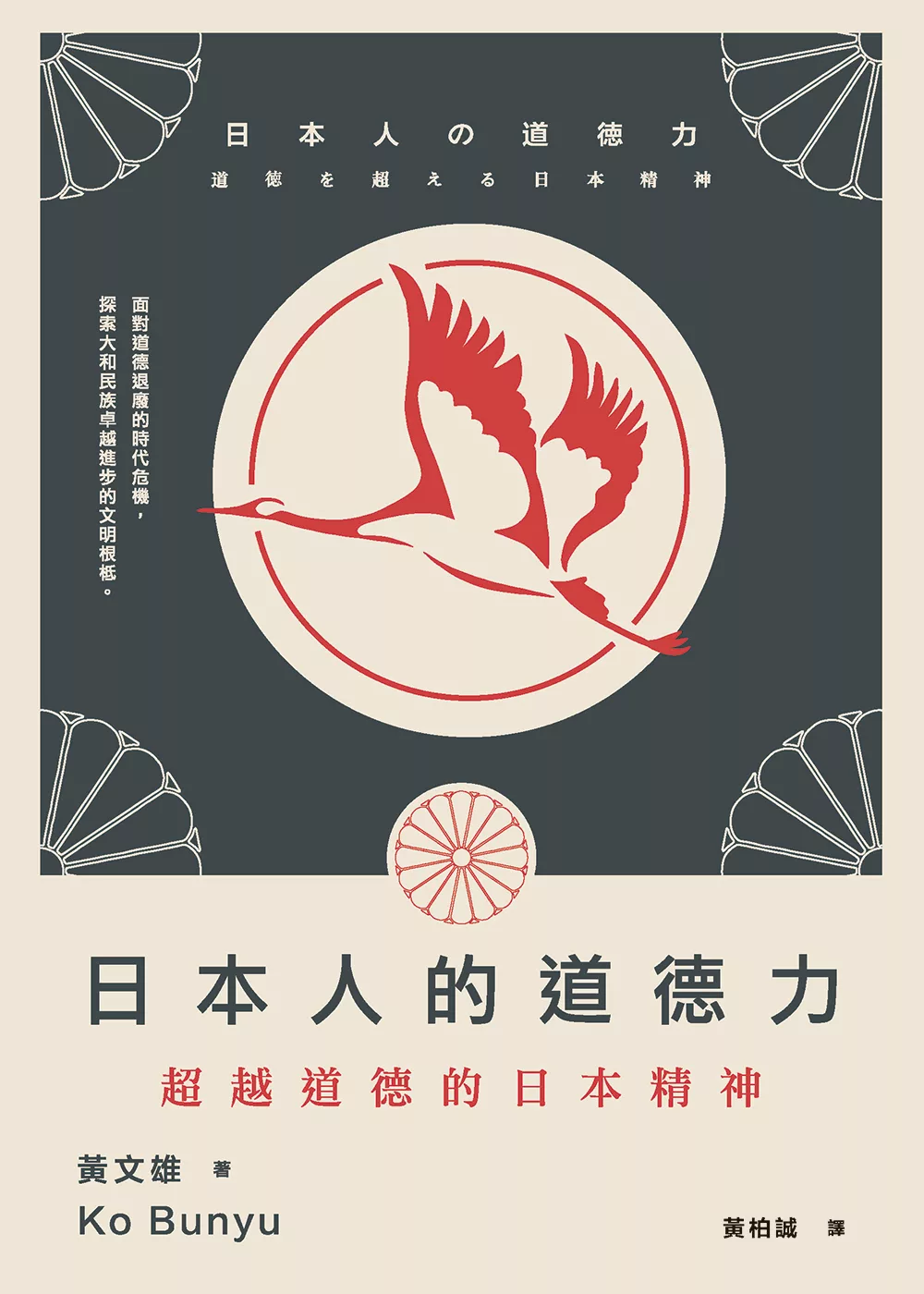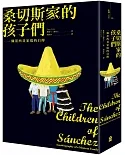前言
近代國民國家的教育上,國民教育和實業教育成為主流。但是,在我進入小學之前,尚仍以《三字經》、《千字文》為開始,也有所謂背誦「四書」的識學教育。雖然小學入學前能夠背誦「四書」的《大學》、《論語》、《孟子》,但不能背誦《中庸》。隨後,在小學一年級時,迎來了終戰。
或許也可以這麼看。我大概是台灣最後的舊漢學書房之生徒,和最後的日本語族之其中一人,是不是呢?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教育畢竟是舊式的。高中的國文以難解的宋代理氣之學、朱子學和陽明學為中心,許多時間主要被用在文詞之註解。在國文的合格標準方面,《論語》和《孟子》的背誦被視為最低必要的條件。
的確,國語或國文科以外,也有「公民」等等的道德教育。因此,「仁義道德」和「善惡」之論議,不得不必然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樣的狀況已成為現實。於此,所謂「成為『道德之國』了嗎?」的疑問,從離開高中開始也都一直都存在著。
進入七○年代時,在我原本一直持有的道德觀上,發生了哥白尼式的轉向。與完全迥異的兩種道德觀之相逢,則是開端。
戰國武將中,著名的伊達政宗之家訓中有「過仁,則弱;過義,則執;過禮,則諂;過智,則辯;過信,則損」。然後,在「智仁勇」方面,有所謂的「過勇,則暴」。對此,明治初期的陸奧宗光外相在獄中有所謂的「義即利」的考察。其為分別不同的發現。
原本,在我幼時所度過的社會環境中,不僅「仁義道德」,「善」也是絕對的價值。哪裡談得上對於傳統、道德、價值的「反論」(Antithese),就連疑問也不被允許。更甚者,是連想都想不到。
日本社會是在多樣性上富饒的社會,是「什麼都有」的社會。以古代的故事作為分野,即便在同樣的近世或近代,雖然中國和朝鮮只容許朱子學,但在江戶的日本,不只是朱子學,無論神道或佛教,國學或陽明學,就連蘭學也都有。
從江戶時代的朱子學者開始,支那學者以及戰後的中國學者,似乎完全把中國諸子百家的思想當作自家藥箱中的至寶而禮讚之。然而,古代中國的諸子百家思想在人類的精神史中,幾乎就只是侷限於「目的方法論」的領域。也可說是古代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這樣若被稱為思想和哲學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不存在從純然「how to」(know how)的論域中脫離的可能性。在中國的思想史中,被冠以「認識論」而開始被談論者,是從佛教傳來之後,大概在七百年後誕生的宋代理學及氣學中出現的。理氣之學的集大成者朱子學也好、陽明學也好,只是盜用佛教哲學的用語,而對古典儒學進行再注釋而已。
作為對中國思想的評價之一例,有空海的「十住心論」。在其中,人類精神史的發展被分成十個階段。第一住心是異生羝羊住心;第二是愚童持齋住心;第三是嬰童無畏住心。從這裡往最高的秘密莊嚴住心,以及住心之發達、開悟的境地不斷地接近。從第一住心開始到第三住心為止被稱為「世俗之三心」,儒教是「第二住心」,老莊思想被歸類為「第三住心」。弘法大師的眼中所見之儒家、道家思想,只是稍微從動物和野蠻人那裡分離開來的東西。
我也在日中的文化摩擦和文明衝突中被育成,是經常冷靜地從第三隻眼的角度,並且從異文化和文明的比較中,嘗試來了解文化以及人的心和魂的其中一人。
中國以獨尊儒家為根基,只容許文人(讀書人、文化人)的士道。而也在兩千年以上的歷程中,想要對萬民強加以士道。
然而,在日本,有作為武士的武士道,也有作為石田梅岩所代表的町人道的「石門心學」,就連二宮尊德的農民道也都有。尤其在日本的精神世界中,有神道和佛道,其多樣性和豐富的精神性,實為世界之冠。這又成為日本人的底力,在無常而轉變成有為的世上,有無與倫比的適應力。
在這裡的半世紀以來,我受到出自日本人的心和魂的道德及支撐著它們的傳統文化的牽引,受其感動不知幾回。
當然,這不只是文化等方面的軟實力而已,我認為也可說是由於事實上,日本是在硬體的多樣性上也相當富足的豐饒社會的緣故。從自然的稟賦,或從社會的結構來看,只有日本才產生出絕對不會陷溺於全體主義國家的結構。對此,我感到相當確信。
正是如此,我也在半世紀的歷程裡,從日本人的心和魂中,持續不斷地探求超越善惡的價值觀。於是,也有不少的發現。
本書是對於從七○年代開始我所不斷追問的「德是什麼?」的問題,在片斷時刻中持續寫出的感想之集成,亦即對於倫理道德之我見。以二○一三年末滯日屆滿五十週年為一個段落,總括對於德之我見而欲促其問世。在這樣的思考下所出版的本書,若能成為讀者朋友們的他山之石,則是甚大的喜悅。
二○一三年十二月吉日
黃文雄 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