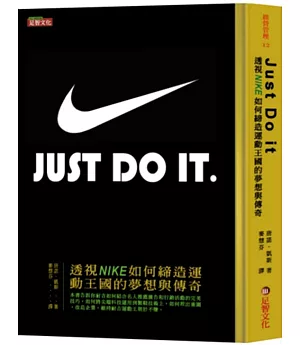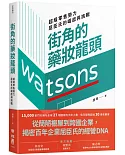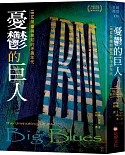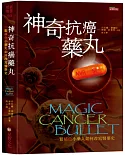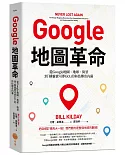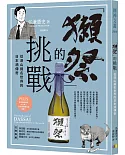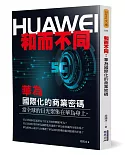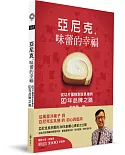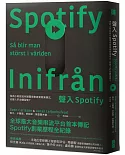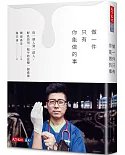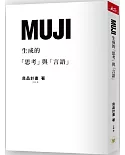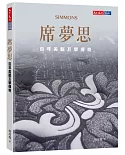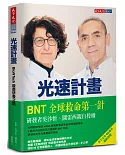前言
當我第一次和耐吉的創辦人兼董事長菲爾‧耐特談到寫這本書的想法時,他並沒有同意。
當時我建議以一九九二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到一九九四年初,這段充滿榮光、恐懼和狂熱經濟行為的十七個月為基準,來描繪耐吉這個公司的成長 。因為以耐吉那種引人注目
、獨特的公司文化和它對外界無所不在的影響力,這本書應該很容易超脫一般用來描寫當代大企業的那種平鋪直敘的筆法。這本書能深人到運動商業的萌芽過程和那屬於超級運動明星的世界。經由信件、電話往來和親身造訪,我不斷地嘗試說服菲爾‧耐特,像這樣一本關於耐吉如何經由本身特殊文化和作法,使品牌受到世人廣大注意的故事,對闡揚行銷學將有莫大貢獻。
這本書將敘述在發達的經濟體系中,如何創造出人們真正想要的工作。在這方面,耐吉幾乎已經成為後工業時代國際化企業的典型。「這是一個讓我困擾的問題,」耐特說:「整個運動和健身工業都在看我們要如何做。其他競爭對手已經逐漸趕上我們了,為什麼我們還要讓大家知道我們要如何做?」
為了給耐特一個不一樣的答案,我對他說因為耐吉本身的歷史和獨特的企業文化,任何模仿的努力都無法得到耐吉的精髓,那就是耐吉對鞋子的狂熱投人。「菲律賓和美國有相同的憲法藍圖,」我繼續說,感覺如履薄冰。「可是菲律賓不可能變成另一個美國。」
耐特笑了起來。可是他又一次拒絕了我。
那個時候 一九九三年夏天 我已經完成了一篇關於耐吉的報導,並即將在運動畫刊(Sports Illustrated)上刊登。在這篇文章頂定刊出的兩星期前,菲爾‧耐特告訴我,他改變了心意,願意讓我再到他的公司去談一談。
這個決定正反映了耐特那種不同於流俗的管理風格。一方面,耐特仍然是所有大企業總裁中最難於接近的,一位新聞媒體眼中與世隔絕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他卻在還不了解運動畫刊中那篇文章的內容前就答應讓我飛往亞洲,自由地參觀耐吉的全球指揮系統。其他的經理人可能會多等兩個星期,等到雜誌公開銷售、看過內容以後再做這個決定。
在參觀耐吉的生產體系時,我和許多在生產線上將鞋子黏合在一起的工人們見面。在中國南方,數以千計的工廠正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同時,我也花了許多時問接觸新澤西州紐渥克市(Newark, N. J.)貧民區內的零售商,加州購物中心中的小企業家、和全國各地運動鞋的小經銷商。我也曾和一些耐吉的運動明星談論籃球、棒球和網球,其中邁可‧喬丹、波‧傑克森(Bo JackSon)、查爾斯
巴克利(Charles Barkley)、安得列‧阿格西(Andre Agassi)、和阿隆索‧莫寧(Alonzo Mouming)等人給我特別多的幫助。我認識了許多耐吉的工作人員。最初,他們多數對我的工作都抱持懷疑的態度,並不認為我能夠真正的了解耐吉;因為在他們心目中 ,
以往所有嘗試報導耐吉那種獨特生活哲學的努力都失敗了。經過幾個月的觀察和旅行,我了解到耐吉所代表的是一種心理狀態和錯綜複雜、幅員廣大的經濟體的綜合產物。耐吉的所作所為像是亞當史密斯「國富論」(The Wealth 0f Nations)中勞力分工和其他經濟行為的現代翻版。一旦你真正的了解耐吉的精髓,你會發現,它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
在我為這本書從事研究工作的幾個月裡,我觀察到耐吉驚人的成長率因為不同的外在環境因素和一些耐特眼中的致命缺點而遲緩下來,剎那間,專業投資人紛紛從耐吉原本價格甚高的股票抽腿,耐特所擁有的兩千五百多萬股耐吉股票也因此損失了超過十億美元。這項損失使他的財產淨值在一九九三年「資本家」雜誌(Forbes)四百位「十億美元俱樂部」的富豪名單中只能列名第三十二位。
我觀察耐吉的這段時間裡曾經發現了一些錯誤的決策,特別是耐吉為了發掘新人而贊助的一次高中籃球錦標賽,幾乎威脅到這此一向受耐吉重視的運動員的球員資格。但是,耐特不僅沒有因此而拒絕採訪,他反而盡量使我了解挫敗給他帶來的感受。雖然他曾經在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的解雇行動後誓言,他以後決不採取類似行動,但是一九九三年九月,他讓我親眼看著他向員工解釋為什麼裁員是必要的。
經常,我提出的問題本身就已暗示這本書將會包括公司的所有缺點以及政策上的反反覆覆,然而,耐特總是平心靜氣地回答。他似乎了解,要真誠地描述一家成長中的公司必然無法逃避錯誤和挫折;他甚至願意表達出他心理和感情的創痛。我完全明白這對他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耐特似乎相信,對一本試圖揭露企業創造與持續再創造過程,以及隨之而來的回績與災難的書而言 ,這一切都相當重要;尤其因為這家公司,套用一句耐特自己的話說,「不僅是一部商業機器,更是一家有靈魂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