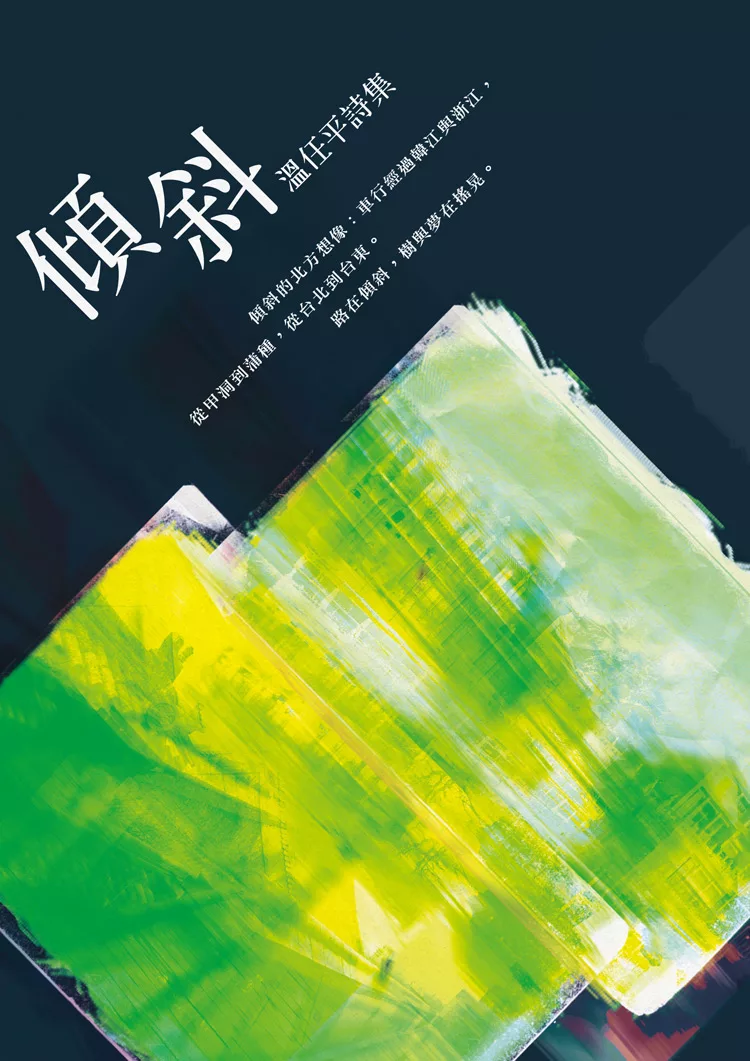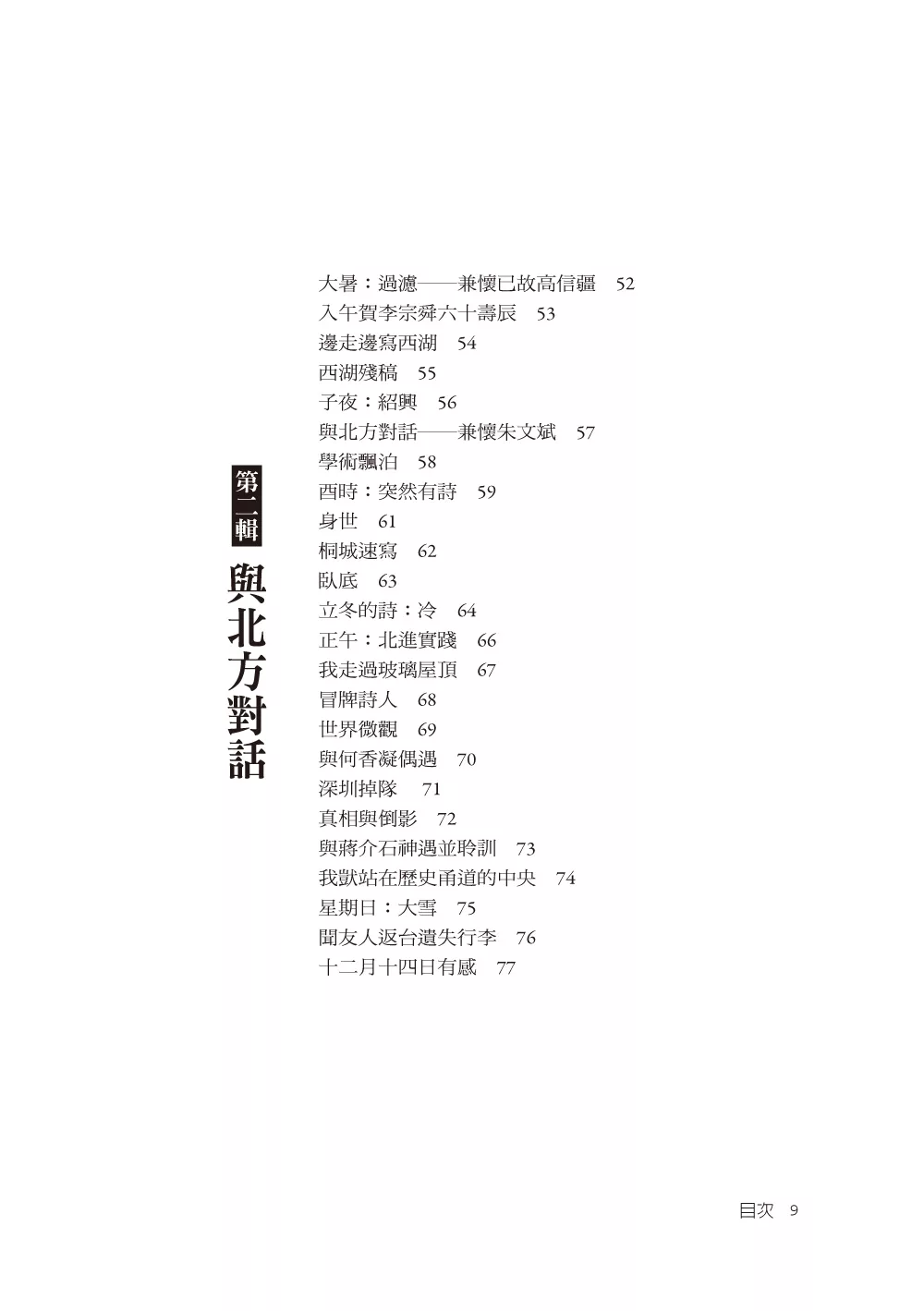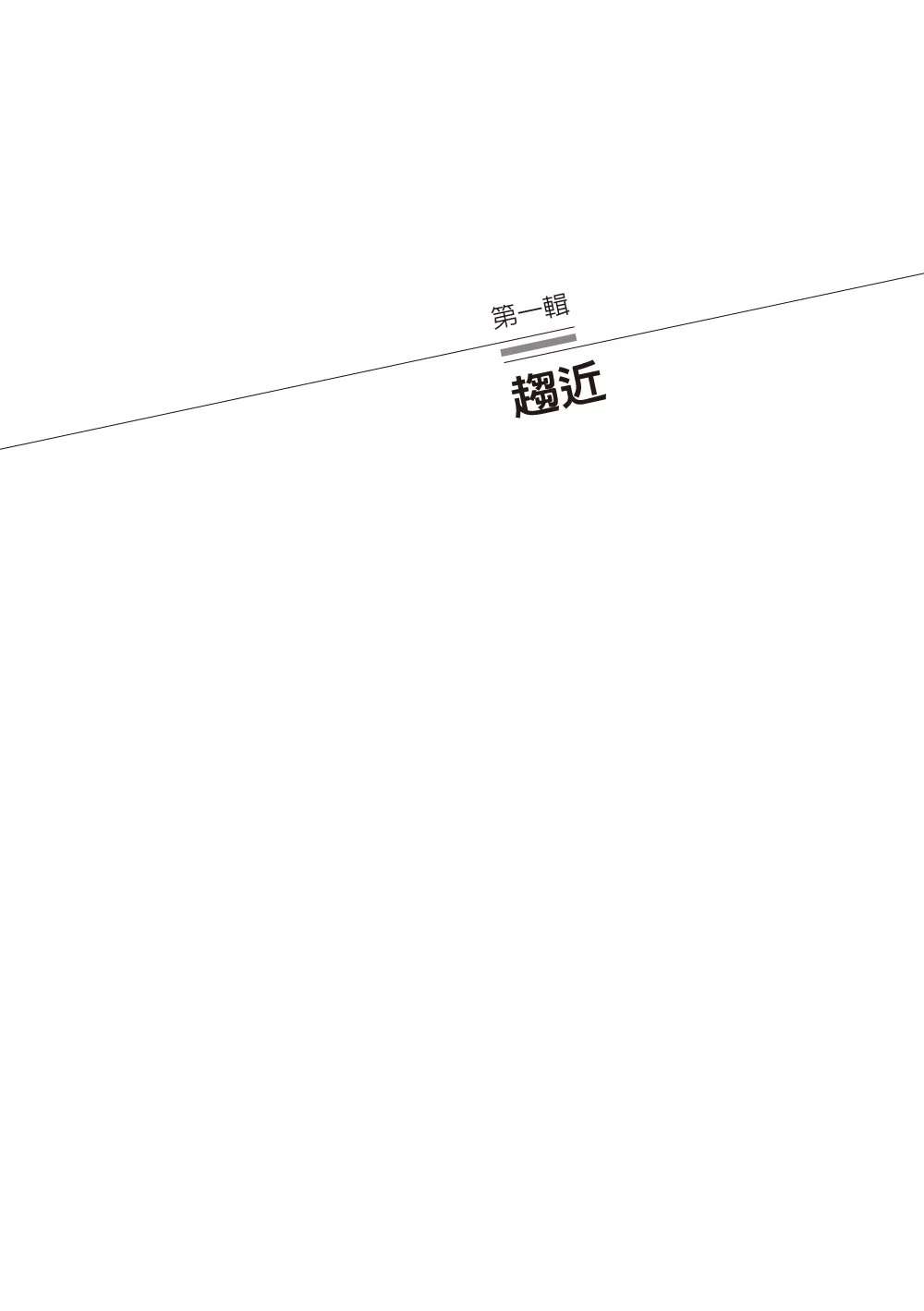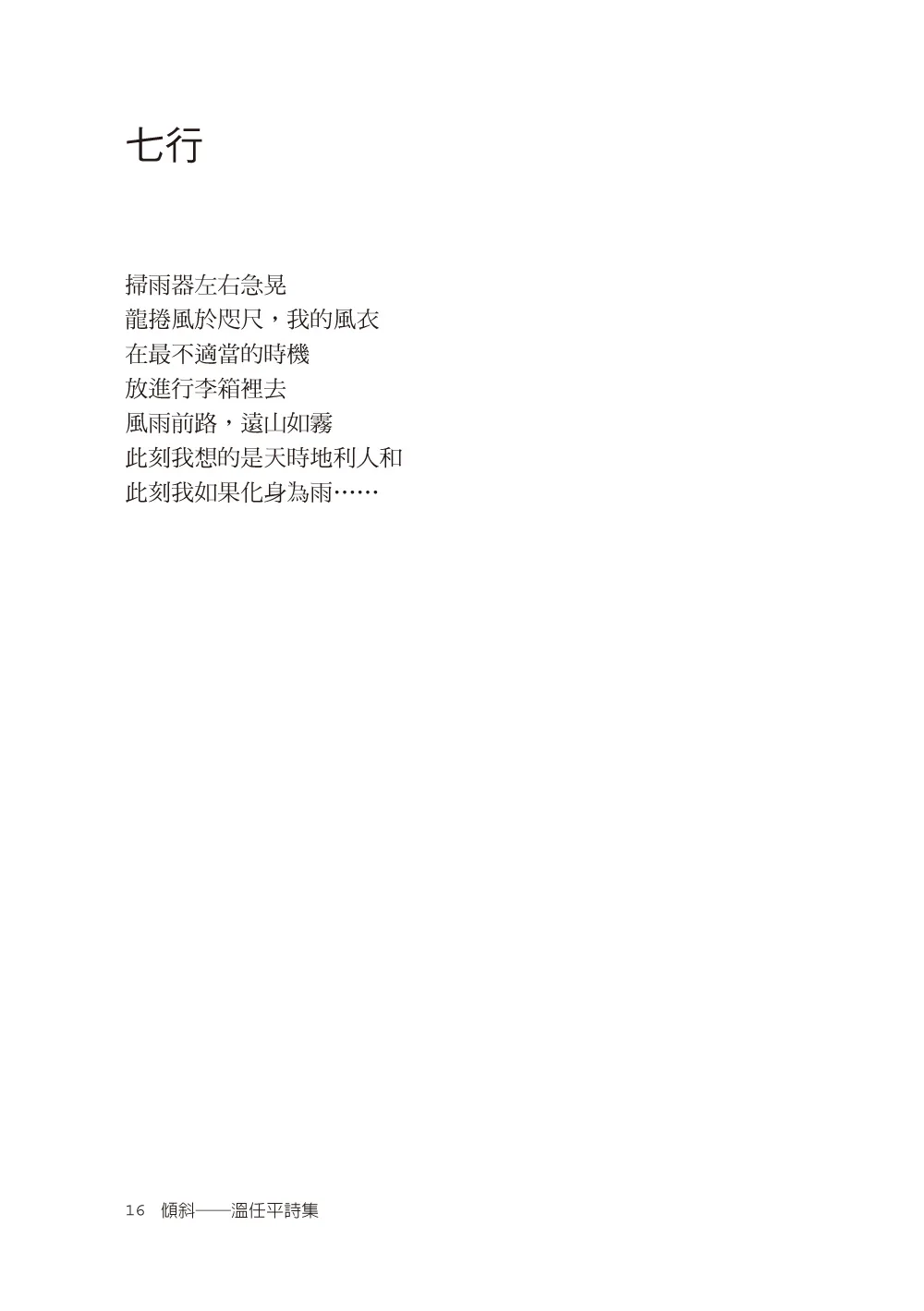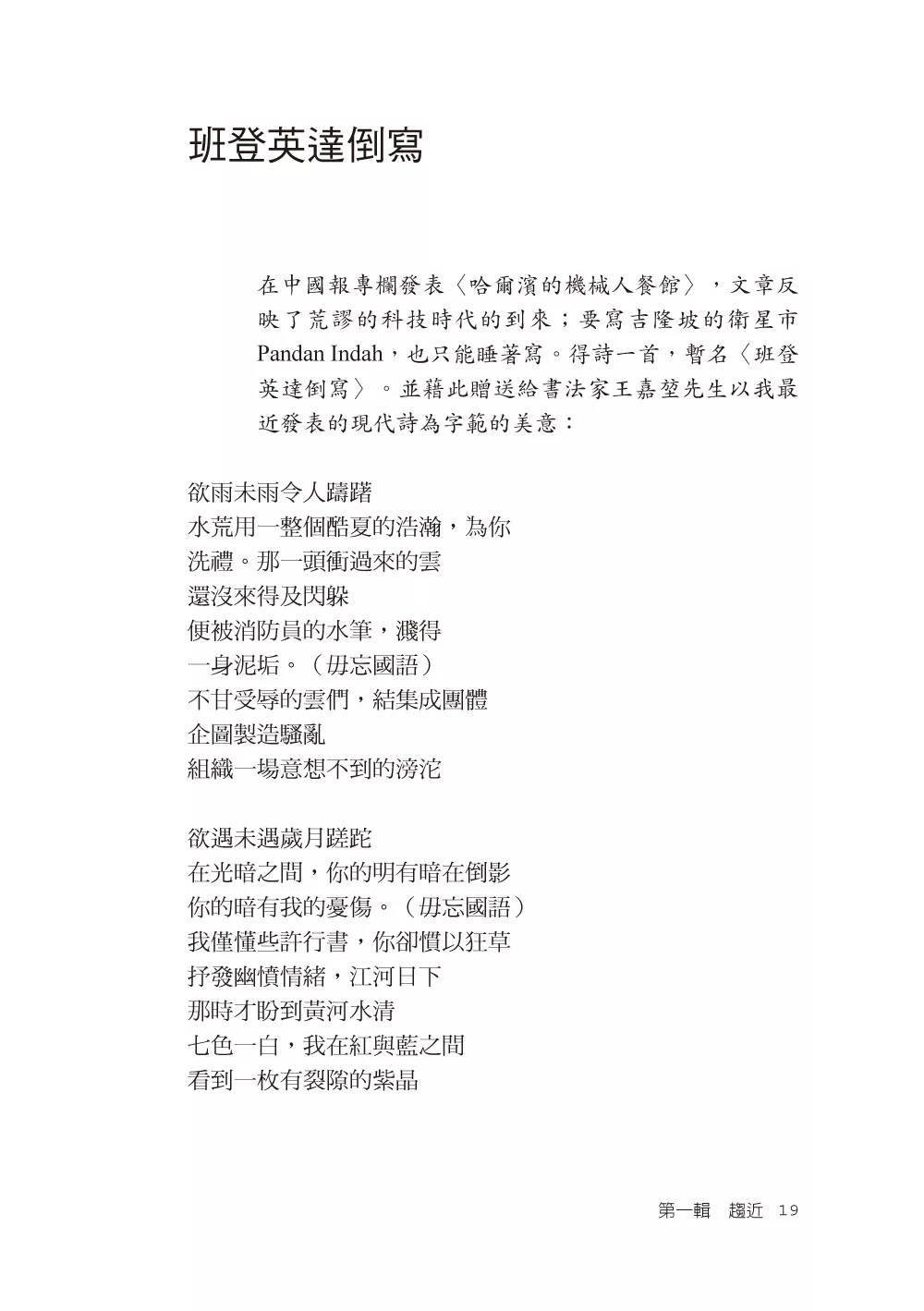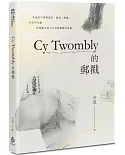自序
上一部詩集《戴著帽子思想》的出版,是二零零七,距今十一年。以為從此之後,我將替報章寫千字專欄為生,偶爾孵研討會論文為樂;生命形式大致定形。追求生活的詩性,卻活在純然生活的知性裡。
但是另外一個我,卻在我的潛意識裡蠢動。我完全能意識,作為一個詩人,我還有話沒說完、沒說好。
詩創作是一種反熵行動。所謂「熵」(entropy)是能趨疲,是信息的負值。語言文字在會議紀錄裡呆板癱瘓,在記者的新聞報導公式化的過程中麻木失能,在政客的話語裡變形變態,只有文學(尤其是詩)可以把它喚醒,並且注入活力。
偶讀《老舍請吃糖瓜》,文章有趣。老舍,誕生於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京派作家。老舍追述自己的一次「語言事件」,他去戲院後台看演員,剛好聽到下面的一段話:
「北京人習慣遛早,見面問個好,肚子吃飽,逛逛天橋。」
唱戲的楊星星順口就答:
「天橋好啊!聽書、看戲、變戲法、吃不盡洋鼓洋號,曲藝大鼓蓮花落,爆肚、火鍋、扣肉、壇肉、燒羊肉、吃飽用不了兩毛。」
北京人的話語音色鏗鏘,猶如快板,落韻有力,親切自然,上面的對話都往好處說。好言悅耳是北京話的特色。
我特注意的是北京話的「活力因素」,語言是個生命體,文字樂音使語言或婉轉、或諧和,或剛健、或雄渾。行酒令其實是唱酒令,少林武當練功的吆喝,也隱含敲擊的音響碰撞。
奇怪的是,受過音樂訓練的人包括音樂系的畢業生,對語言文字的音感多不怎麼敏銳。他們的作品中用上押韻甚至換韻,他們告訴我那是「碰巧」,並非蓄意經營。整體審視唸音樂出身的詩人,我吃驚的發現,他們的作品缺乏的正是音樂性。
我不想從平仄、陰陽、雙聲、疊韻、對仗,駢驪……這些傳統角度去討論上述課題。太多這類的文章了。我建議讀者把詩朗讀出來,讀者不妨身子傾斜一些,聆聽詩內在的聲音與餘弦(nuance)。
只留意詩的音樂性,仍很難使詩存活。現代哲學向語言學靠攏,是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與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先後發現的趨勢。在詩篇裡傳播思想肯定吃力不討好,但我們總是有話要說,對嗎?不一定是結實沉重的思想,只是一些觀察,一些疑問、一些尚未成形的思想點滴,廣義的知識,其實可以通過生命話語尋得出口。
甚麼是生命話語?當然是詩。社會學、人類學以致於經濟學、政治學都得透過詩學,才能有效傳遞知識,撼動人心。我指的當然不僅是中國三十年代的救亡文學與口號詩,那太膚淺了。
我的一些思想點滴,是透過詩的形式與詩的自然過濾,表現出來的。
尼采的修辭問句:「那個人在說甚麼?他說出了的話,他還隱瞞了些甚麼話還沒說出來?」戴望舒說:「詩是一種吞吞吐吐的東西,動機在表現自己與隱藏自己之間。」我的第六部詩集《傾斜》,有意無意間在這兩者之間,尋找著出路。
這過程一定會出現灰色地帶。灰色在這兒不是自貶,而是詩的題旨的「去焦點化」,不在乎世俗的是非道德判斷,甚至不在意人物與情境的虛與實。
我有一個十分狂妄的想法,只有詩或廣義的藝術,讓我有能力超越時空的桎梏羈絆,讓我有能力在三維或是多維空間馳行無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與「你」同為一人,「我」「你」「他」甚至可以同體異生(mutations)。我不懂騎電動車,甚至推不動電單車,在詩裡我卻是那個坐500cc.超級電單車,呼嘯來去的魁梧大漢。詩化不可能為可能。
有關我怎樣騎電動車的作品,多收進另一部詩集《教授等雨停》。一共有十首有關在太空游弋的詩,收進《天狼星科幻詩選》(二零一五),是與詩社社友,在網絡互動、恣縱想像的掛貼之作。那十首詩,不對照其他社友的即時回應,剝離、孤立閱讀,肯定不足。這是《傾斜》不收錄全部科幻詩的原因,收入的三數首,則獨立自足,無須參照其他作品的回應甚至回嗆。
至於我對時間的敏感,可能是年齡使然。這四年來我總不忘在詩末註明日期、註明時間,書要拿去付印,才刪掉準確至分秒的時間註腳,代之以在詩題寫明籠統的時辰。我常為歲序節令寫詩,一方面借物起興,一方面提醒自己:我和我的民族來自農耕文化。
至於中國歷史,歷史人物的懷念,典故與想像的衍伸,純粹是個人的偏嗜。古典與現代交融,應該不僅僅是語言的,也是文化歷史的參照混揉。一些人物與軼事自然會走進我的詩裡。這就不多說了,借古喻今,似乎也較容易動筆。
詩的文字與情節的遊戲性(playfulness),是詩創作的快樂之源。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虛實實,端乎一心。唐高宗那首「四行詩」,是筆者反覆看了《武則天》連續劇有關片段三遍,一字不漏抄下來的。如此文藝腔,當年病入膏肓的李治怎能說得出來?今日的觀眾不管這些,聽了舒服就好。至於武媚娘那段蕩氣迴腸的回答,借自當年十四歲的歌手李文琦,她翻唱白安的歌「是甚麼讓我遇見這樣的你」有幾句歌詞,好傢伙,恁般出色,連現代詩人也未必寫得出來。在這兒作出交代,免被誤以為剽竊。當然讀者也可以將之視為作者的後現代挪用、駁接、戲擬。我是用這兩首實例,說明現代詩要懂得怎樣玩文字於股掌之間,要觀察/傾聽其他的藝術表現,轉益多師。
《傾斜》收錄七夕閃詩八首,詩末註上寫作的準確時間。在匆促的時段內,在七行不可超過七十個字的外在框限內,能寫出些甚麼,wow,腦洞要開,眼明手快。僅收錄端午閃詩十首的其中兩首,六行不超逾五十字的限制,使端午閃詩內容相對單薄。何況詩集《傾斜》,已經另外收入兩首有關端午的中型詩作,不是應景,可慰靈均。
我從大概兩百詩,選出詩作一百五十五首,篩掉四十首詩(不包括科幻詩),有些作品不是寫壞了,而是因為種種因素不得不摘下。十分不捨,我把這些詩組成一個名叫「被遺棄的哭泣之作」的詩檔,並且打算把它寄出去,給幾個……不會對它們不屑一顧的社友。
《傾斜》能在三個月裡成功付梓,詩痴李宗舜付出最多的時間與精力,他的全力投入,已超過朋友加上社友的情誼。秀威資訊徐佑驊小姐全力支援,效率之高,在一般工作情緒趨於緩慢的農曆新年前夕,令我既感動又不安。是為序。
2018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