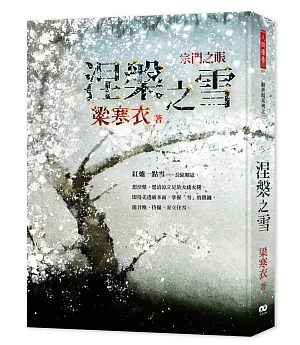推薦序
相約辭世之際的好雪
林谷芳
佛法談悲智雙運,但就外相,禪卻幾乎不言慈悲,就如此,連教下耆宿都常以其偏於一邊,但直言之,此正未入宗門,方有此論。
宗門向舉不二,以分別心乃顛倒纏縛之源。而既立於不二,悲智豈能雙運,更須就是一事。如此,哪有舉智不舉悲的問題!
舉智不舉悲,乃宗門接機之外現,以此而示自性自悟,但學人若真契宗門,也就能領略它那如實而獨有的慈悲。
這慈悲,在禪者身影,一個個活脫脫悟道證道之人,一個個不離世間而即超越的禪家,相對於他宗聖者的屢現神異、解脫之求諸彼岸,有他們,你才知生命竟可如此富含血肉地與道相應,如此凡聖一如地透脫自在。
的確,「禪者的存在就是宗門對眾生示現的最大慈悲」,有他們,你才更知「道不遠人」,才更知修行一事誠不我虛,才知眾生與佛果真無二無別。
這樣的禪者身影鮮烈,奪人眼目,更使得許多人欣羨於禪。可惜此欣羨,畢竟也盡多在行外徘徊。
徘徊,只因世人總見機鋒暢快,卻忽略了禪之根柢只此一句:「了生死」。
生死,是生命最難跨越的一關,歷代禪者卻以其獨有之姿,何只顛覆你原有的認知,更使你知道在此的超越果真存在,果真可期。
這是禪者示現的核心,也是宗門身影最鮮烈之處,它載諸禪籍,可惜向來少人梳理。
少人梳理,一因禪籍多的正是那讓人炫目的機鋒;少人梳理,還因這死生之姿在宗門原只自然之事,常淡掃幾句即止;但少人梳理,真正原因更在只有作家才能會得這淡掃幾句筆下的真意。
而如今,寒衣以一介禪家,既入於燈錄與歷代祖師相應,最終,更幾近嘔心瀝血般,將此風姿直現於世人。
直現,固因與祖師眉毛廝結;直現,也以宗門凌替,道風少見;而直現,更因禪家的死生殷切。以此殷切,寒衣固就體得祖師之恩;以此殷切,也才想將此祖師之恩轉諸有緣。
以寒衣在禪之領略及她特有之筆觸,這直現,何只讓歷代祖師之身影躍然紙上,領旨及書寫的寒衣其道人之風更就直逼眼前。原來,當代也有如此的禪家!
同為禪家,我與寒衣雖未即臨死生,許多地方卻也直映了一句禪語:「同生不同死」。同,在她的禪家原點,在她的宗門之見。不同,則在她高峻拈提下對有缘的殷殷叮囑。但無論同與不同,卻都讓我在禪這「獨行道」上有吾道不孤之感。
就因吾道不孤,禪家的辭世三書乃皆為之序;就因吾道不孤,乃更相約辭世之際的好雪。
作者自序
涅槃之雪──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
「紅爐一點雪」──唐代禪師長髭曠曾如是表述他的道悟。
三界火宅,無明燒燃,愛憎燒燃,不悟道、不裂破本參,則也永永無法親見、認證出此「一點雪」的下落;則火宅儘管是火宅,紅爐也儘管是紅爐……從此至彼,永永坐於人性人際人事的烈火爐鞲中,蒸騰不已、焦煎不止、傾軋難息。不撞碎閘關、撲破鐵面,則永永無法對晤、把掌「雪」的奧秘。
雪。清涼,止息的雪。關閉三界火宅的那一點樞機,那一點青雪。
「惟有涅槃永安!」如來屢屢垂示。想涅槃,想清涼立足於火綫火鞲,即得先透破本面,掌握「雪」的鎖鑰,能召喚、持攝、安立住雪──必須作到隨時作主,雪汛不斷、雪色連緜、器世岑白,不燒不燬,也才算是抵達「涅槃永安」。
準此,便不難會解一則為禪客拈而又拈,卻往往墮失標的的公案了:
龐蘊居士叩訪宗匠藥山惟儼。藥山命十名禪客相送至門首,龐蘊乃指空中飛雪
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
全禪客叩問道:「落在甚處?」
居士遂與一掌。
固然,是個大雪紛拋、境相空靈,依「境」而有的嘆美與提問。但只作「境」會,解釋為「叫人全神貫注欣賞當下美景去!」也未免忒煞辜負。
透曉長髭曠的「一點雪」,也便不難會契龐居士的「好雪片片」:那是一個洞破了「一點雪」的雪跡雪踪,保任熟了,駕馭熟了,隨時隨地皆能捉捏、拋撒大雪的人!也無處不是「好雪片片」!足以暢快淋漓,大作雪踏雪踴「作家」之境。龐居士僅是當機當境,當陽拈出、現前證據而已。
也即臨終的古塔主所云的「雪伴老僧行」的那箇「雪」:若果僅是器世、現象、物質的雪,依境、依他,冬日才有,春、夏、秋不有,則三時、三處斷裂,是談不上「雪伴老僧行」的:須時時「長安訊號不斷」、隨常俱能弄得出雪,且「好雪片片」、相佐相偕、直成貼體道伴才行!
如此,就不難契入圓寂的檜堂祖鑒所垂拈的「紅爐一片雪」:直是坐穩家山,深行深固、「輥」成一片連牀好雪,燒也燒不化!生時,固能於人性烈焰、無明羶臊中坐穩、作用此一片雪色涅槃;死時,亦且筆直冥入此祖、佛不異,常住不動的涅槃之雪。
這點「雪」,宗下或稱為「本面」、「本真」、「本處家山」、「本地風光」;教下則稱為「佛性」、「空性」、「常住法身」、「常住涅槃」。
換句話說,見此「一點雪」,才能如實經驗「舊來不動名為佛」,了「本涅槃」處,也才真正曉了「鄉關何處?」,知如何「歸鄉」、以及「歸家穩坐」。也才算是「手中有雪」:握持有此「涅槃之雪」,知其落點。
由是,就宗門,悟道,本為悟及、見及此「涅槃之雪」;保任,亦為保護持任、鞏固穩定此「涅槃之雪」;直須保得雪色純白,無縫無隙(這是鐵牛持定所謂的「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生死兩岸,人性人際的瘡癤瘡瘤、火綫火網火牆俱無以延燒延燃、荼毒毀裂,也才能算是坐穩「無縫塔」,是「塔中人」。
自此,也才能開堂、示法,「一條拄杖為知己」──為欲透破生死的有情擊碎千關與萬關。
自然,千萬則公案,千萬條身影,東參西參、東指西指,瞬目揚眉、威殺棒喝,俱不離於指陳出此「一點雪」:此涅槃之雪。
當然,惟有「慣行此道」,生時,即已安住磐穩、涅槃之雪嘯喝在掌、且雪色空然的人;辭世之際,也才能開門、關門,透脫瀟灑,一牀白雪,無縫接軌成大地銀雪:僅是「如來去耳。」,與佛同一涅槃本色。
能坐脫得了,俱是有此功夫,把掌了此「雪之印符」。由是「辭世偈系列」(從《花開最末》、《體露金風》至本書),本質上,均指涉「示寂」,也俱是「涅槃之雪系列」;基於這些祖師皆為「弄雪的獅子」,也皆能豁契「雪之真顏」:能悟雪,住雪,證雪,行雪,且「喚雪,雪便來」!祖德《燈錄》本就是「雪之紀事」,記錄一群巍峩獅子,擎拳摩掌,輥著、賽著雪戲雪踴……
拄杖橫斜,東指西指、南敲北打,便要當人返身自見此「紅爐一點雪」!且千叮萬囑,要行者將之坐大、養大,凝聚成摧燒不化的冰山冰堆冰原,生死炎飈中,足以涅槃永安、常住清涼。
三書皆標指為「宗門之眼」,在於它的重點,是為教人「開眼」,而非「閉眼」;不為「死亡」,而為「活卻祖師意」;不止於「出世」、「離世」,更意在世法、出世法間的縱橫自在、無縛解脫。其建構、僅是透過「辭世」──此禪者最末的「一圓相」,重建、指陳此圓弧圓相完整的跡路與軌轍:其追尋、安立的起點、中間……乃至微細微密、潛隱沒滅的綫段與絡索。依此,立體標剖出千載祖師禪嚴明嚴恪的參學系統以及修證風貌──關于「萬里一條鐵」的鐵道、鐵漢,以及其鐵脊、鐵志。
三書的差異,僅是由淺及深,更行更遠,更深入宗門修行的要害與關捩。相較於前二書宗門知見、眼目,初、中機式的肇啟與建立;本書更傾向深機、重量級的「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的保任與修證,也更見精森精嚴、微奧緜密;緣於「情塵不脫,有眼如盲」。所針對的,是具眼、且志欲實修的道流。
「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明代宗匠小山宗書曾如是咐囑傳法弟子。這箇「秋」,乃「一髮危秋」,指宗門凋殘、道法陵夷;也即虛雲和尚所疾呼的「扶起破砂盆」之意。然則,欲「扶起破砂盆」,則得先「扶得起本體修行,扶得起自家法身法性」:不認證、保任此「一點雪」、脫然獨立於人性燎原的心刺、棘叢中、作得了主;則也棘火燎原、自救不了……自己便「盲」、便「破」,就更遑論「扶起破砂盆」了!
而「定作人天主」之道無他,也無非好雪片片,把掌、安立、作用得了此「涅槃之雪」。能如此,則不妨火裡煉冰、冰中鑄火,住持宗門的危絲凋零。
無論當前悟與不悟,小山宗書的叮嚀均是所有志決生死、志欲宗門的禪和須永永貼放顱額的一句。它不是今古有別,世代差異、變通、權衡的問題,而是毘盧遮那巴鼻所在:欲參得了禪,便得先「自肯承擔」,自有獨脫為「眾中尊」的氣魄與志操。
回首,廿四個春秋,長嶺孤默。修行,唯是入雪、行雪,與祖師、古德的對參與對晤。缺乏祖德們拄杖嘯吼、髓旨披剖,山中將難以想像這悠漫持久、重重關隘的跋涉與穿越。
如是,書寫,也無非曬雪:再一次回溫、回魂,對晤宿昔的「老師們」,曬著他們連牀連骨的涅槃之雪,且記錄下雪之行履。還有,那曾一共偕行的奇峻鐵道、浩廣涯域、與答叩。
依此,致敬祖、佛之恩,也敬獻現在、將來的道流。
萬里一缽雪。
──寫于公元二○一八年二月十七日,年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