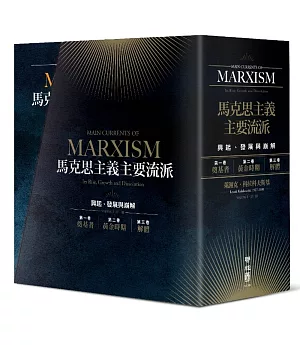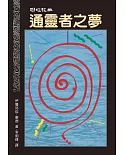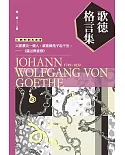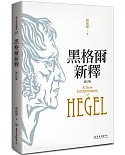推薦序(節錄)
科拉科夫斯基的扛鼎之作──寫在《馬克思主義:興起、發展與崩解》中譯出版之前
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出生於波蘭中部的小城拉多姆。如所周知,正是從這個國家遭到入侵和瓜分起,才宣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爆發。隨即,科拉科夫斯基的父親遭到納粹殺害,而他亦從12歲起便不得不輟學。但此後,他仍以頑強的自學完成了中等教育,並在二戰結束後順利升入羅茲大學,從此便選擇以哲學作為畢生志業。20歲時,科拉科夫斯基即加入了統一工人黨,並很快成為官方理論的後起之秀,從而有資格被派往蘇聯去深造。到了26歲那年,他便獲得華沙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隨即留校任教,並擔任沙夫等人的助手。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他是以批判基督教哲學知名的。再接下來,僅僅在31歲那年,已經身為教授的他又擔任了哲學系主任,同時還兼任《哲學研究》雜誌的主編和《新文化》雜誌的主編。
毫無疑問,這正是俗常所講的那種「錦繡前程」;而同樣沒有疑問的是,一旦到了蘇東轟然解體之後,這種「錦繡前程」也會於瞬間失色,甚至成為鏡花水月乃至行屍走肉的代稱。不過,不管這樣的前程是好是壞,反正科拉科夫斯基是不會安於它了,相反倒是選擇了去主動偏離它,乃至從某種意義上,也選擇了去共同衝破蘇東的體制。實際上,早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起,尚未滿30歲的科拉科夫斯基,便已開始懷疑史達林的教條主義了,並敢於撰文去批判「制度化的馬克思主義」,同時又主張「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我們都知道,無巧不巧也正是在那一年,在波蘭爆發了史稱「波茲南事件」的工人抗議,儘管它隨即遭到了來自蘇聯的嚴酷鎮壓,然而它本身卻也屬於蘇共二十大的餘波,所以也可以說,那也正是波蘭嘗試擺脫蘇聯的一個起點。
到了十年後的1966年,仍是為了紀念這個重要的事件,科拉科夫斯基又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講演,指出了種種「不屬於社會主義」的東西,把矛頭直指對於言論自由的箝制,比如「社會主義不是:一個人們說出他的想法會陷入麻煩、不說出自己的想法會走運的社會;一個沒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會過得更好的社會;一個密探比護士多、坐牢的人比住院的人多的國家;一個哲學家和作家跟將軍和部長說法一致的國家」等等。雖然說,他就此給出的72種「反定義」,馬上就遭到了來自宣傳機構的禁止,卻仍在新一代波蘭人中廣泛流傳著。不過也同樣因此,儘管此時他還認同於馬克思主義,卻竟成了波蘭最著名的「修正主義者」,同時也是波蘭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隨即,他在當年便被開除出了執政黨,兩年後又被解除了教授職務。
在1968年,也即在他被解除教授職務的當年,科拉科夫斯基便被允許離開自己的祖國,開始了在西方學府中的流亡生涯。我們從這一點中,或可窺知當年波蘭政府的相對懷柔。科拉科夫斯基此後任教過的大學,先後有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美國的伯克利加州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美國的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但其中主要還是在牛津眾靈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直至他於1995年從那裡榮休。此外,儘管到西方以後生活相對平靜,可是科拉科夫斯基不斷發表的著作,仍然對自己的祖國產生了持續而深刻的影響。比如他曾經提出,自發組織起來的社會團體,有可能在蘇東的極權體制中,去平緩地擴展市民社會的空間,這就對於團結工會運動有過相當的啟示,而後者又在當代波蘭史中占有顯著的地位。
正因為這樣,儘管科拉科夫斯基確曾在西方多次得過獎──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於2003年獲得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約翰‧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而這個重金的獎項可說是文科領域的諾貝爾獎,居然在首次頒發時就授給了這位波蘭學者——不過對他本人來說,恐怕更重要的還是來自祖國的榮譽。比如,他同時又是1992年重新設立的「白鷹勳章」的得主,這枚很像國徽的勳章作為波蘭的最高獎賞,是要授給「為波蘭國家和人民建立殊勳」的人。再如,波蘭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團結工會的顧問亞當‧米奇尼克,也曾盛讚他是「當代波蘭文化最卓越的創造者之一」。也正因為這樣,當他於2009年7月17日在牛津逝世時,波蘭議會隨即為科拉科夫斯基默哀一分鐘,而華沙大學的校長卡塔辛娜‧哈瓦辛斯卡‧馬楚科夫也是在悲痛中又透著幾分自豪地說,「這不僅是波蘭的,而且是世界的巨大損失。」
這一點,在我看來應該是特別重要。也就是說,儘管當我們閱讀他在各時期的著作時,總難免會產生不一而足的反應,儘管我們針對他進行跨文化閱讀的時候,也確實應當基於本土的經驗來進行利用,但無論如何,對於一位在不同的國度形成其思想的學者,還是應當首先去尊重他本國人民的判定,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再形成自己的判斷。要知道,這位後來雖已享譽國際的科拉科夫斯基,畢竟首先屬於他那一方特定的水土,畢竟是既脫身於、又服務於自己祖國的語境,所以,相比起任何外在的、難免有所隔閡或偏向的視角,他本國人民的看法都會更加圓融而周到,都更能體察他本人的痛苦感受與內心追求,也都更能全面地權衡各個方位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想要對之越俎代庖的結論,無論是來自哪個陣營或哪個派別,也無論是在冷戰前還是在冷戰後,就算還未流於隔靴搔癢和簡單粗暴,畢竟也只具有第二等的參考價值。
當然,這麼說絕不意味著,我們在閱讀外國學者的著作時,就不能得出需要同他切磋的看法了。比如,當我們讀到科拉科夫斯基的後期時,肯定會關注到他又盪回了形而上學的立場:「科拉科夫斯基在《形而上學的恐怖》一書中深入地探討了關於絕對的問題。在此,科拉科夫斯基捍衛被傳統踐行的哲學,在他看來,哲學的科學化的普遍趨勢不應該抹去它的合理內核,即形而上學。他注意到這樣一種事實,即通過追問關於真理、存在與不存在、善與惡、自我與宇宙、有限與無限這些問題,形而上學已經成為幾千年來文化的一個無法消除的部分。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只有當人們假設絕對存在的時候,尋求最終的基礎以及探究真理才是正當的。」
更有甚者,如果再順藤摸瓜地向上追溯,我們還能從他那裡發現一條可以說是「反孔德」的思路。具體而言,如果以往那位實證主義鼻祖曾經認為,人類思維發展的一般公式乃是「宗教神學→形而上學→實證科學」,那麼,現在科拉科夫斯基就正好把它反轉了過來,由實證主義的缺陷而上溯到了形而上學,又從形而上學的內核而上溯到了宗教本身。正因為這樣,他不僅在《理性的異化》一書中描述了形而上學是怎樣被驅出前門又溜進後門的,還更在另一本《日常生活劄記》中以十足「反尼采」的口氣寫道:「如果上帝死了,除了一個吞噬我們和消滅我們的冷漠的虛空外,沒有什麼東西會留下來。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勞作不會留下什麼痕跡;只有質子和電子的無意義的舞蹈。宇宙既不期望什麼也不關注什麼;它沒有什麼可為之奮鬥的目標;它既沒有獎賞也沒有懲處。無論誰說,上帝不存在而一切安好,這都是自欺欺人。」
這使我們不由聯想起了索爾仁尼琴的晚年,此公也同樣是早年捲入了布爾什維克運動,晚年又像科拉科夫斯基一樣返回了宗教。雖則說,在這種朝向原有精神傳統的晚期回潮中,多少都有出於「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正如「在索爾仁尼琴那裡,雖說沙皇時代的俄國,和普京時代的俄國,也未見得就怎樣的好,然而相形之下,卻只有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和葉利欽時代的俄國,才是千真萬確地糟透了」4,可即使如此,對於像科拉科夫斯基這樣的、早年曾以批判基督教哲學而聞名的學者來說,這思想的彎子還是轉得過於突兀、過於戲劇化了。尤其是,如果照我們這個「無宗教而有道德」的現世主義文明來看,或者說,如果照我們這些還掌握著其他文明選項的學者來看,似乎也沒見到他對這種很考驗邏輯的思想陡轉,給出過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釋或論證,——比如到底是為了什麼,一旦他意識到了從前立場的局限性,就再也看不到以往立場的合理一面了;或者反過來說,一旦他意識到了現在立場的合理性,就再也看不到當下立場的局限一面了?
劉東(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2004新版序言
開始寫現在被新編為一冊的書至今,三十年已過。若要問在這期間所發生的事件是否讓我的詮釋過時、離題或者完全錯誤也很正常。不可否認地,當初寫作時為了免於被證明有誤,所以我巧妙地不做預測。然而,我試著在書裡描述的問題仍然存在,而且在思想史或者政治史上仍然具有興味。
馬克思主義是哲學的或半哲學的信條,也是一種政治意識型態,共產主義國家以之為政權合理性的主要來源,以及堅不可摧的信仰。無論人民信之與否,這種意識型態是必須的。在共產統治的上一階段,它絕不是能實際存在的信念,與真實生活差異極大,對共產大同世界的期待也迅速落空,因此統治者(政黨組織)與人民都意識到其空泛。但正因為它是使權利體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因此仍為官方所用。若統治者真的想與人民溝通,他們不會使用荒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信條,而是以國族主義情感,或者以蘇聯來說,就是帝國的光環。最後,這種意識型態跟著帝國一起分崩離析。其解體是共產主義體系在歐洲消失的原因之一。
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機器與有效但弱智的鎮壓剝削工具毀壞之後,作為學科的馬克斯主義似乎被永遠埋藏了,從一片荒煙蔓草中將之挖掘出來毫無意義。但並無為此爭論之必要。我們對這個舊思潮的興趣不在其思想/智識價值,也不在其至今仍存在的說服力。我們研究許多已不存在的宗教之神話,因為不再有信仰者並不會讓這樣的研究喪失趣味。作為宗教史與文化史的一部分,此類研究引領我們洞察人類的宗教活動,以及我們的靈魂與人類其他生活形態間的關係。研究各種思想之歷史──無論是宗教、哲學或政治,都是對自我認同、身心成就之意義的探索。烏托邦歷史的迷人之處不亞於冶金歷史或化學工程。
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而言,還有其他更合理的原因,讓它具有研究價值。長久以來相當受歡迎的哲學教義從來就還沒完全死亡(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與今日的經濟學意義並不相同,它是一種哲學的理想),他們改變語彙,在祕密文化中存活下來,即使很少被看見,他們仍然可以吸引人們,或使人懼怕。馬克思主義屬於思想/智識傳統,以及19、20世紀政治史的範疇;從字面意義來看,馬克思主義—與其不斷反覆(通常也令人發顫)的自我標榜為科學理論—顯然是有趣的。然而,將這哲學付諸行動帶來難以言喻的悲劇性後果,使人類受苦:私有財產與市場被廢止,受共有與國產計畫支配,而這計畫絕無實現之可能。19世紀末,無政府主義者發現若要將人類社會轉化為一個大集中營,馬克思主義信條是很好的藍圖。這當然不是馬克思本意,但卻是他所構思之美好光榮的烏托邦所帶來的無可避免的影響。
理論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在某些學術機構的長廊拖著腳步,一息半存。因其內容貧瘠,故不難想像它會在某些拙劣但響亮的運動支持下獲得力量。這些運動事實上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本質已無關聯,只是在尋找可以模棱兩可地以資本主義或反資本主義的形式存在之議題。
共產意識型態似乎處於死後僵直的狀態,而仍然利用此意識型態的政權極度可憎,因此看似復蘇無望。但我們別急著預言(或反預言),因為利用並受此意識型態滋養的社會仍可能重起爐灶。也許病毒只是處在潛伏期,等待下一個機會,誰能說得準呢?畢竟人類長久以來都夢想著擁有一個完美的社會。
這三本書於1968到1976年間於波蘭寫成,當時只能夢想著他們在波蘭出版。1976年到1978年間,由巴黎的文學出版社(the Institut Litteraire)出版,再由波蘭的地下出版社翻印。1988年,亞涅克斯(Aneks)出版社在倫敦出版新的波蘭文版本。直到2000年,審查制度與共產政權跨臺之後,這本書才在波蘭由涅斯克(Zysk)出版社合法出版。法拉(P. S.
Falla)翻譯的英文版於197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Press)出版。之後有德文、荷蘭文、義大利文、塞爾維亞文與西班牙文譯本。有人告訴我也有中文譯本,但我從未見過。法文譯本只出版二冊,菲雅德(Fayard)出版社無法說明為何沒有第三冊,但我猜是怕引起法國左派分子憤怒,出版社無法冒此風險。
緒論(節錄)
卡爾‧馬克思是個德國哲學家。這似乎不算是特別長知識的話,然而這話卻不像起初顯得那樣陳舊無聊。回想茹爾‧米希勒當年講授英國史,開講總要先交代一句:「諸位先生!英吉利本是個海島。」是單知道英國是海島,還是根據這一點來解釋英國的歷史,大有區別;如此解釋英國歷史,這一點自有一種意義。同樣,說馬克思是德國哲學家,也許言外之意是把他的思想當作經濟分析和政治學說方面出現的一個體系,對他的思想及其在哲學上或歷史上的重要性做出某種解釋。這類講法既不是不講自明,也不是沒有爭議。而且,雖然現在我們很清楚,馬克思是個哲學家,半世紀以前情況可不大一樣。在第二國際時期,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倒認為他是某個經濟、社會理論的創造者。照有些人說來,這個理論同各式各樣的形而上學見解或認識論見解是一致的;而有些人抱持的看法是,恩格斯為這個理論提供了哲學基礎,因此嚴格地說,馬克思主義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精心創造的兩、三個部分理論合成的一套理論。
目前把馬克思主義看作共產主義所依據的思想傳統,受到人們的注意,這種狀況的政治背景大家都很熟悉。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還有他們的反對派,全關心現代共產主義從思想上和制度上講,是不是馬克思學說嫡系後裔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有三種最常見的回答,可以簡短截說表達如下:(1)是,現代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十足體現,這證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帶來奴役、暴政和犯罪的主義;(2)是,現代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十足體現,因此表示人類有獲得解放和幸福的希望;(3)不是,我們所了解的那種共產主義乃是對馬克思的信條嚴重的歪曲,是對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背叛。第一種回答相當於老一套反共產主義正統思想;第二種回答相當於老一套共產主義正統思想;第三種回答相當於形形色色批判的、修正主義的,或「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然而,本書的論點是,這問題的提法就錯了,不值得回答。說得確切些,像「現代世界的各種問題怎樣能根據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或「假若馬克思能看見他的信徒們的所作所為,他會有什麼意見?」這種問題是沒辦法回答的。這兩個問題都是無下文的問題,沒有什麼合理辦法尋求一個答案。馬克思主義不包含任何具體方法,解決馬克思沒對自己提出過的問題,或是他那個時代還不存在的問題。假使他的壽命再延長九十歲,他總不得不改變意見,而如何改變,是我們無從揣測的。
認為共產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或「歪曲」的人,可說是企圖替馬克思開脫對自稱他的精神後裔的人的行動應負的責任。同樣,16、17世紀的異端和裂教者也曾指責羅馬教會背叛自己的使命,企圖辯明聖保羅跟古羅馬人的腐化沒有連帶關係。同樣,尼采的崇拜者也是企圖為他的名字洗刷對納粹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應有的罪責。這種企圖的思想動機倒還清楚明瞭,可是在說明問題方面的價值幾乎等於零。有充分證據表明,一切社會運動都要按種種實際情況來解釋,而運動所依據的思想本源,運動要對它保持忠誠的那個思想本源,只是決定運動所採取的形式及運動的思想行動方式的各個因素中的一個。因此,我們可以預先肯定,沒有一個政治運動或宗教運動,是自己的經典中斷言的那個運動的「本質」的十足表明;但另一方面,這種經典也不僅僅是消極的東西,對運動的進程還是發揮著一種特有的影響。通常情況是,自稱代表某個思想體系的社會力量,比那個思想體系強大,但是對自己的傳統也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性。
因此,思想史家面臨的問題,不在於拿某一種思想的「本質」同這種思想在社會運動上的實際「存在」相比較。問題倒是,原來的思想是怎樣地、是由於什麼情況,成了那麼多相互敵對的不同力量的會合點;換句話說,這種思想本身有什麼模稜兩可的地方和彼此矛盾的傾向,結果造成了它過去的那種發展?有一個大家知道的事實,在文化史上還沒有例外的記載,就是一切重要思想隨著自己的影響不斷擴大,總難免發生分裂和分化。所以,要問在現代世界上究竟誰是「真」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只有你認定正宗著作是可靠的真理來源,誰解釋正宗著作解釋得對,誰一定是掌握著真理,只有你不越出這個思想觀點的圈子,才會發生上面那樣的問題。其實,我們沒有理由不承認,各派運動和思想無論彼此多麼對立,同樣有資格打馬克思的旗號—本書沒有講的一些極端情況不算。同樣,要追問「誰是真正的亞里斯多德派,是阿威羅伊、是托馬斯‧阿奎那、還是龐蓬納齊?」,或者問「誰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喀爾文、是埃拉斯摩、是貝拉民、還是羅耀拉?」,也問不出個名堂。後一個問題對基督教信徒來說也許有一種什麼意義,可是跟思想史毫不相干。不過,歷史學家可能關心考究,到底是原始基督教裡的什麼成分,使得像喀爾文、埃拉斯摩、貝拉民和羅耀拉那樣不同類型的人能引據同一種原始資料。換句話說,歷史學家認真對待人的思想,不認為思想完全服從客觀事件,不具有自身的生命活力(因為假如那樣,研究它就沒有什麼意義了),但是歷史學家卻不信思想代代相傳而意義會沒有多少改變。
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正當的研究項目,但是根據這種關係並不能判定哪些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研究思想史的人,即便是站在意識型態以外,也不等於是站在我們生活周圍的文化以外。相反的,講思想的歷史,尤其是講一向影響最大的思想的歷史,多少可說是練習做文化上的自我批評。這本書裡,我打算根據一種觀點研究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和托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中對於納粹主義及其同德國文化的關係所採取的觀點相似。托馬斯‧曼有理由說納粹主義和德國文化沒有瓜葛,或者說它是對德國文化粗暴的否定和惡意歪曲。不過,事實上他沒有這樣講,而是追問希特勒運動和納粹思想這一類現象怎麼會發生在德國,能發生在德國,是由於德國文化中的什麼成分?他斷言,每一個德國人從納粹主義的獸行中會認出甚至從德國民族文化最高尚的代表人物身上(這是要害)也能看出的文化真面貌的變形,叫他不寒而慄。曼不願意照平常做法,忽略納粹主義的身世問題不談,也不願主張納粹主義沒有正當資格承受一部分德國文化遺產。他反倒坦率地批評那種文化,而他自己正是那種文化的一部分,一個創造性成分。只說納粹思想是對尼采思想的拙劣模仿當然是不夠的,因為拙劣模仿的根本性質是能幫助人認出原人物。納粹黨叫他們的超人讀《權力意志》;要說這件事純屬偶然,本來同樣也可能選中《實踐理性批判》,這話沒有用。問題不是定尼采的「罪名」,尼采個人對他的著作被別人利用沒有責任;然而,別人是如此利用了他的著作,這勢必引起大家的驚恐,不能認為同如何理解他的內心本意無關而不予考慮。聖保羅個人不應對異端裁判所和15世紀末的羅馬教會負責,但是探討問題的人,不論是不是基督教徒,總不願意講基督教讓卑劣的教宗和主教們的行為給敗壞了或歪曲了;他一定盡力要發現,在保羅書信中是什麼東西等到時機成熟造成了卑劣的犯罪行為。我們對待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應當抱同樣態度。按這個意義說,本書不但是一派思想的歷史概述,而且分析了這派思想的奇異命運。這派思想開始是普羅米修斯式的人道主義,發展的頂峰是史達林的萬惡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