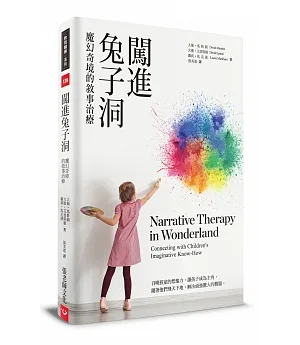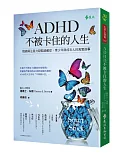推薦序一
期待與兒少及成長精靈會合
秦安琪 敘事治療咨詢、培訓及督導
回想二十多年前第一次閱讀麥克‧懷特和大衛‧艾普斯頓的《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的時候,對敘事治療的理念感到深奧無比,它對每個人的尊重卻吸引著正對於輔導專業和輔導理論感到懷疑的我。到 2007 年於挪威參加敘事與社群實踐國際會議時,才有機會聽大衛‧艾普斯頓的課;七年後,也就是 2014年,我攻讀德威曲中心(Dulwich
Centre)及澳洲墨爾本大學合辦的敘事與社群實踐碩士課程時,有機會在澳洲與他相遇,感覺就像與好朋友久別重逢一樣。能夠在此刻一口氣閱讀他與大衛‧馬斯頓和蘿莉的《闖進兔子洞:魔幻奇境的敘事治療》,讓我感到無比榮幸!
這本書著實太棒了!讓我觸動的地方很多:
「自我是透過故事呈現的」,藉著每位兒少的故事,我有機會與久違了的「想像力」再次相遇。也不曉得打從何時開始,我們都學習了社會文化對兒少的要求——「父母與專業人士同樣密切觀察孩子是否有違背正常規範的行為。孩子必須學習尊敬權威,集中注意力,管理憤怒,延遲滿足,自我規範,好好和別人一起玩」——這個清單誰都不會感到陌生,我們的想像力從此被冰封了。
漸漸地兒少都按照這些要求而編織生活,偶爾對以上規條提出質疑或做出與常規不一樣的行為時,彷彿會為本來「無知」的身分添上另一個「反叛」、「有問題」的稱號。「生命寶藏訪問」讓我們見證的「不只是空洞的讚美,還能奠定基礎發展更理想的身分敘述,凸顯兒少在關鍵時刻能做好因應問題的準備……透過那些孔洞我們或能看到新的世界,對兒少產生意想不到的了解」。此刻,腦海浮現了一些父母和兒少在發現他們獨特的才能時那燦爛的笑容。
兒少的事實應由他們自己來建構,邀請孩子「引領我們,讓我們驚奇」,因他們對問題其實有深厚的了解,他們有足夠智慧與那些繞著他們的「床鋪蟲」、「掃興鬼」、「偷竊」、「尷尬」、「麻煩」、「睡眠賊」、「鬼祟的大號和小號」、「男子漢守則」、「壞脾氣」等比拚,令這些被外化的問題頓時變得力弱,父母和其他人的支持和鼓勵讓兒少對抗問題的力量壯大了,兒少更可隨心編織喜歡的故事和圖案。本書提供了很多外化提問,對於實踐有很大的裨益。
對於「如何做個稱職的母親」及「責母傾向」這兩個議題,讓我深感共鳴。以往任職兒少保護工作的時候,目睹專業人士只把注意力放在暴力行為及對有虐兒行為的母親的指責。曾在一個工作坊聽到一位資深的臨床心理諮詢師說,邀請母親出席多元專業會議是費時的事,因為她們根本不懂專業人士在說什麼,只管要求她們上一些管教兒少的課程便可。今天回憶這個片段,仍令我感到不安的是那台「專業地雷」——高高在上的專業團隊,想要塑造一個又一個「模範母親」,因為她做了傷害兒少的「偏差做法」,為此必須付出代價。敘事不只讓兒少的生命寶藏呈現,也專注於考量父母「對子女的人生做了何種寶貴的貢獻」,讓母親跟兒少一樣,擁有問題以外的身分認同。
「任何事都有可能!」讀罷這本書,好像也喚醒我的想像力,期待與兒少及成長精靈會合,大伙兒走進魔幻世界、潛入地下迷宮、飛越天空之城,讓兒少揮動手上的魔術棒,按他們的價值觀和偏好,編織憧憬的故事。
前言
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一起掉進兔子洞吧!
一個大約四歲的男孩和爸爸走進義式冰淇淋咖啡廳,作者們正在那裡有一搭沒一搭地打電腦。電腦游標期待地閃爍著,坐在角落的作者羨慕地看著男孩眼前那一大球堅果巧克力冰淇淋(還有棉花糖),他顯然無視大人在乎的熱量問題。男孩吃完最後一口,站起來走向不遠處的一個小噴泉。父親猜到他在想什麼,從口袋拿出各種硬幣,找出一分錢給他。男孩拿著錢幣走回噴泉邊,低聲說了些聽不清楚的話,不情願地把錢幣丟進去。回到座位,父親問他許什麼願,他說:「變成忍者龜。」父親笑了,給他第二分錢,同樣的儀式又重複一遍。
「這次你許什麼願?」父親問。
「公主。」男孩答。蘿莉轉向夥伴,低聲嘲諷:「他已經被父權制度吸收了!」
「說不定他許願要當公主?」大衛‧馬斯頓無力地假設。男孩拿著下一分錢回去許了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願望,「動物」。
「哪一種?」父親問。
「河馬。」男孩宣布。在他們離去之前男孩最後一次走向噴泉,親吻外緣的陶石,可能是為了好運,或表示感謝它的魔力。父子看起來一樣滿意,各自在剛剛展演的戲劇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男孩許的願望無疑不同於任何大人敢於懷抱的夢想,這不足為奇。對比較成熟性格的人而言,願望通常是可計算的類型,例如沒有負債的生活、豪宅、中樂透、減肥,或者愛情——基本上都是世俗的東西——雖然有些夢想實現的機會可能比較低。但對一個眼神充滿驚嘆的小孩而言*1,卻可以化不可能為可信。小說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描述兒少透過奔放的想像力超越日常經驗的潛能:
雖然受制於學校以及家庭的管教(尤其是後者),就我們所受的束縛而言,孩提時期遠比任何時期更自由。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在孩提時期自由等同於想像力,這時期一切都是可能的,相較於長大後為了生存不能不順從,還得適應工作的節奏,順服代代相傳且符合一般標準的規則,孩提時期的我們擁有更奔放的自由可以超越家庭與學校,可以活得更獨立。童年的我們是出色的魔術師。(2011, p.58)
身為治療師,我們也許會為孩子的豐富想像力感到驚奇,但因為年紀已長,我們不太可能體認孩子的幻想對於治療有多重要,或是會想要全心全意支持他們的計畫。如果我們讓想像力有發揮空間,理由可能不是要直接運用想像力,而是想到大家比較熟悉的概念,例如培養投契關係,確保安全,讓兒少放縱一下,或是觀察與解讀投射性扮演(projective
play)。既然已經有治療計畫,哪裡還需要想像力?(我可以三言兩語說出問題的名稱!躁鬱症。下一位患者!反應性依附障礙症(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下一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下一位!強迫症(OCD)。下一位!)問題可以快速解決,接著就只需要採取指定措施,然後便可望還給家長快樂、穩定、專注的孩子。
但當我們想要把世界變得完全可以理解,是否為了理論上已獲得證明的道理而犧牲了這世界的奧妙?我們這些專業治療師是否成功地將自己的想像力塵封起來?我們是否只有在不會有任何損失的情況下才保留幻想空間?或者當我們碰到真的很重要的事物時,才恰恰更迫切需要想像力?
在這整本書裡,我們嘗試說明一次又一次訴諸想像力是可能的,即使是極嚴重的狀況也不例外。不論多麼了不得的問題都可以被忍者龜捉弄,被(支持女性主義的)公主以智取勝,甚至被飢餓的河馬完全吞噬。大人無論遭遇何種真實的問題,都不太可能在腦中激發出這樣的靈感,但對兒少而言,卻是輕而易舉。
為何要進入魔幻奇境?
整齊的院子若是有兔子鑽洞,通常會被認為很討厭。每年春天,都可看到人們到本地的五金店和園藝行,希望能探知害蟲防治的祕訣(如驅蟲劑、毒餌、陷阱)。任何冷靜的人絕不會夢想溜下兔子洞,像卡羅(Lewis Carroll)所寫的《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裡的主角一樣,熱切追逐毛茸茸的搗蛋鬼。當害蟲或瘟疫這類問題侵入我們原本秩序井然的世界,這是非常嚴重的,似乎沒有什麼空間可以留給想像或幻想。但當愛麗絲遇到毛茸茸的闖入者,那情景可一點都不尋常。首先,穿著背心的白兔會檢查牠的小兔爪拿著的懷錶。還有牠會說話—苦惱喊道:「天啊!天啊!我來不及了!( Carroll, 2000,
p.2)」愛麗絲看到牠快速鑽入地下時並不感到失望。就像任何富有想像力的小孩,她快速投入未知的世界。
在我們與兒少的會談中,進入反面世界的意思並不是物理上的分離(physical departure),而是從可預期的世界進入不可預期的領域;從所謂事物的正常狀態轉移到絕對不同的狀態。空間的結構被改變了,我們仰賴兒少帶引我們走入新的領域,而不必步出房間一步。我們會讓這種新奇的互動將我們帶到一個缺口,或是心理學家透納(Victor
Turner)(1969)所謂的「閾限」(limen)或臨界點(threshold)。這個進入點可望帶來「假設性的」以及充滿可能性的新奇世界,而不是「指示性的」、在我們眼前顯而易見的東西。這時我們可能會產生一股動力,能夠「跨越或消除結構化、制式化的關係所賴以建立的規範,伴隨前所未有的強烈經驗」(Turner, 1969,
p.128)。兒少可以沿著傳統日常生活的邊緣行走以尋找通道,就像他們最喜歡的故事書或電影裡的人物,一旦找到通道,便會發現有太多東西都是可能的。歐姬芙(Deborah O’Keefe)解釋幻想文學如何為我們指出一條路:
發現神奇所在的虛構角色就像參與宗教儀式的人通過某種「門檻」。幻想故事裡最讓人難忘的場景通常都是轉折的時刻:像是路易斯(C. S. Lewis)書裡的小孩爬進舊衣櫃,出來卻是納尼亞,或是愛麗絲爬進兔子洞,或桃樂絲在屋子裡跟著龍捲風飛上天(2003, p.79)。
我們感興趣的正是這種轉折。這樣的觀點讓我們發現可想像的世界更加豐富,兒少也絕不是軟弱無助的。我們非常願意和兒少站在一起,而不是剪掉他們的想像翅膀,將他們往下拉到有憑有據的理解基礎。歐姬芙認為,嘗試穿越到未知的領域可能對我們都有好處:「人都需要透過造訪不凡的宇宙來看清平凡的生活,這個需要不會隨著長大而消失」(2003,
p.21)。兒少從真實世界前往想像的空間時,我們可能必須提供支持與鼓勵,但過程中他們會給予回報,因為我們會重新熟悉充滿可能性的世界——那是我們已拋在腦後、幾乎遺忘的世界。
發揮想像力的訣竅
這是一本關於想像力的書—包括我們可以在兒少及家屬身上激發的想像力,以及他們可以喚醒我們這些治療師的想像力。我們將想像力定義為「靈活地因應非預期的或不尋常問題的能力」(Imagination, 1992,
p.645)。愛麗絲展開冒險,大膽跟隨白兔進入坑洞沒多久,便明白了邏輯不太管用。一開始她嘗試遵循大人的一貫做法,在墜落的同時一邊思考,是否可透過估計經緯度找出自己的定位,或是計算長長的墜落過程經過了多遠的路程—也許「下墜了四千哩」(Carroll, 2000,
p.4)。但這種計算沒什麼效果。之後她領悟到,要衡量這個新環境需要不同的東西,不是「上面的世界」喜歡倚賴的理性方法可勝任的。就以愛麗絲想要走動時遇到的問題為例。她吃了一塊神奇餅乾後長了九呎高,她明白底下距離遙遠的雙腳可能會故意造反。說不定雙腳會突然將她帶走,這荒謬(但完全可能發生)的狀況讓她大感困擾,因此決定寄聖誕卡片給她的腳,希望這憂慮的舉動會說服雙腳,讓雙腳「乖乖聽話」——至少撐過聖誕節。
我們在為兒少治療時就是希望保留空間給發揮想像力的這類訣竅。大人往往在專家的教導下採取誠懇但老掉牙的建議,到頭來沒有留下多少空間給想像力。有時候我們會感覺專家提議的觀念愈來愈狹窄(如結構、設限、正向強化、示範、界線、一致性等),同時卻又將建議提供給愈來愈廣泛的對象,不太考量家庭與社會生活的差異性。這種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案可能會讓家庭與治療師都變得更加不敏銳。
我們在愛麗絲的故事裡尋求靈感,決定仰賴兒少,在我們的協助與親人的支持下,他們也許會展現讓人意想不到的能力。我們嘗試透過下列方式培養「任何事都有可能」的感覺,發揮創意解決問題:
☆發掘兒少的生命寶藏*2 與發揮想像力的訣竅
☆以個別的、異想天開的敘述取代精神醫學的術語
☆請兒少發揮想像力,實踐他們的價值觀與人生願景
☆依據兒少的技能與知識,找出最好的方法來面對與處理問題*3
☆寄望治療師能體認,這個時機最需要的知識是知道如何發揮想像力
☆號召社會見證兒少的豐富想像力
敘事治療的基礎
書中敘述的所有做法都受到特定的信念影響。我們秉持敘事治療的傳統,廣納各學科的知識以形成直接治療的獨特方法,包括女性主義理論、社會學、人類學、後結構主義與敘事理論等。乍看之下,你可能會想,這些學科和兒少及其想像力、生活上碰到的問題有什麼關係?我必須對年輕案主有多少了解才能開始進行敘事治療?我可以直接跳過理論進入治療嗎(第二章)?答案既肯定又否定。你當然可以採取敘事治療的元素,加入眾所周知的那些技巧(如「我喜歡將問題外化!」),完全不用深入探討是基於何種哲學與政治基礎,我們要捨棄將問題內化與個別化的那種較熟悉的語言治療法(Epston,
1998; Tomm, 1989; White,
1988-1989)。你不必跑到最近的大學招生處申請法國後結構主義理論的額外學位,但思考敘事的基礎可能有幫助,因為我們的這種治療法是建立在一套原則底下。但我們會盡所有力量將觀念的闡述與治療的片段結合,讓內容更活潑。最後我們希望能達到適當的平衡,提供的敘事治療觀點能支撐讀者的想像力,而不是只有我們的想像力。我們的想像力縱使有可取之處(這要由讀者自己決定),但肯定有其侷限。
現在容我們簡單介紹這每一種學科如何影響我們為兒少及家屬提供的治療方法:
☆女性主義理論提醒我們要努力追求平等的立足點。如果一個族群(如大人或專 業人士)掌握高於另一個族群(如孩子和家屬)的優勢,便會壓抑想像力,會強調某一套偏見與做法較優異,讓人相信那就是真實。我們牢記這一點,努力將專業人士的地位與不同世代的階級扁平化。
☆社會學讓我們看到社會秩序的鬆散與破綻,創造力通常就是從傳統習俗的邊緣趁隙突圍。我們把希望寄託在直接治療的邊緣,在那裡想像力可能正等著被開發,兒少更有機會發揮助力。
☆人類學提醒我們這世界的多樣化,以及了解各種文化的重要性,鼓勵我們將自己的西方文化視為「異文化」(Bourdieu, 1988),而不是自居中心地位,彷彿我們是照亮前路的太陽。人類學讓我們懂得謙虛,避免麻木地將其他族類視為「次等文化」。我們也許比兒少強大,也許懂得他們還不懂的事,但如果我們追蹤他們留下的線索,說不定會抵達不虛此行的神奇所在。
☆後結構主義告訴我們,解讀自我的方式永遠不只一種,讓我們可以拋開一定要追根究柢或追究人性本質的科學觀念。當我們面對被附上字母標籤的兒少—就像運動外套或浴巾一樣,如 OCD(強迫症)、ODD(對立性反抗症)、CD(行為規範障礙症)、 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DMDD(破壞性情緒失控症)、BP(邊緣型人格)—我們不會支持一個看似穩定的醫學觀點,而會準備好尋找矛盾與差異。唯有當我們以好奇取代確信不疑,以「可能被巫師激發的驚奇感」取代科學思維(Bracken & Thomas, 2005, p.193),我們的想像力才會被開啟,才能運用多重表現的身分認同。
☆敘事理論告訴我們,自我是透過故事呈現的。當我們或別人在敘說關於我們的故事時,自我便有了清晰的面貌。當我們嘗試了解兒少的困境時,不會接受疏離的、審慎推敲的理由,因為邏輯「是沒有感情的」(Bruner, 1986, p.13)。年幼主角的奮鬥與勝利可以動態地融入故事,推動情節的開展。如此,透過「藝術形式」呈現自我的重述方式將被注入新的活力( Bruner, 1986,
p.13)。敘事一旦有了動力,便能開始流傳,展現一定的力量與真實感。關於敘事的形式我們在第一章還有很多探討。
本書宗旨
我們希望在書裡凸顯孩子有能力採取意向立場(intentional
stance),能透過極富想像力的方式促成戲劇化的改變。這樣的經驗不僅不會讓人感到沉重,還能帶來活力,因為孩子會以夥伴的角色參與家庭生活,而不是過客;或更糟糕的,等著被填塞的空容器。我們從愛麗絲的故事得到啟示,她在跋涉危險的世界時絕非溫馴的乖乖牌。同樣的,我們寄望兒少與頑強驚人的問題正面交鋒時,有能力決定周詳考量過的態度。在我們的提問協助下,他們會在穩固的基礎上展現果斷的行動,在開展中的戲劇裡扮演吃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