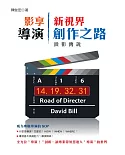前言
很榮幸能夠擔任《服裝設計之路》的編輯,有機會向讀者介紹當代幾位最具才華的設計師。除了〈傳奇大師〉的章節外,本書介紹的服裝設計師皆是仍在執業的專業人士,而且大多數在我聯繫邀訪之際都正參與電影製作。雖然他們在百忙之中撥出時間受訪,但每一位皆大方分享個人的成長背景、奮鬥歷程與設計哲學。本書收錄的藝術作品皆商借於設計師的作品集,繪圖手稿大多數是首次出版。
電影服裝設計師的職責其實很簡單:為電影裡的角色設計服裝。身為設計師,我們對劇情的貢獻不只是為劇組提供服裝。「戲服」一詞無法說明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極度優雅,但「戲服」這個詞很平庸,總讓人聯想到萬聖節、化妝舞會的衣服、遊行、主題樂園、狂歡節、奇幻或古裝片的衣服。
對服裝設計師來說,「服裝設計圖」(costume picture)指的只是下一個即將啟動的案子。關於電影服裝設計主要目標的定義相當模糊,業界和大眾因而對我們的職責更加困惑。電影服裝設計的目標有二,兩者同樣重要:一是創造可信的角色(人物)以支撐敘事;其次是構圖,亦即透過色彩、質地和服裝線條,為景框畫面提供平衡感。
除了創造電影中可信的人物,服裝設計師也為電影的每個「景框」增色。如果對話是電影的旋律,那麼色彩就是為電影提供和弦—完整的視覺整體感,或「風格」。服裝設計師在創造「風格」時,必須建立有力的參考標準。除了法國皇后瑪麗.安東妮的裙撐,或特別強調各年代剪裁的服飾外,電影中的服裝也為場景增添質地和色彩。設計師有很多選擇。事實上,設計師因為當代電影服裝設計的選擇實在「太多」而感覺困擾。
有些設計師偏好純色布料、平面的極簡,有些則偏好使用多種版型,認為這是角色層次的關鍵。為了配合電影的感覺或導演的風格,設計師或許會因而改變設計方式。
現代風的帽T,成為取代當代型男的紳士帽和外套的另一種選擇,例如艾迪.墨菲(Eddie Murphy)在我設計的《你整我,我整你》(Trading Places, 1983)穿的紅色帽T,或是阿姆(Eminem)在《街頭痞子》(8 Mile)穿的灰色帽T(由馬克‧布里吉〔Mark Bridges〕設計),以及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在《不可能的任務:鬼影行動》(Mission Impossible-Ghost Protocol, 2011)中穿的黑色帽T(由麥克‧卡普蘭〔Michael Kaplan〕設計)。帽T可烘托臉孔,並讓目光焦點集中在演員最重要的五官—雙眼,讓演員的台詞更具張力。
色彩是導演和服裝設計師的強大工具,用來支撐敘事,並創造出一致的虛構空間。色彩和配樂一樣,能將場景的情緒迅速傳達給觀眾。由於服裝隨著角色而移動,服裝設計師創作的,可說是動態的藝術。
成功的服裝必須融入劇情,而且必須天衣無縫地交織於電影敘事與視覺的大織錦中。艾姬‧傑拉德‧羅傑斯(Aggie Guerard Rogers)認為︰「我希望服裝不要干擾編劇的台詞。」與一九二○年代標準相較之下,一九三○年代的好萊塢風格已較為寫實,但電影無論如何不能一再訴諸華麗。
電影不是模特兒眼神空洞走上伸展台的時尚秀。他們之所以被稱為「模特兒」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是展示時裝設計師想像力的活衣架。服裝和角色和它們具體呈現的角色一樣,都必須在故事的脈絡中演進。
好萊塢一再為視覺效果凌駕劇情的錯誤決定付出代價。從早期充斥華麗布景及珠光寶氣臨時演員的的史詩鉅片,到今日的超級英雄特效饗宴,好萊塢總是忍不住秀過了頭。服裝設計在電影視覺效果當中當然占有一席之地,不過,不管螢幕上的人物有多少(或他們穿著什麼),觀眾有印象且記得的,是看了一部很棒的電影。能讓觀眾入戲才是最好的電影,與預算無關。當觀眾什麼都沒「注意」到,表示他們已完全相信電影呈現的一切,並且完全融入劇情之中。
無論是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的《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 1999, 卡普蘭設計),或是約翰.塞爾斯(John Sayles)的《致命警徽》(Lone Star, 1996, 雪依‧康莉芙〔Shay
Cunliffe〕設計),電影的每套服裝都是為電影劇情演進的特定時刻而設計的,在某個場景當中,由某位演員穿在身上,以特定方式打燈。設計師裁製電影服裝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導演和劇本的需求。在現代的喜劇和劇情片,觀眾不會注意到演員的服裝,但卻會受到影響。
《致命警徽》是多角色的群戲表演,有多重敘事線同時發展。塞爾斯將複雜的敘事交織成一個精彩的故事,並在康莉芙的協助下,創造出觀眾不會混淆的明確角色。芬奇的《鬥陣俱樂部》是人格分裂為二的故事,分別透過性感的泰勒‧德頓(Tyler Durden)和拘謹的旁白敘事者來呈現。卡普蘭說,這兩個角色迥異的穿著,看起來就像為兩部不同電影設計的。
以上兩個精彩的服裝設計藝術範例,只會在現代服裝的世界出現,因為對觀眾來說,這些角色有可能是他們認識的人,或是他們自己。服裝設計的微妙之處,絕不只是與某個年代的袖子剪裁相關的事,而是深入角色的靈魂。
本書訪談的設計師中,許多位都與導演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例如,布里吉正在為保羅‧湯瑪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電影做服裝設計,這是他們合作的第六部電影。儘管兩人已共事長達十六年,但布里吉說:「這不代表我們不會偶有爭執。」史匹柏的長期戰友喬安娜‧裘絲頓(Joanna
Johnston)也有同感:「我也喜歡與不同導演合作,但我喜歡曾經共事過的導演對我的信任。」珍蒂‧葉慈(Janty Yates)與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正在合作第七部電影。
與導演固定合作能培養默契,節省寶貴時間。現代電影的前製過程如同壓力鍋,與導演已有合作關係相當重要,因為服裝設計師在極短時間內交出的成果會帶來很大影響。由於對揣摩導演想法較有信心,設計師對某個角色或服裝能放膽發揮,但在新的合作關係,則會選擇打安全。
服裝是電影工作者敘事時的工具之一。設計師的挑戰是落實導演的想像,將劇本(及特定的一刻)搬上大螢幕。沒有劇本就沒有場景,也沒有服裝。設計師的工作離不開戲劇脈絡,也是群體合作關係的一環:對白、演員、攝影、天氣、季節、時間、動作編排及其他各種疑難雜症,全都是挑戰。
茱蒂安娜‧瑪可芙斯基(Judianna
Makovsky)說:「有趣的是,許多導演不一定對服裝有興趣……他們對角色及整體世界的視覺效果比較感興趣。」聰明的導演請電影設計師來整合劇本的視覺世界。溝通是其中的關鍵—導演必須告訴設計師他們的想法。服裝設計師和美術總監不是憑空發想的。劇本定義了人物、場地,融合概念與想像,設計師的工作則是讓劇本成真,因此劇本才會被稱為電影設計的語言。設計師喜愛夥伴型的導演,因為他們能啟發設計師交出最佳的成果。
一般認為,古裝片和奇幻電影必須交給專業人士,有時導演和設計師會被歸類於某個電影類型。瑪莉‧佐佛絲(Mary Zophres)回想:「……拍完《謀殺綠腳趾》(The Big Lebowski, 1998)後,柯恩兄弟打給我:『我們接下來要拍的片叫《霹靂高手》(Oh, Brother Where Art
Thou)。』許多好萊塢導演大概會找設計過一九三○年代背景的設計師,但他們不這麼想,他們認為我能設計出他們寫出來的所有東西。」
除了少數例外,電影服裝設計師在職業生涯中參與的主要是現代背景電影。所有設計師都在電影類型和預算間拉鋸,而且每個專案的挑戰都不同。
業界很多人誤以為只要找造型師,並在片中置入行銷時尚名牌和配件就可以了,這在必須取悅廣告客戶的時尚雜誌是常見的事。在以現代為背景的電影裡,服裝設計師選擇某件衣服或某個配件,挑選的根據是角色在他的人生中可能會有的偏好。我們做的是「藝術模仿人生」。
沒有人會在一天之內,在時尚大道或購物中心的某家商店買齊所有衣物,電影裡的角色也不會。現實生活中,除了名流,一般人不會有造型師,也不會每天從頭到腳都穿湯姆‧福特(Tom Ford)或馬克‧雅各布(Marc Jacobs)等名牌服飾,電影裡的角色也不會。
我們都走混搭風:偏愛的舊衣服和新買的戰利品、買來的和借來的衣物,或是祖傳的和他人贈送的首飾。我們穿著的每樣物件都有自己的故事,因此也會預期螢幕上的角色同樣如此。更重要的是,演員必須讓身上的服飾真的就像是他的。衣著和人物都必須有真實感。
時裝設計有時是劇情的重點,《龍鳳配》(Sabrina, 1954)就是一個例子。女主角莎賓娜(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飾)前往巴黎的廚藝學校,回家時已徹底改頭換面,帶回塞滿紀梵希(Hubert de Givenchy)高級禮服的行李箱。在這部電影裡,才華洋溢的導演比利‧・懷德(Billy
Wilder)容許「外表」成為視覺焦點,讓衣著為赫本演戲。她的衣櫃反映了她的轉變—她已在巴黎「成長」。
這類戲劇效果能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穿著Parada的惡魔》(The Devil Wears Prada, 2006, 派翠西亞‧菲爾德〔Patricia Field〕設計)是另一個將衣服做為敘事推動器的灰姑娘故事。為了呈現喜劇效果和鋪陳劇情,菲爾德的服裝費了許多心思。依芳.布蕾克(Yvonne
Blake)如此說明設計師在現代電影中扮演的角色:「對我而言,電影服裝設計和時尚是兩種非常、非常不同的元素。我嘗試創造的是人物。我研究這個人物的心理,以及他們的穿著為什麼應該是這樣或那樣。設計師必須『正確掌握』許多細節。服裝體現角色在劇本某一刻的心理、社會和情緒狀態。除非設計師了解角色,否則不可能為演員設計服裝。」
服裝設計師認為,現代背景的電影比華麗的古裝片複雜多了。不過就像人們以為演員只要隨興發揮對白,他們和電影產業都覺得現代服裝—日常衣著—設計沒什麼,因為每個人每天早上都會換衣服,每個人也都自認是現代服裝的專家。動人的電影必須是觀眾看完後會很肯定地說:「我認識那個人。」
茱莉‧薇絲(Julie Weiss)也有同感:「我的體會是:我的工作是讓角色看起來像觀眾認識的人。在這一行,有些我崇拜的設計師知道如何營造魅力,我受的訓練也教我這麼做。不過,當演員投入他扮演的角色卻始終不對勁時,我有了不同想法。我知道無論哪個年份或哪個年代,我都能發揮作用。」如今的電影設計比以往更強調正確且如實呈現劇本,而且更深入研究。
無論預算高低,每部電影的服裝都有多種來源:購置的、租用的和自製的。時裝業的宣傳造成人們的誤解,以為現代背景的電影服裝是設計師去麥迪遜大道或龐德街的精品店「血拼」來的,連時裝設計師的服裝標籤都沒拿下來就出現在大螢幕上。只要有時裝設計師的服飾出現在大螢幕,就會被大肆廣告和報導。通常製片廠和時裝品牌簽訂的「置入行銷」合約,由品牌提供資金,減少製片廠的製作成本。這不是理想的電影設計。
時間是設計師的勁敵,選角延後完成,開拍日近在眼前,趕去營業到深夜的購物中心是設計師的唯一選擇。在最好的情況下,服裝設計師能夠修改、試裝、染色及作舊處理。設計師的最大挑戰,是混搭時裝,並讓標籤消失。莎朗‧戴維絲(Sharen Davis)補充說:「我很難對某些女演員簡單說明高級時裝設計。對我來說,現代服裝很具挑戰性—必須發揮最大創意,因為我必須設計出角色獨有的外型。」
設計師的工作是深入角色的中心(靈魂),找出這個人物的本質—無論衣服是訂製的、購買的,或從演員的衣櫃角落挑出來的。時裝設計師常認為自己的風格受到某部經典電影或現代電影影響,但他們很少歸功於電影的服裝設計師。然而,激發他們的不是衣服;他們和觀眾一樣,深受故事、電影及迷人角色所吸引,這些角色由於演員深具魅力的特質而煥發著令人著迷的魔力。
迷人角色界定動人的故事風格,劇本由隱身幕後的劇作家撰寫,由千變萬化的演員飾演,至於設計角色外型的,則是為實事求是的導演工作的服裝設計師。參與電影製作時,設計師不會想到引領時尚潮流。電影通常在殺青後一年上映,服裝設計師很難思考如何影響時尚。
首先,觀眾必須愛上電影裡的故事。卡普蘭回想:「《閃舞》(Flashdance, 1983,
卡普蘭設計)上映時造成的潮流躍上《時代》(Time)雜誌,但電影的服裝設計師從未被提及。我從未想過要開創任何風潮。有位導演曾對我說:『我們希望你像《閃舞》一樣引導流行。』我回答:『你知道這跟你也有關係嗎?』他說:『真的嗎?』我說:『對,這部電影必須大賣才行。』」無論是《閃舞》、《安妮‧霍爾》(Annie Hall, 1977, 露絲‧莫莉〔Ruth
Morley〕設計),或是《華爾街》(Wall Street, 1987, 艾倫‧蜜洛吉尼克〔Ellen Mirojnick〕設計),時尚潮流是由能與觀眾產生共鳴的電影和角色所創造的。一部電影大賣或慘賠,全靠觀眾決定。設計師只是以相同的熱誠和執著來投入每部電影。
近十年來,電影的前製作業時間日漸縮短。沒錯,科技已有長足的進步,服裝設計師大量使用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來節省時間。這些手持裝置減少在辦公室、拍攝場地、更衣室或布料店的詢問和確認時間:紅色或黃色、有圖案或素色、短的或長的、棉的或羊毛的?
服裝設計師掃描布料,寄PDF檔或軟體處理過的試裝圖給在世界另一頭的製片廠裡的導演、製片和主管。實體的紙本參考聖經已經式微,設計師架設的網站取而代之,讓創意團隊隨時研究,或讓擔綱的演員瀏覽。現在的設計師很少有時間坐在繪圖桌繪圖,服裝繪圖師成為他們對外的代筆者—如果在前製期能有時間監督繪圖就好了,但通常沒有。從這一行的「傳奇大師」活躍時期到現在,我們在電影裡扮演的角色並無太大改變,但電影業已非往昔。
電影服裝設計一直是高壓力的工作。即使是好萊塢黃金時期如日中天的米高梅,設計師仍未有「足夠」預算或「足夠」時間,完美地完成工作。本書訪談的每位設計師都提到過去十年電影業的巨大改變。康莉芙說明這行的壓力日益增加:「大製作的電影壓力很沉重,我們面對各方接踵而來的意見,他們不斷強調在製作面投入的資金。」許多設計師透過電子郵件寄試裝照給從未見過的高層和製作人,而且並不清楚對方在電影製作層面扮演的角色。
選角太晚完成是這一行的風險之一。設計師經常必須處理這種狀況:星期日才敲定接演的演員,星期一一大早就要定裝上工。這種惡劣的情況已是司空見慣。康莉芙進一步指出:「創作一套服裝所需的時間還是一樣長,試裝修改所需的時間、取得布料和裁剪服裝的時間都絲毫未減。」早上五點上工時,我們已經做好要日夜不休、艱辛抗戰的心理準備。過程很辛苦。裘絲頓反應:「電影服裝設計的性質介於馬戲團和戰爭之間,隨時或每天都交替處這兩個極端狀況之間。」
關於人物的設計屬於「關鍵」劇組成員的職責,但直到今天,美國導演工會(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的季刊並未比照攝影師、美術總監和剪接師,在季刊內列出服裝設計師名單,但所有工作人員都會列名電影演職員名單。美國導演工會長期的忽視,使電影業不公義的性別歧視更惡化。此外,服裝設計師的薪資與其他關鍵劇組成員無法相提並論。我們的最低薪資依照工會合約規定,但這份合約卻受限於製片廠長年不合時宜的前例。
實際上,依照現行合約,服裝設計師的底薪幾乎比剛入行的美術總監少了三分之一。足以提供參考的薪資標竿並不存在。放諸國際標準,服裝設計師的周薪不及攝影師、美術總監和剪接師的最低薪資。無論從業的設計師是男是女,服裝設計都被視為「女人的工作」,薪酬(及價值)相對較低。有些人可能會很驚訝,電影服裝設計師屬於「雇傭」工作者,因而無法擁有其設計手稿,或設計的服裝的所有權。從其設計衍生的產品,如公仔、娃娃、萬聖節服裝或時裝,不僅沒有掛上設計師的名字,他們也無法得到任何收益。
身為職業服裝設計師,我們希望人們能更了解我們的工作內容。至於我們在電影劇組扮演關鍵角色的誤解,我認為可透過電影從業人員教育來導正。例如,戲劇學學士或碩士班應開設服裝設計課,性質是戲劇學院必修課程,戲劇導演(如當年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青年法蘭西斯‧柯波拉)就可在電影服裝部門實習。然而,除了UCLA戲劇、電影暨電視學院等新興的整合性課程外,服裝設計在電影製作及導演課程都付之闕如,學生電影的服裝設計皆不受重視,或後來才補強。此外,大學電影系所的核心課程,必須包含完整的電影美術設計課程。
戲劇學院的教育方式能反映專業的電影製作過程,亦即十幾位專業人士一起分工合作。這樣的教育方式可帶來無窮效益:當天分洋溢的電影人進入業界時,他們可以製作更精緻、更具美感的電影。電影人必須了解,電影角色不是一開拍就能完美登場,而是必須經過設計才能完美現身。
服裝設計師對電影經典影像有如此大的貢獻,經常令選修我的電影課程的學生大感驚訝。我展示我設計的印地安納瓊斯(Indiana Jones)、瑪可芙斯基設計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以及佩妮‧蘿絲(Penny Rose)設計的史傑克船長(Captain Jack Sparrow)。
許多學生導演完全不知如何創造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但對於畫龍點睛的服裝設計增加影片深度的效果感到興奮。電影的主題是人,服裝設計師的工作正是打造人物。
本書收錄許多珍貴資料,書中交織的人生歷程、事業經歷及故事,則是意外的禮物。許多設計師踏入這一行的開始,是紐約的芭芭拉‧瑪德拉(Barbara Matera)戲服公司,或倫敦的班曼及納森(Bermans and Nathans)戲服公司。儘管書中各章節的時間橫跨兩個世代,地理和經濟背景相差甚大,但走向電影服裝設計之路的過程有許多相近之處。
書中訪談的所有設計師皆在年輕時就鋒芒畢露。每位設計師很早就知道自己與眾不同,且擁有特殊天分。他們的父母大多也認為他們相當獨特,並全力支持他們的教育及藝術事業。有些設計師從擔任米蕾娜.凱諾尼羅(Milena Canonero)、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等傳奇設計師的助理開始入行;好幾位從知名設計師理察‧洪南(Richard
Hornung)與茱蒂‧蘭斯金(Judy Ruskin)的助理起步;也有人起初擔任的是劇場服裝設計師或電影服裝總監;還有幾位來自時裝界,他們因為一時靈光一閃,踏入了電影服裝設計。
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大多數服裝設計師都因為恩師大方的轉介而更上一層樓。在他們人生中的某一刻,他們的指導者選擇推掉某份設計工作,而這個機會讓他們開展了事業的康莊大道。
服裝設計師彼此也慷慨提攜。瑪德拉與麥克斯‧班曼(Max Berman)、蒙帝‧班曼(Monty Berman)常將設計案轉介給公司最得力的助理和服裝設計師。西部戲服(Western Costume Company)及加州的戲服公司風氣也同樣無私。國家廣播電台(NBC)服裝部門總監安吉‧瓊絲(Ange
Jones)是我的守護天使。薇絲的名字分別在三個章節被康莉芙、卡普蘭及羅傑斯提起。她的影響力遍及一個世代的眾多設計師。本書的設計師因共同的愛好而凝聚在一起:歷史、文學、戲劇、園藝、時尚和電影。
莫利吉歐‧米南諾提(Maurizio Millenotti)回憶童年時所說的話,正可代表這個群體:「電影是無可倫比的大驚奇。其中的冒險和奢華世界令人心炫神迷。」
電影服裝設計圈的奇才人數不斷倍增,我們也是好萊塢啟發大量國際電影藝術家的寫照:科琳‧艾特伍德(Colleen Atwood, 二○一一年同時擔任兩部電影的服裝設計師,隨時都能出版自己的專書)、喬‧奧里希(Joe Aulisi)、金‧芭瑞特(Kym Barrett)、約翰‧布魯菲爾德(John Bloomfield)、康索娜塔‧波悠(Consolata
Boyle)、亞歷珊黛‧伯恩(Alexandra Byrne)、艾德爾多‧卡斯楚(Eduardo Castro)、張叔平(William Chang)、陳昌敏(Chen Changmin)、菲麗絲‧達頓(Phyllis Dalton)、恩潔拉‧迪克森(Ngila Dickson)、約翰‧鄧恩(John Dunn)、賈桂林‧杜倫(Jacqueline
Durran)、瑪麗‧法蘭西(Marie France)、露薏絲‧法洛格麗(Louise Frogley)、丹尼‧格利克(Danny Glicker)、茱莉‧哈里斯(Julie Harris)、貝西‧海曼(Betsy Heimann)、黛博拉‧哈波(Deborah Hopper)、蓋瑞‧瓊斯(Gary Jones)、蕾妮‧恩利茲‧卡夫斯(Renee Ehrlich
Kalfus)、查爾斯‧諾德(Charles Knode)、露絲‧麥爾絲(Ruth Myers)、麥克‧歐康納(Michael O’Connor)、丹尼爾‧奧蘭迪(Daniel Orlandi)、碧翠絲‧安魯納‧帕斯德(Beatrix Aruna Pasztor)、凱倫‧佩曲(Karen Patch)、珍妮特‧帕德森(Janet
Patterson)、亞麗安娜‧菲利浦斯(Arianna Phillips)、蘇菲‧德拉克夫(Sophie De Rakoff)、湯姆‧蘭德(Tom Rand)、梅‧蘿絲(May Routh)、梅耶絲‧魯比歐(Mayes Rubeo)、麗塔‧萊亞克(Rita Ryack)、黛博拉‧史考特(Deborah Scott)、安娜‧薛波(Anna B.
Shepard)、瑪琳‧史都華(Marlene Stewart)、佟華苗(Huamiao Tong)、崔西‧戴南(Tracy Tynan)、艾咪‧華達(Emi Wada)、賈桂林‧威絲特(Jacqueline West)、麥克‧威金森(Michael Wilkinson),以及其他眾多設計師。
服裝設計師的人數如此龐大,輕易都可再編出十本本書的附篇。決定訪談哪些設計師已如此困難,讀者可以想像,我在撰寫五篇「傳奇人物」章節時面臨的抉擇與兩難。我需要更多篇幅!席奧尼‧奧德瑞吉(Theoni V. Aldredge)、馬汀‧艾倫(Martin Allen)、米洛‧安德森(Milo
Anderson)、安德瑞-奧尼(Andre-Ani)、唐菲爾德(Donfeld)、皮耶洛‧格拉帝(Piero Gherardi)、哈里斯、洪南、歐里-凱利(Orry-Kelly)、安娜‧希爾‧瓊絲頓(Anna Hill Johnston)、伯納‧紐曼(Bernard Newman)、多莉‧崔麗(Dolly Tree)、娜塔麗‧菲莎特(Natalie
Visart)及薇拉‧威絲特(Vera West)只是優異設計師的一小部分,他們個別的事業成就都足以出版專書,但大多默默無名,甚至連最狂熱的電影迷也未聞其名。如今,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在創造角色,引領時尚風潮,推展流行文化,開創電影史。
本書訪談的設計師有些是我的好友,有些是我長久以來期待見面的。我仰慕他們已久,他們作品的美感,以及對工作的熱誠和使命感讓我敬仰。我聯繫的設計師大多數手上都有製作中的案子,置身遠方的拍攝地點。他們查過時區後,提出適合的時間,熱情且和善地回應我的邀訪。我的朋友奧伯多‧法利納(Alberto
Farina)及他優秀的妻子奇亞拉(Chiara)協助聯絡人在羅馬的米南諾提,並將我的問題繕打和翻譯,代我訪問他。我很感謝他們極為寶貴的協助。
我還要感謝艾琳諾‧艾可狄比絲(Elinor Actipis)的堅持不懈。她原本在美國愛思唯爾出版社(Elsevier USA)任職,我與此書系的編輯麥克‧古里吉(Mike Goodridge)透過她的牽線而認識。在催促焦點出版社(Focal Press)改版其電影服裝設計書多年後,伊雷克斯出版社(Ilex Publisher)及副發行人亞當‧朱利波(Adam
Juliper)挺身擔下此重任。伊雷克斯的責任編輯娜塔利亞‧普萊絲-卡伯瑞拉(Natalia Price-Caberera)不辭勞苦地策劃本書,以破紀錄的時間出版本書,同時還生了個寶寶!莎娜‧納康柏(Zara Larcombe)及塔拉‧葛拉赫(Tara Gallagher)與訪談設計師密切聯繫,取得他們的手稿和個人影像,並在我挑選之後,與柯布萊服裝設計研究中心(Copley
Center)的助理納塔莎‧魯賓(Natasha Rubin)及柯柏影像庫(Kobal / Picture Desk)協調,取得劇照,收錄至這本精美的專書內。
服裝設計師常說:「我們的成就是團隊的成就。」我們在職演員表的職稱是「服裝設計師」,但我們的成果向來代表才華洋溢的團隊的貢獻。沒有團隊支援,我們絕無法完成工作。本書的編寫過程也是如此,我的頭銜是作者和編輯,但寫作和研究是由我的工作室共同完成的。我的創意成果也得力於多人協助,包括我任教的UCLA戲劇、電影暨電視學院及泰瑞‧史瓦茲(Teri
Schwartz)院長、戲劇系及系主任麥克‧海克特(Michael Hackett)與艾倫‧阿姆斯壯(Alan Armstrong)、慷慨的資助者大衛‧柯布萊(David Copley)、我的研究生丹妮艾拉‧卡爾唐(Daniella Cartun)、漢娜‧葛林(Hannah Green)、崔西‧娜都(Traci LaDue)、賈桂林‧馬汀內茲(Jacqueline
Martinez)與凱特玲‧塔曼吉(Caitlin Talmage)、忠實的校友萊頓‧包爾斯(Leighton Bowers)、「真正的」專家多立安‧漢纳威(Dorian Hannaway)與布蘭達‧萊斯‧波薩達(Brenda Royce Posada),以及我的先生和最熱情的啦啦隊長—約翰‧蘭迪斯(John
Landis)。要不是聰慧的助理納塔莎,我的進度將永遠停留在第一頁。她就像米其林餐廳的副主廚一樣,兼顧我眾多的工作:統籌本書的研究、手稿、三冊在二○一二年出版的書籍內文、支援我二○一二年在倫敦維多莉亞及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展覽,同時管理UCLA柯布萊服裝設計研究中心的行政事務。多虧納塔莎、約翰及我最棒的團隊,我的名字才得以出現在本書封面。
「設計師若能讓觀眾感覺演員就是角色本身,這樣的服裝設計就很成功。」(艾迪絲‧海德〔Edith Head〕,八屆奧斯卡最佳服裝設計獎得主。)
黛博拉‧納都曼‧蘭迪斯(Deborah Nadoolman Landis)
2012年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