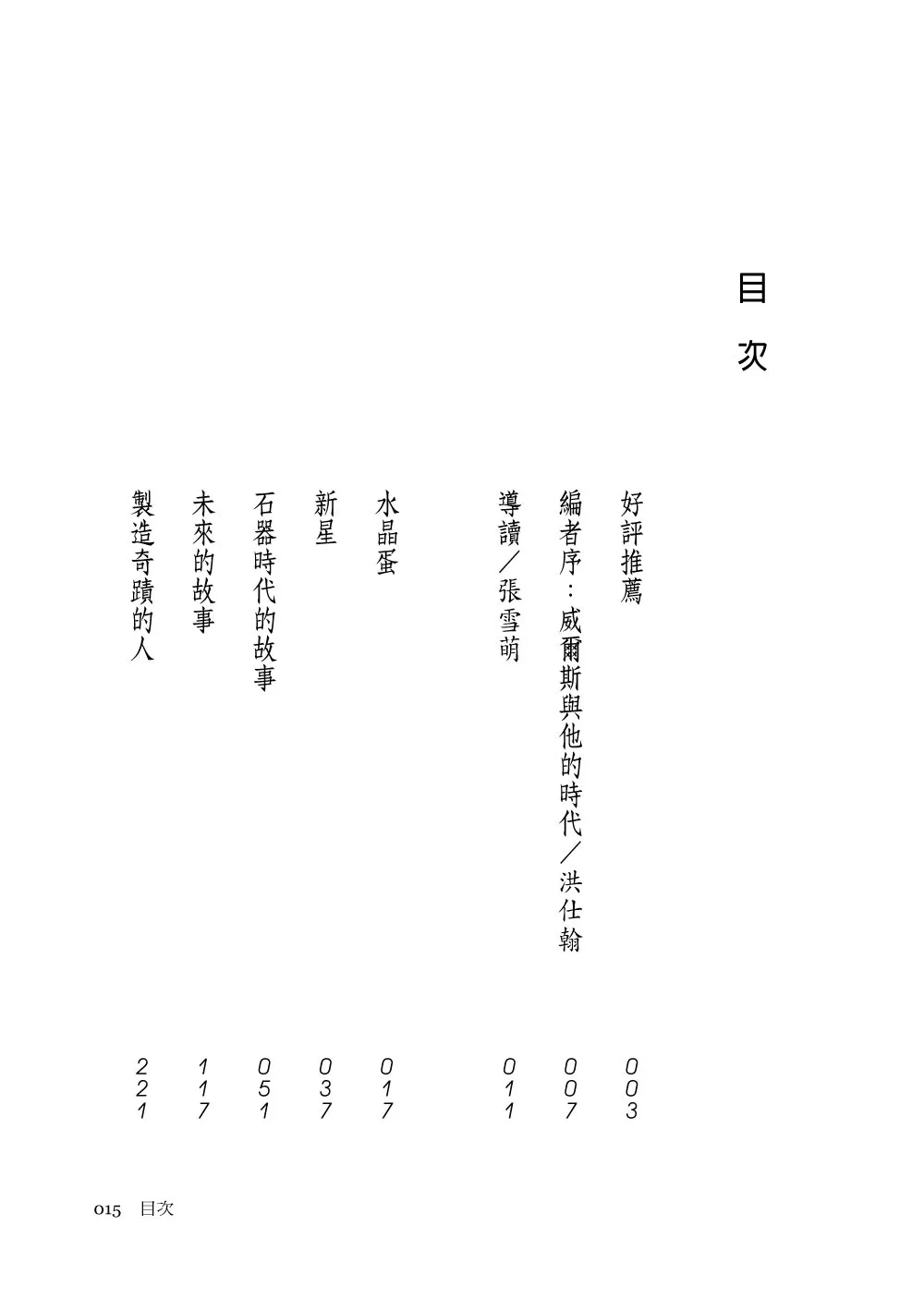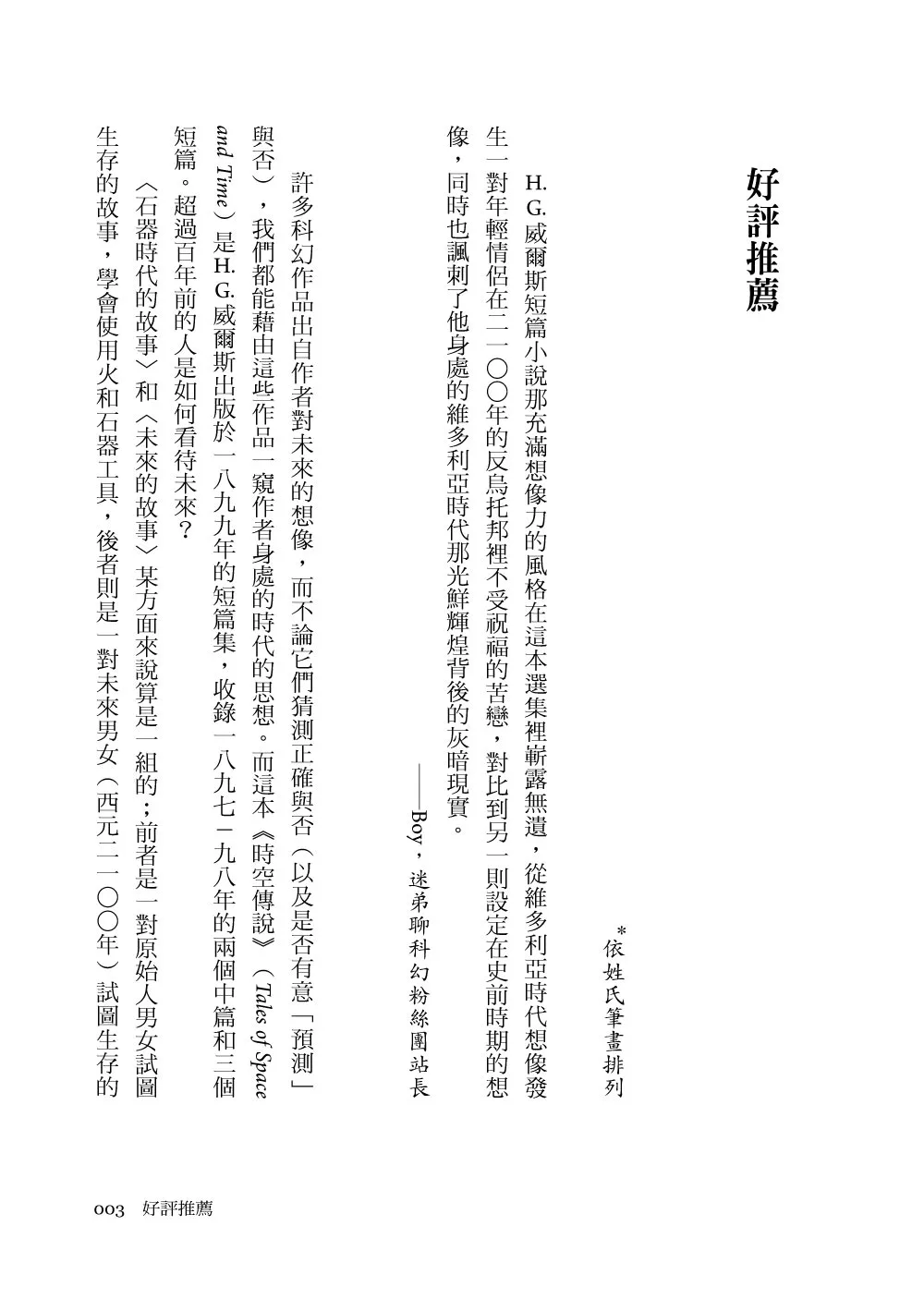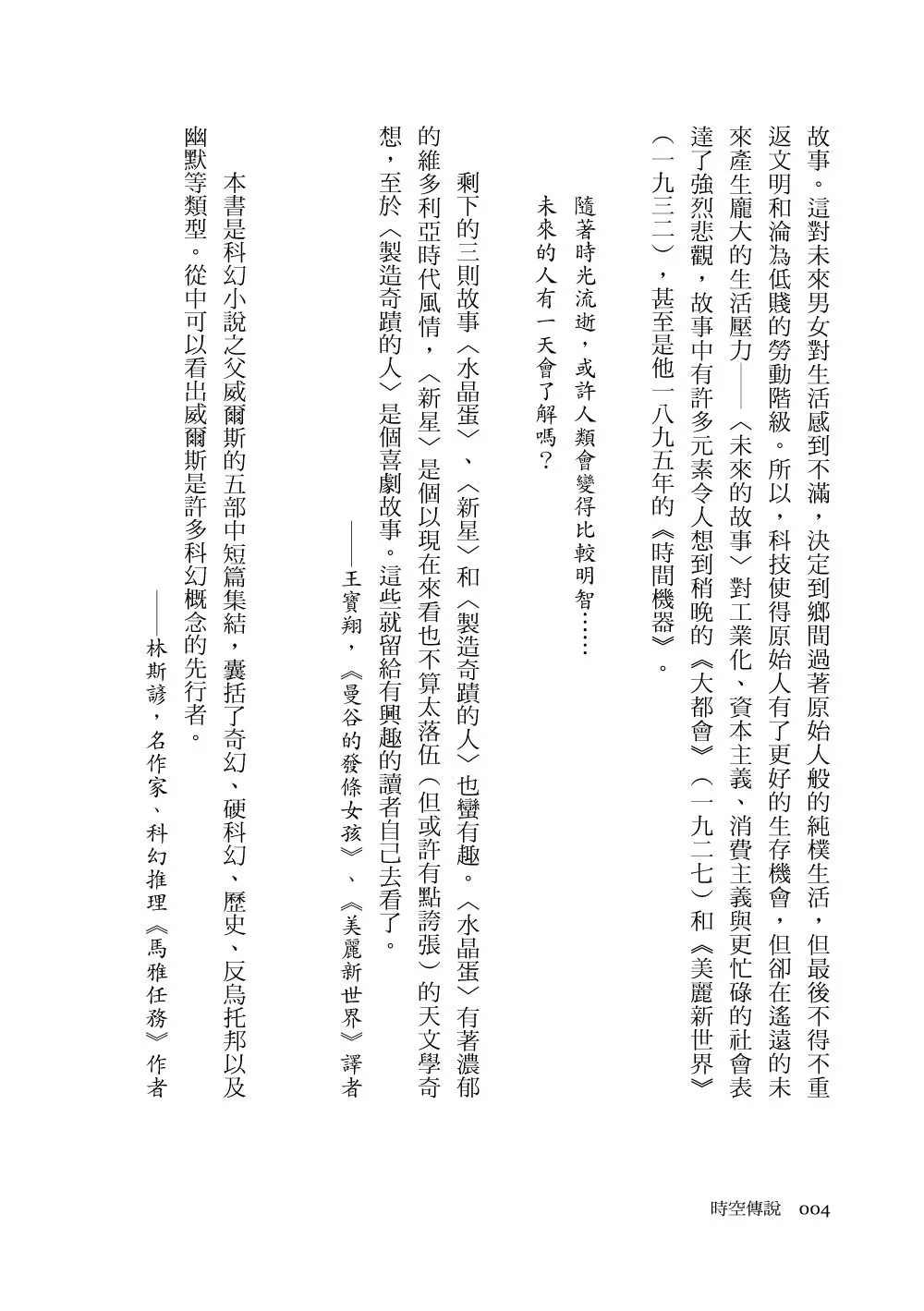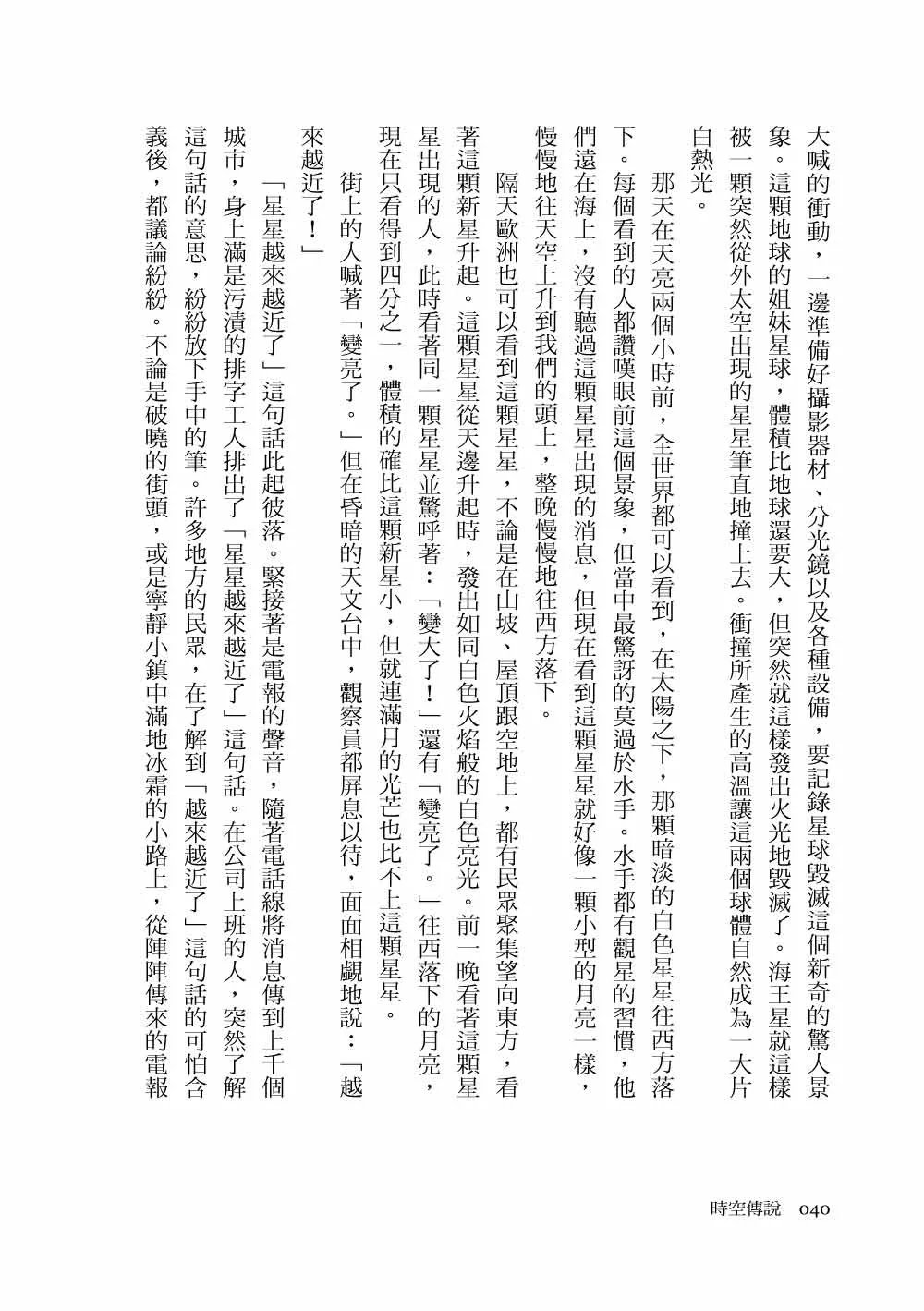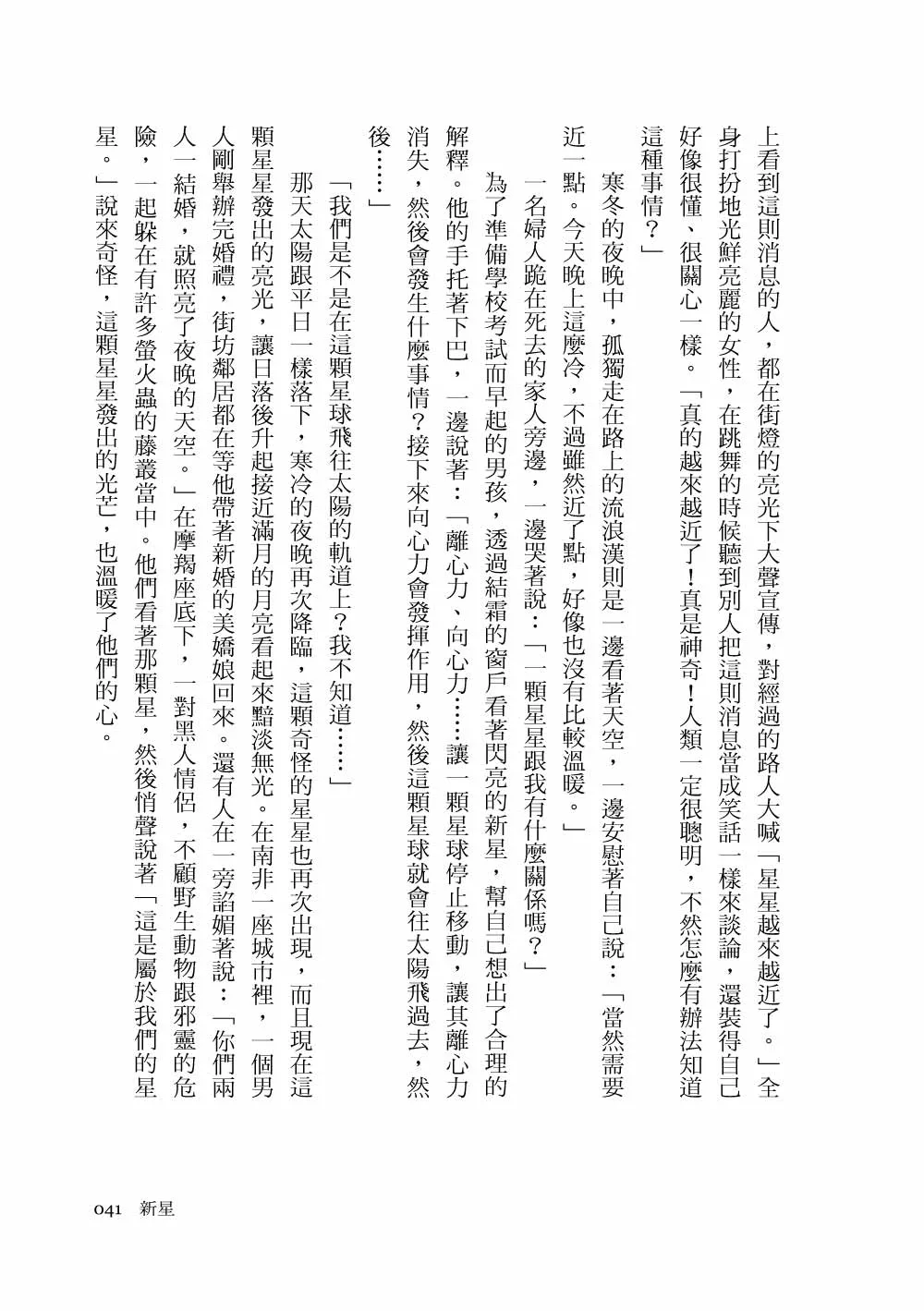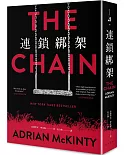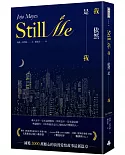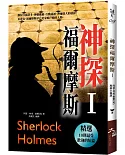編者序
威爾斯與他的時代
洪仕翰
「所有的過去只是開始中的開始,曾經發生過的一切也只不過是黎明前的曙光。」──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時空傳說》(Tales of Space and
Time)是一部誕生於世紀之交的作品,那是距今將近一百二十個年頭的一八九七年。一八九七年是個甚麼樣的年代?東方的大清帝國剛遭逢甲午戰敗,意圖改革的戊戌變法仍有如襁褓中的嬰兒,隨時都會夭折;在西方,美國企業家才剛製造了第一輛福特汽車,而義大利工程師才正要探索無線電這項深奧的科技。那是個沒有手機、飛機與電視機的年代,人們對「高速公路」與「網路」也沒有任何概念。被譽為科幻之父的英國文學家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正是在那樣的年代裡寫下了本書中充滿想像力的情節。他是如何辦到的?想必不會是如同〈製造奇蹟的人〉的主角般獲得天啟。沒有人可以脫離自身的時代,文學家自然也不例外。在進入本書之前,我們必須先稍微回顧威爾斯撰寫本書的背景脈絡,因為理解威爾斯所身處的時代,有助於我們更理解威爾斯與他的《時空傳說》。
威爾斯所處的時代,正是十九世紀末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英國在經過工業革命後,靠著殖民擴張與貿易而成為了全世界最先進、最工業化的國家之一。在那個年代,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彷彿成了新的自然鐵律,應許一個美好的未來;在那個年代,日不落帝國也還尚未經過波爾戰爭(Boer War,
1899-1902)與世界大戰的殘酷洗禮,前途看似一片美好。然而也是在那個年代,觀察入微的威爾斯就已透過小說的文字,「寓言」般地提出了自己對未來的隱憂。相較於同時期對科學進步較為樂觀的作家來說──例如同樣被譽為科幻文學之父、比威爾斯稍早一些的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威爾斯的文字總顯得有些悲觀。威爾斯筆下的未來反映了更多的社會現實,包括看似永無止境的都市化、日益擴大的階級矛盾、來自外界的入侵或戰爭,以及大規模災難出現的可能。
本書所收錄的〈新星〉短篇,幾乎可說是最早具體描寫「慧星撞地球」這樣災難式場景的科幻小說之一。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好萊塢與電子媒體推波助瀾下,慧星撞地球這類末世災難題材早已是十分常見的創作套路,但在影像技術尚不普及的當年,威爾斯的作品是當時讀者想像這類災難情景的重要依據。威爾斯日後還會繼續描繪這種從天而降的災難,包括描寫火星人入侵的《世界大戰》與預測德國空襲倫敦、造成無數生靈塗炭的《空中戰爭》等經典災難作品。一個經典的案例是,一九三八年十月的某個上午,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了由威爾斯小說《世界大戰》所改編的廣播劇,卻意外導致上千名只聽到部分片段的群眾陷入恐慌。今天的讀者或許很難想像,廣播電臺會需要不厭其煩地重申廣播劇內容「純屬虛構」。這樣的「事實」,恰恰說明了在那個虛構與現實不易區分的年代裡,威爾斯所捕捉到的災難隱憂是確實存在於許多人心中的。
隱憂不只來自外部,還存在於社會本身。在〈未來的故事〉中,威爾斯用帶有(反)烏托邦色彩的筆觸(反烏托邦作為一個文類亦是十九世紀開始的現象),描繪了二十二世紀的倫敦:機器逐漸取代人力、人們捨棄農業與人口爆炸則導致了無止境的都市化,並最終使都市人無法離開都市過活。這一切對威爾斯來說都不是毫無根據的空想,因為在威爾斯從出生到寫作本書的這段時間裡,英國的人口幾乎整整翻了一倍,工業機械取代傳統人力與都市化等問題更是如影隨行。在生產方式改變的衝擊下,「階級問題」很快就成為社會的另一大隱憂。狄更斯的小說離威爾斯的年代並不會很遙遠,威爾斯也早在他的成名作《時間機器》中就碰觸到了階級問題──生活在地面上與的底下的兩個世界幾乎就是兩個不同階級的投射。而在〈未來的故事〉中,生活在都市下層的中下階級就連職業都必須接受分配,只能靠著微薄的工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苟延殘喘──與上層社會的富裕形成巨大的反差。今日的讀者或許不禁要懷疑,在這種近乎絕望的貧富差距下,怎麼還沒有人發動革命。而這,或許也是另一個威爾斯無法自外於他所處時代之處。
在威爾斯一生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他都是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他和同時期的大文豪蕭伯納一樣,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成員,他們主張溫和的社會主義改革,反對激進的革命與階級鬥爭。也因此,儘管威爾斯在作品中屢屢碰提及了階級矛盾的隱憂,但他的筆法仍舊是相對溫和與保守的。在〈未來的故事〉中,威爾斯並未給讀者一個不寒而慄的悲劇故事,階級分野並未導致血腥鬥爭,故事最後更靠著一位上層階級的「善念」而得以有相對圓滿的結局。
或許是同樣出身於中下中產階級的緣故,威爾斯最擅長描寫的,既不是上層階級也不是社會底層的苦勞階級,而是那在維多利亞時代急速膨脹的中產階級。他在〈水晶蛋〉這篇小說中對古董店主人卡夫先生的細緻描寫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威爾斯幾乎是用一種鉅細靡遺的方式在描寫卡夫先生店中的擺設,以及他那不怎麼幸福的家庭。要不是靠著一顆在古董雜物中偶然發現的水晶蛋,卡夫先生恐怕這輩子都沒辦法擺脫他那沉悶的生活,去一窺來自新世界的異星樣貌。這樣從日常細節中作展開的寫法或許有助於拉近作品與當時讀者之間的距離。這種加強與現實間連結的寫法,就連在〈石器時代的故事〉這篇奇幻空想風格較重的作品中也可一窺一二。即使表面上是寫石器時代,篇中仍可四處看到威爾斯對當時英格蘭的地貌與人群的連結。
誠然,《時空傳說》中所收錄的五篇故事,對於常閱讀類型小說的現代讀者來說或許並不新鮮。而這自然是因為從威爾斯以降,科幻小說業已經歷了上百年的發展,諸如末世災難、反烏托邦與未來世界等各種子類型更是名作輩出。然而如果我們回望一百二十年前,理解威爾斯與他的時代,那麼我們就能稍稍體會到威爾斯當年在科幻小說這個文類的貢獻。與一百二十年前的威爾斯不同,今天的我們已有了電視機、飛機與手機,但不變的是我們依舊想望著未來,站在威爾斯與他的後繼者們的肩膀上,用穿越時空的傳說,想望著未來。
洪仕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