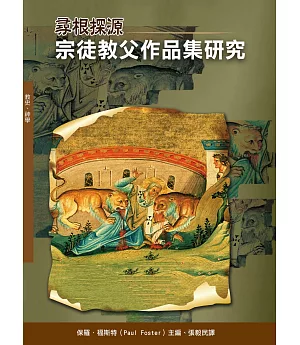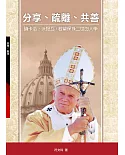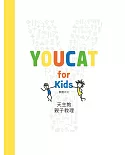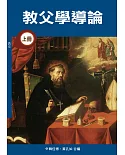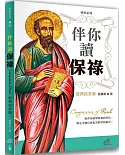本書為近年來英語學界之宗徒教父(the Apostolic Fathers)重要的學術專書。全書共十二章,各章針對單一宗徒教父作品,由重量級學者撰寫專文;文字言簡意賅、扼要精闢,作者們更對近一、兩百年來學界研究成果提出分析評論。
本書介紹的十一件宗徒教父作品,各自反映了不同的文體,與分歧多元的神學面貌。形式上,這十一件作品有教會規範、書信、講道詞、護教作品、神視文字、論述早期基督徒傳統的斷簡殘篇,以及宗徒教父作者之一的殉道歷程。
它們反映出主曆第一世紀中到第二世紀末的宗徒教父,如何以極有創意的方式,表達出重要的訊息。閱讀宗徒教父作品,是一個領略初期教會多元面貌與特質的經驗;也讓我們認識到:宗徒教父為了促使教會的團結合一,奮鬥征戰的實況,以及如何讓原本強調自發性的、神恩性的信仰團體,轉型成為一個強調組織架構、重視宗徒傳統、大公而合一的、神聖的天主教會。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保羅.福斯特教授(Professor Paul Foster)
英國愛丁堡大學神學院新約語言、文學與神學教授。開設課程:新約(對觀福音)、聖經希臘文、文本分析、非正典福音書。學術出版眾多。
保羅.福斯特教授(Professor Paul Foster)
英國愛丁堡大學神學院新約語言、文學與神學教授。開設課程:新約(對觀福音)、聖經希臘文、文本分析、非正典福音書。學術出版眾多。
目錄
譯者序(張毅民)/ V
序:在教父的教導中聖化我們的信仰(陳菀茹)/VII
編審者的話(盧德)/XI
中文譯本之翻譯對照表(附:英文原書縮寫對照表)/XIII
緒 論……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
第一章 宗徒教父與基督徒身分的建立與奮鬥……賀穆‧寇斯特(Helmut Koester)/14
第二章 《十二宗徒訓誨錄》......強納森‧德拉普(Jonathan Draper)/33
第三章 《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簡介......安德魯‧國瑞(Andrew Gregory)/49
第四章 《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與基督徒講道詞意義......保羅‧帕維斯(Paul Parvis)/69
第五章 〈巴必亞碎篇〉……查爾斯‧希爾(Charles E. Hills)/88
第六章 《夸德拉圖斯護教書》……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09
第七章 《何而馬的牧者》......約瑟夫‧范海頓(Joseph Verheyden)/129
第八章 《巴爾納伯書信》......詹姆士‧查頓‧佩吉(James Carleton Paget)/145
第九章 安提約基亞依納爵的書信......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61
第十章 斯米納的鮑理嘉與《致斐理伯人書》......麥可‧何穆(Michael Holmes)/207
第十一章 《鮑理嘉殉道致命紀》......撒拉‧帕維斯(Sara Parvis)/238
第十二章 《致刁臬督書》......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275
序:在教父的教導中聖化我們的信仰(陳菀茹)/VII
編審者的話(盧德)/XI
中文譯本之翻譯對照表(附:英文原書縮寫對照表)/XIII
緒 論……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
第一章 宗徒教父與基督徒身分的建立與奮鬥……賀穆‧寇斯特(Helmut Koester)/14
第二章 《十二宗徒訓誨錄》......強納森‧德拉普(Jonathan Draper)/33
第三章 《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簡介......安德魯‧國瑞(Andrew Gregory)/49
第四章 《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與基督徒講道詞意義......保羅‧帕維斯(Paul Parvis)/69
第五章 〈巴必亞碎篇〉……查爾斯‧希爾(Charles E. Hills)/88
第六章 《夸德拉圖斯護教書》……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09
第七章 《何而馬的牧者》......約瑟夫‧范海頓(Joseph Verheyden)/129
第八章 《巴爾納伯書信》......詹姆士‧查頓‧佩吉(James Carleton Paget)/145
第九章 安提約基亞依納爵的書信......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161
第十章 斯米納的鮑理嘉與《致斐理伯人書》......麥可‧何穆(Michael Holmes)/207
第十一章 《鮑理嘉殉道致命紀》......撒拉‧帕維斯(Sara Parvis)/238
第十二章 《致刁臬督書》......保羅‧福斯特(Paul Foster)/275
序
緒論
二、本書中關於各作品的討論
宗徒教父作品的研究成果近年來不斷增加,反映出學界日趨理解宗徒教父作品的重要性。許多研究宗徒教父作品的學者們想知道,緊接在新約時代之後的教會到底發生了什麼;對此我們應知道,其實若干「宗徒教父作品」的成書年代與新約作品的年代,有重疊的、也有早於新約作品的。另外,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只針對作品本身深入研究,因為這些作品為後人提供一個窗口,讓人得以窺見第二世紀時,在面臨重大改變與關鍵轉型階段的基督信仰運動,其教會的面貌以及外在的宗教社會力量,使得當時基督徒作者們因此使用了風貌各異的、不同的表達方式。
本書第一章的導論介紹,是由賀穆‧寇斯特(Helmut Koester)教授所撰寫。他畢生浸淫於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中,至今已經超過五十年之久。他鞭辟入裡的文章為本書揭開序幕。文中,寇斯特教授涵蓋的範圍,超過了他當時的博士論文。他的博士論文是在探討宗徒教父們對新約作品的使用情形[1]。這件研究成果,是在魯道夫‧布特曼教授(Rudolf Bultmann)---這位二十世紀新約研究與基督宗教源起研究的巨人---指導下完成的。這兩位學界大老,在宗徒教父研究上承先啟後,他們建立的學術譜系與傳統,恐怕亦是巴必亞與夸德拉圖斯非常樂意大聲疾呼的。寇斯特的文章,猶如一股清新之風吹入書中,將他超過五十年的研究心血與結晶編織起來,映入讀者的眼簾。從許多角度來看,他的文章和一般用以介紹宗徒教父作品的傳統文章相較起來,非常不同。他的文章一方面讚賞與推崇宗徒教父作品,同時也提供了極富創意的思考與反省的角度,讓我們重新思考在主曆第二世紀時,到底有哪些力量在影響基督信仰,重新型塑了基督宗教的面貌。閱讀他的文章,使人走入那古老的關鍵年代裡,領略在基督信仰運動方興未艾的關鍵時刻,早期教父們與他人在信仰攻防與爭論的激烈情況。
強納森‧德拉普(Jonathan Draper)教授是研究《十二宗徒訓誨錄》的世界級學者[2]。他為本書所撰寫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這件作品文字極為豐富的資源,讓我們可以不斷反省。讀者可能驚訝地得知,《十二宗徒訓誨錄》是現存最早的一份基督徒作品,它明確地嚴禁男子同性性行為(包括侵犯男童,pederasty)及墮胎;但更重要的是,這件作品讓我們一窺早期猶太基督徒團體的生活樣貌,以及他們對洗禮與感恩禮的看法。德拉普教授認為,《十二宗徒訓誨錄》並不是根據《瑪竇福音》所寫成的;反之,應是《瑪竇福音》使用了《十二宗徒訓誨錄》的內容擴增而成。因此,根據他的看法,《十二宗徒訓誨錄》應是極早期的猶太基督徒歷史文獻,甚至可以追溯到主曆第一世紀中期。
安德魯‧國瑞(Andrew Gregory)博士為本書撰寫《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的分析文章。他討論了這封書信的成書目的,是試圖解決格林多教會的內部衝突。他強調,在初期教會時期,各地教會團體之間已經存在了訊息傳遞與資訊傳播的網絡;而儘管作者未宣稱自己對格林多教會有何既有的權柄(intrinsic authority),但作者極度渴望格林多教會能恢復和諧。國瑞教授強調,《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是一件受到希臘化世界影響的作品,使用了當時常見的希臘修辭學技巧。關於《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使用新約作品情況的討論,也反映出國瑞教授早年對這件作品研究的豐富成果[3]。
保羅‧帕維斯(Paul Parvis)博士為本書撰寫一篇介紹《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的文章。他的好文筆,讓人在捧讀之際,心情愉快。事實上,出於《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作者的尊敬,如果沒有像帕維斯博士一樣的同理心與洞見的觀察力,我們很可能會誤以為《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是所有宗徒教父作品中最無聊、最不具啟發性的作品了。幸虧有帕維斯博士為我們撰寫這篇文章,讓我們不會犯下這種錯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們顯示這件現存最古老的基督徒講道詞中,隱藏在作品本身與寫作目的之中,有如珍珠一般的美麗耀眼智慧。帕維斯對第二世紀基督宗教的研究著力甚深,他針對猶思定的研究即將出版另一本學術著作,是又一個例證[4]。
到底是一個愚蠢的、還是忠信真實的傳統?這是很多人在面對希拉波里斯的巴必亞(Papias of Hierapolis)文字,並試圖分析它時會有的疑問。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們,遭遇的困難在於:巴必亞的作品現僅存有殘篇,是後人擷取與抄錄的內容,主要是在安瑟伯(Eusebius of Caesarea)的《教會歷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中。查爾斯‧希爾(Charles Hill)教授從一個學術的、但也富有同理心的角度來檢視〈巴必亞碎篇〉的文字,對巴必亞《主言句解》(Expositions of the Dominical Logia)五卷作品的殘篇文字,詳盡地加以討論。希爾教授對宗徒教父的學術興趣非常廣泛,他在最近出版的書中指出:《致刁臬督書》的作者不是他人,而就是斯米納的鮑理嘉(Polycarp of Smyrna)[5]。
被安瑟伯抄錄保留在《教會歷史》中的另一段殘篇文字,是夸德拉圖斯的護教書(Apology of Quadratus),它是現存基督徒最早的護教作品。有趣的是,從現存殘篇中看到,夸德拉圖斯護教的方式是舉出受耶穌奇蹟治癒、甚至復活過的證人,這些人在夸德拉圖斯的年代依舊還在,因此是最直接的耶穌見證人。這種護教的論述方式之所以有力,乃因當時仍是耶穌運動(Jesus-movement)興盛的年代,或至少,有人可以與這些曾獲耶穌治癒與復活的人見到面、聽他們親口證實的年代,因此可以把他們聽聞的證詞傳承下來。或許也正因如此,後來繼之而起的護教家們不再採用這種論述方式。夸德拉圖斯的斷簡殘篇向來被人忽略,但本書卻將其與其他宗徒教父作品賦予同等重要性,給予相當的篇幅,而不是被以註腳的方式略予提及。
「奇特」(peculiar)一詞是約瑟夫‧范海頓(Joseph Verheyden)教授介紹《何而馬的牧者》時所使用的形容詞;當然,是否有其他辭彙能被用來形容這部作品,是可以討論的。不過,除了這部作品文字中顯而易見地瀰漫著一股奇怪的末日(apocalyptic,或譯:默示)氣息之外---至少對現代學者們而言是如此,它在早期教會中是一件極受歡迎與重視的作品,不僅以許多不同的手稿方式被保存下來,也頻頻被後代教父援引使用。范海頓教授認為,《何而馬的牧者》的作者是一位以羅馬為主要活動地方的講道人,同時也是一位先知;不過很顯然的,他在當地教會中,沒有任何正式的職務。因此,它顯示出當時羅馬教會是一種由眾多家庭教會形成的、鬆散的邦聯組織形式,任何形式的主教制度(或架構)都是後來才進入這個位於帝國首都的教會中。范海頓教授針對第二世紀的教會,曾為學術專書寫過文章,也曾研究過《何而馬的牧者》作者如何使用新約作品[6]。
詹姆士‧查頓‧佩吉博士(Dr. James Carleton Paget)很巧妙地引導讀者穿越《巴爾納伯書信》的重重困難與障礙。佩吉博士在為本書提供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驚艷的,也許是他面對猶太教與猶太人傳統的態度。《巴爾納伯書信》不斷援引舊約文字,但它卻以「非字面」方式解釋經書內容,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刻意要與傳統猶太釋經不同。《巴爾納伯書信》作者樂於「佔領」猶太經書內容,同時採用極端的分裂主義,要從猶太傳統中分離出來。佩吉博士敏銳地提出疑問:到底這代表著基督信仰與猶太教當時正面臨的激烈分割呢?還是反映出當時這兩大陣營複雜的互動面貌?查頓‧佩吉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許多研究《巴爾納伯書信》的專文[7],在學術界貢獻卓越,他也將相關的主題與廣泛的討論帶到本書當中。
每一個關於安提約基依納爵主教書信的討論主題,似乎都是學界爭議不斷的焦點。儘管大多數學者都樂於接受「中編」(the middle recension)以及七篇較短形式的書信,是真正的依納爵書信,但仍有許多人有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人認為現存所有的依納爵書信都是後人杜撰的、託名撰寫的。現存依納爵書信成書年代的確定,更是另一個極困難、棘手的問題,而這也牽連到如鮑理嘉《致斐理伯人書》(Polycarp’s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成書年代的確定,以及安瑟伯的《編年史》(Chronicon)內容的正確性。另外,依納爵書信中的神學,也經年累月地不斷被學界提出討論,如:教會組織架構的興起、教會牧職的三層模式(the threefold pattern of ministry)、單一主教制(monarchical episcopacy)、感恩禮中耶穌基督的真實臨在(the real presence in the Eucharist),以及關於殉道的神學思想。不論何人---依納爵當代的、或是後代的人---對他書信中提及的這些主題有何看法,不可否認的,依納爵視死如歸的英雄行徑,及他對自己將在羅馬競技場裡慘死的景況毫無畏懼,都使人對依納爵的崇敬與尊重,穿越時空、絲毫不減。
關於鮑理嘉的《致斐理伯人書》,學界許多人認為,現存作品應是原本兩件獨立的書信,經後人合併整理之後而成的。麥可‧何穆教授(Professor Michael Holmes)在此書的專文,對此論點提出反駁,因此可謂一篇學界極為重要的文章。何穆教授強調,這件作品中「義德」(righteousness)的思想與語彙,是論述的核心,這主題(義德)整合了書信中的所有觀點與看法。他不斷申論「正確的思想」(right beliefs)與「正確的行為」(right behaviours)二者是緊密相連、互相影響的。根據鮑理嘉主教的看法,人如果在「正確的思想」上有缺憾,就必導致無法有「正確的行為」,反之亦然。這也解釋了何以鮑理嘉嚴厲駁斥華倫(Valen);何穆教授說:「華倫在自己的行為上,否認了『異端論者』藉著言語所否認的」。何穆教授最為人所知的,是他也編纂了一本宗徒教父作品集[8],而他目前正在為知名的釋經系列叢書 Hermeneia,撰寫鮑理嘉《致斐理伯人書》的分析專書。
《鮑理嘉殉道紀》(Martyrdom of Polycarp)在虔誠的基督徒或學者心中,是典型的頌揚作品之一。這件作品儘管有許多描述鮑理嘉死亡過程的血淋淋文字;但同時,文字也表達出早期基督徒面對死亡時,[與世俗]相反的價值觀與態度。殉道是生活的方式、受苦是走向被舉揚的道路、為耶穌而死能使人在光榮中與祂一同復活。撒拉‧帕維斯博士(Dr. Sara Parvis)在本書中,針對上述這些思想多所發揮與闡釋。她早期曾經針對亞略爭議(Arian controversy)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 Marcellus of Ancyra 這號人物[9]。在本書中,她一方面詳細檢視《鮑理嘉殉道紀》這部充滿疑問、學界討論多年的作品,同時也提出她個人極有創見的看法,尤其是針對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及完整性。她在本書專文中,特別分析了當時羅馬帝國的司法制度,從而協助我們理解《鮑理嘉殉道紀》中描寫鮑理嘉被審判時,不正常的司法運作情形,衝撞我們原本對這部作品的認識與理解。
《致刁臬督書》目前在學者們手中的文字,既無法判斷何時所作,同時很不幸地,也是一部很早就亡軼的作品。它未被任何一位教父所援引使用過。其抄本是在第十五世紀時,被人在魚販店舖中意外發現,結果又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被火燒毀。幸好它被人抄寫下來,而能流傳至今。抄寫本上的空白處,被不同的抄寫員寫下許多各式各樣的筆記與注釋,這表明了:現存的《致刁臬督書》應是一件被編整過的作品,最後兩章是後來附加的(而前十章中,也至少有一個地方是亡軼的空白處)。前十章是一件護教作品,寫給某位名叫刁臬督的人,作者試圖說服他接受基督信仰中的各種主張。書信文字呈現出一種充滿智識與學問的護教論述,以捍衛基督信仰;在表達基督信仰優越性方面,文字洋溢著一股堅強的自信,刻意將基督信仰與當時主要競爭者---外邦宗教與猶太教---的思想加以對比。
[1] H. Koester, Synoptische Überlieferung bei den Apostolischen Vätern,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65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7).
[2] 例如:J. A. Draper (ed.), The Didache in Modern Research (Leiden: Brill, 1996).
[3] A. Gregory, “1 Clement and the Writings that Became the New Testament”, in A. Gregory and C.M.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9~57.
[4] 帕維斯博士目前正與牛津大學黑衣修士院(Blackfriars, Oxford)的單尼斯‧明思(Denis Minns)博士共同撰寫一本書,分析猶思定的《護教書》。
[5] C.E. Hill, From the Lost Teaching of Polycarp: Identifying Irenaeus’ Apostolic Presbyter and the Author of Ad Diognetum (Tübingen: Mohr-Siebeck, 2006).
[6] J. Verheyden, "The Shepherd of Hermas and the Writings that Later Formed the New Testament", in Gregory and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Apostolic Fathers, pp.293~329.
[7] J. C. Paget, "The Epistle of Barnabas: Outlook and Background", WUNT 2.82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94).
[8] M. W. Holmes, The Apostolic Fathers in English, 3rd ed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希臘文版本,請見LHH(關於本書使用之英文所寫,請見縮寫一覽表)。
[9] S. Parvis, Marcellus of Ancyra and the Lost Years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325~345, Oxford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二、本書中關於各作品的討論
宗徒教父作品的研究成果近年來不斷增加,反映出學界日趨理解宗徒教父作品的重要性。許多研究宗徒教父作品的學者們想知道,緊接在新約時代之後的教會到底發生了什麼;對此我們應知道,其實若干「宗徒教父作品」的成書年代與新約作品的年代,有重疊的、也有早於新約作品的。另外,當然也有許多學者只針對作品本身深入研究,因為這些作品為後人提供一個窗口,讓人得以窺見第二世紀時,在面臨重大改變與關鍵轉型階段的基督信仰運動,其教會的面貌以及外在的宗教社會力量,使得當時基督徒作者們因此使用了風貌各異的、不同的表達方式。
本書第一章的導論介紹,是由賀穆‧寇斯特(Helmut Koester)教授所撰寫。他畢生浸淫於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中,至今已經超過五十年之久。他鞭辟入裡的文章為本書揭開序幕。文中,寇斯特教授涵蓋的範圍,超過了他當時的博士論文。他的博士論文是在探討宗徒教父們對新約作品的使用情形[1]。這件研究成果,是在魯道夫‧布特曼教授(Rudolf Bultmann)---這位二十世紀新約研究與基督宗教源起研究的巨人---指導下完成的。這兩位學界大老,在宗徒教父研究上承先啟後,他們建立的學術譜系與傳統,恐怕亦是巴必亞與夸德拉圖斯非常樂意大聲疾呼的。寇斯特的文章,猶如一股清新之風吹入書中,將他超過五十年的研究心血與結晶編織起來,映入讀者的眼簾。從許多角度來看,他的文章和一般用以介紹宗徒教父作品的傳統文章相較起來,非常不同。他的文章一方面讚賞與推崇宗徒教父作品,同時也提供了極富創意的思考與反省的角度,讓我們重新思考在主曆第二世紀時,到底有哪些力量在影響基督信仰,重新型塑了基督宗教的面貌。閱讀他的文章,使人走入那古老的關鍵年代裡,領略在基督信仰運動方興未艾的關鍵時刻,早期教父們與他人在信仰攻防與爭論的激烈情況。
強納森‧德拉普(Jonathan Draper)教授是研究《十二宗徒訓誨錄》的世界級學者[2]。他為本書所撰寫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這件作品文字極為豐富的資源,讓我們可以不斷反省。讀者可能驚訝地得知,《十二宗徒訓誨錄》是現存最早的一份基督徒作品,它明確地嚴禁男子同性性行為(包括侵犯男童,pederasty)及墮胎;但更重要的是,這件作品讓我們一窺早期猶太基督徒團體的生活樣貌,以及他們對洗禮與感恩禮的看法。德拉普教授認為,《十二宗徒訓誨錄》並不是根據《瑪竇福音》所寫成的;反之,應是《瑪竇福音》使用了《十二宗徒訓誨錄》的內容擴增而成。因此,根據他的看法,《十二宗徒訓誨錄》應是極早期的猶太基督徒歷史文獻,甚至可以追溯到主曆第一世紀中期。
安德魯‧國瑞(Andrew Gregory)博士為本書撰寫《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的分析文章。他討論了這封書信的成書目的,是試圖解決格林多教會的內部衝突。他強調,在初期教會時期,各地教會團體之間已經存在了訊息傳遞與資訊傳播的網絡;而儘管作者未宣稱自己對格林多教會有何既有的權柄(intrinsic authority),但作者極度渴望格林多教會能恢復和諧。國瑞教授強調,《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是一件受到希臘化世界影響的作品,使用了當時常見的希臘修辭學技巧。關於《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前書》使用新約作品情況的討論,也反映出國瑞教授早年對這件作品研究的豐富成果[3]。
保羅‧帕維斯(Paul Parvis)博士為本書撰寫一篇介紹《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的文章。他的好文筆,讓人在捧讀之際,心情愉快。事實上,出於《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作者的尊敬,如果沒有像帕維斯博士一樣的同理心與洞見的觀察力,我們很可能會誤以為《克雷孟致格林多人後書》是所有宗徒教父作品中最無聊、最不具啟發性的作品了。幸虧有帕維斯博士為我們撰寫這篇文章,讓我們不會犯下這種錯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們顯示這件現存最古老的基督徒講道詞中,隱藏在作品本身與寫作目的之中,有如珍珠一般的美麗耀眼智慧。帕維斯對第二世紀基督宗教的研究著力甚深,他針對猶思定的研究即將出版另一本學術著作,是又一個例證[4]。
到底是一個愚蠢的、還是忠信真實的傳統?這是很多人在面對希拉波里斯的巴必亞(Papias of Hierapolis)文字,並試圖分析它時會有的疑問。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們,遭遇的困難在於:巴必亞的作品現僅存有殘篇,是後人擷取與抄錄的內容,主要是在安瑟伯(Eusebius of Caesarea)的《教會歷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中。查爾斯‧希爾(Charles Hill)教授從一個學術的、但也富有同理心的角度來檢視〈巴必亞碎篇〉的文字,對巴必亞《主言句解》(Expositions of the Dominical Logia)五卷作品的殘篇文字,詳盡地加以討論。希爾教授對宗徒教父的學術興趣非常廣泛,他在最近出版的書中指出:《致刁臬督書》的作者不是他人,而就是斯米納的鮑理嘉(Polycarp of Smyrna)[5]。
被安瑟伯抄錄保留在《教會歷史》中的另一段殘篇文字,是夸德拉圖斯的護教書(Apology of Quadratus),它是現存基督徒最早的護教作品。有趣的是,從現存殘篇中看到,夸德拉圖斯護教的方式是舉出受耶穌奇蹟治癒、甚至復活過的證人,這些人在夸德拉圖斯的年代依舊還在,因此是最直接的耶穌見證人。這種護教的論述方式之所以有力,乃因當時仍是耶穌運動(Jesus-movement)興盛的年代,或至少,有人可以與這些曾獲耶穌治癒與復活的人見到面、聽他們親口證實的年代,因此可以把他們聽聞的證詞傳承下來。或許也正因如此,後來繼之而起的護教家們不再採用這種論述方式。夸德拉圖斯的斷簡殘篇向來被人忽略,但本書卻將其與其他宗徒教父作品賦予同等重要性,給予相當的篇幅,而不是被以註腳的方式略予提及。
「奇特」(peculiar)一詞是約瑟夫‧范海頓(Joseph Verheyden)教授介紹《何而馬的牧者》時所使用的形容詞;當然,是否有其他辭彙能被用來形容這部作品,是可以討論的。不過,除了這部作品文字中顯而易見地瀰漫著一股奇怪的末日(apocalyptic,或譯:默示)氣息之外---至少對現代學者們而言是如此,它在早期教會中是一件極受歡迎與重視的作品,不僅以許多不同的手稿方式被保存下來,也頻頻被後代教父援引使用。范海頓教授認為,《何而馬的牧者》的作者是一位以羅馬為主要活動地方的講道人,同時也是一位先知;不過很顯然的,他在當地教會中,沒有任何正式的職務。因此,它顯示出當時羅馬教會是一種由眾多家庭教會形成的、鬆散的邦聯組織形式,任何形式的主教制度(或架構)都是後來才進入這個位於帝國首都的教會中。范海頓教授針對第二世紀的教會,曾為學術專書寫過文章,也曾研究過《何而馬的牧者》作者如何使用新約作品[6]。
詹姆士‧查頓‧佩吉博士(Dr. James Carleton Paget)很巧妙地引導讀者穿越《巴爾納伯書信》的重重困難與障礙。佩吉博士在為本書提供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驚艷的,也許是他面對猶太教與猶太人傳統的態度。《巴爾納伯書信》不斷援引舊約文字,但它卻以「非字面」方式解釋經書內容,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刻意要與傳統猶太釋經不同。《巴爾納伯書信》作者樂於「佔領」猶太經書內容,同時採用極端的分裂主義,要從猶太傳統中分離出來。佩吉博士敏銳地提出疑問:到底這代表著基督信仰與猶太教當時正面臨的激烈分割呢?還是反映出當時這兩大陣營複雜的互動面貌?查頓‧佩吉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許多研究《巴爾納伯書信》的專文[7],在學術界貢獻卓越,他也將相關的主題與廣泛的討論帶到本書當中。
每一個關於安提約基依納爵主教書信的討論主題,似乎都是學界爭議不斷的焦點。儘管大多數學者都樂於接受「中編」(the middle recension)以及七篇較短形式的書信,是真正的依納爵書信,但仍有許多人有不同的聲音,甚至有人認為現存所有的依納爵書信都是後人杜撰的、託名撰寫的。現存依納爵書信成書年代的確定,更是另一個極困難、棘手的問題,而這也牽連到如鮑理嘉《致斐理伯人書》(Polycarp’s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成書年代的確定,以及安瑟伯的《編年史》(Chronicon)內容的正確性。另外,依納爵書信中的神學,也經年累月地不斷被學界提出討論,如:教會組織架構的興起、教會牧職的三層模式(the threefold pattern of ministry)、單一主教制(monarchical episcopacy)、感恩禮中耶穌基督的真實臨在(the real presence in the Eucharist),以及關於殉道的神學思想。不論何人---依納爵當代的、或是後代的人---對他書信中提及的這些主題有何看法,不可否認的,依納爵視死如歸的英雄行徑,及他對自己將在羅馬競技場裡慘死的景況毫無畏懼,都使人對依納爵的崇敬與尊重,穿越時空、絲毫不減。
關於鮑理嘉的《致斐理伯人書》,學界許多人認為,現存作品應是原本兩件獨立的書信,經後人合併整理之後而成的。麥可‧何穆教授(Professor Michael Holmes)在此書的專文,對此論點提出反駁,因此可謂一篇學界極為重要的文章。何穆教授強調,這件作品中「義德」(righteousness)的思想與語彙,是論述的核心,這主題(義德)整合了書信中的所有觀點與看法。他不斷申論「正確的思想」(right beliefs)與「正確的行為」(right behaviours)二者是緊密相連、互相影響的。根據鮑理嘉主教的看法,人如果在「正確的思想」上有缺憾,就必導致無法有「正確的行為」,反之亦然。這也解釋了何以鮑理嘉嚴厲駁斥華倫(Valen);何穆教授說:「華倫在自己的行為上,否認了『異端論者』藉著言語所否認的」。何穆教授最為人所知的,是他也編纂了一本宗徒教父作品集[8],而他目前正在為知名的釋經系列叢書 Hermeneia,撰寫鮑理嘉《致斐理伯人書》的分析專書。
《鮑理嘉殉道紀》(Martyrdom of Polycarp)在虔誠的基督徒或學者心中,是典型的頌揚作品之一。這件作品儘管有許多描述鮑理嘉死亡過程的血淋淋文字;但同時,文字也表達出早期基督徒面對死亡時,[與世俗]相反的價值觀與態度。殉道是生活的方式、受苦是走向被舉揚的道路、為耶穌而死能使人在光榮中與祂一同復活。撒拉‧帕維斯博士(Dr. Sara Parvis)在本書中,針對上述這些思想多所發揮與闡釋。她早期曾經針對亞略爭議(Arian controversy)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 Marcellus of Ancyra 這號人物[9]。在本書中,她一方面詳細檢視《鮑理嘉殉道紀》這部充滿疑問、學界討論多年的作品,同時也提出她個人極有創見的看法,尤其是針對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及完整性。她在本書專文中,特別分析了當時羅馬帝國的司法制度,從而協助我們理解《鮑理嘉殉道紀》中描寫鮑理嘉被審判時,不正常的司法運作情形,衝撞我們原本對這部作品的認識與理解。
《致刁臬督書》目前在學者們手中的文字,既無法判斷何時所作,同時很不幸地,也是一部很早就亡軼的作品。它未被任何一位教父所援引使用過。其抄本是在第十五世紀時,被人在魚販店舖中意外發現,結果又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被火燒毀。幸好它被人抄寫下來,而能流傳至今。抄寫本上的空白處,被不同的抄寫員寫下許多各式各樣的筆記與注釋,這表明了:現存的《致刁臬督書》應是一件被編整過的作品,最後兩章是後來附加的(而前十章中,也至少有一個地方是亡軼的空白處)。前十章是一件護教作品,寫給某位名叫刁臬督的人,作者試圖說服他接受基督信仰中的各種主張。書信文字呈現出一種充滿智識與學問的護教論述,以捍衛基督信仰;在表達基督信仰優越性方面,文字洋溢著一股堅強的自信,刻意將基督信仰與當時主要競爭者---外邦宗教與猶太教---的思想加以對比。
[1] H. Koester, Synoptische Überlieferung bei den Apostolischen Vätern,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65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7).
[2] 例如:J. A. Draper (ed.), The Didache in Modern Research (Leiden: Brill, 1996).
[3] A. Gregory, “1 Clement and the Writings that Became the New Testament”, in A. Gregory and C.M.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9~57.
[4] 帕維斯博士目前正與牛津大學黑衣修士院(Blackfriars, Oxford)的單尼斯‧明思(Denis Minns)博士共同撰寫一本書,分析猶思定的《護教書》。
[5] C.E. Hill, From the Lost Teaching of Polycarp: Identifying Irenaeus’ Apostolic Presbyter and the Author of Ad Diognetum (Tübingen: Mohr-Siebeck, 2006).
[6] J. Verheyden, "The Shepherd of Hermas and the Writings that Later Formed the New Testament", in Gregory and Tuckett (ed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Apostolic Fathers, pp.293~329.
[7] J. C. Paget, "The Epistle of Barnabas: Outlook and Background", WUNT 2.82 (Tübingen: Mohr-Siebeck, 1994).
[8] M. W. Holmes, The Apostolic Fathers in English, 3rd ed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6). 希臘文版本,請見LHH(關於本書使用之英文所寫,請見縮寫一覽表)。
[9] S. Parvis, Marcellus of Ancyra and the Lost Years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325~345, Oxford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