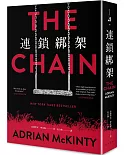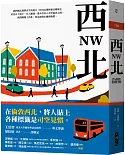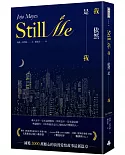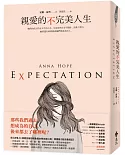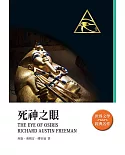導讀
瑞典學院因韋.蘇.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1931─)的作品「結合了觀察入微的敘事與不屈不繞的窮究精神,迫使我們正視被壓抑的歷史的存在,」而將二〇〇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他。說奈波爾的《在自由的國度》、《大河灣》《游擊隊》、《世間之路》等小說或「非小說」如他的「印度三部曲」挖崛了「被壓抑的歷史」,可以說是恰如其份,不過書寫歷史──尤其是被壓抑的歷史──難免令人覺的是「難以承受之重」,殊不知奈波爾的小說另有其滑稽、諷刺、詼諧的一面。
一九五四年五月,來自千里達的印裔青年奈波爾還在牛津,他在致母親家書中寫道:「我不認為自己適合過千里達人的生活了。如果要我在千里達渡過餘生的話那會要我的命。那地方太小了,那裡的價值觀都是錯的,那裡的人小鼻子小眼睛。」一年後,他寫信給姐姐甘拉(Kamla Naipaul)說:「我要當作家,要闖出名堂來。我就知道。我的未來一切都押在這上頭」。
一九五五年一年內他就寫了兩三本書稿,包括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神秘推拿師》(The Mystic Masseur)。這本讓他圓了作家夢的小說,講的是一個原為魯蛇的鄉村教師改當推拿師後攀龍有術,躋身成功人士行列的可笑故事。
其實,奈波爾想出版的第一本書不是《神秘推拿師》,而是信上提到的另一份書稿《米格爾大街》(Miguel Street)。那是一本收入十幾個短篇故事的集子。出版社讀了書稿有興趣出版,但對出版一本新人的短篇集沒把握,奈波爾表示手邊有部長篇稿,編輯讀了前幾章後決定先出這本題為《神秘推拿師》的長篇,然後才出短篇集。
不過,《米格爾大街》要等到一九五九年才面世,奈波爾的第二本書還是一本長篇小說。
這本在《神秘推拿師》與《米格爾大街》之間殺出的長篇小說程咬金,就是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艾薇拉投票記》(The Suffrage of Elvira)
。這是一本政治小說,而且對選舉活動與民主政治冷嘲熱諷,頗有「國族寓言」的意味。一九五八年,千里達成為自治邦,四年後才脫殖獨立。奈波爾在一九五七年就寫了這本小說。小說將時間提前在戰後的一九五〇年初夏,地理背景則設在「艾薇拉」區(「艾薇拉莊園」簡稱,象徵千里達的封建歷史)。在艾薇拉山頂「可以將千里達最美的景致盡收眼底」,但是小說中的候選人之一興都教徒哈本(Harbans)「才不在乎甚麼風景,」勝選才是他「此生頭一遭參選」的目的。
但是「乾瘦、羞怯、病懨懨⋯⋯灰髪稀薄,鼻子細長」的哈本並非小說的主人翁。奈波爾所刻劃的哈本不安、焦慮、心不在焉、低頭、急躁,哀傷,是個不快樂的候選人。他有自己的採石場,屬「地方勢力」,在選舉過程中不停撒錢喬事,當選後拒絕再來艾薇拉。另外兩個候選人,一個是老纏著人問要「石頭或者聖經?」的牧師,一個是「很會賺錢」的裁逢巴克希,他也是穆斯林領袖,挾關鍵少數票再三向哈本索賄,在提名日加入選戰純粹是攪局。
奈波爾這本小說的「主角」其實是「艾薇拉」及這裡的居民。他們信仰不同的宗教,膚色各異,口操各種方言,這些人的愚昧、迷信、貪婪、頑固等種種人的劣根性在一場選舉中顯露無遺。「在艾薇拉,每件事都瘋狂地夾纏不清」,哈本無意中遇見的「兩個白人女子和一條黑狗」居然可以傳說成攸關選舉勝敗的徵兆,死雞死狗都可以繪聲繪影成有人行巫術作法。選舉結果,一如眾人所料,抱怨「每個人都想收賄」的哈本如願當選艾薇拉區國會議員,他離開選區前的最後一句話是:「艾薇拉,你是個爛貨,」小說前一章小的回目卻是「民主在艾薇拉生根,」奈波爾簡直是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很難想像,一九五七年,奈波爾不過二十五歲,竟然就將故鄉政治看得透澈,借事託諷,寫出《艾薇拉投票記》這樣的「第三世界文本」來。
《艾薇拉投票記》出版那一年, 《神秘推拿師》獲得英國的約翰.樂維林.萊斯獎(John Llewellyn Rhys Prize)。次年,《米格爾大街》出版(後來也獲頒毛姆獎Somerset Maugham Award),顯然奈波爾的小說家的身分已備受肯定。米格爾街是他千里達首府西班牙港的路易士街化名,他以寫實的筆觸敘事億往,透過小男孩的眼光,講述街頭巷尾的畸人故事,
書中人物亦多真有其人 。小城大街的市井庶民故事多,《米格爾大街》沒講完的, 這本《島上的旗幟》中的說書人繼續敘說米格爾街上的人事是非。不過奈波爾出版這本小說集,已是《米格爾大街》出版八年後的事了。在兩個集子中間,奈波爾出版了兩本長篇與兩部遊記。
《島上的旗幟》收入十個短篇和一個中篇。這些短篇多詼諧幽默,《艾薇拉投票記》裡頭所挖苦與諷刺的愚昧、迷信、貪婪、頑固、狡詐等人性惡質,這裡也不遑多讓。奈波爾的「神秘推拿師」甘尼什在〈我的姑媽金牙〉中再次現身(他在《艾薇拉投票記》中也呼之欲出),為迷信的金牙指點迷津。她身為興都教徒卻到基督教堂祈禱,祈求自已能夠生育。丈夫染病卻被餵以甘尼什開的香灰,後來敘說者的祖母把金牙的丈夫關在不透風的暗室養病,於是很快就過世了。
這十個短篇中不少是死亡或預知死亡紀事。除了〈我的姑媽金牙〉之外,
〈弔唁的人〉、〈敵人〉、〈小綠和小黃〉都寫死亡,〈心臟〉也籠罩著死亡的陰影。不過奈波特書寫這寫傷逝之請,頗能做到哀矜而不過度感悲。〈弔唁的人〉裡看過逝者相簿的人「不忍心說看過了」,〈敵人〉裡的敘說者兒子描述父親之死:「他永遠不會知道,因為就在我要表演給他看的那個晚上,他死了。」〈小綠和小黃〉中的小綠、小黃和小藍都是小鸚哥,小藍因腳受傷而失寵,籠子被放到室內不起眼處,反諷的是,備受關愛的小綠與小黃死了,小藍仍然存活。〈心臟〉裡的男孩哈利心臟不好,養了小狗來福後則害怕失去牠,然而有一天,他不在家時來福還是發生了意外。
另外三篇故事屬於滑稽、諷刺、惹笑類,但世故而充滿趣味。〈抽獎〉裡的敘說者就叫韋蒂亞陀.奈波爾,住在米格爾街,他的小學老師生財之道就是替學生補習與抽獎──獎品是一隻只會吃東西的山羊。〈夜班警衛的事件簿〉裡的夜班警衛在聯絡簿上與上司經理言辭交鋒,突顯了階級、教育與種族問題。從兩人留言的語氣與語域,不難看出作者對官僚主義的調侃與批判。
〈麵包師傅的故事〉可以視為奈波爾的「亞美文學」文本。小說裡頭那位格瑞那達來的黑人自嘲「黑得跟煤炭一樣」,卻是西班牙港最有錢的人之一。他靠開麵包店發跡,但進入自己的店舖時只能走後門(不過去銀行卻神氣地走大門),所開的麵包店也得假裝是華人開的, 後來乾脆娶個華裔妻子。
〈完美的房客〉 當然也是奈波爾的反筆。從房東的勢利與算計,
房客之間的爭寵,到房東與房客之間的爾虞我詐,都很難用「完美」來形容,對人際關係的諷刺尤其深刻,讀來別有趣味。另一個短篇〈聖誕故事〉裡的興都教徒改奉基督教,試圖改便自己的各種習俗,後來被任命為校長,娶了督學的女兒,生了兒子,退休而不甘寂寞,後謀得學校董事一職,但在聖誕佳節來臨中對預知的失敗深感不安⋯⋯。最後是奈波爾式的諷刺──就在他進退維谷時,小說家安排的「機器神」替他解決了難題,審計部的督察不來了,但他卻無法自我救贖,當個好教徒。
〈聖誕故事〉其實是敘說者的「告白錄」。
中篇〈島上的旗幟〉其實是另一個版本的《艾薇拉投票記》。如果說《艾薇拉投票記》質疑的是美式或英式的選舉與民主制度,〈島上的旗幟〉則是對美國的批判。小說寫於一九六五年,千里達獨立不過三年,離豬灣事件還沒有太久,美國人接手法國介入越戰,千里達在二戰期間美軍在那裡駐軍,戰後順裡成章成為冷戰防線之一,也是「南向」的前線,自有其戰略地位。千里達人在獨立後依然處於英國殖民主義與美國冷戰戰略的網絡之下,面對跨國─殖民─資本主義的入侵自也無力抗拒,就像小說中的來去自如的颶風一樣。這篇小說分現在/過去/現在三部,結構分明,就像殖民/後殖民/新殖民一樣。法蘭克因颶風而重履他過去駐留的島嶼,但見島上的海關大樓上旗正飄飄,但是他沒有見過那面旗。對他來說,「這島嶼曾經是沒有旗幟的」。他問計程車司機「米字旗」呢?「他們拿走了,送來這個。」他答道。在法蘭克的記憶裡,這個無旗的島嶼「是個漂浮的、在時間裡停格、沒有依歸的地方」。島嶼已是懷舊的地方了。
《島上的旗幟》集中的短篇〈聖誕故事〉後半篇已是個「退休故事」,次年的長篇《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1963)似乎是奈波爾意猶未盡,於是大書特書這個中老年危機題材。不過,《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首先是篇「戲擬」(parody)之作,以中世紀傳奇故事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為戲擬對象(小說中也有一把石中劍「艾克斯可之劍」,也有圓桌晚宴)。六十二歲、單身的理查.史東先生在艾克斯可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已屆退休之齡,每天刮鬍子時都在觀察房子後方校園內那棵樹,樹葉枝幹的枯榮彰顯了時間流逝與季節消長,「幫助他確認時光從未斷裂」,「光陰仍在流動、經驗仍在累積,過去也愈來愈漫長」。後來,在那棵樹冒出新芽的春天,他娶了瑪格麗特。
不過,時光連續流動也是弔詭的現象: 他離退休的日子日近。而在這個焦慮不安的時候,「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的新方案應時而生,年輕的專業經理人溫珀成為他的工作夥伴
,以執行這個退休人員拜訪退休人員的關懷計畫。史東先生的「騎士夥伴計畫」頗為成功,人生再度攀上高峰,溫珀也成為他的騎士夥伴。但是「飛逝光陰快速侵蝕他的人生」,時光無法留住,不久兩人關係生變,史東在公司的職位漸漸無足輕重,小說結束時,史東先生走在倫敦街上,擠上公車,回到家,上樓,等瑪格麗特回來。《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是奈波爾的「英國小說」,史東先生就是殖民地來的三十歲小說家眼中的帝國縮影。
張錦忠(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