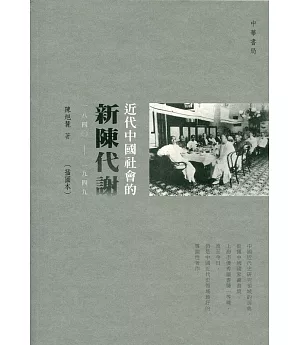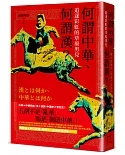初版序/馮契
在老友陳旭麓辭世兩年多以後,他的遺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經過他的學生的整理,出版了。這是對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貢獻。
我在讀這本書稿時,不禁想起了許多往事,也頗增感慨。老友的聲音笑貌不時浮現,他和我在校園中麗娃河畔邊散步邊交談的情景宛在眼前。那種談天時「相忘於江湖」,而困難時「相濡以沫」的友情,是終生難忘的。我們的交談雖總是天南地北,沒一定範圍,但談得最多的還是學術問題。旭麓搞歷史,我搞哲學,兩人專業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卻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互相切磋。我認為哲學演變的根源要到社會史中去找,他認為歷史演變的規律要借助哲學的思辨來把握;所以,我們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問題提出來向對方請教。往往是通過無拘無束的討論,得到對方的啟發和詰難,令問題更深入。1987年夏天,我寫完了《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一書,請旭麓把全部書稿通讀一遍,他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我基本上都採納了。他說等他把《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下面簡稱《新陳代謝》)一書整理出來,也要請我通讀一遍,聽聽我的意見。沒料到1988年12月1日,他竟拋下凝聚了數十年心血的手稿,猝然與世長辭。現在我遵守諾言,通讀了這部書稿,但已無法和他進行討論了。這真是終生憾事!
下面我着重就「史識」問題談一點「讀後感」。
劉知幾謂史家須具「才、學、識」三長,而世罕兼之。旭麓卻是當之無愧的「三長」兼具的史家,《新陳代謝》一書足以證明這一點。此書把史與論有機結合,通過對精練的史實的分析,以闡明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規律,並用生動的文筆表達出來,引人入勝,處處顯示出作者的「才、學、識」融為一體的風格。「三長」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史識」。旭麓說:「史識是治史的眼睛。」又說:「不為歷史現象所迷惑,不為議論家捉弄,要有一雙治史的眼睛。」正因為他有一雙敏銳的治史的眼睛,所以能透過史實的種種現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質聯繫,寫成這部才氣橫溢、情文並茂的著作。
那麼,怎樣才能有治史的眼睛?先決條件是要「解蔽」(荀子、戴震語)。只有解除種種蒙蔽,思想獲得解放,才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歷史的真相。旭麓說:「解放思想就是對自己實行民主。」這是什麼意思呢?民主意味着人人自作主宰。在學術上,解放思想,自作主宰,自尊其心,也尊重別人,正是民主的態度。有了這種民主態度,思想上的束縛解除了,眼睛不受蒙蔽,才能發揮史學家的良知來寫信史、說真話、自由討論,史學才能真正成為科學。
而在中國近代史這一研究領域,多年來確實存在着一些蒙蔽眼睛、束縛思想的東西,所以亟需做「解蔽」的工作。自50年代開始,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形成了一個以階級鬥爭為軸心,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遞進為主線的構架。這種構架標誌着一定歷史階段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然而積久不變,便成了束縛人的框框。正如旭麓所指出的,按這種框框編纂的兩百多部近代史,「只有肥瘦的差異,很少有不同風格和個性的顯現,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稱得上具有完全意義的革命高潮。這就促使人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再認識,由原來認同的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線索之外探討新的線索」。
《新陳代謝》一書,就是作者解放思想,敢於摒棄舊的僵化的框框而代之以新的生動的線索的産物。這無疑包含有「史識」上的躍進。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簡單化、絕對化的傾向被克服了,但不是拋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而是真正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把階級鬥爭的事實同生産方式的演變聯繫起來進行考察研究。作者以為,和中國古代那種靜態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會不同,近代中國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和西方從中世紀到近代是通過自我更新機制來實現社會變革也不一樣,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接踵而來的外力衝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衝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迴曲折地推陳出新(即推封建主義之陳而出民主主義之新)。所以,中國近代社會的演變有很大的獨特性,這需要通過對社會結構、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各方面作具體深入的研究來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在社會結構方面,不僅考察了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革命變革,而且考察了農村社會組織、城鎮中的行會組織在近代的演變,近代社會中特有的會黨組織的作用,不平等條約制度化引起的社會變化等;在社會生活方面,不僅研究了物質生活中衣食住行的變化,而且研究了與之密切相關的人口問題,以及政治革命和外來影響如何引起社會習尚的改變等;在社會意識方面,不僅論述了政治思想、哲學、文學等方面的變革,而且分析了歐風美雨影響下的種種社會心態,並表現為語言構造上的變化等。這樣作了多方面、多層次的考察研究,就使得本書主旨(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展現為非常豐富多彩的內容,而作者傑出的史識也就憑藉其深厚的學力和長袖善舞的才能而得到具體生動的體現。
作者以「新陳代謝」作書名,當然意味着他要探索中國近代歷史的辯證法。他在書中多次提到要「借助辯證思維」,「離開辯證思維和歷史主義是難以解釋其本來意義的」等等,正說明他是一個自覺地運用辯證法作為「治史的眼睛」的史學家。例如,書中關於「中體西用」說的分析,關於中國近代史中的革命與改良、愛國與賣國、侵略與進步等關係的研究,關於會黨在近代史上的雙重作用的考察等等,都充滿着辯證法的光輝,並由於其中某些問題先已寫成單篇論文在報刊發表,所以早就産生了廣泛影響。辯證法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本書對所涉及的事件,不論是重大史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到新文化運動等),或是和一般人生活有關的事件(如辛亥革命時期的剪辮子、禁纏足、廢跪拜等),都能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對所涉及的人物,不論其角色如何,也絕不是簡單地扣個政治帽子了事,而是力求通過具體分析,把他寫成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譬如說,第六章中對那位「不戰不守不和,不死不降不走」的葉名琛的刻畫,對當時處中西折衝之局者三種類型的分析;第十八章中描寫二次革命失敗後的國民黨人和進步黨人的痛苦心情如何因人而異;……這些篇章都寫得形象生動,人物具有個性特色,使讀者很自然地聯想起《史記》、《漢書》的列傳中所運用的筆法。
作者在第十九章論述新文化運動時寫了一段帶總結性的話:「八十年來,中國人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開始,進而『中體西用』,進而自由平等博愛,進而民主和科學。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識世界同時又認識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隨着古今中西新舊之爭。」這裏所列舉的是1840年以來中國先進人物在文化意識上所經歷的主要環節,這些環節構成了文化上的古今中西新舊之爭的辯證發展線索,反映了中國人在奔向近代化過程中認識的逐步提高。經過許多志士仁人艱苦探索,人們終於認識到了應以「民主和科學」為評價文化的標準,「而後才可能有完全意義上的近代中國和近代中國人」。所以說:「中國人認識世界同時又認識自身。」而對世界和自身的認識當然都需要「史觀」。上述文化意識的每個發展環節實際上都以一定「史觀」為視角,而「史觀」也有其新陳代謝的運動。從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中的早期改良派,都持「器變道不變」或「中體西用」說,他們為採納西學找根據,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歷史變易觀取代頑固派的形而上學不變論。到了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把公羊三世說的歷史變易觀改造為歷史進化論;嚴復批判了「中體西用」說,把西方的進化論系統地介紹到中國。這以後,中國的先進人物,不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在歷史觀上都主張進化論,並認為歷史進化的方向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社會。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高揚民主和科學之旗,他們本來都是進化論者,不過隨後發生了分化,陳獨秀和李大釗首先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用社會存在來說明社會意識,用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運動來說明社會歷史進化過程,於是民主和科學的要求就被安放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了。所以,同上述文化意識上的發展線索相聯繫,「史觀」也經歷了由歷史變易觀到進化論、再到唯物史觀的辯證發展過程。「五四」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以唯物史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便促使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這就是中國人所作的「歷史的選擇」(本書最後一章即以此為標題)。
旭麓所用「近代中國」一詞,是指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以「五四」(1919年)為界可劃分為兩個段落:前八十年和後三十年。本書所寫,主要是前八十年的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過程,而對後三十年,只是在最後一章中附帶勾畫了幾筆而已。旭麓原計劃要寫一百一十年,但天不假年,只留下了前八十年的講稿。關於後三十年,雖然他主編過書,發表過許多文章,有很多獨到見解,但生前未能寫成系統化的講稿。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事!
一本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讀者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汲取營養,而對後繼的學者來說,是只有通過它才能超過它的。本書就是這樣一本著作。我相信,它的出版,將會使廣大讀者得益;同時我也期待着青年史學家通過它來超過它。
199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