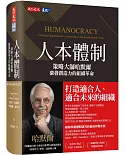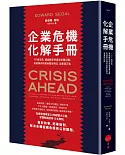序
謙遜的重要
能夠親自拜會杜拉克,是一生中非常難得的機緣,尤其是對我這種已經在商業書籍出版界待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人而言。不僅僅因為杜拉克是大師中的大師、是發明管理學的人;更難得的是,這次他居然打破長期一貫堅持的原則,接受我,一位對他而言相對陌生的作者(多半是因為我所著關於傑克.威爾許的書籍在國外更暢銷的緣故,我在泰國跟新加坡的知名度比在美國還高),進行一對一的專訪。
跟杜拉克共渡這令人難以想像的一天,讓我從中獲益良多。或許我需要花上好幾年,才能真正學到他教給我最寶貴的一課:所有各種領導力的特質中,沒有一項的重要性會超過謙遜。
不懂得反躬自省的人,無法贏得他人尊重;做不到謙遜的人,不會停下腳步提出正確的問題,例如:「如果當初沒有做?我們會有現在的樣子,知道自己掌握的知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你打算如何進行下一步?」
用上述觀念詳細檢視你的每一個事業部,需要謙遜的精神才辦得到;而杜拉克也堅信,將上述觀念轉換成具體作為,是每一位經理人的職責所在。杜拉克認為,有太多公司過於沈溺昨日的包袱,太過依賴曾經身為「金牛」、如今卻已經失去光彩的產品。今天賴以維生的工具,很可能就是明日成長的障礙。經理人必須學會區別,何謂杜拉克所定義的「有目的的拋棄」,並且要能夠具體實踐。
按照計畫、有目的的拋棄,可以用來評估、分析你手下的產品與製程,是否真的符合明日的需求。有太多經理人因為無法跳脫出杜拉克所謂「經理人的自負心態」,以致無法跟昨日種種,揮手告別。
杜拉克教我—儘管不是透過聲嘶力竭的方式—不管是對於商場或是人生,謙遜都是如此重要的關鍵。正因為我們都確信不是每件事都有答案,所以需要學的反而是問對的問題。
本書與其他杜拉克作品的不同之處
很多人問我:「既然杜拉克自己有那麼多經典著作,為什麼還需要讀這一本書?」這真是一個好問題。確實,杜拉克自己出版了三十八本書,當中更不乏經典之作;然而這也正是問題之所在!就算可以輕易接觸到杜拉克的智慧結晶,但是很多讀者往往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這就是這本書價值之所在。
《進入彼得‧杜拉克的大腦,學習經典十五堂課》(Inside Drucker’s Brain)這本書有兩個主要目的:
1.界定、說明杜拉克最具有影響力的十五項管理學原理。一方面呈現這些深具啟發性的想法,就算時至今日,也還是跟當初剛提出時一樣適切要領;另一方面,則顯示這些想法該如何應用在今日競爭越形激烈的全球化市場中。
2.呈現出杜拉克人性的一面。在我這一生所接觸各種形形色色的人物中,杜拉克竟然是當中最謙虛的一位。他花上好幾個小時告訴我,他「完全不懂如何從當局者的角色看待管理」,因為他從來就不是一位經理人。杜拉克還告訴我,他並沒有成為一位經理人的條件,因為他「沒辦法做出招募、解雇的決定」,而且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獨行俠」;他自己做出的結論是:「想要成為一位經理人,我這個人完全不行。」
總而言之,杜拉克正是一位百年難得一見的思想家,在適當的時間,實現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建立管理學架構,使之成為社會科學的一支。在杜拉克出現之前,我們既不能教導、也不能學習何謂管理。正是透過杜拉克的著作跟貢獻,管理學才能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成為每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組成元素。
傑佛瑞.克拉姆斯(Jeffrey A. Krames)
《進入彼得‧杜拉克的大腦,學習經典十五堂課》作者
推薦序
穿越時空的智者
楊照(作家)
彼得.杜拉克不是管理學大師,不是美國人,甚至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理解杜拉克的關鍵,就在於看穿他遠超過一般世俗印象的背景與關懷,不能被「當代美國管理學大師」定位、範限的部分,才真正促成了杜拉克的成功,也讓他的成就,和其他所有同類「大師」拉出距離來。
杜拉克是跨越世紀的人
即便還活著的時候,杜拉克就已經不屬於這個時代。他身上始終帶著濃厚的前一個時代的氣息。他成長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維也納,還來得及看到歐洲十九世紀最後的光華,這件事非同小可。
英國史家霍布斯邦寫十九世紀歐洲史,必須在書名裡特別標明「長十九世紀」,因為他的歷史不是從一八○一年寫到一九○○年,而是開端於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終結於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中間含括的一百多年,才是霍布斯邦認定的「十九世紀」。
杜拉克在他精采的回憶錄《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裡,一開頭就是寫「戰前歐洲」。他講的「戰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也就是霍布斯邦概念中十九世紀的最後時光。那同時是樂觀進步信念的最後時光,同時是歐洲帝國榮景的最後時光。
從這個角度看,杜拉克是「跨越世紀」的人,在他懵懂卻又敏銳的童年,就親歷了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巨大變化。
那變化,大到難以想像。幾乎所有原本被視為當然的東西,在幾年內全都變了樣。最重要、最核心的,當然就是帝國的瓦解,原先依附在帝國之上的一切,「戰後」都必須重新調整。
不只是帝國的榮光,還有帝國擴張性的樂觀,還有帝國內部的組織原則。民族國家取代帝國,成為最普遍的政治實體,也就創造了新的政治形式,發展出人與人、人與政府很不一樣的新關係。
企業為何的世紀大哉問
比杜拉克早一個世紀的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窮盡一生心力研究官僚體制,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官僚體制像擁有生命的怪獸般快速成長,取代了帝國原本鬆散、人治的性格,建立為民族國家政府組織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官僚組織背後,是冷冰冰的理性規範,是不理會個人差異的原則,官僚的擴張,一定會和個人自由、個人主義精神產生牴觸,韋伯悲觀地看待這樣一段人類歷史「除魅」變化,逼迫自己去正視社會組織的脫胎換骨。
從一個意義上看,杜拉克一生所做的事,和韋伯有著緊密的呼應,因為他的出發點,是和韋伯一樣的「世紀之交」歐洲大變化。人類在尋找新的互動、合作、隸屬與管轄關係。十九世紀帶高度個人性、帶浪漫色彩的組織(或無組織)原則,進入二十世紀顯然越來越不合宜了。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快速崛起,呼之欲出。
韋伯從公部門,看出官僚體制的重要性;杜拉克則從私部門,很快預見企業與公司,會是二十世紀人與人關係的新樞紐。弄清楚什麼是企業、什麼是公司,成了從舊時代跨越進入新時代的杜拉克,根本的興趣與熱情所在。
杜拉克瞭解、記得企業尚未扮演重要角色的舊時代,所以他不可能將企業視為理所當然。杜拉克眼中看到的企業,是一種新興的現象,是人類進入二十世紀後,配合複雜主客觀環境變化,應運而生的組織原則。因此杜拉克能夠從最根本的地方叩問「企業是什麼」,然後才在這根本理解上,進而試圖回答「企業應該是什麼」。
文藝復興人打造新專業
舊時代歐洲文明留在杜拉克身上的另一層影響是—他沒有二十世紀以降明確的專業訓練限制,他從來沒有習慣問單一學科內的制式問題,他的眼光裡沒有學科壁壘。
他不是社會學家,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是經濟學家。他沒有從純粹社會學、心理學或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企業與企業管理,甚至,他沒有從純粹的任一學門角度來看待他所處的世界。
他是個「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豐富多樣的知識掌握,無法用現代觀念、現代規範予以描述。即使最信仰最崇拜杜拉克的人,大概都說不出杜拉克的學問來歷吧!他是哪所學校哪個科系畢業,專攻什麼樣的碩士博士論文題目?
用這種框架去套杜拉克,注定失敗。他的來歷,是老歐洲的貴族夢想—人文教養(Bildung)。相信知識、學問不是技術技能,而是讓人能夠脫離自然、野蠻狀態,臻及人文化境的手段。文學、歷史、哲學、科學當然都在應有的學習內容中,但唸文學不是為了培養文學家或文學研究者,唸歷史也不是為了培養史學家……,這些都是通往一個完整人文視野的多重管道。
杜拉克是最後一代接受這種「無用之用」人文教養的歐洲人。從一個角度看,時代開了他巨大的玩笑,等他吸收了這套人文教養後,人文教養賴以存在的社會就瓦解消失了。「戰前」與「戰後」最大差異正在這裡。第一次大戰後,歷史的力量逼著每個社會放棄高蹈的人文理想,改持可以用數字計算的利益衡量法,原本人文教養中的貴族,快速淪夷為新時代不合時宜無用的累贅。
的確,我們看到許多杜拉克同輩的歐洲菁英,在二十世紀快速沒落。他們或許自命清高、鬱鬱而終;或許和周遭環境格格不入,孤獨以沒;或許憤世嫉俗成為別人眼中的怪物。最悲哀的,他們越有學問,知識越豐富,反而只是越顯示出他們的無能無用,與時代現況的荒謬落差。
杜拉克不然。他擁有驚人的適應能力,卻又能不拋棄身上由人文教養鍛鍊而來的眼光與基本價值,所以他應付新的學術專業潮流的方法,既不是逃避,也不是馴服順從,而是—用自己的能力,打造一門之前不曾存在過的新專業。
沒有杜拉克沒有管理學
杜拉克開創的,當然就是「管理學」。在杜拉克之前,沒有「管理學」這門專業,因為杜拉克,才有「管理學」。「管理學」奠基的開端,是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杜拉克鉅著《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半個多世紀來管理學蓬勃發展,管理學的運用日益多元,今天從企業、行政一直到藝術、運動都有其「管理」的分支門號,這樣的熱鬧局面,讓我們格外難以回首想像「前管理學時代」會是怎樣的荒涼景況,也就格外難以追問一個關係管理學出生命運最簡單、又最關鍵的問題。
如果沒有杜拉克,還是會有管理學嗎?乍聽之下,這個問題蠻誇張蠻荒謬,因而也蠻容易回答的。有企業組織就會有管理的需求,不是嗎?人事要如何安排、流程要如何安排、會議該怎麼開、利益該怎樣產生……,有沒有杜拉克,企業、公司都還是得解決這樣的問題,不是嗎?
是,但讓我們分辨清楚,這些問題的解決,是管理的實際做法,卻不必然是「管理學」。杜拉克沒有發明管理上千千百百種實際的做法,杜拉克發明創建的是「管理學」。「管理學」把千千百百種實際做法統納進一套系統裡,然後尋求這套系統的內部價值與內部邏輯。
有管理實際需求,不必然會有管理學。我們甚至可以講得更精確些,正因為有管理實際需求,所以很難有管理學。管理做法因應各種不同變化情境產生的辦法,裡面充滿了高度即興、彈性風格。有那麼多種不同的企業,從事那麼多種不同的生意,面對多樣且多變的市場,管理做法必然因公司而異、因人而異,必然五花八門,怎麼可能統合成「管理學」?
是靠杜拉克驚人的能力,才將管理做法整合成管理學,然後將管理這件事顛倒站立起來。一九七三年的鉅著,標題講得明白透徹:《管理學:使命、責任與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lities, Practices),只有使命有責任,才能討論實務、理解實務。
沒有人會被杜拉克嚇跑
打造起「管理學」,杜拉克依恃兩種相關卻不相同的能力。第一種是他寬廣卻又徹底的視野。他直覺地將公司企業放置在組織的大課題裡來理解,又將公司企業的組織形式,放置在長遠人類歷史以及複雜的現代局面下予以評價衡量。如此一來,他看到的公司、企業,與一般人認定的大不相同。公司、企業之所以值得特別注意、認真探究,因為這是歷史上新興的組織形式,卻在極短時間內取代了過去其他主流組織,成為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難以逃開的頭號組織經驗,甚至是挑戰家庭、軍隊、鄉紳俱樂部的傳統地位。
越來越多人在公司、企業裡工作、生活,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沒有道理不把什麼是公司、企業組織搞清楚。而要搞清楚,不能從單一、狹小、具體的公司企業來看,要能看到眾多過去、現在乃至未來企業的形貌樣態,以及其形貌樣態的演化發展原則。
有幾個人能提供這種尺度的觀察與思考?幾個能夠「從大著眼」進行全面思考的人,會去注意公司、企業?
杜拉克另外一項重要能力,是溝通,是清楚表達。這方面我們也同樣太容易視之為理所當然了。畢竟,管理學的成立,不能關在學院裡,如果整理出來的管理知識,對實際進行管理的人,和在組織系統中被管理的人,沒有影響,管理作為一門學問必然走不遠的。
要讓公司、企業內部的人認識管理學,是件困難重重的事。對身陷管理實境的人,管理知識不是太簡單就是太複雜。要嘛是他本來就知道的事,要嘛就是他認定與他無關的事。
在這點上,我們不能不佩服杜拉克不著痕跡的用心與設計。杜拉克曾經多次提到當年得以進入通用汽車公司進行實地調查的重大意義。通用汽車公司讓杜拉克看到龐大企業內部的動態運作,更重要的,通用汽車給杜拉克一項珍貴的資歷,讓他可以用企業「內部」觀念,來試驗他對管理的種種想法。通用汽車資歷,使得其他企業人不能想當然耳地將杜拉克視為「外人」,以一種「你不可能懂」的內部輕蔑態度對他所言充耳不聞。
誰敢說自己的企業比通用汽車龐大複雜?誰敢說自己的企業比通用汽車成功?杜拉克的洞見從通用汽車而來,又反過來對通用汽車大有幫助,這個護身符解除了多少人的防衛戒心!
杜拉克是位語言文字的天才,這指的不是他能精通運用多國語言,而是他能寫出最乾淨及最直截明白的英文。他的英文沒有人讀不懂,而且他的寫作慣常一環扣一環,讓人自然一直追索閱讀下去,但是最神奇的地方畢竟還在—那麼普通乾淨文字所傳達的訊息,卻也沒幾個人有本事一眼就看透吸收。
杜拉克喜歡「從頭說起」,從我們都能同意、都不得不同意的簡單前提說起。然後一步步一層層將我們導引到合理卻令人意外的天地裡去。讀者赫然發現:那麼熟悉的東西原來藏著這麼豐富的道理!我們為什麼從來不曾用杜拉克的方式整理過自己的經驗與想法,以至於從來看不到他所揭示的華麗、陌生光景?
沒有人會被杜拉克難倒,更沒有人會被杜拉克嚇跑。這是他擅加利用企業人熟悉的前提經驗製造的效果。可是他雖然自熟悉出發,卻絕不理所當然往熟悉之路徑上走,跟隨杜拉克,你很快就會覺得自己在熟悉的環境裡迷路了。
在熟悉的環境裡偏偏看到我仍不曉得存在、甚至以為絕對不會存在的風光。這種矛盾感受克服了企業讀者原來會有的反抗阻力,收服他們陸續成為杜拉克的信徒。
管理學是「有系統的無知」
杜拉克的語言天分還展現在他塑造的名詞概念。他的名詞不追求眩惑耀眼響亮,卻有極其堅實的相應內容作為後盾。早在六○年代,杜拉克就開始闡釋「知識工作者」在新企業環境中的重要性,那時候,全美國、甚至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認定自己是「知識工作者」,然而杜拉克鍥而不捨地描述討論,不斷增加、擴充這個名詞的意義,充分為八○、九○年代新興經濟做好了準備。那波潮流襲捲中,我們於是可以用杜拉克發展多年的觀念為定錨,看清楚造成變化的主流內幕,來自「知識工作者」的發達革命。
又例如杜拉克描述管理學的工作是「有系統的無知」(organized ignorance),也是神來之筆。沒有人能夠預見、掌握一切變化,變化必然帶來之前我們不知道、無從知道的新事物新道理,而且往往這些未知具備最大的衝擊力量。如果管理學處理現有已知,等到實務被整理成知識,豈不又被認定過時了嗎?
杜拉克主張,管理學學的不是現有管理實務技術,而是從現有管理經驗累積,投射出面對未知的積極態度,不是假裝自己知道,而是明白自己擁有的是「有系統的無知」。對於我們的無知盲點,我們習得一種有系統的準備、防衛。這才是管理學的精髓所在。
這本書的主訴目的之一,是提醒我們,最近眾多轟動一時的管理暢銷書,其內容早已在杜拉克的作品裡出現過。換句話說,寫來寫去,這些暴得大名的「大師」,誰也沒有脫離杜拉克的如來佛掌中。進而一個當然的結論—我們應該閱讀杜拉克,應該重讀杜拉克。
然而我想補充的是—就算有人把那些最暢銷的管理學全部閱讀吸收了,也還是不等於閱讀杜拉克的經驗。他們每個人從杜拉克那裡取走一點智慧洞見,予以舉例詮釋發揮,就能寫成暢銷書,而那許多被他們取走的智慧洞見,全部加起來,還是不等於杜拉克。
因為裡面沒有杜拉克的整合精神,沒有杜拉克堅持在表面繁華現象裡看出普遍原理的執著。本書作者感慨地問:為什麼現在沒有那麼多人讀杜拉克?其中一個答案應該是:因為杜拉克的書不夠熱鬧、討論那麼多實證實例。實證實例很好看很容易讀,累積數十上百實例也可以產生感覺上如排山倒海而來的洗腦說服力,所以讀者愛讀。可是實證實例多了卻也往往讓讀者迷失在繁雜的現象中,失卻了自己去歸納出道理原則的機會。
杜拉克不寫那樣的書。他在意道理、原則,還更在意追求道理、原則的道理、原則,這不是故弄玄虛的繞口令,而是為了彰顯杜拉克終極關懷不得不用的說法。畢竟杜拉克看到、親歷了從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全面變化,他知道耽溺於追求那些變化,和耽溺地拒絕接受變化,同等危險。不在變化中滅頂唯一的方法,是尊重變化,卻有耐心有毅力地找出變化的法則,進而拿對變化法則的理解來應付未來更多的變化。
穿越時空的杜拉克智慧
一直到今天,體驗杜拉克神奇智慧的一種方式,就是拿出他一九七三年出版的《管理學:使命、責任與實務》大書。那是不折不扣經歷近半世紀的舊書老書。從一九七三年到今天,世界變了多少,我們也自然可以想像企業性質、企業內容變了多少。然而翻開杜拉克的舊書,認真找找,裡面有多少明白過時落伍的內容?
我敢負責地說:幾乎沒有。我們可以指稱杜拉克書裡缺少了哪些後來新出的管理課題,然而我們卻很難在杜拉克寫出的內容裡,指出已經不適用的部分。
杜拉克怎麼做到的?三十多年前,他如何預見今天的管理者都還是需要具備的觀念、知識和技能?讀著那部老書舊書,真會讓人有一種時空的錯覺,彷彿杜拉克擁有穿越時空的神奇魔力,曾經來我們這裡走過一遭,再含笑從容地回到七○年代寫他的書。
我們忘了,杜拉克甚至已經不在這個世間了。他最神奇的貢獻卻還留在這哩,幫助我們看穿時間與變化的煙幕,找到管理的根源意義。連最現實、最難有定律的管理,杜拉克都能輕鬆自信有效地找出其中的一套恆久邏輯,在這種智慧相伴相助下,對於未來未知,我們當然可以生出許多安心勇氣來。
為什麼說,管理學是由他開創的?
許士軍(元智大學講座教授暨校聘教授/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理事長)
時間過得真快,杜拉克這位長期引領我們的管理導師己經離開整整三年了,但是此刻有機會再次重炙他留給我們的智慧,突然間彷彿他仍然活著,用他那種帶有濃厚德國口音的英文,娓娓指點我們有關企業和管理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場景栩栩如生。他所教誨的道理,此刻聽起來都仍然切中時弊,發人深省—尤其在人類正身陷空前未有的金融海嘯困境之際。
《聽彼得杜拉克的課—百年經典十五講》能問世,幸賴作者把握這位哲人生前寶貴的時刻,親自專訪,根據他口中傳授,整理出十五個管理學最重要的觀念。如作者所說,杜拉克在這一次專訪中「顯然已經下定決心要從較大的歷史背景中,定位他自己的貢獻」。
儘管杜拉克被譽為「大師中的大師」,其一生博學多聞,知識淵博,不過在這短文中要討論的乃在於他留給我們的最大貢獻,就是開創「管理」這一門知識領域。如湯姆.畢德士(Tom Peters)所說,「在他以前,並沒有管理學」。
留給我們的最大貢獻
說管理學由他開始,並不是說,在他之前世界上沒有管理這種活動或實務—畢竟自有人類以來,就不可能不依靠群體的合作而生存;也不是說,在他之前,人類對於群體合作的道理不曾思考或有所悟解。問題在於杜拉克與一般的管理學者不同,他不僅一方面能緊緊扣住現實的時代潮流和脈動,同時又能超越瑣碎的細節和窠臼,所見乃大。
以人為本的中心思想
首先,杜拉克之所以不同於他之前的學者,在於以前人們只重視經濟學中所稱的生產因素,如機器、土地、資金等,對於管理的認識,只是一些原則性觀念或作業技巧;他們心目中的組織,也只是限於層級結構下的職位而已。至於早期的管理學者,包括被尊稱為「科學管理」之父的泰勒等,他們所關心的事物,主要聚焦於「工作」這一單位,希望透過諸如「時間與動作研究」這些工具,理性地尋求具有普遍性的「最佳工作方法」,以提高特定工作的效率(efficiency)。
然而在杜拉克眼中,人不是機器,每個人有其特殊個性、態度以及價值觀念,將一律化的工作方法強加在他們身上,基本上是違反人性的。何況,更重要的是,人類真正的價值,是在他擁有的知識和智慧,所以管理更應努力善用人類這種能力,這才是管理創造價值的源泉。也由於這種觀點,他一反過去將人只當做成本的看法,率先將人視為機構的真正資產。這也使得他發展的管理學建立在「以人為本」的中心思想上。
據稱,杜拉克在英國期間,每周都搭火車去劍橋,聆聽凱因斯主持的研討會。但是去了幾次以後,他就不去了,因為杜拉克發現「滿屋子的人,包括凱因斯本人以及既聰明又有才華的學生們,在所謂『經濟人』的假定下,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物品的行為。」相對而言,他所關心的,卻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會想像的人。
以整體的組織為對象
其次,如前所說,他的管理學觀念,除了以人為本外,也是以整體的企業組織—而不是個別的工作—為對象。依杜拉克自稱,他之所以對於管理產生興趣,源自於一個機遇。他應邀進入當時世界上一家規模最大的企業—通用汽車—進行一項長達十八個月的內部觀察。這次深入觀察的結果,不但引導他一生選擇管理為最愛的志業,而且讓他寫了第一本以「組織」角度分析企業的著作:《企業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1946)。在這本書中,他強調:「每個企業都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具備不同的技能與知識,執行各種不同性質的工作。」因此,「管理的任務,就是要讓這一群人有效發揮其長處,儘量避開其短處,從而讓他們共同做出成績來」。
《企業的概念》這本書之所以被稱為是劃時代之作,可以從出版時各界的反應上看出。它既不是人們所熟悉的「經濟學」,也不是「政治學」;當時人們竟然不知道怎樣給這本書歸類,以至於書評家也茫然不知該怎樣寫書評。他任教學院的院長還警告他說,出版這種書,將會毀了他的學術前途。甚至,支持他進行研究的通用汽車公司主管也感到失望,因為這本書探討的不是公司的營收和利潤,而是「把重點放在別的地方」。事實上,正是在這些錯愕的反應中,一門新學科領域—管理學已宣告誕生。
在《企業的概念》的基礎上,杜拉克又寫了好多本有關管理的著作,但是真正將其管理學園地發展得最完整的,是二十年後的《管理學:使命、責任與實務》(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1973)。在這書中,他從一個組織或機構的觀點,探討企業的使命策略、社會責任以及組織的創新和成長,或是像董事會、高層主管所扮演的角色等等,這些都是過去未曾觸及的管理學課題。然而這本書既沒有數學公式,也沒有圖表,竟然超過八百頁,原因在於—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本書「包含了所有企業主管應該知道的東西,凡是這本書裡沒有談論到的,也都是主管不用知道的。」
不過他並不是個固執成見的人,隨著外界環境和條件發生改變,他也毫不留戀地改變自己的觀點,譬如進入一九九○年代後,由於他看出「多年來以管理為名所傳授和實踐的內容,其背後的假設多數已顯然不符實際了」,毅然在一九九八年的《富比士》 (Forbes, Oct 5)文中,倡言一種「管理的新典範」(Management’s New Paradigms)的誕生。
著眼未來世界的變化
第三,杜拉克將管理界定為掌管機構績效的器官,但是怎樣做到這一點,他認為管理所提供的答案卻會隨著外界環境條件和主觀願景的改變而不同,而且僅僅看當前的情況也不夠,必須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狀況予以預應(proactive)。比如他在《杜拉克談未來管理》(Managing for the
Future)這本書就特別強調,這裡「每一個章節都在嘗試解釋未來世界會有什麼變化,而這些變化對經濟、人、市場、管理及組織會有什麼意義。」企業為了未來,一切都可拋棄,底特律的汽車公司今日陷入困境,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捨不得拋棄那些過氣的金牛。
對於今後的社會,他早在一九五九年所著的《明日的地標》(Landmarks of
Tomorrow)就提出「知識工作者」的觀念。他預見,在人類邁入一個所謂「知識社會」的新階段中,知識工作者將會崛起,取代製造業藍領工人成為時代重心。這時知識性生產能力將取代實體財產成為一種新的財產權觀念,而教育也將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安全形式」。更重要的,他從政治的觀點,期待知識能取代金錢和暴力成為新的權力基礎。
管理要讓社會更建全
第四,世人對杜拉克的尊敬,可從尊稱他為「管理大師中的大師」看得出來。因為和一般大師相比,他不將自己囿限於傳統管理的小圈圈內,而將管理放在整個社會的歷史脈絡中;他所關心的,是一個運作健全的社會。舉例來說,他在二戰甫告結束之際出版了《全新的社會》(The Next Society, 1950),當時他就期望企業在未來社會扮演主要建設性的角色。
但是由於日後他一方面對企業以及政府承擔任務的表現感到失望,同時又發現「非營利組織」蓬勃發展的事實,因而他又將注意力轉移到這類組織身上,並預期它們成為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這種關注焦點的轉移促成四十年後他寫下《使命與領導:向非營利機構學習管理之道》(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總之,他並不堅持偏愛某種性質機構,重要的是誰能對社會有貢獻。在這觀點下,管理只是達成有效社會這一理想的最關鍵工具和手段。這也說明了,何以他在二○○二年親自蒐羅六十年來自己著作的選集時,他所取的書名就是《運作健全的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
對於台灣讀者的箴言
特別值得在此提出,當《杜拉克精選—管理篇》(The Essential Drucker on
Management)中文版在台灣推出時,他特別為台灣讀者寫了一封信。在這信中,他指出「台灣在過去五十年內的最大成就,乃是培育出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個個在不同領域內發揮所長的專業人員和經理人,然而這些人能否創造績效,取決於我們的社會以及企業能否為這一群人提供一個有效發揮他們能力的環境和機制,也要形成足以激發他們熱情和創意的願景和任務,如果沒有這些環境和誘因,徒然有人才也是無能為力的。」這一段話不但說明了管理的作用和價值,也根本反映了他真正關懷的還是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