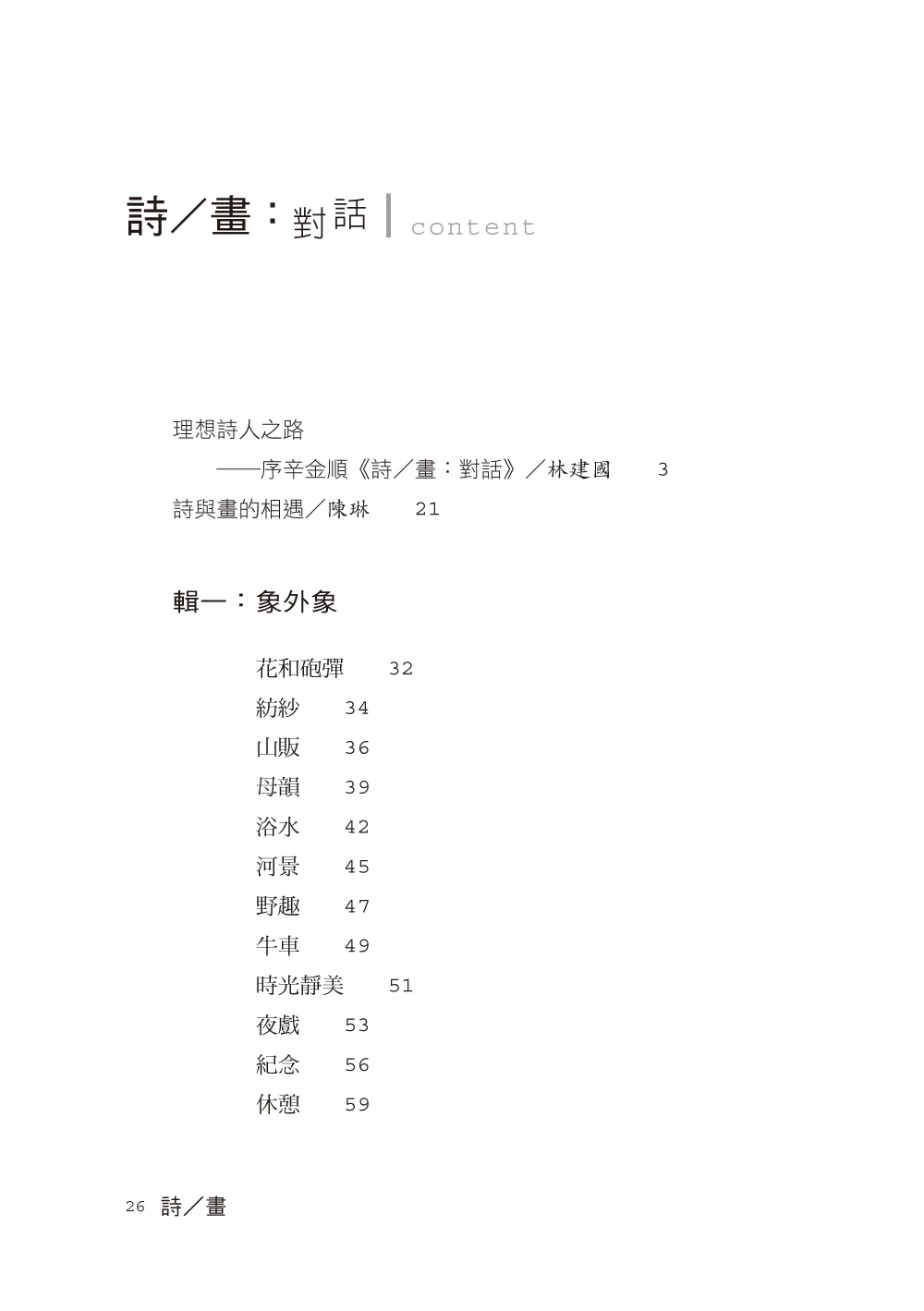序
詩與畫的相遇
記得2012年4月的那個如夢般春日嗎?草長鶯歌。天,藍極了,像一塊巨大的潤玉。南中國海的海風吹來,大海掀起層層波濤。我躲進一朵浪花裡,兩隻賊眼窺視著,偷獵馬來西亞的民族風情,收集油畫創作素材。
在結束對西馬的采風後,我乘飛機去了東馬,到了古晉,詩人吳岸接待了我。
此刻砂勞越以格外炎熱的氣候迎我,那份熱情,如同「鴿子」一樣慈祥的吳岸兄跳動底眼神。行經青山秀水,耳聞漁歌陣陣,讓人感覺拉讓江美極了。我正陶醉在古晉歷史和詩人吳岸的傳奇中。適巧,拉曼大學的辛金順博士也來到了古晉,他與吳岸老師有事相商。
順理成章,我與辛金順博士有緣千里來相逢,一見如故。
當晚我們三人參加了砂撈越的一個民族歌舞晚會。興起,手牽手地上臺也跳起了當地原住民舞蹈,甚為快樂。
辛金順博士對我說:「詩歌的創作,在於作品背後所要傳達的內在意涵。讀者對於詩歌的閱讀,其感受是不相同的,這都取決於讀者的人生經歷和生活背景。我們所追求的詩歌或文學作品,都希望能夠隨著時間的淘洗,永遠在不同的時代,能讓讀者讀出不同的意境來,這就是作品的生命力」。其實,這也是我油畫創作所要追求的理念和標準啊!
正是因為我倆都著力於藝術文化的探索,作品以不同形式流露出對美學的追尋,以此來表達內心的逸氣和凝重的情懷,於是也就有許多說不完的話了。
辛金順是現、當代文學博士,對民俗風情和人文藝術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和造詣。由此,我倆侃侃而談,如遇知音。他喜歡我的油畫,提及可為油畫寫詩,我喜歡他的那些如夢境般的詩句。於是,我們就商量著要以一種油畫視覺具象藝術與詩歌語言抽象藝術的有機對話,從而產生一種別樣的藝術效果。就這樣,我倆迸出了火花,一拍即合。當即,讓他在我的電腦中挑選了幾十幅油畫作品,讓辛博士回校後為油畫作詩……。
後來,我就去詩巫采風了。
雖然我旅居老撾,辛博士則人在馬來西亞,遠隔千山萬水。但我卻常常可從網路裡搜尋到辛金順博士在新、馬和臺灣刊登「詩與畫」的詩作。
而那些詩作,展示了美學的情境和鮮活的生命力。那是詩人從畫意中感思而成的詩意,涓涓從筆尖流出,匯成了一行行美麗而感人的詩句,為油畫增添了另一種色彩。讀後,讓人感動、深思和回味無窮。這些詩作,無疑也使畫作提升到了更高的情態和境界。
我雖然不懂詩,但對於辛金順博士《詩/畫:對話》這本詩集感觸頗深。詩集中的許多詩作處處撥動了我的神經,情感也為之觸發不已。一如詩集中「輯一:象外象」中的第一首詩〈花與炮彈〉中的詩句:「……炮火栽種在遙遠的歷史一頁裡/煙硝散去後的清晨/鐘擺搖盪著死亡和新生的笑/……/只有稚真的眼神/恬靜/並與和平/慢慢茁壯,長大」,表達出詩人對於人類和平的嚮往。雖然戰爭已經遠去,但歷史仍然記錄著死亡的痛苦和生命降生的歡笑。和平是永恆的,人們會在和平中慢慢地成長、成熟。因此可以說是,詩中寄託了詩人的反戰意識。
而我創作這幅油畫的背景是在2010年10月。那時119個國家正在老撾簽訂「禁止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集束爆彈的和平協議」。會前幾個月,聯合國清除未爆炸彈組織帶我去了當年越戰時期的重災區。那滿山遍野未爆炸彈如今仍給當地人們和野生動物帶來生命的威脅;人們養牛養羊的目的,是讓牛羊走在人前排雷。死人的事件仍天天發生。我震驚極了!彷彿看見了人們在死亡線上痛苦的掙扎,聽見了地獄門前哭聲的畫面。在這裡,生存與死亡相依,美麗與醜陋共存。回來後我創作了一批由於荒唐的戰爭帶給戰後人們苦難的油畫和速寫作品,在會前展出,向世界宣揚和平!
在此,詩人卻用他那細膩的情感和洞察人世悲痛的眼睛,以詩祈求一種寧靜的和平:「野地開出的花和童年/鴿子飛滿的天空/……/曠野沒有回音/土地收納了黎明/摘下煙花/這裡留下一片乾淨的空氣」一顆赤誠的詩心,深入畫裡,張望著遍野埋伏的地雷和開放的鮮花,以及孩童未來成長的路向,同時也闡述著詩人對戰爭的厭惡,和戰後仍處於惘惘威脅處境的同情心緒。
又如詩集中「輯二 觀妙悟」中〈趺坐〉一詩:「幻化之相,佛說: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就可照見人間苦難的臉」是的,詩人的創作意向與畫家當下的畫意不謀而合。
我創作這幅油畫是在2009年。這一年,我在佛國老撾的郎勃拉幫采風寫生,香通寺對面山上塑有一尊佛像,佛像腳下還塑有五個和尚打坐聽經。我感覺佛陀那微笑而慈祥的面容似乎在張口對我說:「苦難過後就是大自在了」。於是,在我回到老撾的首都萬象我的畫室後,腦海裡一直迴盪著佛陀在冥冥中給我的啟示。同時又憶起在我剛到老撾那一年,被一個小偷盯上,兩個月內偷了我四次,最後一次的確也沒什麼東西可偷了,小偷還是將我的半鍋飯給端走。這件事被寺廟裡一個主持和尚知道後,他每天化緣給我送來吃的。還用化緣得來的錢給我買來畫筆、畫紙,鼓勵我要勇敢地面對現實,鼓足生活的勇氣。
我將這兩者聯繫在一起,創作了這幅油畫。並採用對比的手法,以佛陀「大自在」喜悅的臉與修行者飽經滄桑疲憊而又堅貞不屈的表情展現出來,一如詩中的陳述:「每條皺紋是深深淺淺的小徑/延伸著/遺棄在寺院角落黯淡的光」。有意將修行者肩上的紅色綬帶平展地鋪出一條大道,大道分為三級,一級比一級更困難:「揭諦,揭諦,波羅揭諦/佛說:躺下/即成大道」。詩人道出了畫外之意,詩意也深刻的展現了佛法和修行者大慈悲心的真諦。
再如「輯三 賦比興」中的〈織衣〉:「針線密密,織出野地的白合/微風吹過髮梢/吹走了屋後三兩聲的吠叫」。多麼美妙的詩句啊!彷彿又讓我置身在緬甸采風時為織女寫生的場景。姑娘在屋前靜靜地織繡,偶爾的一句對話交流,都是日常的畫面。如詩中:「一列鵝影搖擺走過/走進一匹布上,那錦繡的/年華,交談復交談/彼此的流光,在矮竹凳上/坐老了黃昏」詩情、詩景、詩意湊泊而成,把畫中景象,完全詩化了。這顯現了詩人詩心所在,詩和畫也就能疊合如一。
因此,在辛金順博士的《詩╱畫:對話》的詩集裡,我讀到了詩人寬闊的心胸和美好的情懷。那些時而如雨後初晴,氣象如洗的美麗詩句,流淌著迷離的陽光,明明暗暗,瑟瑟繽紛,多麼地曼妙。那神秘的原野,神秘的光,如同步入夢境一般,詩意在心中流淌,閒適暢快。時而又如同熱帶雨林沉默棕櫚般的情感,雖只有幾片劍葉,仍華蓋如蔭,劍指長空。在如火如荼的黃昏,亭亭屹立,眼角眉梢都是安詳的笑意。這些美妙的詩句,躍入心間,撥動了人的心中琴弦,彈奏出了一支支動人的歌曲。
在此,我非常感謝辛金順博士,是您的這些美妙的詩句,給了油畫新的生命。是您的這些精練語言和細膩的情感,讓讀到這些詩的人如同捧著一碧清泉,不忍暢飲更不忍讓它從指間流失,只想用自己手心之熱去溫暖它那顆純潔、清涼的詩意。
陳琳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廣西南寧
後記
詩與神會,意與境同
2012年4月,因為某個研究計畫需要到東馬砂勞越古晉作實地考察,並與老詩人吳岸見面。吳岸提及有一位旅寮的中國畫家,正好行腳到古晉尋找畫作寫生題材,遂介紹認識。畫家,當時歇宿於海唇街的客棧中,見面時甚感親切,言談誠懇。閒聊中大致瞭解其際遇,婚姻情感的波折、生命的飄泊,以及歲月與命運淬鍊下的生活狀態;後來也敘說了其旅寮十多年,從身無立錐之地到漸漸有了安身立命之感,以及藝術追尋的故事。
然而,在那初次見面的談話中,留給我的卻是更多的想像。據說,他初抵寮國時,在街頭賣肖像畫,一幅只掙得兩元馬幣,殊未料及,十年後,他的畫作卻叫價十萬馬幣以上,而且各國收藏者都爭相到寮國向他求畫。但從他謙卑和樸實的笑談中,卻絲毫未見倨傲之氣。後來他打開電腦,展示了一些被各國博物館和收藏者購下的畫作圖片,那些調和了中國畫風的人物和景緻,不論農村婦女、鄉間小孩、部落獵者,或廟宇的比丘和小沙彌等,都相當寫實和生動的展現了畫家內在生命的情態。
那些色彩鮮艷的油畫,處處繪寫了寮國和東南亞各地民生風俗,宗教和庶民精神的特性。一幅幅的,吸引了我。那時,我對著共同看畫的吳岸說,這些畫可以入詩啊!吳岸微笑以對,陳琳卻回應說好,於是將電腦儲存庫裡2009年至2012年的畫作圖片,全轉入我的隨身碟裡。因為這份機緣,所以才有後來五十六首詩與畫的對話之作。
對於陳琳的畫,其實我相當喜歡他畫中人物生活的純樸,那是未經全球化資本主義肆虐的生活場景,一如我記憶中童年時期(七○年代)的故鄉,不論是晨雞棲啼高腳屋旁、少女在屋前舂米、小孩大人在清澈的溝間和溪邊浴洗、童年的遊戲,或是頭頂貨物的婦女行過村落等,自然和寫實的展現了鄉間庶民充滿生命力的生活型態,且在畫家精湛的油彩色調調度中,揉合出了另一種童話般的力量與光澤。
而陳琳的這些畫作,自有其心靈和視覺接受的體驗和觀照,那或許是來自於社會基層的共知共感,讓他的視角選擇了這些畫作的素材與存在狀態。毫無疑問的,主體的生命經驗,也在這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故其畫具象(representational)得近乎寫實,卻沉澱著其生活的感悟,以及精神與情感的投注。畫中的人與物,具現了畫者的心靈姿態和生命的律動,並深埋於色彩濃郁與靜默的深處。那是來自畫者內在生命的一種展現。如梅洛.龐蒂(M.
M. Ponty)所謂由「眼與心」編織而成的彩繪世界,在「可見」與「不可見」間,展示了其畫作的存有意態。
像其中一幅畫描繪了一白髮老婦在河間刷洗,身前有一中年婦女,身邊則有一童女和少女,身後卻另有背過身去的女子。五個女人,隱喻了五個年齡階段的生命歷程,在那流淌不息的時間長河中,遞換年歲,展現了女人一生的全貌。其中轉過身去的女子,則予人留下了想像的空間。那是記憶的形象?或即將遠離的未來?存在的韻律在那色彩符號中,迴轉與交錯,讓現象的身體,在畫裡開顯了某種象徵的意義。
同樣的,在陳琳的幾幅畫中,可見美軍在越戰時留在寮國土地上的許多未爆彈。這些未爆彈被當成廢鐵賣,或當著裝飾品,高腳屋的房柱,以及廚房生火的支架等,然而它卻往往造成了無數突發性的爆炸傷害和慘劇。如其一畫上的姊弟,於野外採摘小白花,身前身後的草叢中,卻棄置了一些未爆彈殼,在此,花與砲彈,戰爭與和平,以及童稚的生命,無疑構成了極其強烈的視覺與知覺效果。那是過去戰爭留下的殘餘,卻也留給了寮國人集體的記憶創傷和巨大的惡魘。而畫家善於捕捉此一現象背後戰爭的無情與殘酷,在「可見」的人/物現象中,陳述了其內心「不可見」的不捨、憐憫和悸動的情緒。
除此,一些畫中女孩遊戲的天真笑貌、母親為女兒撥髮捉蝨的恬美時光、布施者的虔敬、小沙彌在晨修時的戲耍、比丘們的渡江、勞動者的負軛等等情景,交織了畫家的心識,體現了其對生命情境一份活潑潑的感悟。另一方面,其畫色彩濃郁鮮活,保持了自然與形象深刻的視覺呈現,使得其畫作即使放在其他眾多畫作裡,也很容易會被人看到。
然而,在我面對陳琳的畫作時,我必須篩選出能與我底知覺形成共感的作品。畢竟我不是以詩入畫,或以詩進行註解的工作。而是以一種對話的方式,將畫作的情境和意涵,納入到我的存在情境裡,以自我觀照,借畫起興,並讓主體情感神入畫中,進行另一類創思。易言之,「詩/畫」均處於互為主體的位置,在相參相照裡,形成各自情境的存有意向。所以,這與傳統的畫上題詩迥異,在此,詩不附屬於畫作,而具有其自我獨立的生命姿態。因而詩題與畫題,在此也並不相同。
在藝術世界中,感悟有時候具有其之玄秘性。感官經驗所感的,固然是經驗世界裡的經驗事物,但就如知覺現象學所強調的,知覺主體與被知覺的對象,並非截然二分,兩者之間仍然有所聯繫,但彼此內在卻各自具有各自的意涵。
是以,畫家以其人生經驗的積澱促成畫作的景象,而詩,必須通過語言的考驗來完成其之藝術表現能力。語言成了詩的存有,生活視野和情感經驗的體現,則可將詩引向一條更深邃的道路去。因此,在與陳琳的畫進行對話過程中,詩言主體藉由了移情作用,通過詩性言說,企圖展現出更多的個人意志和想像。所以,詩可以說是在畫中,也可以說是在畫外進行了另一類的創作。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曾提及「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這是一種直觀感相的渲染,生命感知的傳達,意由境生,境由意出,因此目觸所及,意象相交,感悟其間,也就有了自我主觀的創造。而在讀畫過程裡,我比較注重的是畫中的意蘊、物象的構圖,以及色彩的敘事,尤其後者,雖然深靜沉默,然而卻潛伏著很大的感染力,是展現畫中意/境的關鍵點。
所以由讀畫而形成對話, 是一種心性境地的轉換。詩在此,也就成了體會意象而再意識的一種表現,或反求諸己,迎求自我深心,探向自我生命的創作。當然,「詩/畫」都具有其自律性的內在形式和特質,但藝術心眼的觀照卻是相同的。在詩中,我所要捕捉,是當下存在的那一分認知和意識,那分遮蔽在物象和語言深處的存有感悟。
而選入於這詩集裡進行對話的五十五幅畫,大部分呈現了寮國村民、兒童、比丘們和少數部落民族的鄉間生活型態,也有幾幅畫涉及了台灣高山族和東馬原住民的狩獵情景,物資貧乏卻充滿純樸與和諧的境地,未受資本主義侵略的村落和平民,勞動者的勤懇,一大片山脈和田園,處處呈現出了生活樸實的自然情態與可貴。而畫家的畫筆,在畫中,往往意在象外,別有言說,於是也讓詩在那一幅幅畫作的彩光裡,找到了可以對談的空間。使得詩意與畫境在此神會,並讓詩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妙悟裡,找到了另一種意趣。
大致上,在這本詩集裡,我企圖攏絡一些詞語,並通過了畫境,而站在畫外,去窺探遠方光影的閃爍。像雲投給了遠山淡淡的影子,像回憶裡的故鄉、童年、生活和夢,像一些走過時間的老人和故事,生和死。似乎,那裡頭,都有時代火光的炯亮和陰影,不斷明滅;都有了詩的聲音,輕輕在塵揚的大地上唱起。
或許,詩與畫的交會與交錯,是一種生命體現的歷程。是思與詩的迴盪。尤其是在電子文明迅速穿透生活方寸之間而不留餘地,全球資本主義的怪獸無孔不入,四處伸張的時代,這些帶給生命靜定而純樸的畫,卻讓我感到在那些國際財團和機械神仍無法抵達的地方,依然有夢可以創造,有詩可以在星空翱翔的喜悅。
最後,必須在這裡感謝畫家陳琳無償授權提供畫作影像和贈序,長居台灣的老鄉林建國的序文(建國年少時曾以軟牛的筆名寫詩),以及感謝歲月贈我以烘爐,熬煉出一顆不死的詩心,讓詩,成了個人存在裡,最美好的生命註腳。
辛金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