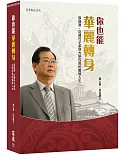自序
一個充滿莎士比亞靈光的世界
我最近常問朋友與學生一個問題:「如果不考慮時間與金錢,你願意飛去埃及看金字塔嗎?」沒有意外,答案都是興致勃勃,看來大家對這個世界的好奇仍沒有消失。但我的第二個問題,則迎來猶豫與抗拒:「如果你家旁邊有塊地要蓋金字塔呢?」迄今只有一個女孩子在課堂上表示歡迎,她的理由很實際:「這樣會吸引很多觀光客,我可以擺攤賺錢!」
莞爾之餘,我也不禁自忖這畫面恐怕早晚會發生,因為我心繫的對象不是金字塔,而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而這已經是現在進行式了:「如果對住家旁邊的金字塔會感到奇怪,那,看著許多用中文改編演出的莎士比亞,卻又為什麼不奇怪?」
如果我們可以先放下聰明,用誠實來抗拒虛榮,不沉溺在「追求共通人性」、「經典與當代對話」這類「拉關係」的觀念中,那我們就不難明白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莎士比亞不是自己人,他就是四百年前那位英國佬,在倫敦劇壇工作,為他的觀眾寫劇本。儘管他學問淵博,恐怕還是不知道台灣在哪裡。那麼,為什麼各式各種莎士比亞在台灣的演出,不讓我們感到奇怪?這種「不奇怪」本身,難道不是我們應該要奇怪的一件事?
拜全球化之賜,我們對這個世界似乎愈來愈熟悉了,但也是這份熟悉,讓台灣的文化,特別在都市裡,顯得過分早熟又世故;少見多怪、大驚小怪,在這裡不會是被鼓勵的美德。我們的文化什麼都有,百花齊放,但更像一大盆沙拉──裡面食物的原味都被調料的味道掩蓋,一如中文演出的莎士比亞,同樣需要導演創意來掩蓋文化與語言的隔閡。
代價是:我們的文化味覺可能因此遲鈍了,連帶地是失去對陌生文化驚訝的能力。
1936年,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一文中,憂心地指出一個事實:大量的複製品固然讓藝術唾手可得,拉近了與我們的距離,但藝術品從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刻,在原來的時空背景下所具有的「氛圍」(aura,或譯成「靈光」),反而在複製品充斥的世界中消失了。
莎士比亞死後四百年的今天,我們也有許多把莎士比亞變自己人的努力,鼓勵我們不斷投射自己的生命經驗、感情、觀察到他的作品中。但別忘了,我們也用同樣的方式,投射在《聖經》、《論語》、《金剛經》,以及任何有能力指導人生價值的著作上。做為「自己人」的莎士比亞,因此有很多不同的面貌,但在不知不覺中,他本來的面貌也模糊了,他的靈光也萎縮在我們的文化中。
但是在我們太世故的文化裡,總有人還是想去埃及看金字塔,總有人對陌生的文化還保有一種人類學式的興趣,一種單純天真的好奇。那麼,一定還存在這樣的渴望,不是加工後的速食替代品,而是那位莎士比亞,在遠方。
的確,限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很難如實地還原莎士比亞本來的面貌,遑論他寫作的企圖,這導致「沒有莎士比亞」、「莎劇不是莎士比亞寫的」等等說法,加上「作者已死」之類的新興觀念推波助瀾,不甩莎士比亞的本來面貌益發顯得理直氣壯。
我也不相信「本來面貌」這種事,但我相信閱讀帶來的認識與想像,可以讓我們接近這位在遠方的莎士比亞,感受當時的氛圍,為莎士比亞的靈光驚訝。
在這樣的想法下,我著手寫這本《莎士比亞不做的事》。生活中,其實我們都明白一個道理(雖然很容易忘記):看一個人,不但要看他做了什麼,也要看他不做什麼。在看待莎士比亞的時候,幾乎很少例外,人們只注意他做的事──主要是他的劇本與詩行,那麼,他不做的事呢?
這本書一樣從史實出發,譬如,我們的確知道宗教改革對英國產生的影響,的確知道莎士比亞劇團在1598年底搬家,知道他的遺囑只留給妻子「第二好的床」……,但在這些事件的牽動下,他選擇了哪些事情不做,卻留給我們很多想像與臆測的空間。
因為沒做,所以也鮮有研究會往下認真探討,這反而提供了想像空間,去重塑一個時代的氛圍,恢復環繞莎士比亞與其作品的靈光。我不會妄言這本書是一本嚴謹的著作,因為我的想像與猜測不全然有白紙黑字的證據可以證實。但也正是這些想像,讓我可以與中文的讀者對話。
我特別想要對話的對象,誠實說,不過是我的朋友。就是我這一代,在年輕時剛好遇上解嚴後的台灣,因為一個變動失序的社會強烈撞擊了心智,也打造了個性上的質疑與反叛,再一路努力活到現在的朋友。我看著有人投入社會運動,有人在名利場中追求;有人在劇場中探索身體,有人用戲劇助人,也有人早失去了理想的面貌,或更糟,只有理想的面貌而已。我特別想為你們寫書,是因為莎士比亞的劇場生涯,從1590年前後到1616年他過世為止,與我們從年輕迄今所經歷的時間相仿。
在莎士比亞與我們都還年輕的時候,這個世界變動得很激烈,許多新科技與新觀念被發明出來,挑戰了原來習以為常的價值與信念。莎士比亞所處的時代被稱為英國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或是「早期現代」(the early
modern),許多今天深深主宰我們生活的知識與觀念,那時才剛剛萌芽:理性剛剛露出曙光,地球才被證明是圓的,時鐘上有分針還很新奇,劇場開始成為人們熱衷的公共媒體……,很多我們今天太熟悉而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那時正處處給人帶來驚訝。
同樣地,約莫二十年前,台灣政治解嚴,進入民主的進程,社會上所有領域也因此經歷了一場「合法性危機」,知識上許多被認定的正典被質疑(為什麼莎士比亞是偉大的?),網際網路興起,小劇場運動更以游擊隊之姿,撞擊了我們對戲劇的想像……
柏拉圖說:「哲學起源於驚訝感。」我想,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莎士比亞無所不談的詩句有一種令人驚豔的反省高度;也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天還是有人像我一樣,對過分世故卻讓人失去驚訝能力的文化,會感到不安。
約莫莎士比亞職涯與生涯的晚期,英國社會的衝突像是體制化了,國王與國會的緊張,幾乎規範了整個社會的變動,劇場的商業化也漸上軌道,而這與台灣僵化對立的政局與文化產業化的局面相仿。莎士比亞是歷史上少數選擇退休的劇作家(而不是寫到不能寫),或許跟我一起經歷過去二十年的朋友,能體會為什麼。
一直以來,我研究莎士比亞的過程像是在兩個世界之間徘徊擺盪:在那個世界鑽得愈深,對這個世界的侷限就愈能了然;而投射在那個時代的想像,我心底明白,不過是來自我們共同經驗的滋養。
歷史於是與記憶相融。說是她走了過來,更像是我自己走了過去。記憶讓歷史知識有了活力,結晶成島嶼,佇立在遺忘的海洋中。
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島嶼,但對仍不太世故的讀者,我希望它能成為一個阿基米德式的立足點,為你們撐起一個充滿莎士比亞靈光的世界。
謝誌
這本書的完成有點意外。本來,只是為了洽談《如何教你的孩子莎士比亞》(How to Teach Your Children Shakespeare)這本書的翻譯與出版,我走進了遠流,然後,像馬克白遇上女巫一樣,出來時,我竟然答應要幫遠流寫一本書。說實話,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迄今還是有點迷迷糊糊的。
直到看見排版的書稿,我才驚覺這本書的完成有多麼不容易。遠流的編輯群們在過程中不但給了我很寶貴的意見,他們為這本書的成形付出的努力讓我驚訝不已。謝謝江雯婷小姐、廖宏霖先生,在初稿時給我的意見,還有在校對與行銷上的費心。鄭祥琳小姐是我最早與遠流的接觸,也是這本書最後的責任主編,她灌注在本書的心血,讓一位作者感到非常幸運。另外,師大的蔡亞臻小姐在確定引文出處也幫了我很大的忙,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總編輯曾文娟小姐,也就是那天的女巫,在催生這本書的過程中給我的鼓勵與建議,讓她的可愛抹除了可怕。如果任何人覺得這本書的出現有一些價值,她厥功至偉。
推薦序
從「不做」看莎翁創作及莎劇特色
在古往今來的世界作家中,莎士比亞的名望首屈一指,介紹剖析的論著層出不窮,以致罕見新意。何一梵博士在《莎士比亞不做的事》裡,從不要、不給及不寫等八個觀點探討,反而能讓我們看到莎翁的創作生涯及莎劇的特色。
何博士在序文中提到,莎翁創作的時代,與台灣約莫二十年前相似:政治解嚴,各種新思潮風起雲湧。載荷時代脈絡的莎劇,也因此和我們的經驗非常接近,極易引起共鳴。
胡耀恆(國立臺灣大學外文及戲劇學系名譽教授)
推薦序
在莎士比亞中照見自己
我不是莎士比亞的粉絲,也不太能相信他是所有的時代、所有人的莎士比亞。但是,我很快樂地把何一梵的這本小書《莎士比亞不做的事》一口氣讀完了。關於莎士比亞的書,我們都知道,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打著莎士比亞招牌的演出,中外皆然,狂風暴雨一般地輪番掃過觀眾不毛的心靈之地。然而,《莎士比亞不做的事》依然值得台灣讀者青睞:幾乎不可能的事──它拉近了莎士比亞跟我們的距離。
從台灣劇場的世系來說,一梵屬於台灣小劇場運動(1980-89)晚期的那一代。雖然我不記得他曾經隸屬過哪一個「實驗劇場」或「前衛劇場」,但是,他很認真又蠻疏離地出現在小劇場的許多現場。
那是1987年吧,一梵正在念台大中文系,每個星期他都會出現在我的現代劇場課堂上。那時候的國立藝術學院僻處蘆洲,一梵跟母親和妹妹住在新店,因此他必須公車輾轉到蘆洲來旁聽關於亞陶、布萊希特、葛羅托斯基、謝喜納等等二十世紀劇場拓荒者的討論。我不只問過一次:你為什麼要來旁聽啊?這些現代劇場大師幾乎都是「經典可以休矣」的同路人,亦即,他們都主張我們的劇場不必再以莎士比亞馬首是瞻──這種劇場觀離外文系很遠,我心裡想,離中文系更遠吧?
一梵後來念了台大的戲劇碩士(論文是關於亞陶的殘酷劇場)、美國邁阿密大學的戲劇碩士,以及英國威爾斯大學的戲劇博士(論文跟易卜生和現代性有關),等到學成歸國,真正踏入大學講堂已經年過四十了──我記得調侃過他不只一次:我們都屬大器晚成型的啊?為念書而念書,我們好不流俗呢!
我們亦師亦友的學術情誼從來不曾很親密過,但是,也似乎沒有疏遠過,即便是近幾年來,我們有機會坐下來聊天時,他話題總是會──剛開始──有點彆扭地轉到莎士比亞和他的時代。我好像又問了不只一次:你怎麼愛上莎士比亞的(潛台詞:移情別戀)啊 ?
《莎士比亞不做的事》很容易讀,讀完還會想要再讀,因此,我連續讀了兩次。第一次讀,被一梵筆下的莎士比亞這個鄉巴佬迷住了──他就像從屏東北上在電視台八點檔謀得一口飯吃的熱門編劇一樣(我腦中浮現的是不怎麼貼切的「吳念真」;一梵的父親早逝,也是名編劇)。在一梵的想像中,莎士比亞相當幸運:他不捲入政壇惡鬥,不給觀眾簡單舒服的答案,不媚俗,不趕流行,不為搞笑而搞笑,不急功近利,但是,田都元帥賞他飯吃,整個劇本寫作事業一帆風順,在家鄉買田、買房,還買了家徽當起了仕紳。
總之,一梵在自序中總結︰莎士比亞是有「氛圍」(aura,常常譯為「靈光」,不喜歡新潮術語的,直接讀成「靈魂」就對了)的,而這種「氛圍」、「靈光」或「靈魂」,卻是我們這個手機網路時代瀕臨絕種卻不受任何國家保護的稀有物種呢。
讀第二遍時,有很多時間我都在讀「何一梵」這個多年前無端闖入我課堂上的那個年輕人。莎士比亞說:劇場就是映照出萬物本性的鏡子。原來如此:一梵在莎士比亞中照見了自己,折射出我們過去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好男好女,而我們也就在他的「好好說話」中,被捲進了一個靈光乍現的當下。
這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有「靈光」的好書,很好讀,我誠摯地推薦給每一個熱愛或熱愛過劇場的人。
鍾明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
推薦序
對生命的某種擇善固執
我經常懷疑:自己可還有堅持一些「不做的事」?
記得中學時代,對莎士比亞這名字特別抗拒,讀他的著作,是我「不做的事」!也許,那時正是我的青少年反叛期,對任何老師推薦的「名牌讀物」,會無知地做出不假思索的排斥。
到了在美國侯斯頓大學念戲劇的年頭,後知後覺的我,才懂得反問:「從沒切實認識過莎士比亞是何許人,或做過什麼事,我憑什麼不喜歡他呢?」
那年,重看義大利導演法蘭高.齊費里尼(Franco Zeffirelli)於1968年拍攝的電影《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記起少年時代口裡常哼上的主題曲「What is a youth?」(什麼是青春?),竟讓我打開了生平第一部莎士比亞的劇本!讀後,不但覺得它比電影好看多了,更興起閱讀他所有著作的野心。每看完一部作品,內心的滿足難以言全!
於我,閱讀猶如一種尋找作者身影的行動,於字裡行間,深耕當中的留白地帶,給周邊世界延伸想像……
閱讀莎士比亞的戲文,猶如被邀請觀摩一群活在不尋常年代的人物,透過其言行物語間未道盡的種種,借鑑觀照當下的自身……
閱讀何一梵的《莎士比亞不做的事》,讓我回到大學時期一堂十分喜愛的劇場歷史課,當安東尼.柯林斯教授(Professor Anthony R. Collins)談到英國伊莉莎白女皇年代的戲劇面貌,其語調和神緒,猶如他口中提及昔日舞台劇名演員李察.柏貝芝(Richard Burbage)在環球劇院(The Globe)上演出般精彩。
何一梵的書寫,直接要吸引一群「聽眾」(audience),像昔日說書人,給讀者一邊「講古」,一邊借莎士比亞引發思考:在這個年代,可有像四百多年前,依然有著理應「不做的事」?
活在資訊泛濫的今天,回想自己三十多年來的舞台創作生涯,我油然自問:
可如何面對此間那些只管賣弄或推銷「特殊技術」的演員?
可怎樣從眾聲喧譁中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可如何跨越「廉價俗氣」的圍剿,不忘創作的初衷?
可怎樣不被傳播媒體壟斷了思索,保持獨立的思考?
可如何理解和接受人生的不確定性,學懂謙卑的意義?
可怎樣面向虛飾的時勢,提出徹底的叩問?
可如何重拾「好好說話」的藝術?
可怎樣真實地回到自身(家)的勇氣?
何一梵眼下的莎士比亞,並不是時下流行的「創意產業符號」,他是一個低調而處處切實面對身處年代的人。莎士比亞,藉著詩詞,成就舞台上的「戲劇行動」,貼切地回應一切隨時代逆轉的光怪陸離。他的故事,可牽引出的文化想像,立體而真實,猶如回歸到一個既可謙卑自處、亦可創作無限的文化空間!
假如莎士比亞今日仍在世,他會否依然「不做」如何一梵提出的「事」?相信作者正要邀請你和我,做為身處這消費年代的讀者(或文化「聽眾」),認真地重新借故事建築思辨,各自一起延伸創造一個「真實的我」……
假如「不做」,不是為逃避錯誤,而是一種對生命某種擇善固執的話,莎士比亞活過的世界,其實和你我很近!
何應豐(香港舞台劇創作人)
推薦序
一場文學與歷史的「實」「幻」對話
與一梵老師認識是很偶然的機緣。當時我應邀到台師大歷史系進行一場歐洲宗教改革的演講,講演結束後的Q&A時間,一位看起來「很專業」、「不太像學生」的先生舉手提出問題。我只記得當時心裡面的第一個反應是:厲害的來了。我已經忘記當初那個提問的內容,但猶記得對自己的答案不甚滿意,果然人之所知非常有限。這便是我與一梵老師的「初次見面」。
與一梵老師結識的時間雖然不長,卻頗有共鳴之感。他談到身處劇場實務與文學理論間的跼促,這讓我想起自己初從文學領域跨足歷史學界所經歷過的惶惑。跨領域的期待是不同取徑間的融合與對話,但經常淪落的景況是「失去落足點」的尷尬。
接到一梵老師的邀請,要我為他的新書撰寫推薦序時,我一度懷疑:我是適合的人選嗎?雖然曾為莎士比亞相當著迷,但學界較我「有資格」的莎士比亞專家比比皆是。然而,在翻開編輯寄來的文稿後,我恍然大悟,這本書根本就是莎士比亞的文學與歷史間的實幻對話!
讀過莎士比亞的人都會知道,學界有一個「莎士比亞問題」,那就是:「莎士比亞的戲劇是莎士比亞寫的嗎?」(乍聽之下,這是一個邏輯不通的荒謬問題。)又或者:「莎士比亞真的存在過嗎?」「那個『莎士比亞』是這個『莎士比亞』嗎?」(這是什麼問題呀!)最後,我們得以「安頓身心」的阿Q做法是──「作者已死」。不管莎士比亞是何方神聖,絲毫無損莎劇的藝術價值與地位!
但一梵老師不死心,他不甘心讓這位作者「就這樣死了」。他看見他在倫敦的劇場間穿梭,瞧見他在演員的夾縫裡露臉。他忍不住大聲地告訴大家:莎士比亞在這裡!他是這樣「受、想、行、識」,是這樣「悲、歡、離、合」。他面對他的時代,他體驗他的挫折。於是,莎士比亞「活了過來」。透過一梵老師那屬於文學家的想像力,我們看到了一個活脫脫的歷史人物──莎士比亞。
一梵老師在邀請信中跟我說:「我寫了一本小說,叫《莎士比亞不做的事》。」我想我可以再加上兩個字:一梵老師寫了一本「歷史」小說,叫《莎士比亞不做的事》,「一半根據史料,一半根據推測」。突出的歷史作品通常具有這樣的特質:確切的歷史事實加上豐富的想像力。是誰說「詩比歷史更接近真實」(應該是亞里斯多德?),不管它是歷史,是小說,還是一本歷史小說,且讓我們隨著一梵老師的步伐,勇敢地踏進莎士比亞的世界吧!
李若庸(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推薦序
莎粉要做的事
上課的空隙,出側門買個午飯。一梵突地從巷弄中冒了出來!我說:「不在新竹待著,跑我們師大來幹嘛?」他說:「開會。」又突地一轉話題,像是在心裡堵了多時,早決定一見到我就得說:「阿綱,謝謝你上次請我看戲,也謝謝送我劇本。但是,你在書裡附載的文章寫說莎士比亞把戲都分成五幕?那是莎士比亞不做的事。」
我熱衷於出版劇本,這跟當年受過的刺激有關。捧著劇本,到知名大出版社求見高層,卻得到「三大毒藥」之說:報導文學、現代詩,及「毒中之毒」劇本,是絕對沒人要讀、絕對賣不出去的書。
三十年下來,也算不負壯志,在台灣創作劇本,加入當代極少數的作者行列,算是合力建構出一種出版類型。為了豐富書本的內容,劇本之外,還得撰寫文章、製作圖表、貼照片、畫插圖。好比1970年代後期,「變形金剛」玩具剛問世時的宣傳概念:「一次購買,兩種樂趣」。
劇本出版的同時,附帶規劃推銷活動,專題演講、主題書展,最有成效的,是演出後的簽名會,觀眾很開心,演員很虛榮。劇作者該監督劇本印製?還是放手,交給出版商全權處置?
一梵是我的大學同學,他是台大學生,卻三天兩頭往蘆洲跑,到國立藝術學院(現在關渡,北藝大)戲劇系來聽課,在好幾個課堂裡與我同班。狂吸智慧資訊不算,還拐帶走一個可愛的學妹、現今的何夫人。我同期的戲劇系同學裡,都沒能出一個透徹莎士比亞的專家,一梵倒是下了決心、力學,成為五年級一代最好的幾位戲劇學者之一,且不時地提供意見、砥礪同學。
1964年出生的我,剛好是在莎士比亞出生後的四百年,而老莎只活到1616年,剛好是我今年的年紀?看來,是有機會多活幾年,只能勤懇創作,絕不敢懈怠。我們這些「莎粉」,無非是想在前人的身上,建立楷模,找到成功的因素。
應為智慧楷模的中央研究院卻在此時鬧出笑話。敦厚的蔡元培若是知曉,會再跌倒十次,清廉的胡適,心臟也炸碎成一萬片!可悲的名嘴、法匠、學閥,又為這個笑柄進行畫蛇添足,提出「以民主機制產生人選、任期規制」云云。諸葛亮若是我們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你會希望他的任期有期限嗎?抑或說,在目前的任期、選舉魔掌箝制下,永遠出不了諸葛亮這個等級的領袖?認為自己有權去建立規則的少數人,把全盤遊戲玩僵了。
所以,另有一群人,用跨越時空的方式尋找典範,超越政治、超越種族、超越藩籬,不經政治關說,不甩投票機制,直接邀請莎士比亞坐在戲劇的席位上,沒有任期!以各人自身的才能,進行擷取仿效。可惜這個世上再無人能超越,因為,莎士比亞已被層層模塑,成為無可超越的理想典範。
越扯越遠。關切根本、為人正直的一梵又要跳出來說:「阿綱!那些都是莎士比亞不做的事!」
馮翊綱(當代劇作家,【相聲瓦舍】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