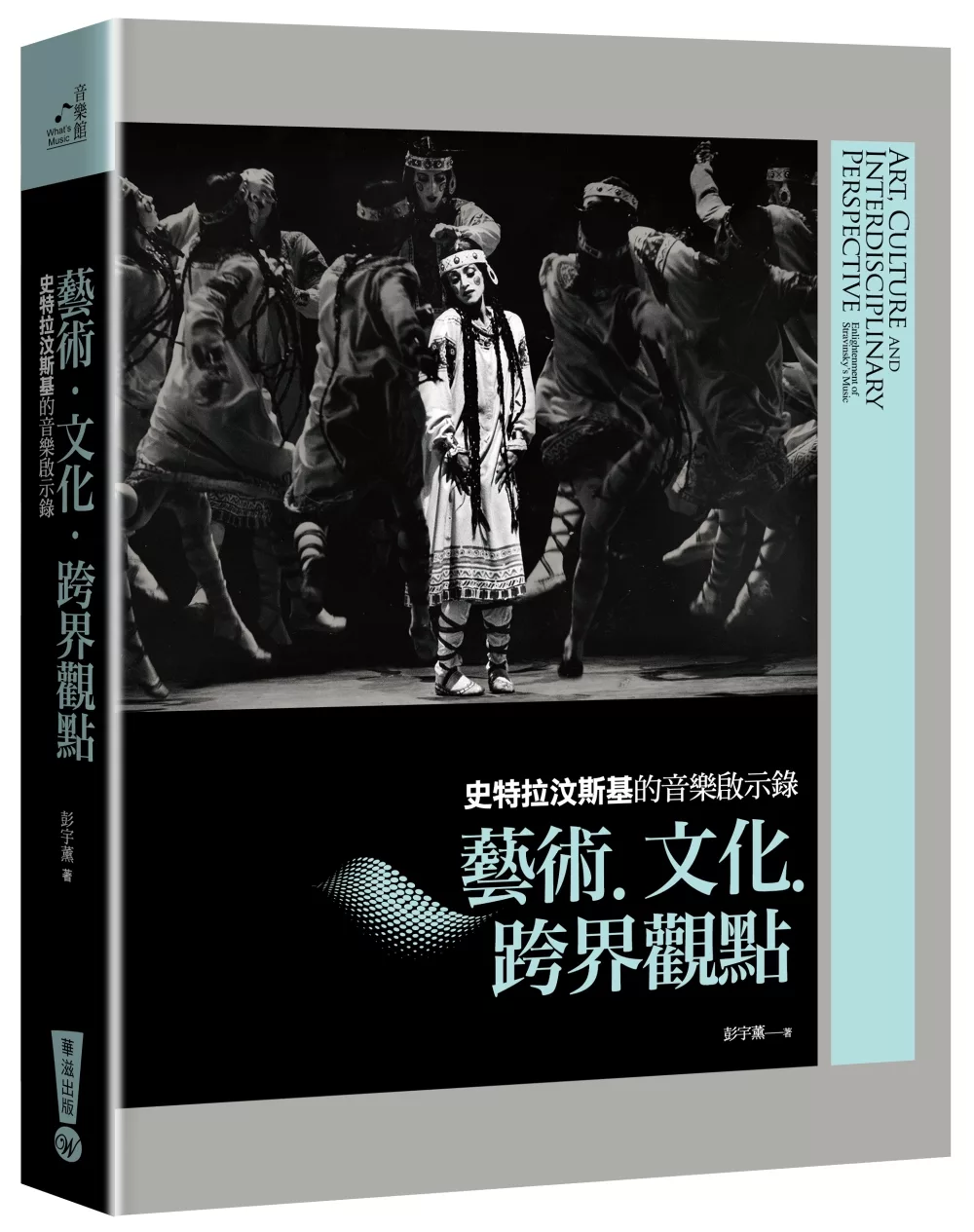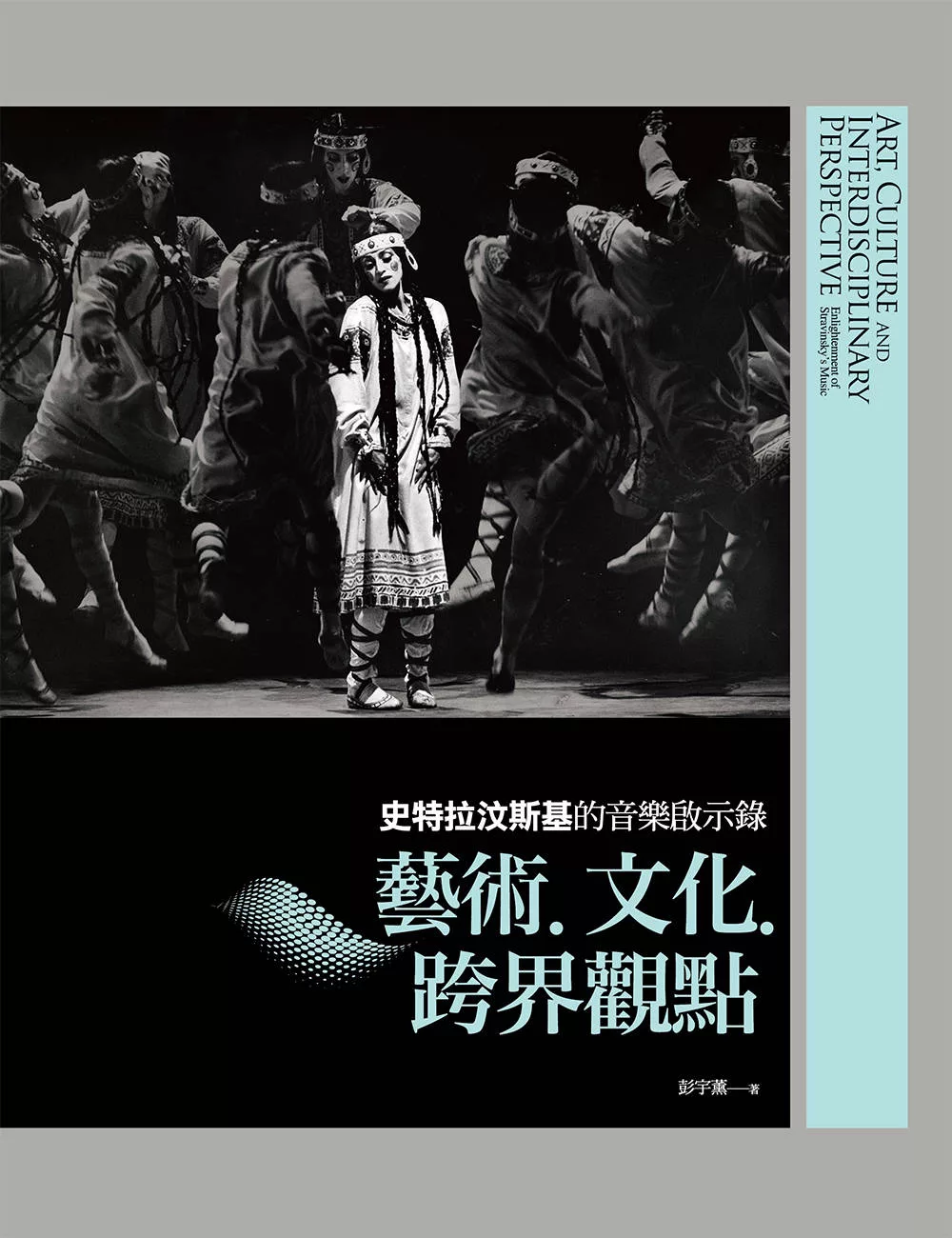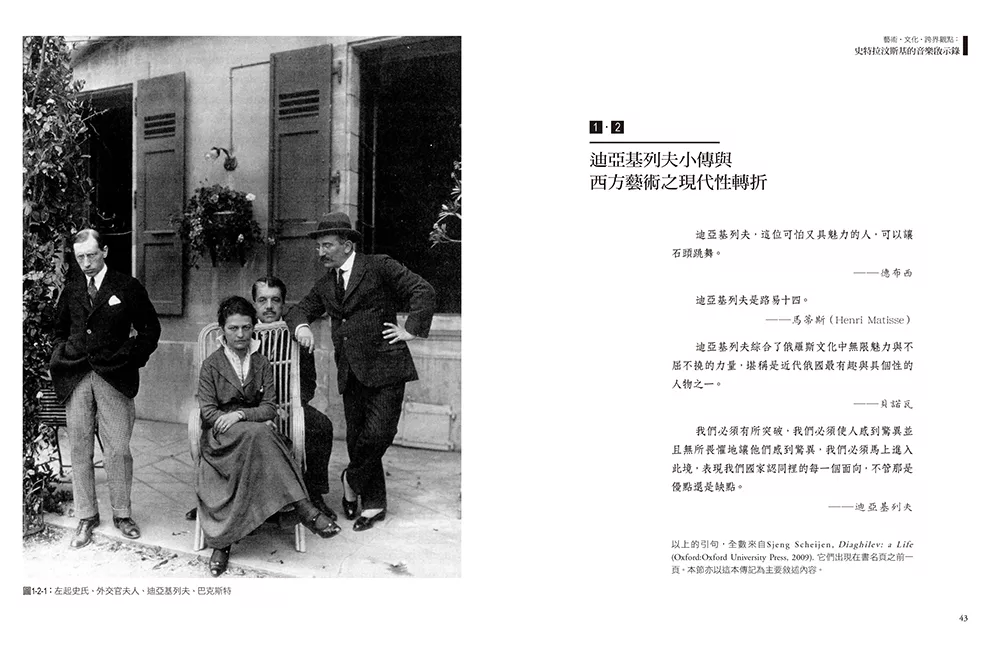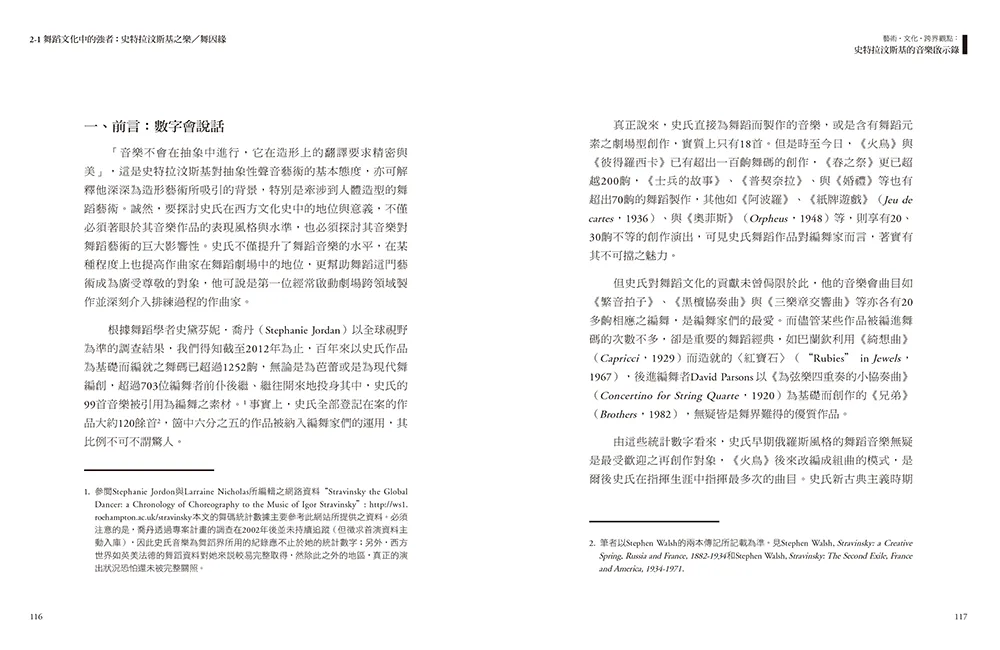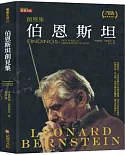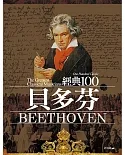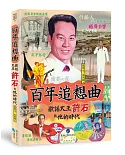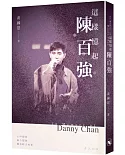自序
猶記得我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求學時,台灣正經歷一個經濟起飛的80年代,彼時行有餘力的家長們莫不趕送兒女進入古典音樂的學習殿堂。須臾間,有限的音樂教師變得炙手可熱,週末與課餘的個別授課常是人滿為患。每當聯招術科考試前夕,各大專院校音樂系的教授處所更是門庭若市,學子們莫不期盼經過教授的高招指點,能一舉進入名校。
那是一個西方古典音樂在台灣蓬勃發展的年代,中小學音樂班的開辦正方興未艾,「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則是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對出生於小康家庭的我來說,雖然學習古典音樂需要花費的時間與金錢都不算少,但它並不見得是所謂「貴族」的特有活動,一種西方式的文化教養正在這個島嶼生根。縱使不少現今四、五十歲的知識份子曾表達,當年因家境關係而無法學習樂器的遺憾,但一般說來,他們總有基本的古典音樂文化素養,
並且總是嚮往更深刻的理解與欣賞。
隨著90年代留學期間的美國經驗以及覺醒的台灣意識,我對古典音樂教育裡只為音樂而音樂的態度逐漸感到不滿,對於學界甚囂塵上的形式主義亦感到有所缺憾;在此,絕對與客觀的理論多數淪為學術智性的考驗,現代主義中唯我獨尊的西方大敘述系統,更讓非我族類無以翻身。我認為,不可避免的西化運動是一個在地化文化藝術更新的前置工程,但怎的現代性古典音樂就愈走愈益孤遠、愈益疏離?西方音樂如是,台灣本地亦不遑多讓;
知識份子縱有嚮往之意,卻難有著墨之心。
最近七、八年來,我幾次隨著台灣的「中華民國大專藝文協會」代表團前往中國參訪,由於團員中沒有人專精於聲樂,
我這位大學時期以聲樂作為第二副修的音樂人,遂不時被拱出來代表台灣團唱歌娛樂大家。學生時代所學的義大利歌曲早已拋諸腦後,幾首中國藝術歌曲倒還拾回一些,〈紅豆詞〉、〈西風的話〉、〈我住長江頭〉勉強讓賓主盡歡吧,但在新疆面對維吾爾人時,我徹底感到一己代表性之不足——於是,我複習早期的民間流行歌曲〈望春風〉,新學了一首客家平板,才覺得踏實心安些。猶記得2013年七月間在內蒙古民族歌舞國家劇院的臨時演出,簡單優美的〈望春風〉變成團員的驕傲與我個人演唱的「高峰」。是的,我來自台灣,但是我用什麼表示我身為音樂人的台灣主體性呢?
書寫俄國音樂家史特拉汶斯基的初始緣由,只是我一系列藝術跨界詮釋的延續性研究。史氏與視覺藝術界、舞蹈界的互動固然不是新聞,他的離散性命運、他的身份變動、他跨越現代與後現代的世代氛圍、他長達一甲子的創作——在在提供了新鮮的視野與有趣的議題。我不得不承認,古典音樂的確帶著它貴族的血液,跌跌宕宕地走入後現代多元、解放的民主情態,史氏作品以其特殊存活之道,使他成為極少數能被一般人指認出來的現代音樂大師。然而,優秀的作曲家何其多,為什麼被老天、被歷史揀選的是這一號人物呢?
晚近在後現代的反思情境中,文化研究的探勘角度為我解答了些許疑惑。史氏個人的歷史切片或許無法代表所有的文化現象,但由其音樂所折射出的變動世界,讓我深刻意識到藝術文化在型塑過程中,免不了權力階級、差別待遇,更免不了意識形態的介入、價值觀的扭曲。我們很難想像,在不久前的美國,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可能比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還要困難;我們很難想像,號稱最民主自由的美國,也是監視竊聽人民私聯通話的高手。真情與假象之間,距離其實不是那麼遙遠;藝術的真與美,
也從來不是那麼絕對。
即使歷史中反覆著種種難以迴避之人類「惡習」,我相信植基於文化研究的這些議題仍有偌大的探討空間,它們值得藝術界更嚴肅地面對與反思。當然,盡學西方的東西,無非不是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好好汲取其精華從而展現出更能代表自己的、更卓越的藝術文化。雖然史氏的狀況和我們有所不同,但俄國人自西歐化以來所歷經之種種轉折,乃至史氏流亡後所有的應對策略,
對我們皆是某種具「本土意識」參照的基礎。當然,唯有對史氏音樂以及其跨領域性質做深入探討之後,才能為文化研究鋪設良好的基礎,而〈音樂與視覺藝術的類比〉、〈舞蹈文化中的強者〉、〈《春之祭》世紀遺澤〉等章節即是修改自過去在學刊、論文研討會發表的文章,它們皆是我進入文化研究探討不可或缺的前置作業。不過,由於全書包含太多外國相關名稱,為減少冗贅之氣,有些較不重要或無法翻譯的外文就保留原貌,年代資訊亦予以省略,相信讀者可以體諒箇中形式上的某些缺憾。
在過去以寫作為主要成長方式的年頭裡,感謝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楊聰賢、王美珠老師的鼓勵,以及輔仁大學音樂系徐玫玲學姐的關照,音樂人的共鳴固然使我開心,但國寶級畫家林惺嶽老師不時的激勵與啟示,更讓我在起起伏伏的學術寫作過程中,不至懈怠與灰心。在此同時,我也要感謝信實文化出版團隊的全力協助與林呈綠先生為我的引薦,以及科技部研究計畫評審委員的支持,使這次的出版能以相當豐富的圖文規模呈現。除此之外,和我一同成長的旅伴Jenny、Sean
總是貼心關懷——這是讓我無所後慮而能夠持續閱讀與筆耕的基礎呢。
「我們從一段文句中萃取一句話,而當這句話和我們讀過的其他文字、著作、想法及作法產生共鳴時,這句話變成為一種可行的原則,一種哲學的位置。」1
是的,不只是一句話,有時候是一個舞步、一個姿態,有時候是一個形象、一個造型,它們不時為我設定一種哲學座標,為抽象的音樂提供了延伸性、溝通性、共鳴性的接合。倘若我離開音樂,其實是為了更接近音樂;個人長久書寫中的喜悅、不平、批判、讚嘆——箇中點滴,願與藝術思考者,一同分享!
彭宇薰
2016年二月 於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