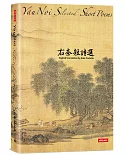推薦序
心存一念
講台上,來到了戰爭時代的抒情詩人,馮至,上個世紀三零年代留學海德堡大學,深受德語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影響,而寫下《十四行集》;聽教授講述著,在「史」的年代,「詩」及其衍生的自由、歧義、抒懷,創作主體性以至倫理的承擔,都是何其艱難。落過一場春雨的窗外校園,林葉和屋脊閃爍著眼底的光,像新世界。我便也想起《給青年詩人的信》裡,馮至的譯序,寫道多年前1931的春天,無意翻讀到那一小冊里爾克寫給年輕詩人的書信集而深刻的感動,「禁不住讀完一封信,便翻譯一封,為的是寄給不能讀德文的遠方的朋友。」
是晚,我在網路上讀到一段你的札記,「這是影響我寫作很重要的一本書……里爾克的詩句常帶給我很多的靈感,以及對於文學和隱喻之間的關係,有著更深一層的認識。」(2012年9月28日)你並且一字一句將全文鍵入,為的只是,抄錄給未能隨身攜此書信的遠方的朋友。
譬如我。我重新閱讀著轉抄的文字,也彷彿信來自於你。第一封中,詩人已摯誠坦言了貫穿往後五年間通信的主旨,「請你走向內心」;此外,還能多說任何的什麼呢?如果有可以多說的,或許也只是,在書桌前重讀的此時,我竟隱然感覺到原來詩、書信,翻譯,乃至抄寫之間,之於一位詩人,似都有如此接近的本質。也在這一刻,他人才能體會這麼多年,你生活意義的核心。
長期投入詩的創作、文學的翻譯,暫停一間名之為「布拉格」的書店,或只是為了前往真實的他方,力行抒情的生活。而這些遺跡,都留在你自上一部詩集《古事記》(2011年)到這一部《羊宇宙的沉默》了。你所不知道的是,我特別喜歡的,正是那些你貫上以「妳」為傾訴對象的詩行,〈五月病〉、〈空椅〉、〈心裡住著猿猴與馬匹〉……,口語日常,音韻在段落間複沓,讓紙頁上每句話語,都像在戀人小小的耳朵旁吟唱。
彷如書信。甚至連同另外一些徘徊於環墟的沉思,那些疊韻或回聲著里爾克到馮至所繫身的大時代命題的〈一無所有〉、〈德國零年〉或其他,在詩裡,除纏繞成更形複雜的構句外,無有分別地,被你摺起、封緘,沉甸甸地抵達遠方。
即便回音必然沉默,那也就是〈羊宇宙的沉默〉,「當整個宇宙沉睡/而你獨自清醒的時候」你說,「哲學家就誕生了」,詩人就誕生了,寄件和收信的人,唯有在這一句詞語寫下的所在誕生了。我們最感好奇的,難道不就是十封書信的起首註記下的時間、地名,巴黎、比薩、羅馬、瑞典……,從1903年2月17日,到1908年耶誕節第二日;但除此之外呢?橫亙於遷徙、在此和彼之間的廣袤荒漠呢?如同你寄給我的詩作,如同你同樣細心記下的時地(2011至2014間,卻收錄有一篇1998年9月6日〈夢曾經來過〉);單向投遞的話語,給三島、給飛翔者、給死難者、給妳、你、祢。
只要展讀,便令人想像起抄寫著文字的你靜默的身影。此外我們竟不知能再多說什麼。里爾克感謝遠方寄來的詩,遂手抄下,重附信中,「現在我又把它謄抄給你,因我以為能在別人的筆下再度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很有意義並且充滿新鮮的體驗。」於是此刻若還有一句話可說,我願敬謹抄下,在你曾面對人世艱難時,寫下的一句:「心存一念,唯有寫詩。」
李時雍
後記
很長一段時間,我寫不出詩,什麼都寫不出來。我當作自己廢掉。我什麼想法都沒有,像飄浮在人間的遊魂,像一把被遺忘在車站月台的雨傘。那段日子,白晝很短,黑夜特別漫長。書本在我身邊,但我沒辦法去讀它;電影在上映,但我沒有興致去戲院看它。我沒有專注力在任何事物上頭,過日子充其量不過是在數饅頭,而且還是又冷又硬的饅頭,嚼之無味又棄之可惜。
肚子餓,該吃飯了,有點累,該睡覺了。任由日子如流水,沒有任何意義附著其上,也不是沮喪,也不算憂鬱,只是有點提不起勁,感覺倦怠,對所有事都無能為力,一種強烈的無力感,或許察覺自己的變化總是比較慢。像是走進自己黑暗的洞口朝內在探索前進的感覺,愈走進去愈幽暗,漸漸的進入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那是所有色彩胡亂攪拌之後,形成一團濃稠化不開的黑暗。
妳說要找到一個完全懂得自己內心想法的人很難,要覺得他是懂妳的,而妳亟欲訴說的一切只有他明白,能全部接納進去不需要多餘的言語,妳覺得這個人將會是妳生命的出口,那專屬於妳絕對性的唯一,不做第二人想,就是他沒錯!可是要找到這樣人何其困難,或許終其一生也找不到怎麼辦?怎麼辦啊,妳忍不住想要吶喊,那個人別害羞趕快現身吧。多希望就是現在。
妳說的那樣的人,於我而言通常都是死掉的人。我覺得很懂得我的人,大部分都是死掉了留下著作的人。在書裡面,無關乎死亡,可以進行無邊際的對話,妳說對話或許有用,但它不能擁抱你。沒辦法呀,他已經死掉了,我只能擁抱他的想法,揣想他說話的神態,發亮的眼神,滔滔不絕的魅力。妳說體溫很奇妙,是啊很多話想說的時候,體溫很簡單地說明了一切,解釋了一切,也寬恕了一切,有些話再說也是多餘,所以人們如此渴望擁抱彼此,卻時常找不到可以擁抱的人。
對於擁抱,我沒什麼特別的想法。但坐擁書室,被逝去的亡靈們圍繞,有莫名的安心感,不知怎地,我特喜歡睡在圖書館的感覺。波赫士曾說過「在我心中,天堂就是圖書館的模樣。」在我的夢境中,曾到過各式各樣的圖書館呀,比方說,亞歷山大的香料圖書館,這個世界上只要你叫的出名字的香料,在這座圖書館的中庭花園都有種植,有專人為你解說香料的歷史,產地,特性,以及它們如何調理在各類食物之中使其增加味蕾的觸感,香料的魔力乃至於渴望擁有珍貴香料的人們所引發的戰爭,圖書館收藏著大量典籍記載著香料王國的崛起與殞滅,聞香室收藏著各式香料暫存的芳芬和獨特氣味,它有著難以形容描述卻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質。
至於飛翔者的圖書館,分門別類收藏了將近十萬種各式鳥類的羽毛,會飛的史前獸類藉由骨骼化石數位重塑的模型高掛於圖書館的天井之上,古生物學家發現的始祖鳥、飛蜥蜴,還有那些名不見經傳,卻真實存在於地球歷史上的飛翔者,從牠們曾經存在過的痕跡去想像當時的天空多麼地擁擠,而人類是多麼地疏離。藉由造型各異的翅膀去揣想億萬年的遷徙和流浪,藉由飛機的殘骸去領略人們永不停歇的進化欲望以及權力鬥爭史。有沒有一雙隱形的翅膀,可以載我去月球漫步數日,有沒有一雙堅強的翅膀,可以讓我毫無畏懼的面對每一天精神層面的攻擊和損傷。
以前啊,有位朋友對我說,他覺得我這個人給他的印象就是一個微笑有點神秘的古堡主人,擁有數不清的房間,裡頭收藏著珍奇的各式寶物之類,而且是不輕易示人的那種。其實我還有好幾個房間,專門用來蒐集世界各地流傳的故事,或是從朋友那裡聽到奇人異事,要進行這樣的蒐集並不容易,你必須時時刻刻保養好你的耳朵,要夠專注才能聽見細節,別讓故事近在眼前卻溜走了,蒐集故事要有充足的耐心,敲不壞的好奇心,也不能有差別心,任何故事都有它的教訓和意義,能活在故事裡多麼幸福啊!
我曾經遇過一個在故事森林走失了的孩子,他衣衫不整,他淚眼婆娑,他的鞋子不知掉到哪兒去了,他的腳趾髒黑,他的身體發抖,他驚怖的眼神像是在述說這整起事件的離奇和慌亂。我心疼因為他如此像過去的我,曾經沿著樹根和落葉找尋遺落的麵包屑,曾經繞過蜘蛛網和露水,尋找屬於永無島的捕夢網,曾經以為長大之後,很多事情的狀況會好轉,曾經以為努力就會有收穫,但仍舊一事無成,一無所有。當我們仔細計算失去的時候,我們失去的更多。
因為害怕失去,我又重新開始寫作。
剛開始什麼都寫不出來,這種情況很正常。下筆的第一句最難寫,深怕變成什麼詛咒似的,於是我試著亂寫,先從紊亂的思緒中,隨便抓一句抄寫下來都好,我好慌亂,我毫無頭緒,但是下筆之後,情況有了好轉,那些如蒼蠅無主亂飛的思緒,好像因為抄寫這個動作,而被牢牢釘在思緒的捕蠅紙上。反正是亂亂寫,反正也不會有人認真看,我寫得輕鬆自在,更肆無忌憚。我只是想寫東西而已,我不是想寫文章,我只想寫給自己看,我不是什麼文學作家。我寫只是因為我渴望從腦袋中孵出些什麼,健達出奇蛋也好,石安牧場溫泉蛋也好,我想寫是因為不寫會死,我害怕自己變成了生活的機器,按照不知是誰規定的步調上緊發條,最後的目的只是為了衝向死亡的終點。
每次當我面對電腦搜索枯腸,靈感匱乏的時候。總有一些影像最能勾起我的記憶,我不能任由滴答的秒針折磨自己脆弱的神經線,所以我必須從記憶裡去深掘那些以為早已被遺忘了的故事,我必須努力去書寫並記錄自己成為一個不甘於成為生活俘虜的人,我必須隻身去對抗時間無情的侵蝕,不管是肉體的衰亡還是靈魂的腐敗,我必須透過書寫更加了解自己的軟弱和無助,醜陋與不堪。透過書寫試著去安撫不規則跳動的心臟,透過書寫與他人建立若有似無親密的連結,透過書寫去建構一個不存在的帝國,看它狂妄的無限擴張又在瞬息之間崩毀消失,一如昨夜嘔吐的穢物,早晨起來已被勤勞的清道夫打理的連渣也不剩了,我的夜間生活如同鬼魅,總在曙光乍現時煙消霧散。
很長一段時間,我寫不出詩,什麼都寫不出來。
後來,一個字一個字,我透過鍵盤打出來,然後是一個句子接著一個句子,一隻鳥接著一隻鳥,我渴望擁有的翅膀,如今又羽毛漸豐的茁長。那些原本無意義的字串組構成行,連綴成篇。我恍惚的夢境又變成了具體的影像,彷彿在意識裡重新活了一遍那樣清晰自然,鮮活躍動,歷歷如目。於是有了詩,有了文章和故事,有了小說情節,我說不出的感激,瞬間的狂喜和悲傷,如針刺向我的心臟,所幸這顆心沒有被冰凍起來,沒有僵固硬化,沒有被現實的鎖錬所綑綁,所幸我還有做夢的能力,我還願意試著去飛翔,用我敲鍵的手指,用我柔軟的意志,傳遞這些訊息給遠方的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