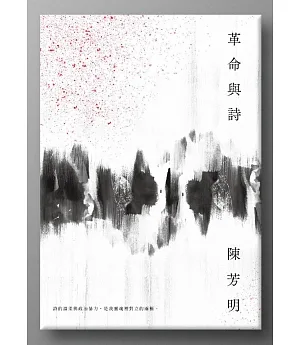序
殘酷與唯美的辯證史
自剖的文字,便是剖開時間的假面與神情的表面,再一次深入內心世界探索曾經有過的喜悅與悲涼。也許對許多人來說,記憶是美好的體驗,可以再次召喚發生過的幸福與喜悅。捧讀那樣的記憶時,我常常情不自禁給予祝福,因為那是我未曾企及的境界。當我開始回頭眺望自己在海外的流浪生涯,潛伏許久的痛楚隨著文字的浮現而再次回到我心裡。對於那十餘年在海外所承受的鄉愁,有很多時刻簡直是不堪回首。每一個人生都有飛揚與沉落的時刻,我也不能例外。每次造訪舊金山唐人街的時候,我會告訴孩子,在一九八○年代來這個陳舊街道散步之際,正是我處在人生的最低點。兒子與女兒總會帶著迷離的眼光注視我,那段時期他們那麼開懷又那麼興奮,怎麼可能會與父親的落魄時刻連結在一起。他們可以看到我的表情,卻無法進入我的心情。舊金山的繁華與喧囂,在我生命軌跡烙下深深的刻痕。
兩年前開始寫「晚秋書」時,便是帶著一種期待,希望在記憶裡重新走過我的七○、八○年代。那時的主觀願望是,只要勇敢面對從前發生過的一切,便是在進行一場精神治療。那樣的願望,並沒有像預期那麼順遂。那些年發生太多複雜的事件,每個過程都像刑求那樣極其漫長,極其殘酷。那麼多年已經過去,常常有人情不自禁問我,如果生命可以重來一次,你還會繼續投入海外的政治運動嗎?那是沒有確切答案的提問。只要想起那種時間與空間的凌遲,我必須承認自己也會感到畏怯。但是如果換一個方式問我,對於那長期的漂泊會不會感到後悔?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絕對不會。人生從來沒有捲土重來的機會,對於發生過的一切,究竟以怎樣的態度去接受,恐怕才更貼近內心的感覺。
我曾經動搖過,甚至瀕臨崩潰。那是二○○八年貪腐事件爆發時,我驟然感覺微近中年時期的投入是那樣不值得。懷抱過那麼多的夢想,追求過那樣高的價值,卻因為政治領導者的脆弱,使得自己建立起的心靈城池幾乎搖搖欲墜。在那段時期,我一夜之間失去許多朋友,也招來排山倒海的誤解。那個情境多麼像極洛杉磯時期的孤立,曾經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卻換取了一無所有。所有的理想已經在望,卻在瞬間被剝離淨盡。在絕望的末端,總是有一股聲音祕密傳來,如果終於怯懦了,在海外穿越過的那些折磨便更加不值得。在驚險時刻,反而是流亡時期所累積起來的意志,挽回了我。憑藉那股意志,我繼續完成夢想中的《台灣新文學史》,並開啟日後無窮無盡的書寫。
在教書生涯的最後階段,好像是迴光返照那樣,蓄積了更多的創造力,同時也鍛鍊了百毒不侵的勇氣。正是藉由這樣的轉折,我決心更進一步去直視千迴百轉的漂流生命。二○一四年初春,終於開筆寫出海外記憶的第一篇文字〈詩的湖泊〉。那時我便預見許多挫折、痛楚的記憶,又將不斷回來。這本回憶散文,與過去自己的文學作品,有很大的落差。尤其二○○八年完成《昨夜雪深幾許》時,充滿了太多喜悅。同樣是回憶過去發生的事情,我專注在幾位長者的描寫。他們在知識上、人生上,帶給我太多的啟蒙與引導。寫出那部散文時,無疑是向我自己成長的歲月頻頻致敬。
如今站在太平洋這一邊自己的土地上,回望另一個海岸所發生的生命起伏,不時會感受到時間如洶湧的海浪席捲而來。所有的書寫都是淨化的過程,許多不堪的、黯淡的、污穢的記憶透過文字過濾,可以到達某種程度的昇華。然而,一旦陷入記憶深處,許多企圖遺忘的經驗事蹟,竟然是那樣生動地浮現在眼前。穿越在時間的甬道之際,彷彿是走過死蔭的幽谷,那些遠逝的魂魄再度回到我的桌前。那些靈魂,無疑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他們一個一個死於匕首與刑求之下,似乎也在告訴我,他們的命運也就是我的。揭開記憶的封面時,死亡的氣息撲鼻而來。與死魂靈相對時,我也一樣被帶到一個看不見光的黑暗所在。只因為我的政治信仰與意識形態,與那些劊子手全然兩樣,就必須接受那殘酷的暴力審判。到現在我還深深相信,他們的赴死,其實就是為我付出代價。
一個正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書生,有必要為了知識以外的信仰,而投入政治漩渦嗎?在靈魂底層,我頗知自己是一個唯美的浪漫主義者。那種浪漫往往帶著無可實現的狂想,只要能夠實現一點點理想的夢幻,便覺得付出任何代價都非常值得。政治場域是所有污穢價值的集散地,凡是落入其中,就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拉進無窮深淵。身為台灣戰後的知識分子,長期受到權力的綁架,受到鷹犬的監視。即使稍有不慎的言論,就有可能招來殺生之禍。我的唯美,其實只在追求生命的最低尊嚴。畢竟面對的那個時代,是多麼殘酷、多麼充滿暴力。如果沒有親身陷身於泥淖裡,就不可能獲得救贖的契機。
身為唯美的理想主義者,對於美的定義其實是非常寬鬆。只要不受到誣衊,或不受到侵犯,這個世界就值得活下去,而稀薄的人生也可以堅持下去。政治從來都是無所不在,權力也是無時無地在運作。在政治(politics)與詩意(poetics)之間,常常存在著緊張關係。權力干涉多一點,詩意就減少一點。而詩學增加之際,政治就可以退縮一些。如果不投入醜陋的政治裡,在那個時代就永遠處在被支配的位置。於我而言,人權與生命尊嚴往往不容於權力在握者。我對人權議題看得特別嚴重,因為那是生命美感的本色。只要放棄了抵抗,大約就放棄了做人的權利。面對鐵蒺藜圍起的權力城堡,反抗行動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展現。
縱身投入起伏不定的政治運動中,一方面要抵禦來自當權者的迫害,一方面又要忍受來自同樣陣營不同路線的挑戰。在兩面作戰的過程中,幾乎可以探測到生命的韌性與耐性。那時不斷提醒自己,只要能夠完成一篇批判的文字,生命版圖就可以擴張一點點。尤其發現自己的文字,能夠回到故鄉發表,便覺得有一種偷渡的快感。更重要的是,覺得自己又回到島上與朋友對話。然而,我不能不覺得感傷,經過了美麗島事件、林家血案、陳文成命案、盧修一事件,不能不讓我覺得返鄉的道路是何等崎嶇難行。
如果關在書房專注書寫論文,把整個邪惡的時代關在窗外,其實也可以心安理得。然而不然,加入了國際人權組織之後,故鄉不再是我青春時期的夢土。那麼多的羞辱、損害、屠殺,在暗地裡祕密進行,必須到達異域之後才全盤理解。知識的建構,究竟是在現實的基礎上,或是在脫離現實的夢境裡。這樣的懷疑曾經在我的內心展開激辯,我終於不能不承認,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者,不會這樣輕易饒恕自己的逃避。有一把美的標尺暗藏在心底,那也是以人的尊嚴為基準,如何去衡量外面那可疑的世界。被放逐在遙遠的異域,我從未輕易放棄那把尺。雙重視野的對比,在任何時期都存在著。當權者在島上施行的暴力與迫害,我都是用人權的準則進行批判。站在我的對面,是不斷墮落的權力慾望;存在我的內心,對人權的尊崇則未嘗稍懈。這是我的流亡生活,永遠進行著辯證思考,一正一反的詰問也未嘗稍讓。
海外流亡生涯為我保留的遺產,便是不斷向權力講真話。我寧可站在被損害、被屈辱的這一邊。而這樣的思考,也延伸到我日後的歷史書寫、文學創作、政治批判。長期在海外的生活,讓我養成了離群索居的脾性。我從來不會成群結隊,也不會譁眾取寵,在恰當時刻,我勇於參與遊行示威,願意與被壓迫的弱者站在一起。即使生活在最孤獨的空間,我與我的家國時時都在進行無盡止的對話。能夠回到自己的土地,我為自己感到慶幸。這樣我可以確知,有一天自己的骨骸就要葬在這個海島,葬在燥熱而潮濕的土壤裡。只有嘗盡漂泊滋味的人,才知道這樣的夢想是多麼美,是多麼無懈可擊。尤其進入晚境時刻,回顧自己曾經參與過的每場戰役,我確實是盡情燃燒了自己的生命。穿越過無數的醜惡,那麼多無數的試煉,我一直都是義無反顧。坐在書窗前,一字一句寫下我的晚秋書之際,我為自己身為台灣人感到驕傲無比。
2016.3.18 政大台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