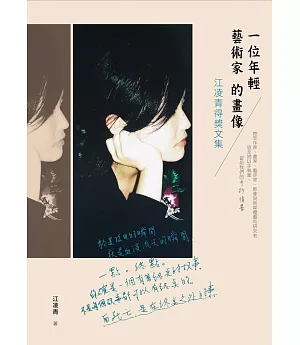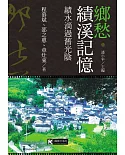序
我頭痛,故我書寫
這是一本關於江凌青(1983-2015)─一位才華洋溢的年輕藝術家─的得獎文集,她的早逝令人婉惜。我們僅以這本書表達對她的不捨與思念。
凌青的突然過世讓我們發現原來我們對她並不熟悉。江凌青是誰?為何她走得如此突然?她對文學、藝術的中心思想是甚麼?她的突然離去驅使我們得認真思考這些問題。2015年1月17日,我與幾位學術同好約好在台中高鐵站的一家咖啡廳碰面討論一些事情,大家都到了,唯獨凌青還沒來。這很不尋常,印象中凌青不曾遲到。我的一位學術界好友打了電話給她但沒接通,不久後我再試看看。電話接通了,是凌青的弟弟。他說他姊姊半夜突然走了,所以再也無法履行到高鐵站與我們碰面的約定。
跟每個人的反應一樣,我覺得對方講了一個不好玩的玩笑,雖然我顫抖的聲音告訴我事情恐怕不妙。掛完電話後,我們幾個人呆呆坐著,相視無語,我想我們應該保持了有一個世紀的沉默吧!當天我們要討論一些重要議案,我也不知道接下來的討論是怎麼進行的,只覺得這家咖啡廳好吵好吵。我想到了Emily Dickinson的這一首詩:
I heard a Fly buzz – when I died –
The Stillness in the Room
Was like the Stillness in the Air –
Between the Heaves of Storm –
The Eyes around – had wrung them dry –
And Breaths were gathering firm
For that last Onset – when the King
Be witnessed – in the Room –
I willed my Keepsakes – Signed away
What portions of me be
Assignable – and then it was
There interposed a Fly –
With Blue – uncertain stumbling Buzz –
Between the light – and me –
And then the Windows failed – and then
I could not see to see –
創傷過後,我們慢慢開始建構意義與秩序。透過凌青家人、朋友、同學,還有她留下的日記(根據江爸、江媽轉述,凌青一直保持著幾乎每天寫日記的習慣),我們一步一步走出創傷驚嚇,開始拼湊「事實」。其實凌青生前已經有一些病症,包括頭痛、心律不整、心跳過快等問題,只是她不常提及這些問題,我想即使她說了,我們也只會一笑置之,看成是像小感冒一樣的身體反應吧!因此我們一直都只看到她不凡的才華,以及那可愛到不行的誇張笑容。江爸告訴我,凌青死亡證明書上寫的死因是心房中膈缺損、腦血管狹窄硬化以及窒息性腦病變休克。雖然我很難把凌青跟這些專有醫學名詞聯想在一起,但我們不得不接受在她快樂天真的外表下應該一直存在著一具經常作怪、經常找她麻煩的身體。我在想她的頭痛、心律不整、心跳過快是否與她驚人的創作力有關?她的書寫是不是一種頭痛/書寫?
認識凌青是一個偶然。2013年,我還在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研究發展組組長,當時整天想的都是如何深化臺灣人文研究等事情。瞎忙了一段時日後終於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每個人能夠完成的事情畢竟有限,唯有培養一批年輕人,臺灣學術界才有未來。長遠來看,個人雖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制度和系統。當時流浪博士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了,眼看著那麼多優秀博士無法將其所學即時回饋給國家社會(畢竟知識也是有保鮮期的),這一點讓已經在體制內享有安全位置的我感到惶恐與不安。既然有機會提攜後進,我當然必須全力以赴。秉持著這樣的想法,我們發出了博士後研究的徵才啟示,在厚厚一疊申請書中,凌青毫不意外地被挑中了(事後得知其實不是我們挑中她,是她挑中了我們。以她的條件,她大可選擇別的地方)。當時我只覺得她很優秀,但沒想到她這麼優秀。
凌青生長的世代是後現代雜食主義的年代,這時代的年輕人有著前一代所缺乏的資訊與科技資源,如果再輔以個人才情,的確能夠創造出前人難以達到的成就,凌青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在她身上我們看到眾多個人與社會力量互相嵌入的烙痕,短短三十一年的歲月,她實踐了多重身分的展演:文字創作者、畫家、藝評家、影像與新媒體藝術研究者等。2014年取得英國萊斯特大學美術與電影史博士學位後,她選擇了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正要開始展演她另一身分─學者─時,一切又突然終止了。
對凌青來說,文字、影像、繪畫、多媒體藝術等之間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小小年紀她已經將觸角伸進這些不同的領域。平常人得花上一輩子時間鑽研,她卻四處游走,遊刃有餘,看似不專情,不專心,實際上反映了她從小到大的不凡野心,企圖在所有藝術領域都能交出出類拔萃的成績單。這一點已經在她學生時代作品中表現出來。在〈禱──羅丹對自然的頂禮膜拜〉中,凌青如此描述羅丹這位藝術家:「羅丹的雕塑作品充分展現文學的質感、戲劇的表情、繪畫的延伸、音樂的凝結。其實不至雕塑如此,各種藝術都有互通的語言」。這段話與其說是凌青對羅丹雕塑作品的評論,倒不如說反映了她從小到大隱藏在內心深處的一個秘密,那就是試圖找出存在於所有藝術品(包括文學、戲劇、繪畫、音樂等)的共同語言或「互通的語言」。或許是如此偉大的企圖心,以及伴之而來的焦慮感,她才能夠找到生命的意義,但不幸地或許也因如此,才種下了早逝的遠因。對凌青而言,生命與死亡或許原來就是一體的兩面吧!
聽凌青父母親提起,凌青的日記本曾數次提及缺乏痛苦、焦慮的生命不是生命。我想凌青想要表達的是,生命的意義在於勇於面對否定生命的一切。在世時凌青經常頭痛,過度劇烈的運動也會讓她的心臟承受不住。某方面來說,這些身體的不適反應與從事文字、繪畫或學術論文創作時的焦慮感類似,都是令人不舒服,甚至痛苦的經驗。它們都是否定生命的力量,但這些力量因為讓生命產生危機感,反而肯定了生命的價值。凌青日以繼夜的工作,成天在「趕進度」,我想她應該體會到否定生命的力量的無所不在吧!本書名為「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實際上乃是這位藝術家面對生命與死亡的辯證時的心血結晶。從凌青身上我發現了書寫或創作原來是要否定那些否定生命的力量:我頭痛,故我書寫。從她短暫生命所爆發的驚人創作能量,我們看到了她在世時如何持續堅定地對抗頭痛,如何否定否定生命的力量。雖然她的身體已不復存在,但透過本書裡那些爬滿頁面的文字,我們找到了另一具身體,另一個生命。還好生命、死亡、書寫,三者互為因果,沒有先後,只能共存。〈獻給自己的手抄情書〉中寫到,「還好,我曾經那樣寫作過;穿越荊棘之林那般,耗盡力氣卻又不知目的的寫作」。我說,還好,凌青曾經那樣寫作過。還好,她留給我們這本書。
對凌青來說,生命與死亡、文字與非文字藝術之間本來就不是壁壘分明的兩極。凌青的跨界還不僅於此,她的作品也經常跨越了真實與虛構、自傳與小說的界線。〈畫室裡的斑光〉有這麼一段話: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繼續去學畫,也許只是把畫室當作一本小說手稿來閱讀,也許只是因為安靜的畫室讓我想到Stanley Kubrick導演的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這部對白稀少的電影,以《藍色多瑙河》為配樂來襯托電影中輪形太空站與太空旅行的場景……
凌青總是這麼跨界、這麼拼貼:繪畫可被當作小說來閱讀,也可視為電影以及電影配樂。小小年紀她就早熟地追求那隱藏於各個藝術形式之間的共同語言。但這裡的敘述者「我」如此熱愛繪畫,不免讓人聯想到「我」是不是凌青本人?凌青過世後,我數度到她位於霧峰的老家探望。江媽媽告訴我,凌青很會想像,她作品裡的有些東西明明在現實世界從未發生,但她卻能夠寫得好像有這麼一回事。的確,凌青的小說有時反應了她的生活經驗,有時卻又只是小說。但何謂「只是小說」?在我跟凌青合編的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論文集《新空間.新主體:華語電影研究的當代視野》中,我們討論到許多關於生命、藝術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多少反應在我們共同撰寫的導論中。在這名為〈以電影發動的細微革命〉的導論一開始,我們就點出了真實與小說、生命與藝術的界限本身其實是虛構的,而評論者的目的就在於打破此種虛構的界限。我們以美國名劇作家Tennessee
Williams的《慾望街車》中的女主角布蘭奇(Blanche)所說的「我不需要寫實主義,我需要魔術」作為思考點,主張藝術不應該只是被動地反映現實,而必須否定、扭曲現實,甚至創造真實。文字是生命的見證,也是死亡的遺留,我與凌青合寫的這篇導論,現在讀起來特別令人不勝唏噓。生命太過寫實,太過醜陋,因此需要想像,需要虛構。凌青那麼熱愛電影,或許是因為電影夠「假」吧!
從小到大凌青得到的文學獎項無數,本書僅收錄她從高中一年級(1999年)以後的得獎作,共37個獎項,38篇作品(2014年獲得的第九屆葉紅女性詩獎包括了〈鐵皮島〉和〈沒有人行道的國家〉兩首詩)。最後一篇〈獻給自己的手抄情書〉雖然不屬於得獎之作,但它在凌青走後才出版,而且總結了凌青關於寫作的想法(對她而言,寫作是生命,但何嘗不是死亡呢?),與江爸、江媽討論後,決定將本篇收錄於書本最後的附錄當中。一個人的一生總是包含了無數的面向,凌青的一生特別如此。雖然我們永遠無法完整地捕捉江凌青這位年輕早逝的藝術家,但我想如果讀者想要透過一本書來勾勒她的話,這本書應該是相對完整的選擇。
還記得2015年1月17日那一天的下午,台中的天空沒有因為冬天而憂鬱,反而給了人們燦爛的陽光作為奢侈的禮物,但直到那天我才明白原來冬天的暖陽可以如此之殘酷,因為我們失去了凌青。時間是無感的,哀傷不能止住時間的腳步,春天、夏季畢竟還是來了、也又過了。還好我們來得及趕在凌青逝世一周年之前完成本書出版。在這裡我得感謝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邱貴芬老師的大力幫忙,還有書林出版社蘇恆隆先生以及劉怡君主編的全力配合與協助。此外,中興大學外文系的學生們(包括楊雅蓉、何屏、洪翊芝、劉詞、高瑩芝、陳怡欣、郭宗儒、葉舒文、張寧、吳映儒、郭蕙嘉、李佳喻、詹佳玟、李佳珮等同學)在此過程中也幫我做了許多的連絡、打字、校對等繁瑣事務,在此一併致上我最真誠的感謝。最後,感謝江爸、江媽,還好有你們;還好,還有江凌青,她給了我們不同的世界,而世界也因為她而變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