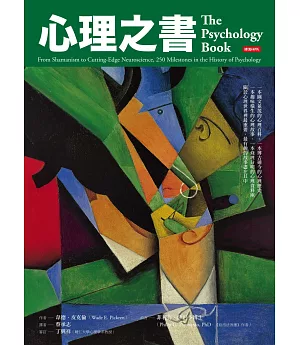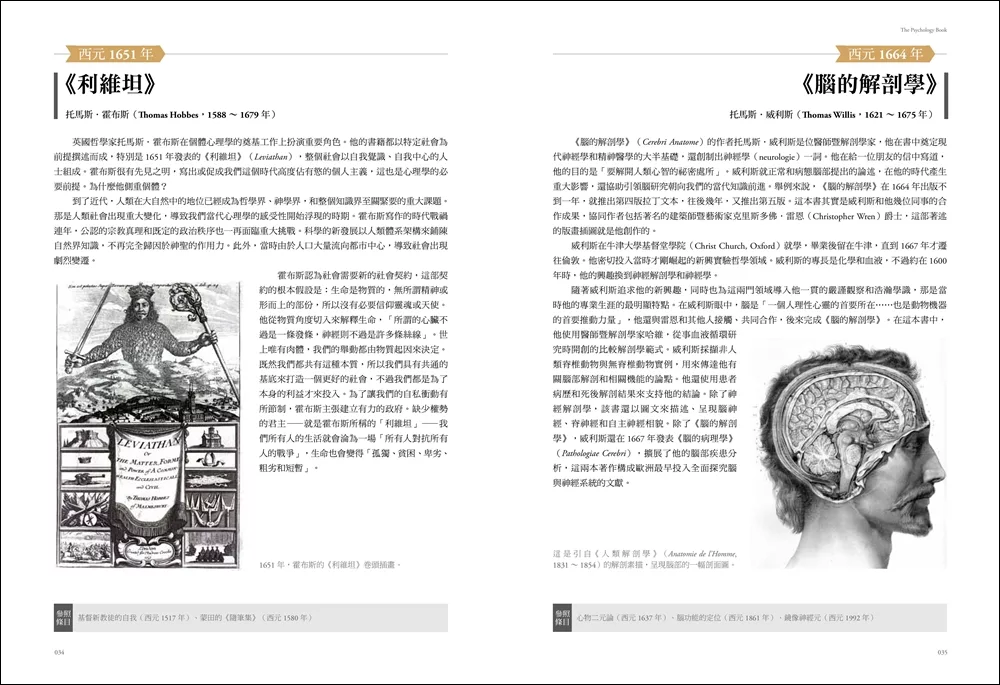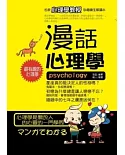前言
人心自成方寸之地,於此方寸,自可化地獄為天堂,天堂為地獄。
──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失樂園》(Paradise Lost),1667年
四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項實驗,結果讓我惶恐不安至今。當時我探究的問題是,「在哪些情況下會滋生惡?」我要志願受試的大學生到史丹福大學地下室,參加一處模擬監獄的角色扮演操練,卻眼見他們甘於犯下殘酷惡行。事實上,這項預定執行兩週的實驗,只做了六天,我就看不下去了,不得不喊停。提前終止的原因在於,那群白人中產階級的年輕男子,經隨機指派為「犯人」或「獄卒」之後,在行為和心理都出現急遽轉變。除了我的研究之外,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也曾論證顯示,絕大多數成人很可能受誘盲從不義的權威,我們的研究都以戲劇性方式闡明,情境力量對民眾性格傾向具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幾十年過後,美軍犯下(2004年)阿布格萊布監獄戰俘凌虐事件,證明了史丹福監獄經驗的真實性。我在2007年著作《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拿這兩種情境做了比較,清楚闡釋當這種明顯的權力不對等情況被誘發之時的心理動力。這種動力包括去個人化、對權威服從、自我辯證、合理化和去人性化。尤其是後者,更助長讓正常人變得冷漠無情甚至恣意妄為,成為心懷偏見、作惡邪徒的核心要素。除了探究滋生惡行的力量之外,我對於人心和情境當中會導致無所作為、大眾冷漠(public
apathy)之惡的種種力量,向來都很感興趣。我希望了解令人漠視旁人苦難的作用因素,那個因素就是在緊急狀況或霸凌情境下的旁觀者效應。
我的專業生涯,大半都投入研究惡的心理學,促使我這樣做的因素,也同樣驗證一種由滋生罪惡之「系統性力量」,塑造成形的更寬廣情境具有何等威力。大蕭條期間,我在紐約市南布朗克斯的貧民區度過清寒的童年,那段成長歷程塑造了我對生命和事情輕重緩急的看法。在都市貧民區過日子,最重要的是養成有用的「街頭智慧」求生本領。意思就是要搞清楚,誰掌握可以用來對付你或幫你的力量,哪些人你該避開,哪些人你該奉承討好。這就表示你必須解讀微妙的情境線索,來決定何時押注、何時棄牌,目的就是要創造互惠對等義務。對我這個瘦弱多病的小孩來講,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要具備哪種本領,才能從被動的追隨者轉變成活力充沛的領導者。對我來講,這就要在種種不同情境之下觀察的兩種人。一旦得知行為和風格上的關鍵差異,要永遠當個領導者、首腦,或者經遴選、推奉為總裁(甚至當上美國心理學學會的會長),也就不是難事了。
在那個時代,貧民區生活就是一無所有的人過的生活。這其中有些孩子成為暴力受害者或加害者;有些我以為良善的孩子,最後卻做出很壞的事情。有部份原因是由於他們受到較年長混混誘惑所致,因為那些人的行為舉止就是想讓那群孩子做壞事來幫他們賺錢,好比販賣毒、偷東西,甚至出賣身體。在我看來,那群孩子和我另一群沒有逾越善惡邊際的其他朋友,有個明顯的差別:就是能夠保持積極價值觀的那群人,比較可能來自父親大半時間都待在身邊的完整家庭。
不過連我們大半保持良善的孩子,都有個東一五一街成年禮儀式。街頭幫派有個入幫步驟,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到雜貨鋪偷東西,和其他更晚近才加入的另一個小孩打架,表現某種大膽舉止,還得脅迫旁人。我們心中,那些舉動完全不是惡行,甚至不是壞事;我們不過是聽從團體領導人,服從幫派的規範而已。從這樣的成長背景就能清楚看出,我是從哪裡養成對腐化權威力量的好奇心,並確立公開反抗貪腐的終生職志──包括批判迫使美國捲入越南和伊拉克兩場邪惡戰爭的政治勢力。
我在美國心理學學會時期的前同事,韋德.皮克倫蒐羅心智和行為研究,彙總出一組出色的歷史里程碑,為讀者帶來範圍更廣闊、意義更深遠的內容,來釐清四十多年前在史丹福大學那處地下室開展的事件。當然,這部獨一無二的讀物,作用還不只於此──它為我們鋪陳一幅生動鮮活的歷史脈絡,帶我們深度領會構成「人類條件」(Human
Condition)的內情。從史前時代開始,我們人類總是力求更深入認識彼此,了解我們自己。有關一個人的殘暴傾向,各方解釋層出不窮,包括邪靈附身到體液失衡,乃至於反社會人格疾患。二十世紀期間,攻擊性衝動已經追溯自心理性慾情結(psychosexual
complexes),或腦部扁桃體的過度神經性活動。當然,暴力是源自生物、心理和環境等因子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然而廣大研究體系卻也證明,即時「情境」作用力在多方背景脈絡塑造我們行為的威力,其實都勝過我們體認的程度。
史丹福監獄實驗的最主要結論之一是,眾多情境變項能發揮無遠弗屆卻又相當微妙的力量,來支配一個人的抗拒意願。接著還有個「系統」──創造「情境」的強大作用力複合體。這是先天存在於政治、經濟、宗教、歷史和文化母體當中的固有力量,能界定情境並裁定情境勢力是屬合法或者非法。然而,多數心理學家對於這種系統性力量的更深層源頭的敏銳度,卻向來都很低落。我們不能只專注於「壞蘋果」,我們必須了解,要想通盤認識惡,就得先披露裡面偶然擺了「好蘋果」的「一桶桶壞蘋果」的本質,而且還得判定誰是「製造滿桶壞蘋果的人」。因此我主張,要想通盤體認人類行為的動力原理,我們就得先認清個人力量、情境力量,和系統性力量影響所及與其侷限。
心理學領域的相關重要事項之一是,有關人心的所有探索,最後終極目標是從個體和社會的基礎來改善生活品質。毫無疑問,認識各種心理疾患和反常的基礎生物學機制,正是落實這點的關鍵要務。過去百餘年,我們對於腦的認識已經有長足進展,然而,根據新近估計結果,皮質和小腦所含神經元數高達千億,證實腦子比宇宙其他事物都更複雜、更難解。美國歐巴馬總統最近發布「開發創新神經技術大腦研究方案」(BRAIN
Initiative),這項措施肯定能清楚闡釋,在各式各樣的腦神經元活動和心理狀態及其所衍生的行為之間,存有哪些至關緊要的連結,不過我們對於這種奇妙器官,恐怕永遠無法完全認識透澈。
神經科學確實為我們帶來有關腦子運作的重要細部資訊,然而,就如短視學者有可能見樹不見林,腦科學固然能就人類生命方面,還有就身為人類的經驗方面,為我們帶來一些知識,卻同樣有其侷限。相較而言,社會心理學的視角就寬廣多了,這門學問退一步觀察個體在文化框架內的交互作用。要改變、防範個體或團體的不良行為,就得先了解這類舉止為特定情境帶來哪些長處、優點和弱點。接著我們還必須更周密體認,在特定行為背景發揮作用的情境力量的複雜性。這其中有些力量是文化規範要件,外人不見得能夠看出箇中原委。著眼改變這些力量或者學習防範之道,就能產生較大的衝擊,從而減弱個體的不良反應,成效超過只針對該情境中的民眾來促成改變的補救措施。
我們用來處理社會問題的補救計畫,多半著眼於藉由教育、宣導、治療、懲罰、凌虐、監禁和流放來改變民眾。然而若是禍首出自情境或系統,或者遇上具有不同反應作風的個體,好比側重現在導向而非未來導向的人,這些做法就很難如願發揮效用。我認為,這表示我們應該放下針對治療現有個體疾病或缺失的正規醫療模型途徑,改採公共衛生途徑,針對一般大眾來推廣預防之道。然而,由於該系統的真正威力總是藏身在一層神祕的面紗背後,除非我們對那種力量養成敏銳的感覺能力,並能完全理解其本身的一套定則和規律,否則行為改變都會是瞬息即逝、虛幻不實的情境式變化。
就我來講,當前心理學的美妙之處就在於,新的廣度和更廣袤的深度媒合──這其中有一些同行投入開發新方法和新程序,期能縱跨文化和世代,破解個體、群體,和社會的心、腦和行為的祕密。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博士,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榮譽退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