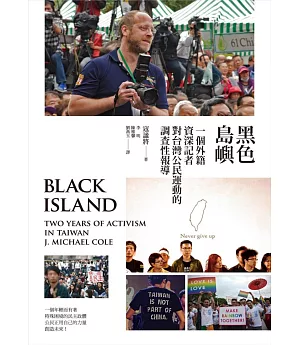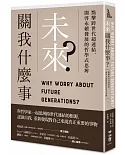推薦序
福爾摩沙圍城紀事
“We shall meet in the place where there is no darkness.”
—George Orwell
在芝加哥經院裡困頓多年,輾轉流浪到美麗的早稻田,最後終於回到了故鄉台灣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世界的目光已悄悄遠離這個過去英文媒體總愛形容為「有著繁榮經濟與活力民主的島國」,轉移到隔鄰那個正在兇猛地甦醒的帝國之上了。我們的外國主流媒體界朋友們似乎覺得,這個穩定的民主小國如今已經喪失了戒嚴時期那種迷人的「第三世界式」悲劇特質——獨裁、反抗、鎮壓,以及輩出的英雄烈士,還有九零年代民主化時期那種
「大衛對抗歌利亞,光明戰勝黑暗」的好萊塢史詩格局。台灣是民主化了,但也變得無聊了。他們於是把自己的東方主義之眼,轉向那個鼓動著一顆黑暗之心的,巨大的叢林。
然而正好就在世界的目光逐漸背向台灣之際,台灣島開始進入一段波濤洶湧的,完全不可測的新歷史航道之中。從兩千年初期以來,在中國「以商圍政」攻勢、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滲透,以及政治領導與制度性失敗等多重因素匯聚下,台灣民主體制逐步倒退,所得分配日益惡化,九〇年代一度短暫形成的社會團結也開始腐蝕,整個國家面臨崩解、從屬化,乃至被併吞的危機。然而也就是在此時,一場可以稱之為「第二波民主運動」的鬥爭悄悄出現,一齣充滿寓意,引人深思的道德劇(morality
play)在台灣揭開了序幕。這次的主角不再是過去那些擅長在街頭煽動人心的反對派政治菁英,而是整個公民社會——個由關懷各種進步議題的NGO、學者、學生、個別公民行動者與公共媒體所構成,透過宣傳與直接行動,從社會整體公共利益的角度抗衡國家與市場的網絡。從二〇〇五年前後到此刻的十年間,台灣人見證了這個極度活躍的公民社會的快速崛起、成長與擴張;在民進黨近乎瓦解癱瘓,完全喪失制衡能力的數年之間,台灣公民社會網絡扮演了實質的反對黨角色,有效地制衡了掌握絕對權力的馬英九政權,並且在最終創造了巨大的政治能量,重創這個政權,使坐困愁城的民進黨得以復甦、重整,乃至重返執政。
這是一段全新的歷史,湧現出許多新生事物與人物,裡面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但其中最令人動容的,或許是一整個新世代學生運動與公民運動行動者的出現與成熟。他們以青春的理想主義與熱情緊緊擁抱這個正在崩裂的島,撫慰與療癒她的傷痕,讓她重新變得完整,美麗,而且尊嚴。我何其有幸在這個歷史時點返鄉,從一開始就直接參與、見證了這段歷史,認識了這群新世代的知識分子與行動者,並且在此後幾年間和他們在許許多多大小戰役中並肩作戰,目睹他們從青澀到成熟,從脆弱到茁壯,見證他們如何用自己的身體與智慧創造了一股讓島嶼重生的暖流,巨大的黑潮。然而在這段激動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的外國主流媒體界朋友大多是缺席的——他們要等到這兩年忽然覺察到了島內一個新的「勢」已經形成,注意到東亞地緣政治的鐘擺又擺回了美麗島,才又好奇地轉過身來,帶著一點懷疑,一點犬儒,很多上國的傲慢
(condescension),以及幾乎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的無知。 《黑色島嶼:一個外籍資深記者對台灣公民運動的調查性報導》的作者寇謐將(Jean-Michel
Cole),是其中極少數的例外,他在這段國際媒體的空窗期,生活在台灣,站在台灣政治與社會的第一線,深入觀察,有時甚至還親身參與了這整段活生生的在地歷史,而且是謙遜地,同情地,甚至是熱情地。在這段世界對台灣視線的漫長空白中,他以他熱烈、即時、細膩的英文報導寫作為台灣發聲與辯護,並且有力地教育和駁斥了一群無知卻掌握傳播權力的上國犬儒,硬是為被掩蓋、遺忘、和抹煞的台灣打開了一道隙縫,將這一代台灣青年的吶喊與希望,這一波台灣人民試圖突破資本與帝國包圍,連結普世價值的民主奮鬥,刻印在那片空白的邊緣,讓他們有了面貌、發出聲音,讓他們終於驕傲地現身於這個世界。這本書,像是一冊當代福爾摩沙的圍城紀事
(a chronicle of the besieged Formosa)。
事實上,我們如果把這本書放在某種台灣文化史─外籍人士對於台灣的報導式書寫─的脈絡中觀察,它的意義會更加凸顯:達飛聲 (James W. Davidson) 著名的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1903)見證了台灣民主國的苦鬥與驚鴻——瞥的台灣民族國家想像,而一百一十二年後寇謐將的《《黑色島嶼:一個外籍資深記者對台灣公民運動的調查性報導》》,則近身記錄了一個以社會為主體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的降生。
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
是《黑色島嶼》的關鍵字,也是寇謐將對台灣近年來公民運動的定性。在比較政治學上,公民民族主義通常指涉一種在共同的領土上,基於共享的公民德行、價值與制度,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公民主觀的共同意志而產生的民族主義。它也可以視為一種以前述要素來界定民族成員身分的原則。公民民族主義與強調推定的共同血緣(經常是虛構的)與客觀文化特徵(如語言)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成為鮮明的對比。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各地區因其不同的歷史條件常導致不同的民族國家形成路徑與民族身分界定原則:德國、義大利、中國與日本的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族群文化與血緣色彩,而法國與美國、加拿大等國則強調公民德行、制度與共同意志才是構成民族 (nation) 的要素。出身魁北克法語區,同時深受法國政治文化與加拿大聯邦主義薰陶影響的寇謐將使用civic
nationalism一詞來描述台灣的公民運動,必須從這個脈絡來加以理解,其語意與當代政治哲學中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所說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頗有重合之處。 在英文或法文中使用civic
nationalism不會成為問題,也不會被誤解,然而台灣公共論述深受當代中國漢語用法的影響,經常把「民族主義」一詞窄化成族群或血緣民族主義,以致常常忽略了在公民德行與政治意志基礎上形成的nation與nationalism類型,從而引發了許多誤解與衝突。
寇謐將把當代台灣公民運動定位為一種公民民族主義是具有洞見的,不過我們或許可以為這個命題做幾點補充說明。首先,當代台灣公民社會的公民民族主義並不是台灣政治史上最早出現的公民民族主義,而只是最近的一種型態。一九二〇年代出現的第一波台灣民族主義雖然帶有漢族中心色彩,但基本上是建立在共同領土與共同政治命運的基礎之上,到了霧社事件後終於在論述中納入了原住民,因此已經可以看到某種多族群的「公民」特性。戰後初期廖文毅的台獨運動一度提出血緣民族主義的主張,但是很快就被六〇年代的王育德和史明強調領土、歷史乃至階級的民族論取代。一九六四年,醉心於法國史家Ernest
Renan公民民族主義思想的彭明敏教授提出〈台灣自救宣言〉,則是台灣政治史上出現的第一個完整的公民民族主義論述。一九七〇年雷震在〈救亡圖存獻議〉中提出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主張,則是外省人首度提出的公民民族主義論。在前述這些論述基礎上,一九七〇年代中後期興起的黨外民主運動與其後的民進黨所提出的台灣民主自決論,已經是成熟的公民或自由民族主義 (liberal
nationalism)。九○年代李登輝的兩國論試圖融合 「中華民國」與台灣領土,在性質上也是公民式民族主義。因此我們大體可以說,早在當代公民社會的公民民族主義出現之前,某種以台灣為領土範圍的公民民族主義早已成為台灣政治場域中的主流共識。
其次,當代台灣公民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公民民族主義與政治場域的公民民族主義雖然有所重疊─兩者都支持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但仍然有一個關鍵的差異:前者以「社會」為核心,具有高度社會自主性,後者則以「國家」為中心。對於公民社會而言,愛國心或者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必須受到他們所信仰的進步價值的檢驗與制約,否則將失去正當性。
第三,寇謐將指出台灣公民運動的公民民族主義不是突然出現,而必須放在脈絡之中才能正確理解。這個說法雖然方向正確,但卻不完全:我們不僅要回溯兩年來學運份子如何在歷次運動中獲得鍛鍊與成熟的歷程,更要追索整個台灣公民社會從一九七、八〇年代隨著民主運動而出現的三、四十年來,如何經歷成長、擴張、被政黨收編,最終脫離政治場域而產生自主性的複雜歷程。換言之,當代台灣公民社會的整個網絡、組織、論述與路線的形貌,是過去三十餘年台灣民主化的成果,它象徵了數百年來被強大的外來國家傳統壓制的民間社會終於形成了一定的自主性。理解了這個社會自主的脈絡,我們才能正確理解當代公民社會的台灣認同之進步意義:民主,就是自決,而自決則表現在社會對國家的馴服與控制。
時序已經進入二〇一五年年底,而台灣這座黑色島嶼的歷史即將進入另一個轉折:第三次政黨輪替將要出現,本土派將第二度建立政權,然而中國擴張之勢不衰,美國正在重返亞洲,日本積極再軍備,整個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勢將為一個進步的台灣本土政權設下重重限制,使它左右為難,動輒得咎。台灣國家必須在國際政治的險惡現實中追求生存發展,然而台灣社會也不可能放棄公平正義的願景,那麼國家與社會該如何重新磨合、彼此鑲嵌,在安全與正義之間找到一個最適的平衡─或者到底存不存在一個最適的平衡?──將成為我們不可迴避的共同課題。未來的道路只會更險峻,我們也只能不斷前行,但我們期待寇謐將繼續為我們熱情地、介入地書寫他的黑色島嶼紀事,書寫我們的徬徨、失敗與持續不輟的奮戰,書寫我們對自由、尊嚴與正義的想望。
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〇一五十一月二十五日,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