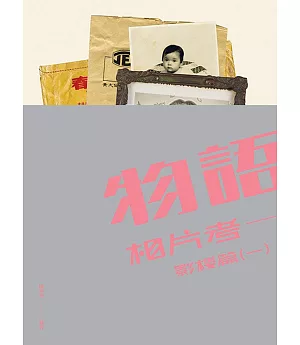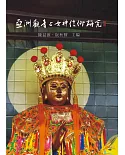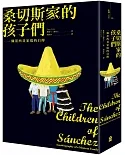我們每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裡,都需要拍照。而在數碼攝影未普及之前,我們要拍照便要上影樓。所以曾經有段時間,香港的影樓遍佈各區,多如現在的便利店。可是時至今天,影樓行業已經式微,逐漸消失於這個城市。然後大量的遺留在影樓裡的相片,都隨着影樓結業而被當作垃圾看待。幸好,鍾燕齊在這幾年間,將部分「拯救」回來,並編著成這本書《物語:相片考──影樓篇(一)》,讓大家可以重新審視香港攝影行業的興衰,以及每一張相片與我們之間的關係。
《物語》是鍾燕齊編著的系列書名,希望藉由他多年來從坊間收集回來的老好物件,來述說物件與時代和城市之間的故事。「相片」是其中一個主題,分為影樓篇、生活篇及技術篇三本。及後還會推出其他主題系列,如文具及玩具等器物。
《物語》系列
鍾燕齊沉迷拾荒,最初可能單純是出於戀舊情意結,但當他的收藏品越堆越多,慢慢便發現到每一件物品器具上面,原來都留下了時代的痕跡。這些痕跡靜靜地訴說着一段回憶、一個時期、一種生活、一次變化,甚至是一個人的人生經歷。透過各種各樣的舊物,我們更可以串聯出香港這個城市舊時的人文生活風貌,以及內裡蘊藏着的無數個關於香港人的故事。於是我們便想到用《物語》這套系列書,來承載這些故事。「物語」一詞,本是傳統日本文學的一種體裁,原意為「談話」,後引伸為故事、傳記、傳奇等,是一種擴大化了的,具有散文性質的、用來敘述故事的文學體裁。我們以「物語」作為書名,便是想帶出「以物件來說話」、「以器具來講故事」的含義。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鍾燕齊
出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為戰後第二代嬰兒潮一員。成長過程見證和體驗了香港的不斷成長、發展和耗損!
中學畢業後修讀商業設計,之後投身廣告創作行業,工作了數年,隻身跑到日本東京留學。在留日期間認識了北原照久先生,從此北原先生成了鍾燕齊人生中的一位啟蒙老師,老師讓他明白到尊重和關注自身國家歷史的重要。鍾燕齊留學回港後重新整理收集有關香港兒童生活古道具的方向,不時通過不同渠道舉辦相關的展覽和教育工作坊,把各式不同的古道具與不同年齡和階層的人士分享。
鍾燕齊收集物品,包括了大英帝國(香港製造)的玩具、本土漫畫、教科書、兒童文學作品、殖民地時期的教育文獻、本土包裝設計、老店賬簿、影樓相片和器材等等……還有九龍皇帝的墨寶真跡!他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為香港建立起一所永久的兒童文化研究館,好讓全世界都能欣賞上幾代香港人所創造的文化遺產。
2014年修讀香港樹仁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之跨學科文化研究系文學碩士課程,受教於王建元教授門下,也得到很大的啟示,特別是在思考上的執着,獲益不少。
鍾燕齊
出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為戰後第二代嬰兒潮一員。成長過程見證和體驗了香港的不斷成長、發展和耗損!
中學畢業後修讀商業設計,之後投身廣告創作行業,工作了數年,隻身跑到日本東京留學。在留日期間認識了北原照久先生,從此北原先生成了鍾燕齊人生中的一位啟蒙老師,老師讓他明白到尊重和關注自身國家歷史的重要。鍾燕齊留學回港後重新整理收集有關香港兒童生活古道具的方向,不時通過不同渠道舉辦相關的展覽和教育工作坊,把各式不同的古道具與不同年齡和階層的人士分享。
鍾燕齊收集物品,包括了大英帝國(香港製造)的玩具、本土漫畫、教科書、兒童文學作品、殖民地時期的教育文獻、本土包裝設計、老店賬簿、影樓相片和器材等等……還有九龍皇帝的墨寶真跡!他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為香港建立起一所永久的兒童文化研究館,好讓全世界都能欣賞上幾代香港人所創造的文化遺產。
2014年修讀香港樹仁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之跨學科文化研究系文學碩士課程,受教於王建元教授門下,也得到很大的啟示,特別是在思考上的執着,獲益不少。
目錄
序一 影像之迷戀 記憶的誕生 謝至德 008
序二 關於照相館的一二 周佩霞 012
序三 人像相片價值最後的避難所 禾日水巷 016
編者序 《物語》系列:透過物件講故事 鄧烱榕 018
自序 物之存在 與物對話 鍾燕齊 020
第○章 從人人照相到人人拍照 024
第一章 人與相片出生入死 032
一 ──童年篇 044
二 ──校園篇 060
三 ──證件篇 072
四 ──肖像篇 084
五 ──婚宴篇 100
六 ──家族篇 112
第二章 影樓的設計美學 126
「家庭」在影樓的誕生 黃寶群 128
一 ──影樓商標設計 142
二 ──相片卡紙套 158
三 ──菲林底片袋 166
四 ──人手上色 宋寶儀 180
跋 被光榮結業 186
序二 關於照相館的一二 周佩霞 012
序三 人像相片價值最後的避難所 禾日水巷 016
編者序 《物語》系列:透過物件講故事 鄧烱榕 018
自序 物之存在 與物對話 鍾燕齊 020
第○章 從人人照相到人人拍照 024
第一章 人與相片出生入死 032
一 ──童年篇 044
二 ──校園篇 060
三 ──證件篇 072
四 ──肖像篇 084
五 ──婚宴篇 100
六 ──家族篇 112
第二章 影樓的設計美學 126
「家庭」在影樓的誕生 黃寶群 128
一 ──影樓商標設計 142
二 ──相片卡紙套 158
三 ──菲林底片袋 166
四 ──人手上色 宋寶儀 180
跋 被光榮結業 186
序
推薦序一
影像之迷戀 記憶的誕生
謝至德
1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兩點十九分我開始寫這本書的序言,這是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溫暖的陽光穿過落地玻璃斜斜照進我的工作室,金黃色的陽光剛好落在舊木床板造的茶桌上。我這一道光放了一尊謙倉時代木製上了金黃色油漆的地藏王菩薩,打開iPad上的Evernote準備寫作,喝一口熱水,開始去寫以下的文字。」
大家看着上面的文字時,心裏有否想像到我所描述的情景?文字會令我們的腦袋產生很多想像,但每一個人所想像的情景都很不一樣,而這些不同的情景其實均建構自我們成長中所經歷過的記憶。我們大部分的記憶都是來自眼睛所看見的,也許大家看見的是相同的景物,但各自會用不同的情感去理解所看見的景物。有人看見金門橋會想起和他的戀人駕駛開篷車在橋上奔馳的一個下午;有人會想起一個陌生人吃了一餐午飯便從這條橋跳下的情景;有人回想起曾經在這裏拍過一張十分漂亮的日落相片;總之內心反應各有不同,因此所看見的影像會令大家產生出獨一無二的回憶。
今天我們攝影師利用攝影去保存真實,而遠古的人類則利用繪畫嘗試把眼睛所看見的記錄下來。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害怕遺忘,或是希望和一代又一代的人分享,把故事流傳下去。而在文字尚未出現的原始時代,「影像」的存在就是那些刻在岩洞裡的壁畫,可以說是人類有意識地「保留影像」的起源。我會相信,這些史前壁畫可能是當時大家完成狩獵活動後,回到洞穴消遣互相交流的閒暇活動!直到今天,我們人類對「保留影像」的原始意識並沒有改變,只不過現在Facebook取締了古代的洞穴,而簡單沒有文字敘述的壁畫,則換成千百萬張數碼相機拍下來的影像。題材千變萬化,但最終的目的仍是分享、抒發情感、等待回應和互相鼓勵,有些分享會成為社交話題並引起迴響。
當我們能夠把圖像、聲音、影像和文字,在一眨眼間傳送到幾千公里遠的地方,我們會為現今人類科學感到驕傲,而對保留和分享影像的迷戀幾千萬年以來也保留在我們體內的基因之中。然而古代洞穴壁畫的內容是從前人們眼前所看所見直接描繪出來,攝影最初任務也是直接交代所看見的,可是今天攝影所交代的影像卻是複雜而不可信,背後甚至還隱藏了很多目的。從一個年代到另一個年代,攝影所製造的影像數量只有增加,影像所承載的訊息對我們而言,不只是紀錄、回憶、提供愉悅和宣傳等作用。我們迷戀影像並不斷透過傳播媒介去吸收影像,用眼睛去消費影像的同時,我們也被影像消費。購物這個行為就是其中一個我們不知不覺的被消費的例子。布希亞說:「消費者購買物品不是要表達他們是誰的既存意義,反之他們是想透過自己消費的東西,來創造出他們是誰的意義。」
我們喜歡閱讀影像,它是製造「消費慾望」最有效的工具,從前我們的交易是建基於對物質的需要,日常生活也不過是衣、食、住、行,和原始人打獵一樣,只是攝取所需的,但資本主義令所有事情都只會從商業價值角度上去計算,因此我們每天的生活差不多是為了消費而存在。如果用因果關係去作一個總結,我會認為幾千萬年來對影像迷戀的習性是因,然而今天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自主性卻成了果。
2
記憶,誕生在一個漆黑的環境中。就像嬰兒出生前在母親漆黑一片的子宮內。如果大家對相機有一點認識,便會知道如果沒有一個漆黑的空間給予影像產生,影像是沒有辦法被記錄下來。這個「空間」的攝影術語稱之為「暗室」,一個密封不透光空間。早在公元前四七○年,中國的墨子已經發現了暗室現象,比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達文西更早。達文西在其科學著作中也有研究暗箱影像的記載,並推薦人們利用這工具來寫生繪畫。直到法國人達蓋爾(Louis J M Daguerre, 1789 – 1851)和英國人塔爾博特(Fox Talbot 1800–1877)在一八三九年都分別發現了攝影術,攝影很快便在西方世界流行起來。
而我相信最早發明攝影術的應該是上帝,我們只是去發現它的創造。因為眼睛其實就是一個暗室,嬰兒睜開眼睛的一刻,從子宮內走出來,打開眼睛就啟動了上天給我們的立體攝影裝置,瞳孔後面的感光細胞就是紀錄的介面。傳統攝影就用底片作為紀錄介面,現今的數碼攝影則以電子感光晶片去取代,就好像人眼睛的感光細胞可重複使用。直到死前我們都不斷去記錄世界,同時也不斷地把世界遺忘。影像在我們的腦海裏就像輪迴一樣一生一滅,我們看見萬事萬物的連續動作其實都是由一幅又一幅的影像疊加起來所組成。就好像電影中利用二十四格影像去產生一秒畫面,所以當你觀看一分鐘的電影時,其實是在觀看一千四百四十幅靜止的影像。
記憶也是由一幅幅的影像加起來,而相片就是封存記憶的方法。在攝影術面世的一百年裡拍攝一幅影像是十分珍貴的,人們會把銀版攝影的家人肖像鑲在非常精緻小巧的玻璃鏡框內,方便去跟別人分享,以後這些相片也便成了珍貴的回憶。所以,我們保存相片就是保存記憶。一張張收藏在家庭相簿中的相片,它們的命運很多時候也隨着主角在世上消失而消失。每一張相片的誕生同時也展示着那個時代的文化氣息、生活方式和時代精神。現今人們已經失去沖曬相片的衝動,因為所有影像的複製都是數碼,而且可以隨身攜帶的電子屏幕就在每一個人的口袋中,我們翻看影像再不需要印刷品,把至親的相片放在銀包的人相信沒有太多,因為我們十分容易就可以翻看幾千張儲存在手機的影像。機械複製的時代已經過去,只要一兩個按鍵的動作我們便可以輕易地拍照、複製並傳播影像,這就是這個年代的時代精神。時代精神沒有好與壞,但總有開始、經過和結束,一個時代的精神有多久我們無法預計,就好像人們多年以來利用傳統攝影去保留記憶,在十多年之間被數碼攝影很快取代並為城市人的生活帶來劇變。翻看上一個年代的相片不單單是懷緬過去,更深的一層意義就是去發掘今天所遺忘的,我們曾經擁有很多好的習性,以致我們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擁有對萬物的同理心,而不是為了消費而活着。今天我們在這個超真實(Hyperreal)的世界裡,我們有十分好的工具去對抗遺忘,可同時我們卻在不斷失去着過去某些道德和價值觀……
推薦序二
關於照相館的一二
周佩霞
時代,在空間中展示。
空間,隨時代而變。
照相館,在攝影機發明後生;也在攝影技術越來越普及和數碼化後,逐漸消亡。從前,攝影機比較昂貴,不是人人可以擁有,到影樓拍照所費不菲。所以一般平民,都是在重要時刻,才到照相館拍照。因為珍貴,大家都會隆重、認真對待。我的包租婆,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本港出生,三歲時嫁到另一農村當童養媳,十八歲結婚時,因為負擔不起,沒拍過一張照片。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她的丈夫到英國打工前,一家人才第一次上照相館,拍了第一張全家福,而她亦於那時,才拍下第一張和丈夫的合照,當時她已是二子之母。照相館特別是那些舊式的拍照絕不是「快照」,但就如社會學家布爾狄亞(Bourdieu, 1990)所言,家庭的(快怕)攝影不能脫離生產這些照片的家庭生活場合與時機,家庭照片乃是「融合的儀式」(ritual of integration)。當攝影還未普及時,因為家人移徙而在影樓拍攝的家庭照片,不單透視着攝影的階級性,它們還展示了影樓的歷史和社會意義─影樓作為記錄及凝固變動加劇化下的社會的場所。
我父親的全家福,也是由照相館「製造」出來。父親出身於內地一個農民家庭。上世紀六十年代時因為大飢荒,跟姊姊偷渡來港。來港前,也是因為經濟原因,沒有拍過家庭照。後來,他和姊姊恐怕不能重返家鄉與家人重聚,於是讓家人在內地影一張合照,由香港的影樓師傅,再把他和姊姊加上去。一個曾在中環環球大廈一小時沖印店工作的朋友說,九十年代的時候,他們也是不斷為菲傭做同樣的事情。空間轉移了,而一小時沖印店的出現,更直接沖擊影樓的生意,但這些例子正好說明了照相館曾經扮演的歷史角色,以及相片作為社會關係再現的特性,那管相片中的再現,是不同「現實」重疊、補充、修正的產物,而不是純粹外在世界的複製。
照相館所拍的相片,又比照相館以外拍的,更能呈現社會關係的結構及意識形態。照相館裡雖然也有佈景和陳設,但那是一個抽離、虛擬的現實空間,當人們到影樓拍照,不單照相者會穿上最「恰當」的服飾,認真、嚴肅、全神貫注地直視鏡頭,企圖以最好的形象,把自己以及其他在鏡頭裡出現的人,凝固在相紙上。他們還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攝影師的導演和自我安排的共同效應下,按照着特定的社會框架與期望,盡力演好在相片中飾演着的身份,無論那是一張個人證件照,還是家庭照、畢業照、結婚照或其他。簡單地說,證件相中的主角,最好頭髮衣衫整齊,面帶笑容,因為這樣的形象,意味着主角是個循規蹈矩的人,可以融入社會。家庭照則長幼有序、男尊女卑;結婚照則大多顯示女性小鳥依人,男人氣宇軒昂。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大家在照相館拍照時已不一定那麼嚴肅,但是那些傳統框架,依然是拍照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這樣,照相館可以說是傅柯(Foucault)所說的「異托邦」或「異質空間」(heterotopia)。「異托邦」是「烏托邦」的變異。在題為「論其他空間」(Of Other Places)的演講中,傅柯指出烏托邦是理想世界,不存在於現世。但異托邦是現實中的具有特異性質的空間。「某些特定的場址,它們以非常特別的性質與所有其它的場址產生關係,但它們卻擱置、中性化、或是顛倒了它們本來被指定要反射或是再現的種種關係。那些空間與所有其他的空間都有關聯,但是卻與其他所有的場址有所不同。」鏡子就是這樣的異托邦。一方面,鏡子中反射了一個虛擬的現實世界;另一方面,主體透過凝視鏡子中的自己,知道自己所在與不在那裡,從而認清自己的位置,並可由此重新建構。換句話說,鏡子讓各種空間相連結,但又同與一般現實空間產生對比和競逐,從而產生對話和批判的可能。
以攝影機為中心的照相館,是一個比鏡子更實體但又同時更具想像性的異托邦。首先,攝影機既是鏡亦非鏡。是鏡,因為攝影機的原理本來就是鏡像的原理。在攝影機前的東西,反射到鏡頭內,再留在菲林上。但是,這個鏡像,又非如真實的鏡子般,讓主體可以看見。鏡像裡的東西,在攝影數碼化出現前,是要到照片沖晒出來後,才可被看見。
不過,讓照相館成為異托邦的關鍵,乃是上照相館「再現」和濃縮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的特性。有趣的是,相片中的社會關係再現,卻又不如鏡子中的鏡像,是純粹外在現實的產物;它以想像的方式,先於相片而存在,並且透過攝影機而具體化。是故,照相館像神殿般,當人們嚴肅地在那抽離的空間拍照時,他們不單可以觀照自己和自己的位置;整個富有儀式性的攝影過程,亦同時為某種關係某個時刻,加以確認,而攝影機就是賦予那些時刻或關係神聖意義不可或缺的中介。
當然,人們到照相館拍照的時刻,如嬰兒誕生、幼稚園小中大學畢業、結婚等等亦倒過來幫助奠立照相館的神聖性。那些時刻都是人生中的重要階段,它們往往象徵人生的某種跨越。在傳統社會裡,那些跨越需要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確立,成人禮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在照相館照相,成為現代社會裡獨特的通過儀式。真正的出生、畢業、結婚,在醫院、在學校禮堂、在婚姻註冊處或教堂進行;人們亦往往在那些場所,進行了相應的儀式,甚至拍下照片;但是,到照相館正正式式拍一張照,總會讓人覺得事件更完滿。而照相館與多個人生重要時刻的連結,亦加強了照相館作為異托邦的特性,因為異托邦的第四原則,就是不同時性的共存。
因為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因為攝影技術普及化,人人都可以是攝影師。作為異托邦的照相館,有些消失,有些轉型。如果照相館真的帶有神聖性,特別在確立及強化社會關係上,那麼,照相館的消失,是否亦意味着社會關係越來越不穩定,就像Instagram或其他即時性的傳訊工具段,一切講求即時與當下,而我們已徹徹底底在Bauman(2000)所謂的液態現代性中生活下去!
推薦序三
人像相片價值最後的避難所
禾日水巷
本雅明在(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1936)中表示,隨着機械複製技術湧現,一種新的文化將會在西方社會逐漸形成。將會導致「傳統的大崩潰」。他指出:人類生活方式的演變,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的感性認識方式是隨着人類群體整個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演變。
早期照相攝影以人像為中心,這點絕不是偶然的。在對遙遠的或已經消逝的愛進行緬懷,抱着崇敬的心來「朝拜」它。
這正如在現實或電影當中,在早期的社會或戰爭時候,被徵召到前線的軍人,都會把家中成員的照片隨身攜帶。早年香港很多男性都要擔當行船或出海捕魚的工作,而每次上船離開,往往都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回到家庭成員身邊,一個月至半年或更長不等,真是聚少離多。這個時候隨身的人像照。在獨自一人的時候,照片釋放出的韻味便發揮以上本雅明所提出的作用。
相片裏肖像的價值找到了其最後的避難所,在早期照相攝影中,韻味通過人像面部的剎那間表情還在作最後的道別,構成這最後道別的就是攝影那憂鬱的無與倫比之美,可是,當人像在照相攝影中消失之時,展示價值便首次超越了緬懷價值,那麼,韻味到底是甚麼?
本雅明提出韻味在傳統藝術中日漸消失的事實,但並沒有大力反對機械複製技術的。複製技術動搖當時民眾根深蒂固的思想,促進大眾文化的湧現。而大眾文化的出現,是有助社會統建群眾思想。縱然有學者擔心這或許會成為國家利用的工具,以達至其政治目的。然而,本雅明對其抱有積極樂觀的心態,對它充滿憧憬。他看見這股新興的社會力量日益聚集擴大,認為它可以發掘社會潛能,作為鼓動革命的一種力量,改變社會。
編者序
《物語》系列:透過物件講故事
鄧烱榕
鍾燕齊自詡為「垃圾佬」,經常往垃圾堆裡鑽,將別人棄不足惜的「垃圾」拾回來當「寶」。從荔園結業那天開始,近三十年來他拾到大量物件,有玩具、文具、照片、相機、包裝袋、書籍(包括一個世紀以來的香港教科書,兒童文學作品、漫畫和經典中文文學作品)、賬簿、單據、學校傢俬、擺設、聖誕燈泡、月餅模具……真係古靈精怪乜都有。這些收藏品當中,有殘缺的也有老舊的,但更多竟是完好無損。我們都驚訝為甚麼他可以時常「執到寶」,他總是笑說現代人太習慣「丟掉」。只要用家認為物件不再有價值,它就會被「丟掉」成為「垃圾」。然而在鍾燕齊眼中,這些「垃圾」其實仍擁有另類的存在意義─作為時代的見證。
鍾燕齊沉迷拾荒,最初可能單純是出於戀舊情意結,但當他的收藏品越堆越多,慢慢便發現到每一件物品器具上面,原來都有時代的痕跡遺留下來。這些痕跡記錄着時代的演變和流逝。鍾燕齊會去思考當時那個人是抱着怎樣的心情將這件物件買回家,物件與用家之間曾經有過怎樣的回憶,它在他或她的生活裡擔當過怎樣的角色,後來又因為怎樣的原因使到這件物件變成垃圾。明白到原來每一件物件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而一個故事又關聯着更多的故事。這些故事靜靜地訴說着一段回憶、一個時期、一種生活、一次變化,甚至是整個人的人生經歷。即使早已人去樓空蒼海桑田,這些故事卻透過一件件不同的物件,反而得以保留下來。所以,多得鍾燕齊的拾荒有道。因為他手上那些上千上萬件不同種類的收藏品,不單只是可以串聯出香港這個城市舊時的人文生活風貌,內裡更蘊藏着無數個關於香港人的故事。
幾年前,鍾燕齊開始跑遍港九新界各地,為各家快將結業的傳統影樓留下紀錄,當然也將他們不要的東西統統打包回家。後來他問我有沒有可能出一本關於相片的書,因為他從影樓收集回來的照片已過千張,好好整理結集成書的話,應該可以從中看到攝影在香港這幾十年間的變化─從影樓到手機,從專業到日常。鍾燕齊還想到一個非常貼切的書名《物語》。「物語」是傳統日本文學的一種體裁,原意為「談話」,後引伸為故事、傳記、傳奇等,是一種擴大化了的,具有散文性質的、用來敘述故事的文學體裁。用在這裡當書名,更語帶相關地點出「以物件來說話」的含義。經過幾次磋商,我甚至建議他把文具及玩具的收藏都編輯起來,成為一套系列書,讓大家除了展覽之外,可以有多一種途徑,看到這些本已為「垃圾」的再生及意義。奈何文具和玩具的數量和種類更加龐大,需要更多時候去整理和逐一拍攝,所以今次以﹁相片﹂主題先行,往後再繼續努力編集其他《物語》。
自序
物之存在 與物對話
鍾燕齊
這個有關香港民間物件出版項目的展開,正好給我機會,讓我與從香港各處不同空間撿拾回來,各種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物件來一次好好對談,好讓它們都能成為真正的「存在」。
「物」之為物,因有其物質屬性:木(紙)、金屬(銀鹽)、塑膠等等。「物」只能處於「存在」的狀態下,才能等待人們來發現。「存在」的認知觀可以理解為:從發覺、識別、屬性、了解、功能,到作用、利弊、用途、效果、控制等系統化的歸納。而物件除了有物質性以外,還有物之「意義」,這又離不開人的「六識」。佛家語為:眼、耳、鼻、舌、身及意,是人類的六種感官認知。「六識」導使我們感知物件的存在,繼而產生不同的慾望。而當物件與事件(event)相關,成為事物,其性質又超乎了物質性。正如這本書,我們通過物件和出版,產出了超乎了一個個別物件原本的功能和意義。因為當物與事互相結合,物件的意義便會變成具有多樣性和不穩定,呈現出「在其間」(in between)的特質:一物的意義總是與他物有所關聯。所以宇宙萬事萬物都有其一定的關聯性。這種伸延,也是通過物件來說故事最有趣地方。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 – 1976)是廿世紀德國最有創見的哲學家,他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1927)中第一次提出了「存在主義」這個概念。海德格爾認為,一直以來西方的思想史只關注「存在着的事物」,而遺忘了「存在着的事物」的「存在」。這是哲學研究上的一個很大的突破!他借用了他的老師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 – 1938)的「現象學」作為工具。「現象」這個詞在希臘文中表示「自行顯現」,故海德格爾認為,現象學即意味着讓事物自己來說明自己的企圖。他說:「只有我們不去企圖把事物硬塞進我們為其製造的觀念的框框中去時,它才能向我們顯現自己。」存在主義提出物體的本質先於物體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先於人的本質。存在主義思考人的絕對,人是絕對的個人。只有人先存在,人才追逐自由。
作為系列性書籍跟一般獨立書籍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整個系列的名稱,在系列當中擔當起說故事的都是一件一件不同的物件,所以聯想到日文裡的一個漢字詞彙「物語」。「物語」既是日文又是中國漢字,它們的存在關係也很值得探究。經過徵詢一眾編輯後都覺得可以使用這個來作系列的總名稱。
第一本《物語》將會以香港影樓和影樓拍攝的照片,去探討攝影跟整個社會和我們的存在關係。一張張經過人手沖曬出來的照片跟數碼世界下的虛擬照片的存在價值。攝影是一種很弔詭的行為。嚴格來說,攝影師在拍攝時,正因忙於和專注拍攝工作,而變得「不完全在場」,所以在拍攝的過程裡,他其實不斷地錯過了很多精彩的畫面,失去了聆聽周邊環境聲音的機會,也沒有感受到周邊其他人生經驗的時刻。結果,他可能在拍下一張照片的同時,也失去了更多的按快門的機會;他是得到了,但失去的更多?或是有失去,但得到的更多?
今天,攝影的技術趨發普及,拿出手機就可以拍照,但卻令到人們習慣於用攝影這個行為來取代經驗本身,所以人們變得好像只在乎照片,或更精準的說,大家都只在乎上傳照片,不再在乎經驗。其實無論何種題材的攝影作品,其背後都要有一個美好的心靈為依托。這在中國傳統哲學領域裡面也能找到一些有力依據,例如中國佛教文化有一本書叫《指月錄》,記載了歷代禪學高僧全燈講法的言行故事。「指月」這個詞就是比喻我想要通過某種方法或形式告訴你一個物體的存在,但要大家做到「見月忘指」,可是當中很多人還停留在只見「指」,不見「月」的階段。這絕對與大多數的群眾脫離社會和遠離生活有密切關係。
我們以為照片是恆久,但它其實只是一種暫存;而相機(拍攝工具)對於今天的人來說,幾乎就是身體的一部分伸延,但假如有一天,大家都失去了這個工具,對眼前存在的一切事物,我們又將會如何處理?
導演李安曾經在電影中說:「人生最大的悲傷就是沒有說再見。」我覺得,攝影其實就是讓我們學會說再見。所以當這本書出版的時候,也是我跟照片說再見的時候!
影像之迷戀 記憶的誕生
謝至德
1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兩點十九分我開始寫這本書的序言,這是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溫暖的陽光穿過落地玻璃斜斜照進我的工作室,金黃色的陽光剛好落在舊木床板造的茶桌上。我這一道光放了一尊謙倉時代木製上了金黃色油漆的地藏王菩薩,打開iPad上的Evernote準備寫作,喝一口熱水,開始去寫以下的文字。」
大家看着上面的文字時,心裏有否想像到我所描述的情景?文字會令我們的腦袋產生很多想像,但每一個人所想像的情景都很不一樣,而這些不同的情景其實均建構自我們成長中所經歷過的記憶。我們大部分的記憶都是來自眼睛所看見的,也許大家看見的是相同的景物,但各自會用不同的情感去理解所看見的景物。有人看見金門橋會想起和他的戀人駕駛開篷車在橋上奔馳的一個下午;有人會想起一個陌生人吃了一餐午飯便從這條橋跳下的情景;有人回想起曾經在這裏拍過一張十分漂亮的日落相片;總之內心反應各有不同,因此所看見的影像會令大家產生出獨一無二的回憶。
今天我們攝影師利用攝影去保存真實,而遠古的人類則利用繪畫嘗試把眼睛所看見的記錄下來。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害怕遺忘,或是希望和一代又一代的人分享,把故事流傳下去。而在文字尚未出現的原始時代,「影像」的存在就是那些刻在岩洞裡的壁畫,可以說是人類有意識地「保留影像」的起源。我會相信,這些史前壁畫可能是當時大家完成狩獵活動後,回到洞穴消遣互相交流的閒暇活動!直到今天,我們人類對「保留影像」的原始意識並沒有改變,只不過現在Facebook取締了古代的洞穴,而簡單沒有文字敘述的壁畫,則換成千百萬張數碼相機拍下來的影像。題材千變萬化,但最終的目的仍是分享、抒發情感、等待回應和互相鼓勵,有些分享會成為社交話題並引起迴響。
當我們能夠把圖像、聲音、影像和文字,在一眨眼間傳送到幾千公里遠的地方,我們會為現今人類科學感到驕傲,而對保留和分享影像的迷戀幾千萬年以來也保留在我們體內的基因之中。然而古代洞穴壁畫的內容是從前人們眼前所看所見直接描繪出來,攝影最初任務也是直接交代所看見的,可是今天攝影所交代的影像卻是複雜而不可信,背後甚至還隱藏了很多目的。從一個年代到另一個年代,攝影所製造的影像數量只有增加,影像所承載的訊息對我們而言,不只是紀錄、回憶、提供愉悅和宣傳等作用。我們迷戀影像並不斷透過傳播媒介去吸收影像,用眼睛去消費影像的同時,我們也被影像消費。購物這個行為就是其中一個我們不知不覺的被消費的例子。布希亞說:「消費者購買物品不是要表達他們是誰的既存意義,反之他們是想透過自己消費的東西,來創造出他們是誰的意義。」
我們喜歡閱讀影像,它是製造「消費慾望」最有效的工具,從前我們的交易是建基於對物質的需要,日常生活也不過是衣、食、住、行,和原始人打獵一樣,只是攝取所需的,但資本主義令所有事情都只會從商業價值角度上去計算,因此我們每天的生活差不多是為了消費而存在。如果用因果關係去作一個總結,我會認為幾千萬年來對影像迷戀的習性是因,然而今天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自主性卻成了果。
2
記憶,誕生在一個漆黑的環境中。就像嬰兒出生前在母親漆黑一片的子宮內。如果大家對相機有一點認識,便會知道如果沒有一個漆黑的空間給予影像產生,影像是沒有辦法被記錄下來。這個「空間」的攝影術語稱之為「暗室」,一個密封不透光空間。早在公元前四七○年,中國的墨子已經發現了暗室現象,比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達文西更早。達文西在其科學著作中也有研究暗箱影像的記載,並推薦人們利用這工具來寫生繪畫。直到法國人達蓋爾(Louis J M Daguerre, 1789 – 1851)和英國人塔爾博特(Fox Talbot 1800–1877)在一八三九年都分別發現了攝影術,攝影很快便在西方世界流行起來。
而我相信最早發明攝影術的應該是上帝,我們只是去發現它的創造。因為眼睛其實就是一個暗室,嬰兒睜開眼睛的一刻,從子宮內走出來,打開眼睛就啟動了上天給我們的立體攝影裝置,瞳孔後面的感光細胞就是紀錄的介面。傳統攝影就用底片作為紀錄介面,現今的數碼攝影則以電子感光晶片去取代,就好像人眼睛的感光細胞可重複使用。直到死前我們都不斷去記錄世界,同時也不斷地把世界遺忘。影像在我們的腦海裏就像輪迴一樣一生一滅,我們看見萬事萬物的連續動作其實都是由一幅又一幅的影像疊加起來所組成。就好像電影中利用二十四格影像去產生一秒畫面,所以當你觀看一分鐘的電影時,其實是在觀看一千四百四十幅靜止的影像。
記憶也是由一幅幅的影像加起來,而相片就是封存記憶的方法。在攝影術面世的一百年裡拍攝一幅影像是十分珍貴的,人們會把銀版攝影的家人肖像鑲在非常精緻小巧的玻璃鏡框內,方便去跟別人分享,以後這些相片也便成了珍貴的回憶。所以,我們保存相片就是保存記憶。一張張收藏在家庭相簿中的相片,它們的命運很多時候也隨着主角在世上消失而消失。每一張相片的誕生同時也展示着那個時代的文化氣息、生活方式和時代精神。現今人們已經失去沖曬相片的衝動,因為所有影像的複製都是數碼,而且可以隨身攜帶的電子屏幕就在每一個人的口袋中,我們翻看影像再不需要印刷品,把至親的相片放在銀包的人相信沒有太多,因為我們十分容易就可以翻看幾千張儲存在手機的影像。機械複製的時代已經過去,只要一兩個按鍵的動作我們便可以輕易地拍照、複製並傳播影像,這就是這個年代的時代精神。時代精神沒有好與壞,但總有開始、經過和結束,一個時代的精神有多久我們無法預計,就好像人們多年以來利用傳統攝影去保留記憶,在十多年之間被數碼攝影很快取代並為城市人的生活帶來劇變。翻看上一個年代的相片不單單是懷緬過去,更深的一層意義就是去發掘今天所遺忘的,我們曾經擁有很多好的習性,以致我們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擁有對萬物的同理心,而不是為了消費而活着。今天我們在這個超真實(Hyperreal)的世界裡,我們有十分好的工具去對抗遺忘,可同時我們卻在不斷失去着過去某些道德和價值觀……
推薦序二
關於照相館的一二
周佩霞
時代,在空間中展示。
空間,隨時代而變。
照相館,在攝影機發明後生;也在攝影技術越來越普及和數碼化後,逐漸消亡。從前,攝影機比較昂貴,不是人人可以擁有,到影樓拍照所費不菲。所以一般平民,都是在重要時刻,才到照相館拍照。因為珍貴,大家都會隆重、認真對待。我的包租婆,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本港出生,三歲時嫁到另一農村當童養媳,十八歲結婚時,因為負擔不起,沒拍過一張照片。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她的丈夫到英國打工前,一家人才第一次上照相館,拍了第一張全家福,而她亦於那時,才拍下第一張和丈夫的合照,當時她已是二子之母。照相館特別是那些舊式的拍照絕不是「快照」,但就如社會學家布爾狄亞(Bourdieu, 1990)所言,家庭的(快怕)攝影不能脫離生產這些照片的家庭生活場合與時機,家庭照片乃是「融合的儀式」(ritual of integration)。當攝影還未普及時,因為家人移徙而在影樓拍攝的家庭照片,不單透視着攝影的階級性,它們還展示了影樓的歷史和社會意義─影樓作為記錄及凝固變動加劇化下的社會的場所。
我父親的全家福,也是由照相館「製造」出來。父親出身於內地一個農民家庭。上世紀六十年代時因為大飢荒,跟姊姊偷渡來港。來港前,也是因為經濟原因,沒有拍過家庭照。後來,他和姊姊恐怕不能重返家鄉與家人重聚,於是讓家人在內地影一張合照,由香港的影樓師傅,再把他和姊姊加上去。一個曾在中環環球大廈一小時沖印店工作的朋友說,九十年代的時候,他們也是不斷為菲傭做同樣的事情。空間轉移了,而一小時沖印店的出現,更直接沖擊影樓的生意,但這些例子正好說明了照相館曾經扮演的歷史角色,以及相片作為社會關係再現的特性,那管相片中的再現,是不同「現實」重疊、補充、修正的產物,而不是純粹外在世界的複製。
照相館所拍的相片,又比照相館以外拍的,更能呈現社會關係的結構及意識形態。照相館裡雖然也有佈景和陳設,但那是一個抽離、虛擬的現實空間,當人們到影樓拍照,不單照相者會穿上最「恰當」的服飾,認真、嚴肅、全神貫注地直視鏡頭,企圖以最好的形象,把自己以及其他在鏡頭裡出現的人,凝固在相紙上。他們還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攝影師的導演和自我安排的共同效應下,按照着特定的社會框架與期望,盡力演好在相片中飾演着的身份,無論那是一張個人證件照,還是家庭照、畢業照、結婚照或其他。簡單地說,證件相中的主角,最好頭髮衣衫整齊,面帶笑容,因為這樣的形象,意味着主角是個循規蹈矩的人,可以融入社會。家庭照則長幼有序、男尊女卑;結婚照則大多顯示女性小鳥依人,男人氣宇軒昂。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大家在照相館拍照時已不一定那麼嚴肅,但是那些傳統框架,依然是拍照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這樣,照相館可以說是傅柯(Foucault)所說的「異托邦」或「異質空間」(heterotopia)。「異托邦」是「烏托邦」的變異。在題為「論其他空間」(Of Other Places)的演講中,傅柯指出烏托邦是理想世界,不存在於現世。但異托邦是現實中的具有特異性質的空間。「某些特定的場址,它們以非常特別的性質與所有其它的場址產生關係,但它們卻擱置、中性化、或是顛倒了它們本來被指定要反射或是再現的種種關係。那些空間與所有其他的空間都有關聯,但是卻與其他所有的場址有所不同。」鏡子就是這樣的異托邦。一方面,鏡子中反射了一個虛擬的現實世界;另一方面,主體透過凝視鏡子中的自己,知道自己所在與不在那裡,從而認清自己的位置,並可由此重新建構。換句話說,鏡子讓各種空間相連結,但又同與一般現實空間產生對比和競逐,從而產生對話和批判的可能。
以攝影機為中心的照相館,是一個比鏡子更實體但又同時更具想像性的異托邦。首先,攝影機既是鏡亦非鏡。是鏡,因為攝影機的原理本來就是鏡像的原理。在攝影機前的東西,反射到鏡頭內,再留在菲林上。但是,這個鏡像,又非如真實的鏡子般,讓主體可以看見。鏡像裡的東西,在攝影數碼化出現前,是要到照片沖晒出來後,才可被看見。
不過,讓照相館成為異托邦的關鍵,乃是上照相館「再現」和濃縮社會關係與意識形態的特性。有趣的是,相片中的社會關係再現,卻又不如鏡子中的鏡像,是純粹外在現實的產物;它以想像的方式,先於相片而存在,並且透過攝影機而具體化。是故,照相館像神殿般,當人們嚴肅地在那抽離的空間拍照時,他們不單可以觀照自己和自己的位置;整個富有儀式性的攝影過程,亦同時為某種關係某個時刻,加以確認,而攝影機就是賦予那些時刻或關係神聖意義不可或缺的中介。
當然,人們到照相館拍照的時刻,如嬰兒誕生、幼稚園小中大學畢業、結婚等等亦倒過來幫助奠立照相館的神聖性。那些時刻都是人生中的重要階段,它們往往象徵人生的某種跨越。在傳統社會裡,那些跨越需要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確立,成人禮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在照相館照相,成為現代社會裡獨特的通過儀式。真正的出生、畢業、結婚,在醫院、在學校禮堂、在婚姻註冊處或教堂進行;人們亦往往在那些場所,進行了相應的儀式,甚至拍下照片;但是,到照相館正正式式拍一張照,總會讓人覺得事件更完滿。而照相館與多個人生重要時刻的連結,亦加強了照相館作為異托邦的特性,因為異托邦的第四原則,就是不同時性的共存。
因為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因為攝影技術普及化,人人都可以是攝影師。作為異托邦的照相館,有些消失,有些轉型。如果照相館真的帶有神聖性,特別在確立及強化社會關係上,那麼,照相館的消失,是否亦意味着社會關係越來越不穩定,就像Instagram或其他即時性的傳訊工具段,一切講求即時與當下,而我們已徹徹底底在Bauman(2000)所謂的液態現代性中生活下去!
推薦序三
人像相片價值最後的避難所
禾日水巷
本雅明在(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1936)中表示,隨着機械複製技術湧現,一種新的文化將會在西方社會逐漸形成。將會導致「傳統的大崩潰」。他指出:人類生活方式的演變,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的感性認識方式是隨着人類群體整個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演變。
早期照相攝影以人像為中心,這點絕不是偶然的。在對遙遠的或已經消逝的愛進行緬懷,抱着崇敬的心來「朝拜」它。
這正如在現實或電影當中,在早期的社會或戰爭時候,被徵召到前線的軍人,都會把家中成員的照片隨身攜帶。早年香港很多男性都要擔當行船或出海捕魚的工作,而每次上船離開,往往都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回到家庭成員身邊,一個月至半年或更長不等,真是聚少離多。這個時候隨身的人像照。在獨自一人的時候,照片釋放出的韻味便發揮以上本雅明所提出的作用。
相片裏肖像的價值找到了其最後的避難所,在早期照相攝影中,韻味通過人像面部的剎那間表情還在作最後的道別,構成這最後道別的就是攝影那憂鬱的無與倫比之美,可是,當人像在照相攝影中消失之時,展示價值便首次超越了緬懷價值,那麼,韻味到底是甚麼?
本雅明提出韻味在傳統藝術中日漸消失的事實,但並沒有大力反對機械複製技術的。複製技術動搖當時民眾根深蒂固的思想,促進大眾文化的湧現。而大眾文化的出現,是有助社會統建群眾思想。縱然有學者擔心這或許會成為國家利用的工具,以達至其政治目的。然而,本雅明對其抱有積極樂觀的心態,對它充滿憧憬。他看見這股新興的社會力量日益聚集擴大,認為它可以發掘社會潛能,作為鼓動革命的一種力量,改變社會。
編者序
《物語》系列:透過物件講故事
鄧烱榕
鍾燕齊自詡為「垃圾佬」,經常往垃圾堆裡鑽,將別人棄不足惜的「垃圾」拾回來當「寶」。從荔園結業那天開始,近三十年來他拾到大量物件,有玩具、文具、照片、相機、包裝袋、書籍(包括一個世紀以來的香港教科書,兒童文學作品、漫畫和經典中文文學作品)、賬簿、單據、學校傢俬、擺設、聖誕燈泡、月餅模具……真係古靈精怪乜都有。這些收藏品當中,有殘缺的也有老舊的,但更多竟是完好無損。我們都驚訝為甚麼他可以時常「執到寶」,他總是笑說現代人太習慣「丟掉」。只要用家認為物件不再有價值,它就會被「丟掉」成為「垃圾」。然而在鍾燕齊眼中,這些「垃圾」其實仍擁有另類的存在意義─作為時代的見證。
鍾燕齊沉迷拾荒,最初可能單純是出於戀舊情意結,但當他的收藏品越堆越多,慢慢便發現到每一件物品器具上面,原來都有時代的痕跡遺留下來。這些痕跡記錄着時代的演變和流逝。鍾燕齊會去思考當時那個人是抱着怎樣的心情將這件物件買回家,物件與用家之間曾經有過怎樣的回憶,它在他或她的生活裡擔當過怎樣的角色,後來又因為怎樣的原因使到這件物件變成垃圾。明白到原來每一件物件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而一個故事又關聯着更多的故事。這些故事靜靜地訴說着一段回憶、一個時期、一種生活、一次變化,甚至是整個人的人生經歷。即使早已人去樓空蒼海桑田,這些故事卻透過一件件不同的物件,反而得以保留下來。所以,多得鍾燕齊的拾荒有道。因為他手上那些上千上萬件不同種類的收藏品,不單只是可以串聯出香港這個城市舊時的人文生活風貌,內裡更蘊藏着無數個關於香港人的故事。
幾年前,鍾燕齊開始跑遍港九新界各地,為各家快將結業的傳統影樓留下紀錄,當然也將他們不要的東西統統打包回家。後來他問我有沒有可能出一本關於相片的書,因為他從影樓收集回來的照片已過千張,好好整理結集成書的話,應該可以從中看到攝影在香港這幾十年間的變化─從影樓到手機,從專業到日常。鍾燕齊還想到一個非常貼切的書名《物語》。「物語」是傳統日本文學的一種體裁,原意為「談話」,後引伸為故事、傳記、傳奇等,是一種擴大化了的,具有散文性質的、用來敘述故事的文學體裁。用在這裡當書名,更語帶相關地點出「以物件來說話」的含義。經過幾次磋商,我甚至建議他把文具及玩具的收藏都編輯起來,成為一套系列書,讓大家除了展覽之外,可以有多一種途徑,看到這些本已為「垃圾」的再生及意義。奈何文具和玩具的數量和種類更加龐大,需要更多時候去整理和逐一拍攝,所以今次以﹁相片﹂主題先行,往後再繼續努力編集其他《物語》。
自序
物之存在 與物對話
鍾燕齊
這個有關香港民間物件出版項目的展開,正好給我機會,讓我與從香港各處不同空間撿拾回來,各種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物件來一次好好對談,好讓它們都能成為真正的「存在」。
「物」之為物,因有其物質屬性:木(紙)、金屬(銀鹽)、塑膠等等。「物」只能處於「存在」的狀態下,才能等待人們來發現。「存在」的認知觀可以理解為:從發覺、識別、屬性、了解、功能,到作用、利弊、用途、效果、控制等系統化的歸納。而物件除了有物質性以外,還有物之「意義」,這又離不開人的「六識」。佛家語為:眼、耳、鼻、舌、身及意,是人類的六種感官認知。「六識」導使我們感知物件的存在,繼而產生不同的慾望。而當物件與事件(event)相關,成為事物,其性質又超乎了物質性。正如這本書,我們通過物件和出版,產出了超乎了一個個別物件原本的功能和意義。因為當物與事互相結合,物件的意義便會變成具有多樣性和不穩定,呈現出「在其間」(in between)的特質:一物的意義總是與他物有所關聯。所以宇宙萬事萬物都有其一定的關聯性。這種伸延,也是通過物件來說故事最有趣地方。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 – 1976)是廿世紀德國最有創見的哲學家,他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1927)中第一次提出了「存在主義」這個概念。海德格爾認為,一直以來西方的思想史只關注「存在着的事物」,而遺忘了「存在着的事物」的「存在」。這是哲學研究上的一個很大的突破!他借用了他的老師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 – 1938)的「現象學」作為工具。「現象」這個詞在希臘文中表示「自行顯現」,故海德格爾認為,現象學即意味着讓事物自己來說明自己的企圖。他說:「只有我們不去企圖把事物硬塞進我們為其製造的觀念的框框中去時,它才能向我們顯現自己。」存在主義提出物體的本質先於物體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先於人的本質。存在主義思考人的絕對,人是絕對的個人。只有人先存在,人才追逐自由。
作為系列性書籍跟一般獨立書籍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整個系列的名稱,在系列當中擔當起說故事的都是一件一件不同的物件,所以聯想到日文裡的一個漢字詞彙「物語」。「物語」既是日文又是中國漢字,它們的存在關係也很值得探究。經過徵詢一眾編輯後都覺得可以使用這個來作系列的總名稱。
第一本《物語》將會以香港影樓和影樓拍攝的照片,去探討攝影跟整個社會和我們的存在關係。一張張經過人手沖曬出來的照片跟數碼世界下的虛擬照片的存在價值。攝影是一種很弔詭的行為。嚴格來說,攝影師在拍攝時,正因忙於和專注拍攝工作,而變得「不完全在場」,所以在拍攝的過程裡,他其實不斷地錯過了很多精彩的畫面,失去了聆聽周邊環境聲音的機會,也沒有感受到周邊其他人生經驗的時刻。結果,他可能在拍下一張照片的同時,也失去了更多的按快門的機會;他是得到了,但失去的更多?或是有失去,但得到的更多?
今天,攝影的技術趨發普及,拿出手機就可以拍照,但卻令到人們習慣於用攝影這個行為來取代經驗本身,所以人們變得好像只在乎照片,或更精準的說,大家都只在乎上傳照片,不再在乎經驗。其實無論何種題材的攝影作品,其背後都要有一個美好的心靈為依托。這在中國傳統哲學領域裡面也能找到一些有力依據,例如中國佛教文化有一本書叫《指月錄》,記載了歷代禪學高僧全燈講法的言行故事。「指月」這個詞就是比喻我想要通過某種方法或形式告訴你一個物體的存在,但要大家做到「見月忘指」,可是當中很多人還停留在只見「指」,不見「月」的階段。這絕對與大多數的群眾脫離社會和遠離生活有密切關係。
我們以為照片是恆久,但它其實只是一種暫存;而相機(拍攝工具)對於今天的人來說,幾乎就是身體的一部分伸延,但假如有一天,大家都失去了這個工具,對眼前存在的一切事物,我們又將會如何處理?
導演李安曾經在電影中說:「人生最大的悲傷就是沒有說再見。」我覺得,攝影其實就是讓我們學會說再見。所以當這本書出版的時候,也是我跟照片說再見的時候!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75折$435
-
新書79折$458
-
新書79折$459
-
新書85折$493
-
新書9折$522
-
新書9折$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