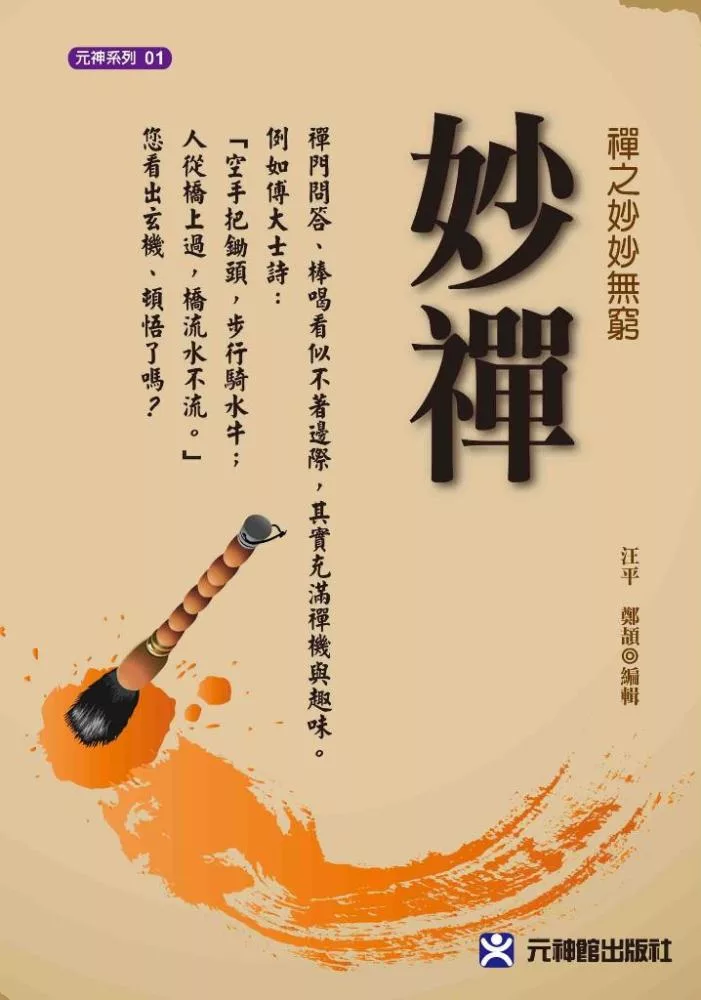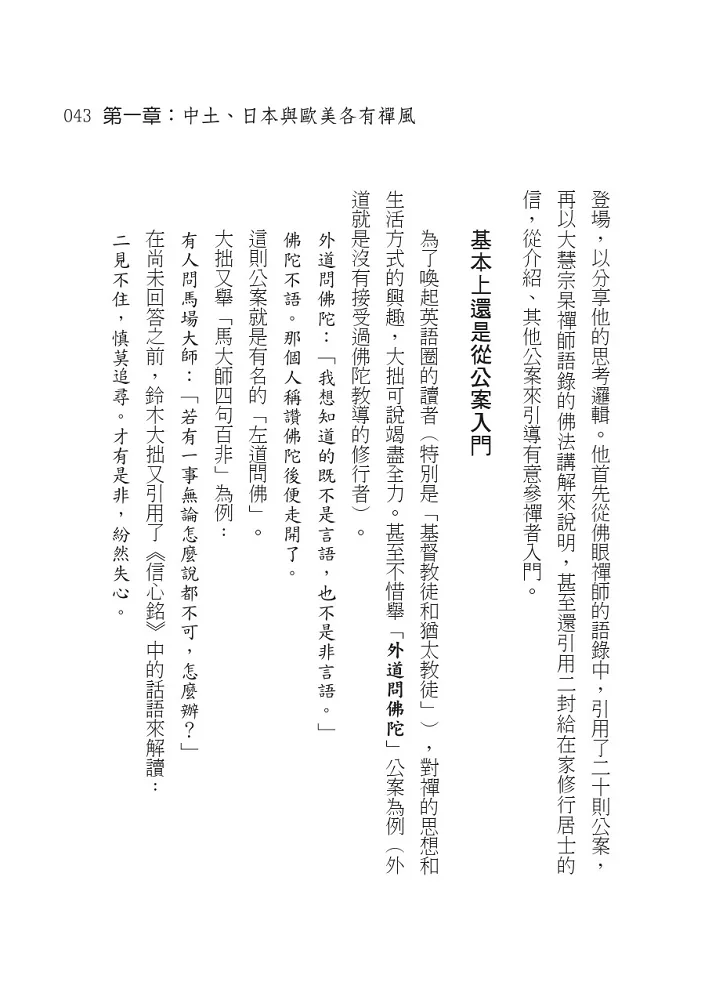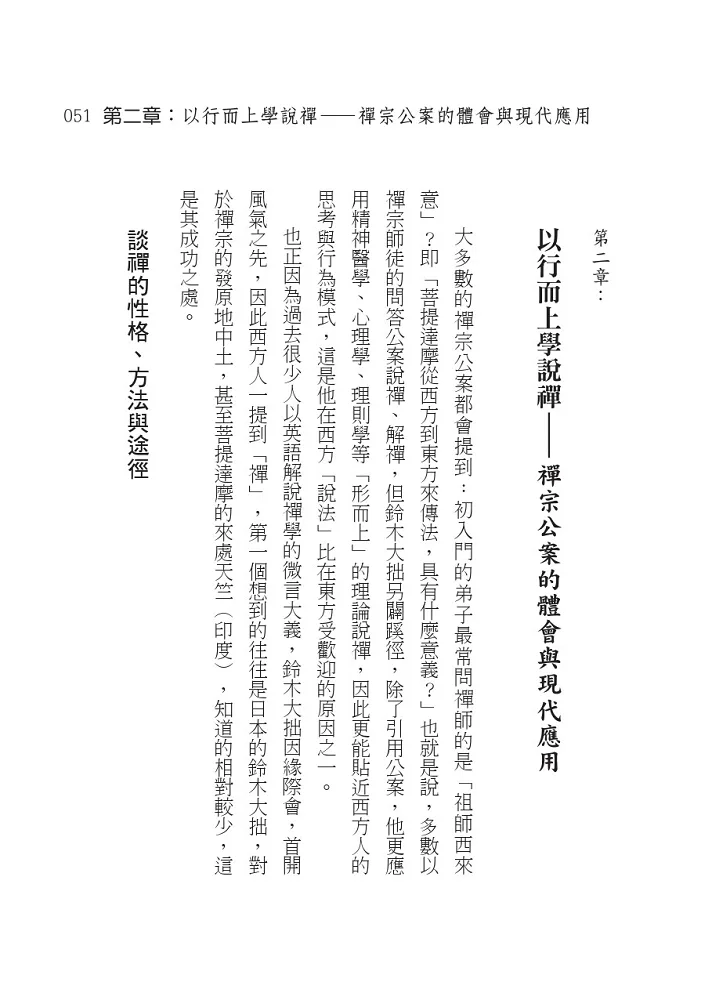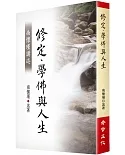序
禪說、說禪——禪講究言語道斷、不立文字
日本的禪宗大師鈴木大拙過世後,人們將其人生最後幾年在歐美演講的內容,輯成「最後禪八講」一書,其文稿原本是以英文寫成,但因禪門講究「言語道斷、不立文字」,如何將源自中國的禪學,以適當的英文解釋給西方人理解,那又是一門學問;因此後來編成書後,為了存真,還把每一講的標題編成章名,成為兩種文字並存的特殊書籍編輯形式。
仔細拜讀之後,我暗自問自己:讀懂了嗎?因為必須像我這種門外漢看得懂,一般讀者才看得懂,才有出版的價值。
老實說,似乎懂了一些,又似乎還不完全懂。事實上這就是禪學的奧妙處,禪宗特別講究「頓悟」,甚麼叫「頓悟」?就是忽然間就開悟了、想通了、理解了。在開悟之前,對禪的一切言語、文字與行為都如霧裡看花,似懂非懂。
再老實一點講,我並沒有完全理解禪,更沒有去實踐。既然如此,怎麼還能說禪心、禪意呢?哪有讀不通歷史的人寫歷史書、不懂科學的人寫科普書的呢?
這正是禪的特色。我國的禪宗大師和日本鈴木大拙所講的禪基本上一樣,禪是超越理性、不依常理思考,甚至是不可得的。而我們都太理性了,因此很難用理性的語言、文字去瞭解超越理性、不可得的禪!這也正是坊間有很多自認為已很了解禪的人,寫了一系列專門著作來「說禪」,可是一般人怎麼讀還是不懂。因為他們都太理性了,都以常理來解說禪,當然無法道斷禪的精髓。作為禪學的門外漢,我只能一方面學習、一方面欣賞,以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稍稍理性的梳理一下禪的流傳過程與簡單的演變,以一種導讀的形式呈現給讀者。
簡單說,我們日常所說的“禪”,多半只是生活經驗所能理解的禪。菩提達摩禪師傳來中國之前的禪,最初的原型在印度被稱作“禪那”(梵語讀作Dhyāna),達摩大師把“禪那”傳到中國後,中國根據“禪那”的意思翻譯成“禪”(CHAN)。中國的“禪”到了日本之後,禪還是“禪”,但被讀作了ZEN。鈴木大拙向西方講解的禪就是ZEN。
禪這個東西從印度的“禪那”(Dhyāna)到中國的“禪”(CHAN)又到日本的“禪”(ZEN),現在又在西方傳播。這過程中,禪發生了哪些演變,不是我們一兩句能講清楚的。那我們怎樣來把握禪的精髓呢?
我們先回到原點。“禪那”的意思,是“思維修”或“靜慮”,也有譯為“棄惡”或“功德叢林”者。這裡的“思維修”或“靜慮”的意思,說的是一個具體的動作和行為,換句話說,要採取某種行為去實踐“禪”,通過實踐禪,達到禪的境界。我們達到了禪的境界,就解決了人生的生與死的問題。我們的心就有所安。反過來說,我們如何讓自己的心有所安?這就是禪。禪的境界是解決我們生與死的意義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修行的過程。
這本書不是看了文字就懂得書,不是看完了這本書就能懂禪。我們知道這是鈴木大拙講禪的書,如前所述,禪是需要實踐的。如何實踐?鈴木大拙做了介紹,以我們(尤其是歐美人)能夠看懂的文字,聽懂的語言引導我們如何去實踐。這是一本需要自己看了之後去實踐,然後參考別人的體驗去實踐的書,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實踐的大書。換句話說,這是一本引導我們去體驗、實踐的書。如果不去實踐,這就是一本毫無意義的書。
去實踐什麼?從去實踐把心放在哪裡的“安心”開始。我們的心應該安在哪裡呢?這是我們人生最為重要的問題。政治家把心安在國家大局上,經濟學家把心安在民生經濟和經濟資料上,科學家把心安在可以實現的科學目標上。數學家把心安在了數位排列與組合上。醫生把心安在了通過藥物治病救人上。他們做了這些,他們就安好了心。那麼,我們普通人把心安在哪裡呢?我們只好把心安在我們普通人的心上,這就是我這個俗人所理解的“禪”的意義。
我們普通人如何把心安在我們普通人的心上?方法就是修行。什麼是修行?我們日常的一舉一動就是修行。這樣講,也許會為禪道高人所恥笑。因為禪在中國是很高深的,很玄的東西。歷來主張要“坐禪”。我們為了生計勞碌奔波的普通人哪能有條件去坐禪呢?坐禪是思維修的一種方式,以靜坐的姿勢在靜靜地思考,這是外人看到的模樣,坐禪者怎樣考慮,怎樣靜修,這就需要禪師的指導了。據說,要拋棄一切雜念,不思不慮才行。坐讓自己的身體安靜下來,不思讓自己的思維和思想靜止下來,這才是坐禪。這樣心就安下來了。這樣也許能達到禪的境界。這正如鈴木大拙講的「修禪」的毛病之一:騎著驢子不肯下來。我們不必執著於“坐”或者某種特定的形式。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一舉一動都在修行,只要意識到。
禪不是要我們靜思,不思不慮,無意識嗎?對!修行就是來往於意識的無意識、無意識的意識之間!禪告訴我們,我們處在這個理性但同時又超越理性的世界,我們就要具有理性的方法和超越理性的方法應對這個世界。讀者不妨實踐體驗一下。體驗之後就應該安心了。
知道(體驗到)了心有所安後,那就是體驗“空”了。
我不懂禪,真的不懂禪。但我可以要求自己去體會、體驗、體悟。
我真想離禪近一點,再近一點。
這就是我這一段時間的體驗,這是一個損失與收穫同時發生的過程。
汪平 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