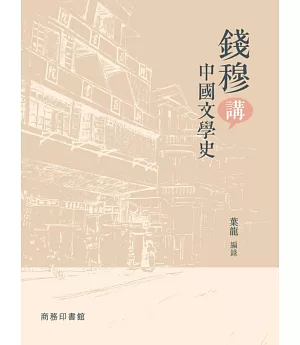國學大師錢穆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罕見的通儒,一生著述超過80本,可是從沒有一本關於中國文學史的系統專著。後人僅從他散落的演講文章,及一些長篇散文中讀到錢師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真知灼見。
錢穆五十年代曾在新亞書院開授兩次《中國文學史》課程,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講到清末章回小說,自成一套完整體系,惜始終未有機會將課程講稿整理成書。師從錢穆多年的葉龍,把60年前的課堂筆記加以整理,搜遺補漏並加上注釋,編成本書。
全書三十多篇文章,由堯舜禹講至清末,體例以時間為序。錢穆以「史」及「人」的標準衡量文學,在講稿中針對具體朝代和文學流變,提出許多新創見,並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及誤解作出了考證和解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葉龍
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曾師從錢穆多年。後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文學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歷任中學及大專文史科教師,講述先秦諸子經濟思想、中國經濟史、史記導讀、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國佛教史等科目。
著有《錢穆講學粹語錄》、《錢穆講中國經濟史》、《桐城派文學史》、《桐城派文學藝術欣賞》、《中國古典詩文論集》、《王安石詩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學研究》、《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等。葉氏課餘在報章撰寫散文,筆耕甚力。
葉龍
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曾師從錢穆多年。後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文學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
歷任中學及大專文史科教師,講述先秦諸子經濟思想、中國經濟史、史記導讀、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國佛教史等科目。
著有《錢穆講學粹語錄》、《錢穆講中國經濟史》、《桐城派文學史》、《桐城派文學藝術欣賞》、《中國古典詩文論集》、《王安石詩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學研究》、《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等。葉氏課餘在報章撰寫散文,筆耕甚力。
目錄
駱玉明序
陳志誠序
葉龍序
第一篇 緒論
第二篇 中國文學的起源
第三篇 《詩經》
第四篇 《尚書》
第五篇 《春秋》
第六篇 《論語》
第七篇 中國古代散文
第八篇 《楚辭》(上)
第九篇 《楚辭》(下)
第十篇 賦
第十一篇 漢賦
第十二篇 漢代樂府
第十三篇 漢代散文──《史記》
第十四篇 漢代奏議與詔令(附書札)
第十五篇 漢代五言詩(上)──蘇李河梁贈答詩
第十六篇 漢代五言詩(下)──古詩十九首
第十七篇 建安文學
第十八篇 文章的體類
第十九篇 《昭明文選》
第二十篇 唐詩(上)(初唐時期)
第二十一篇 唐詩(中)(盛唐時期)
第二十二篇 唐詩(下)(中、晚唐時期)
第二十三篇 唐代古文(上)
第二十四篇 唐代古文(下)
第二十五篇 宋代古文
第二十六篇 宋詞
第二十七篇 元曲
第二十八篇 小說戲曲的演變
第二十九篇 明清古文
第三十篇 明清章回小說
第三十一篇 結論
跋
陳志誠序
葉龍序
第一篇 緒論
第二篇 中國文學的起源
第三篇 《詩經》
第四篇 《尚書》
第五篇 《春秋》
第六篇 《論語》
第七篇 中國古代散文
第八篇 《楚辭》(上)
第九篇 《楚辭》(下)
第十篇 賦
第十一篇 漢賦
第十二篇 漢代樂府
第十三篇 漢代散文──《史記》
第十四篇 漢代奏議與詔令(附書札)
第十五篇 漢代五言詩(上)──蘇李河梁贈答詩
第十六篇 漢代五言詩(下)──古詩十九首
第十七篇 建安文學
第十八篇 文章的體類
第十九篇 《昭明文選》
第二十篇 唐詩(上)(初唐時期)
第二十一篇 唐詩(中)(盛唐時期)
第二十二篇 唐詩(下)(中、晚唐時期)
第二十三篇 唐代古文(上)
第二十四篇 唐代古文(下)
第二十五篇 宋代古文
第二十六篇 宋詞
第二十七篇 元曲
第二十八篇 小說戲曲的演變
第二十九篇 明清古文
第三十篇 明清章回小說
第三十一篇 結論
跋
序
駱玉明序
在老一輩學術名家中,錢穆先生以學問淵博、著述宏富著稱。不過,他對古代文學這一塊說得不多。《錢賓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冊,談中國古今文學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冊《中國文學論叢》中,佔全集的比例甚小。這些文章論題相當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國文學史概觀》一篇,略為完整而系統。因此,如今有葉龍先生將錢穆先生1955至1956年間在香港新亞書院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錄整理成書,公之於眾,實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情。錢先生是大學者,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學術的一個以前我們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對於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來說,更能夠得到許多有益的啟迪。
從前老先生上課大多自由無羈。我曾聽說蔣天樞先生講第一段文學史(唐以前),學期終了,楚辭還沒有講完。錢穆先生的文學史分成三十篇,從文學起源講到明清章回小說,結構是相當完整的了。不過講課還是跟著述不一樣,各篇之間,簡單的可以是寥寥數語,詳盡的可以是細細考論,對均衡是不甚講究的。而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啊漏記啊也總是難免。要是拿專著的標準來度量,會覺得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
但筆錄也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之所處,常常會冒出些「奇怪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若是做文章,就算寫出來也會被刪掉。譬如錢先生說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這話簡單好懂容易記,卻又是特別中肯。蓋孔子最要講的是一個「誠」,連說話太利索他都覺得可疑。「百貨公司,貨真價實」不好用作學術評價,但學生若是有悟性,從中可以體會出許多東西。而現在我們作為文本來讀,會心處,仍可聽到聲音的親切。
要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我們知道它是起於西洋;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也不是中國人寫的。但絕不能夠說,中國人的文學史意識是由外國人灌輸的。事實上,中國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學現象在歷史過程中的變化。至少在南朝,如《詩品》討論五言詩的源流,《文心雕龍》討論文學與時代的關係,都有很強烈的文學史意識;至若沈約寫《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寫《南齊書‧文學傳論》,也同樣關注了這方面的問題並提出了出色的見解。中國文學有自己的道路,中國古賢對文學的價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來,錢先生講中國文學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既認識到它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特質,同時又深刻地關注中國傳統上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意識。在眾多重大問題上,錢先生都避免用西方傳統的尺度來衡量和闡釋中國文學現象,而盡可能從文化機制的不同來比較中西文學的差異,使人們對中國文學的特點有更清楚的認識。也許,我們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與錢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卻是有普遍意義的──這還不僅僅由文學而言。
錢先生是一個樸實而清晰的人,他做學問往往能夠簡單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細瑣的考論。譬如關於中國古代神話,中日一些學者發表過各種各樣的見解。有的說因為中國古人生活環境艱苦,不善於幻想,所以神話不發達;有的說因為中國神話融入了歷史傳說,所以神話色彩被沖淡了,等等。但這樣說其實都忽略了原生態的神話和文學化的神話不是同樣的東西。前些年我寫《簡明中國文學史》,提出要注意兩者的區別,認為中國古代神話沒有發展為文學,而這是受更大文化條件制約的結果。我自己覺得在這裏頗有心得。但這次看錢先生的文學史,發現他早已說得很清楚了:
「至於神話,故事則是任何地方都有的產物。中國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學而已。在西方則由神話、故事而有文學。中國之所以當時沒有形成文學,是由於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評,只宜從歷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說明中西為何有異。」
我們都知道錢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傳統的學者。儒家對文學價值的看法,是重視它的社會功用,要求文學有益於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錢先生是認同這一原則的。所以,在文學成就的評論上,他認為杜甫高於李白,陶淵明高於謝靈運,諸如此類。站在儒者的文學立場上,這樣看很自然,也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與此同時,令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錢先生對文學情趣的重視和敏感。他說:
「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純真與自然。真是指講真理、講真情。鳥鳴獸啼是自然的,雄鳥鳴聲向雌鳥求愛固然是出於求愛,但晨鳥在一無用心時鳴唱幾聲,那是最自然不過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的開放,如空谷幽蘭,它不為甚麼,也沒有為任何特定的對象而開放;又如行雲流水,也是雲不為甚麼而行,水不為甚麼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這是最純真最自然的行與流。寫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學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這些議論使人感到,錢穆先生對文學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視美感的一面。他特別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為它輕快自如,毫不造作(這和魯迅一致)。而且在錢先生看來,正是因為曹操文學的這一特點,他在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錢先生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後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
錢先生對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賦比興,有不同尋常的理解,這和他重視文學情趣的態度也是有關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釋賦比興之說,歸結其意,謂:「意即無論是賦,是比,或是興,均有『物』與『情』兩字。」然後解釋道:
「俗語說:『萬物一體。』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學家都會講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種哲學思想均寓於文學中,在思想史中卻是無法找到這理論的。我們任意舉兩句詩,如,『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我人沉浸在此種情調中時,但不能說是寫實文學,因為它不限時、地、人;也不能說其浪漫;且狗吠雞鳴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觀,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與合一,是賦,對人生感覺到有生意有興象之味,猶如得到生命一般。」
賦比興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這個說法以前是沒有的。但確實,我們在讀這些文字時會感到一種欣喜,我們會感到自己對詩歌有了更親切的理解。
從歷史與社會來說文學,從文化環境說文學,從中西比較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眼界開闢、立論宏大的一面;從自然灑脫、輕盈空靈的個性表現說文學,從心物一體、生命與大自然相融的快樂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偏愛性靈、推崇趣味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
至於錢先生講課一開始就說:「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這倒沒有甚麼特別可以感慨和驚奇的。以中國文學歷史之悠久、作品數量之龐大、文學現象之複雜,文學史寫作幾乎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至於「理想」的文學史,只能是不斷追求的目標吧。
陳志誠序
繼《錢穆講中國經濟史》之後,學長葉龍教授有意將他珍藏多年、修讀錢賓四師「中國文學史」時的筆記整理,然後付梓出版。現在已經整理完成,書名就叫《錢穆講中國文學史》,並囑咐我為這本書寫篇序。我一方面感到萬分的興奮和榮幸,另一方面,我又深感慚愧,我哪有資格為這本書寫序?恐怕葉師兄之屬意於我,一來因為我們是同門師兄弟,無論是在新亞書院抑或新亞研究所,他都是我的前輩。二來,恐怕也是最主要的,我們都先後修過錢師的「中國文學史」,彼此應該有些相關的話題和體會。葉師兄盛意拳拳,我就只好勉力而為,答應過來。但談的都是個人的感受和印象,而且拉雜說來,稱不上是篇像樣的書序。
葉師兄和我雖然先後都修讀過錢師「中國文學史」的課,不過,效果卻可並不一樣。首先,他修讀的時間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而我修讀的則在六十年代初。其次,他修讀的是整年的完整課程,而我修讀的只是半年的課,下半年即由另一位老師替代了。那是因為作為新亞書院的六十年代初,他已因書院要併入中文大學作為三所成員學院之一而非常忙碌,無法多兼教學工作,所以「中國文學史」課只教了半年便沒有繼續下去。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葉師兄是江浙人,他聽錢師課的能力比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學生強,吸收上比較容易。再加上他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態度都相當好,所以,他的聽講筆記詳細而精確,可以充分反映錢師的講課內容,堪稱是課堂的實錄。
眾所周知,錢賓四師是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譽滿中外,著作等身。他又非常熱愛自己的家國和中華文化,「九‧一八事變」之後,因應教育部將「中國通史」成為大學必修科以振起國魂之規定,他在大學講授該科,所編寫的講義即成為日後部定大學用書的《國史大綱》。是書不但足以喚醒國魂,亦加深國人對國史的認識,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而錢師也奠定了他在史學權威的地位。除《國史大綱》外,他的著述包括《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莊老通辨》、《莊子纂箋》、《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文化學大義》、《中國思想史》、《國史新論》、《宋明理學概述》、《四書釋義》、《論語新解》、《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記地名考》、《中國文化精神》、《陽明學述要》、《中國文化叢談》、《朱子新學案》、《中國文學講演集》等,洋洋大觀,非常豐富。
細看錢師的著述內容,都是以史學、經學、文化、思想、考據、理學等範圍的學術性論文為主,屬於文學的,就只有《中國文學講演集》而已。這本《中國文學講演集》,原是錢師有關中國文學的講演紀錄,計共十六篇,1963年由香港人生雜誌社出版。篇幅雖不太多,但涉及的範圍卻相當廣闊,所提的論點也很深入,頗多獨到的見解。此書1983年增加了十四篇,共三十篇,改名《中國文學論叢》,由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除了這些偏重作品欣賞與研究的文章外,錢師也有些情文並茂、感人至深的文學作品,如《朱懷天先生紀念集》、《潮上閒思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靈魂與心》、《雙溪獨語》、《晚學盲言》等抒發個人思想與感情之作。顯然地,我們的史學權威、國學大師,一直都沒有忽略對文學的興趣,至於「中國文學史」,更是他經常在教壇上要講授的課。
錢師個子不高,但步履穩重,雙目炯炯有神,使人望之而生莫名之畏。加上他在講課時,聲音嘹亮,抑揚有致,徐疾有度。在講壇上往來踱步之間,散發出一股非常獨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國文學史」課之時,同學們都全神貫注,靜心聽講。他的每一課就像每一個專題一樣,非常吸引。
我們新亞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每個月都會有個月會舉行,全校學生都會參加,除了簡單的校務報告外,還會邀請嘉賓或校內老師主題演講,演講辭都由學生作紀錄,然後刊登在定期出版的《新亞生活》刊物上。錢師是主要講者之一,這些講辭,其後都彙集成書,取名《新亞遺鐸》。此外,錢師也往往受邀到校外機構作專題演講,不論是校內校外,大都有一位同學獲指派替他作紀錄。而在這些同學之中,我們廣東籍的學生往往只是偶一為之而已。就記憶所及,替錢師作紀錄最多的,葉師兄應該是其中極少數者之一。他一直追隨着錢師,也一直好好地珍藏着他所記錄的錢師筆記。他應該是錢師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早前他在報刊所發表的錢師論經濟、《錢穆講中國經濟史》以及《錢穆講學粹語錄》等,都是他積存多年下來的成果。而對錢師學術的傳揚,也可說貢獻良多,居功至偉。
如今,錢師講授的「中國文學史」講義就要出版了,這真是莫大的喜訊。尤其像我這麼樣的後輩,只修讀過半年的課而已。現在雖已是垂暮之年,但依然有機會看到錢師完整的「中國文學史」面世,圓了多年未完之夢,又怎能不喜出望外呢?而於葉師兄一再推廣錢師學術、惠益後人的初衷,又怎可以只是向他再三致謝而已呢──是為序。
在老一輩學術名家中,錢穆先生以學問淵博、著述宏富著稱。不過,他對古代文學這一塊說得不多。《錢賓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冊,談中國古今文學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冊《中國文學論叢》中,佔全集的比例甚小。這些文章論題相當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國文學史概觀》一篇,略為完整而系統。因此,如今有葉龍先生將錢穆先生1955至1956年間在香港新亞書院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錄整理成書,公之於眾,實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情。錢先生是大學者,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學術的一個以前我們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對於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來說,更能夠得到許多有益的啟迪。
從前老先生上課大多自由無羈。我曾聽說蔣天樞先生講第一段文學史(唐以前),學期終了,楚辭還沒有講完。錢穆先生的文學史分成三十篇,從文學起源講到明清章回小說,結構是相當完整的了。不過講課還是跟著述不一樣,各篇之間,簡單的可以是寥寥數語,詳盡的可以是細細考論,對均衡是不甚講究的。而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啊漏記啊也總是難免。要是拿專著的標準來度量,會覺得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
但筆錄也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之所處,常常會冒出些「奇怪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若是做文章,就算寫出來也會被刪掉。譬如錢先生說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這話簡單好懂容易記,卻又是特別中肯。蓋孔子最要講的是一個「誠」,連說話太利索他都覺得可疑。「百貨公司,貨真價實」不好用作學術評價,但學生若是有悟性,從中可以體會出許多東西。而現在我們作為文本來讀,會心處,仍可聽到聲音的親切。
要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我們知道它是起於西洋;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也不是中國人寫的。但絕不能夠說,中國人的文學史意識是由外國人灌輸的。事實上,中國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學現象在歷史過程中的變化。至少在南朝,如《詩品》討論五言詩的源流,《文心雕龍》討論文學與時代的關係,都有很強烈的文學史意識;至若沈約寫《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寫《南齊書‧文學傳論》,也同樣關注了這方面的問題並提出了出色的見解。中國文學有自己的道路,中國古賢對文學的價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來,錢先生講中國文學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既認識到它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特質,同時又深刻地關注中國傳統上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意識。在眾多重大問題上,錢先生都避免用西方傳統的尺度來衡量和闡釋中國文學現象,而盡可能從文化機制的不同來比較中西文學的差異,使人們對中國文學的特點有更清楚的認識。也許,我們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與錢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卻是有普遍意義的──這還不僅僅由文學而言。
錢先生是一個樸實而清晰的人,他做學問往往能夠簡單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細瑣的考論。譬如關於中國古代神話,中日一些學者發表過各種各樣的見解。有的說因為中國古人生活環境艱苦,不善於幻想,所以神話不發達;有的說因為中國神話融入了歷史傳說,所以神話色彩被沖淡了,等等。但這樣說其實都忽略了原生態的神話和文學化的神話不是同樣的東西。前些年我寫《簡明中國文學史》,提出要注意兩者的區別,認為中國古代神話沒有發展為文學,而這是受更大文化條件制約的結果。我自己覺得在這裏頗有心得。但這次看錢先生的文學史,發現他早已說得很清楚了:
「至於神話,故事則是任何地方都有的產物。中國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學而已。在西方則由神話、故事而有文學。中國之所以當時沒有形成文學,是由於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評,只宜從歷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說明中西為何有異。」
我們都知道錢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傳統的學者。儒家對文學價值的看法,是重視它的社會功用,要求文學有益於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錢先生是認同這一原則的。所以,在文學成就的評論上,他認為杜甫高於李白,陶淵明高於謝靈運,諸如此類。站在儒者的文學立場上,這樣看很自然,也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與此同時,令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錢先生對文學情趣的重視和敏感。他說:
「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純真與自然。真是指講真理、講真情。鳥鳴獸啼是自然的,雄鳥鳴聲向雌鳥求愛固然是出於求愛,但晨鳥在一無用心時鳴唱幾聲,那是最自然不過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的開放,如空谷幽蘭,它不為甚麼,也沒有為任何特定的對象而開放;又如行雲流水,也是雲不為甚麼而行,水不為甚麼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這是最純真最自然的行與流。寫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學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這些議論使人感到,錢穆先生對文學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視美感的一面。他特別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為它輕快自如,毫不造作(這和魯迅一致)。而且在錢先生看來,正是因為曹操文學的這一特點,他在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錢先生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後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
錢先生對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賦比興,有不同尋常的理解,這和他重視文學情趣的態度也是有關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釋賦比興之說,歸結其意,謂:「意即無論是賦,是比,或是興,均有『物』與『情』兩字。」然後解釋道:
「俗語說:『萬物一體。』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學家都會講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種哲學思想均寓於文學中,在思想史中卻是無法找到這理論的。我們任意舉兩句詩,如,『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我人沉浸在此種情調中時,但不能說是寫實文學,因為它不限時、地、人;也不能說其浪漫;且狗吠雞鳴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觀,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與合一,是賦,對人生感覺到有生意有興象之味,猶如得到生命一般。」
賦比興都是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這個說法以前是沒有的。但確實,我們在讀這些文字時會感到一種欣喜,我們會感到自己對詩歌有了更親切的理解。
從歷史與社會來說文學,從文化環境說文學,從中西比較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眼界開闢、立論宏大的一面;從自然灑脫、輕盈空靈的個性表現說文學,從心物一體、生命與大自然相融的快樂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偏愛性靈、推崇趣味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
至於錢先生講課一開始就說:「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這倒沒有甚麼特別可以感慨和驚奇的。以中國文學歷史之悠久、作品數量之龐大、文學現象之複雜,文學史寫作幾乎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至於「理想」的文學史,只能是不斷追求的目標吧。
駱玉明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志誠序
繼《錢穆講中國經濟史》之後,學長葉龍教授有意將他珍藏多年、修讀錢賓四師「中國文學史」時的筆記整理,然後付梓出版。現在已經整理完成,書名就叫《錢穆講中國文學史》,並囑咐我為這本書寫篇序。我一方面感到萬分的興奮和榮幸,另一方面,我又深感慚愧,我哪有資格為這本書寫序?恐怕葉師兄之屬意於我,一來因為我們是同門師兄弟,無論是在新亞書院抑或新亞研究所,他都是我的前輩。二來,恐怕也是最主要的,我們都先後修過錢師的「中國文學史」,彼此應該有些相關的話題和體會。葉師兄盛意拳拳,我就只好勉力而為,答應過來。但談的都是個人的感受和印象,而且拉雜說來,稱不上是篇像樣的書序。
葉師兄和我雖然先後都修讀過錢師「中國文學史」的課,不過,效果卻可並不一樣。首先,他修讀的時間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而我修讀的則在六十年代初。其次,他修讀的是整年的完整課程,而我修讀的只是半年的課,下半年即由另一位老師替代了。那是因為作為新亞書院的六十年代初,他已因書院要併入中文大學作為三所成員學院之一而非常忙碌,無法多兼教學工作,所以「中國文學史」課只教了半年便沒有繼續下去。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葉師兄是江浙人,他聽錢師課的能力比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學生強,吸收上比較容易。再加上他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態度都相當好,所以,他的聽講筆記詳細而精確,可以充分反映錢師的講課內容,堪稱是課堂的實錄。
眾所周知,錢賓四師是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譽滿中外,著作等身。他又非常熱愛自己的家國和中華文化,「九‧一八事變」之後,因應教育部將「中國通史」成為大學必修科以振起國魂之規定,他在大學講授該科,所編寫的講義即成為日後部定大學用書的《國史大綱》。是書不但足以喚醒國魂,亦加深國人對國史的認識,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而錢師也奠定了他在史學權威的地位。除《國史大綱》外,他的著述包括《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莊老通辨》、《莊子纂箋》、《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文化學大義》、《中國思想史》、《國史新論》、《宋明理學概述》、《四書釋義》、《論語新解》、《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記地名考》、《中國文化精神》、《陽明學述要》、《中國文化叢談》、《朱子新學案》、《中國文學講演集》等,洋洋大觀,非常豐富。
細看錢師的著述內容,都是以史學、經學、文化、思想、考據、理學等範圍的學術性論文為主,屬於文學的,就只有《中國文學講演集》而已。這本《中國文學講演集》,原是錢師有關中國文學的講演紀錄,計共十六篇,1963年由香港人生雜誌社出版。篇幅雖不太多,但涉及的範圍卻相當廣闊,所提的論點也很深入,頗多獨到的見解。此書1983年增加了十四篇,共三十篇,改名《中國文學論叢》,由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除了這些偏重作品欣賞與研究的文章外,錢師也有些情文並茂、感人至深的文學作品,如《朱懷天先生紀念集》、《潮上閒思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靈魂與心》、《雙溪獨語》、《晚學盲言》等抒發個人思想與感情之作。顯然地,我們的史學權威、國學大師,一直都沒有忽略對文學的興趣,至於「中國文學史」,更是他經常在教壇上要講授的課。
錢師個子不高,但步履穩重,雙目炯炯有神,使人望之而生莫名之畏。加上他在講課時,聲音嘹亮,抑揚有致,徐疾有度。在講壇上往來踱步之間,散發出一股非常獨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國文學史」課之時,同學們都全神貫注,靜心聽講。他的每一課就像每一個專題一樣,非常吸引。
我們新亞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每個月都會有個月會舉行,全校學生都會參加,除了簡單的校務報告外,還會邀請嘉賓或校內老師主題演講,演講辭都由學生作紀錄,然後刊登在定期出版的《新亞生活》刊物上。錢師是主要講者之一,這些講辭,其後都彙集成書,取名《新亞遺鐸》。此外,錢師也往往受邀到校外機構作專題演講,不論是校內校外,大都有一位同學獲指派替他作紀錄。而在這些同學之中,我們廣東籍的學生往往只是偶一為之而已。就記憶所及,替錢師作紀錄最多的,葉師兄應該是其中極少數者之一。他一直追隨着錢師,也一直好好地珍藏着他所記錄的錢師筆記。他應該是錢師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早前他在報刊所發表的錢師論經濟、《錢穆講中國經濟史》以及《錢穆講學粹語錄》等,都是他積存多年下來的成果。而對錢師學術的傳揚,也可說貢獻良多,居功至偉。
如今,錢師講授的「中國文學史」講義就要出版了,這真是莫大的喜訊。尤其像我這麼樣的後輩,只修讀過半年的課而已。現在雖已是垂暮之年,但依然有機會看到錢師完整的「中國文學史」面世,圓了多年未完之夢,又怎能不喜出望外呢?而於葉師兄一再推廣錢師學術、惠益後人的初衷,又怎可以只是向他再三致謝而已呢──是為序。
陳志誠
香港城市大學語文系前主任及
新亞研究所前所長
香港城市大學語文系前主任及
新亞研究所前所長
內容連載
第一篇 緒論
所謂史者,即流變之意,有如水流一般。吾人如將各時代之文學當作整體的一貫的水流來看,中間就可看出許多變化,例如由唐詩演變下來即成為宋詩和宋詞是也。
以植物言,植物是有生命的。水似無生命,但水有本源,故由唐詩之變宋詞,如貫通來看,兩者實二而一,故通常說詩變成詞,這便是淵源,即是同一流,要明此說,就得分別了解詩、詞及其中間之變化過程。
吾人如要講文學之變化,須先明白文學的本質;文學史是講文學的流變,即須由史的觀點轉回來講文學的觀點。
唐詩之所以變成宋詩(詞),有其外在和內在之原因。由於時代背景不同,因此,我們又得自文學觀點轉入史學觀點了。故講文學應先明白歷史,並非就文學講文學,文學只是抽出來的,並非單獨孤立的。
再進一步說,我們不但要說明文學之流變,而且還要能加以批評。
至於文學的價值,不僅在其內部看,還要從其外部看。例如兩漢文學之成為建安文學(按:此處之「建安文學」,錢師是指曹操、曹丕及曹植三父子),必有其原因,不能用政治來講,當時之政治亦由兩漢之統一變為分裂,但是不能用政治史來說明文學史;建安文學如何興起,則可先講建安時代。
文學是一種靈感,其產生必自內心之要求。從東漢時代到三國時代,其人情、風俗及社會形態都不同了,故思想、觀念、信仰及追求之目的亦都不同了。故文學亦變了。例如曹操身為統帥,但卻輕裘緩帶,與前人不同;此皆因生活情調、風俗觀點都改變了。又如唐人愛用五彩,宋人則喜用素色簡色;唐代用彩畫,宋則用淡墨,風格自各有不同。
文學是文化史中的一項,而非政治中的要目。文化史則包括文學、藝術、宗教及風俗等各項。
又如唐代韓(愈)柳(宗元)之古文運動,則單講政治背景便不夠,所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那麼我人應先讀《昭明文選》,然後才來讀韓文,如此才能容易了解,這就是先要加以比較。我們學習文學史,亦需要加以比較。我們如亦想讀西洋文學史,也可以與中國文學史來比較,一比之下,才可知道中國文學史有其獨特的面貌。
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按:錢師此處所說「直至今日」,是指他開講這門課程的1955年9月初的一天。)
所謂史者,即流變之意,有如水流一般。吾人如將各時代之文學當作整體的一貫的水流來看,中間就可看出許多變化,例如由唐詩演變下來即成為宋詩和宋詞是也。
以植物言,植物是有生命的。水似無生命,但水有本源,故由唐詩之變宋詞,如貫通來看,兩者實二而一,故通常說詩變成詞,這便是淵源,即是同一流,要明此說,就得分別了解詩、詞及其中間之變化過程。
吾人如要講文學之變化,須先明白文學的本質;文學史是講文學的流變,即須由史的觀點轉回來講文學的觀點。
唐詩之所以變成宋詩(詞),有其外在和內在之原因。由於時代背景不同,因此,我們又得自文學觀點轉入史學觀點了。故講文學應先明白歷史,並非就文學講文學,文學只是抽出來的,並非單獨孤立的。
再進一步說,我們不但要說明文學之流變,而且還要能加以批評。
至於文學的價值,不僅在其內部看,還要從其外部看。例如兩漢文學之成為建安文學(按:此處之「建安文學」,錢師是指曹操、曹丕及曹植三父子),必有其原因,不能用政治來講,當時之政治亦由兩漢之統一變為分裂,但是不能用政治史來說明文學史;建安文學如何興起,則可先講建安時代。
文學是一種靈感,其產生必自內心之要求。從東漢時代到三國時代,其人情、風俗及社會形態都不同了,故思想、觀念、信仰及追求之目的亦都不同了。故文學亦變了。例如曹操身為統帥,但卻輕裘緩帶,與前人不同;此皆因生活情調、風俗觀點都改變了。又如唐人愛用五彩,宋人則喜用素色簡色;唐代用彩畫,宋則用淡墨,風格自各有不同。
文學是文化史中的一項,而非政治中的要目。文化史則包括文學、藝術、宗教及風俗等各項。
又如唐代韓(愈)柳(宗元)之古文運動,則單講政治背景便不夠,所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那麼我人應先讀《昭明文選》,然後才來讀韓文,如此才能容易了解,這就是先要加以比較。我們學習文學史,亦需要加以比較。我們如亦想讀西洋文學史,也可以與中國文學史來比較,一比之下,才可知道中國文學史有其獨特的面貌。
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按:錢師此處所說「直至今日」,是指他開講這門課程的1955年9月初的一天。)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78折$312
-
新書79折$316
-
新書79折$316
-
新書85折$340
-
新書9折$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