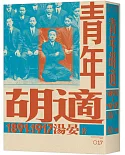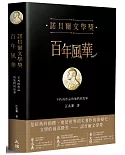前言
志清晚年的願望是發表張愛玲給他的信件及他與長兄濟安的通信。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雞湯,雞湯從鼻子裡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協和醫院(St. Luke’s
Hospital)急診室。從我家到醫院,只需過一條馬路,所以我們是走去的,以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點,志清口乾肚餓,叫我回家給他拿熱水和香蕉。不料等我回到醫院,他床前圍了一群醫生,正在手忙腳亂地把一個很大的管子往他嘴裡塞,讓他用機器呼吸。原來護士給他吃了優格(yogurt),掉進了肺裡,即刻不能呼吸。這管子上頭有一個大球,放在嘴裡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聲,後來就在他脖子上開了一個小口,插上通氣管,志清即不能說話。有一陣病危,他向我交代後事,用筆寫下保存張愛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莊信正來替他完成心願。信正是濟安的高足,也是張愛玲最信賴的朋友,自是最合適的人選。志清經過六個月的奮鬥,居然取下了通氣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裡,可是不良於行,精力大不如前,《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監督下由我完成,於2012年《聯合文學》出版。2013年志清進出醫院頻繁,他每日念叨著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醫院、療養院看他、陪他吃飯,替他刷牙,不等我離開,他已經睡着了,沒有機會讓他讀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夢中安詳地走了,出版志清與濟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濟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腦溢血病逝於柏克萊(Berkeley),志清帶回濟安所有的遺物,包括他們的通信、郵簡及明信片。濟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給他的信有352封,珍藏在一個綠色的鐵盒子裡,放在他書桌底下,預備隨時翻閱。他給濟安的信則分散在四個長方形紙製的文件盒子裡,放在我們的儲藏室,也有260封,共有612封。如要全部發表,需輸入電腦,外加注釋,是一件耗費時日的大工程,如選一部分發表將失去連貫性。我選擇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寶貴的時間花在打字上,實在難以啟齒。我沒有找信正,預備自己做,7月間買了一台蘋果電腦,想利用它的聽寫功能把信念進去。沒想到這蘋果智慧不足,聽不懂我的普通話,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詞用語。我只好改用鍵盤操作,先把信文輸入,再加上「按語」,如此費時兩週,才做完10封信,按這樣的進度,估計得花上五年的功夫,才能做完這些信件,太慢了。我就請王德威教授給我介紹一位可靠的學生打字,把信文輸入電腦。德威盛讚蘇州大學文學院的水準,推薦由季進教授領導,參與信件的編注。
2004年季教授曾訪問過志清,事後寫了一篇名「對優美作品的發現與批評―夏志清訪談錄」登在《當代作家評論》雜誌上。志清看了很喜歡,對這位來自家鄉的年輕學者倍加讚許。德威將這篇專訪收錄於《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聯經出版公司,2010)。志清大去後,季教授也應《明報》邀約,寫了一篇「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懷念夏志清先生」的悼文,對志清的著述有獨到的見解。2008年季教授曾請德威和我到蘇州、鎮江、無錫遊玩,共處三日,我和季進也變得很熟了。我寫信給季進,請他幫忙,他一口答應,承擔起編注的重任。
德威計畫在2015年4月為志清在中研院舉辦一個學術研討會,希望在會前先出版一部分書信,我就選了前121封信,由志清乘船離滬來美至濟安離港赴台。在這段時間,國共內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毛澤東成立了人民政府。多數知識分子及人民嚮往共產政權,濟安卻堅決反共,毅然離開北平飛上海,乘船至廣州,落腳香港。濟安在信裡,時常報導政局戰況,對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關注,時常想念滯留在北大的同事。濟安非常喜歡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語不通,阮囊羞澀,也常常向志清訴苦,對在港的親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謂來自上海的「白華」,時有詳盡的描述。
濟安從小有理想,有抱負,廣交遊,有外交長才。志清卻是一個隨遇而安,只知讀書的好學生,他除了同班同學外,沒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濟安在光華大學的同學。宋奇來訪,總是看見志清安靜地讀書,偶遇濟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戰末期,濟安去了內地後,宋奇仍常來看志清,談論文學,借書給志清。志清在上海初會錢鍾書也是在宋奇家裡。他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宋奇寄給他許多書,特別推薦張愛玲與錢鍾書,對《小說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貢獻。宋奇是中國戲劇先驅宋春舫(1892-1938)的哲嗣,家道殷實,相形之下,夏家太窮了,所以在濟安與志清的筆下,常說他們家窮。其實他們家境小康,不能算窮。
他們的父親夏大棟先生,因早年喪父,輟學經商,娶何韻芝為妻,育有子女六人:濟安居長,大志清五歲,三個弟弟夭折,六妹玉瑛,比志清小十四歲,與濟安相差十九歲。父親長年在外經商,濟安就負起管教妹妹的責任。玉瑛對大哥有幾分敬畏,對二哥卻是友愛與依賴。特別是父親與濟安到了內地以後,家中只剩下母親、志清與玉瑛。志清對幼妹,非常愛護。他母親不識字,生活全靠父親接濟,父親的匯款,不能按時收到,他們不得不省吃儉用,與滬江的同學相比之下,也是窮。
濟安中小學讀的都是名校,有些同學,後來都成為名人。志清讀的都是普通學校。他初進滬江時,覺得自己的英文口語比不上來自教會學校的同學,但他的造句卻得到老師的讚賞,大二時他就是公認的好學生了。他們班上最有成就的就是他和張心滄(1923-2004)。張心滄也是系出名門,父親是吳佩孚的幕僚張其鍠(1877-1927),母親聶其德是曾國藩的外孫女,有顯赫的家世。志清同班要好的同學,除了心滄,還有陸文淵、吳新民及心滄當時的女友、後來的妻子丁念莊。他們都來自富有的家庭,難怪志清篇篇文章說自己窮了。
志清大學畢業後,考取了海關,在外灘江海關工作了一年,抗戰勝利後,隨父執去台灣航務局任職。濟安從昆明回到上海,覺得志清做公務員沒有前途,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1946年9月兄弟二人攜手北上,到了北大不足半年,志清報考李氏獎金(Li Foundation),寫了一篇討論英國詩人布萊克(Blake, 1757-1827)的文章,很得著名文評家燕卜蓀(Empson,
1906-1984)欣賞,獲得文科獎金,引起了「公憤」。西語系落選的講員助教,聯袂向校長胡適抗議,謂此獎金只應頒給北大和聯大的畢業生,怎麼可以給一個教會學校出身的夏志清?胡適秉公處理,仍然把李氏獎金頒給夏志清,志清得以負笈美國。胡適似乎對教會學校有偏見,召見志清時,一聽志清是滬江畢業,臉色即刻沉下來,不鼓勵志清申請名校。當時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的真立夫(Jelliffe)教授正在北大客座,志清就申請了奧柏林,也申請了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這兩所學校,以大學部(undergraduate)著稱,都不適合志清。蒙「新批評」學派的領袖藍蓀(Ransom,
1888-1974)賞識,寫信給Brooks(1906-1994)推薦志清去耶魯就讀。志清何其有幸,得到「新批評」學派三位健將的青睞。
志清一生跟「窮」脫不了關係,因為他從1950年起就接濟上海的家,一直到1987年,從沒有機會儲蓄。在滬江,在耶魯,沒有餘錢約會(date)女孩子,只好用功讀書,唯一的娛樂是看美國電影,其實他看電影,也是當一門學問來研究的。沒有女友,既省錢又省心,能夠專心讀書,在耶魯三年半,即獲得英文系的博士,之後請得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寫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為自己奠定了學術地位,也為現代文學在美國大學裡開闢了一席之地。
濟安為弟弟的成就很感驕傲,常對人說:「你們到紐約找我弟弟,他會請你們吃飯。」我1961-1963年在柏克萊讀書,我和朋友在一個小飯館,巧遇濟安,他就對我們說過這話。我當時不信夏志清真會請哥哥的學生吃飯。直到我和志清結婚,才知此話不假,濟安的朋友學生,志清都盡心招待。濟安維護弟弟,也是不遺餘力。1963年春天,我去斯坦福大學東亞系參加一個小型的討論會,聽濟安滔滔不絕地發言,原來他在駁斥普實克(Průšek,
1906-1980)對《小說史》的批評,為志清辯護。他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快,有些口吃,不修邊幅,是個平易近人的好老師。他的學生劉紹銘曾對我說跟濟安師有說不完的話,與志清卻無話可談。志清說話更快,而且前言不接後語,與其說些讓人聽不懂的話,不如說些即興妙語,使大家開懷大笑,私下也很少談學問,指導學生,就是改他們的文章,叫他們去看書。話說1967年9月我來哥大工作,暫時被安排在我老闆丁愛博(Albert
Dien)教授的辦公室,翌日進來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聞大名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長臉屬國字型,身高中等,衣著整潔,舉動快捷,有些緊張(nervous)的樣子,乍看長相舉止一點也不像夏濟安。細看他們的照片,二人都是濃眉,大眼,直鼻,薄唇,來自他們的父母。志清臉長,像父親,濟安臉圓,像母親。
濟安與志清,雖個性不同,但興趣相投,他們都喜好文學,愛看電影,聽京戲。濟安交遊廣,童芷苓,張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裡,除了談論時政家事外,就講文學,評電影,品京劇,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時候是談女人與婚姻。1947年,濟安已年過三十,尚未娶親,是他們父母的一樁心事。濟安感情豐富,每交女友,即迫不及待地趕緊寫信給弟弟,志清必為之打氣,濟安每次失戀,志清必訴說自己失戀的往事安慰哥哥。二人對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濟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結一次婚,如不能跟心愛的女子結婚,寧肯獨身。志清卻把結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經驗。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結婚,結了婚,私下還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權利。正因為濟安把婚姻看得太神聖,終生未娶。我讀濟安的日記,知道他內心很痛苦,他的日記是不願意給別人看的,志清不顧濟安的隱私,在1975年發表了《夏濟安日記》(時報文化出版)。志清覺得濟安記下了抗戰末期的政局、物價,是真實的史料,暗戀李彥,對愛情的專一,更難能可貴。現在基於同樣的理由,志清要發表他與濟安的通信。記得2010年,在志清九十歲的宴會上,主桌上有些貴賓,當年是中學生,都看過《夏濟安日記》,對濟安的情操,讚口不絕。
志清1982年以前不寫日記,往往以寫信代替日記。他寫過幾篇散文,講他童年與求學的經過,在「耶魯三年半」裡(見《聯合文學》第212期,2002年6月),即提到計畫發表兄弟二人的通信,從而有助於研究文學的學者對夏氏兄弟學術的瞭解。若在世,今年濟安九十九歲,志清九十四歲,他們平輩的朋友大半作古,學生也是古稀耄耋,其中不乏大學者,名作家,為求真起見,不改信中的人名。他們對朋友是褒多於貶,希望他們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這些後輩也可從信中瞭解他們父母離鄉背井,在人地兩生之地謀生的艱辛。
濟安的信,有的是從右至左,由上而下直書;有的是從左至右橫書,格式不一,字大,容易辨認,夾雜的英文也不多。志清的信都是從右至左,由上而下直書。志清為了省紙,常常不分段,他最早的兩封信,已在1988年分別發表於《聯合文學》(2月7-8日)和《香港文學》(5月),篇名「四十年前的兩封信」,採用的是「散文」體。分段後,加上「按語」,介紹人名時往往加上自己的意見。現在收入《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第一卷》,由季進教授重新作注。
這些信,大部分有信封,可是年久,郵戳模糊,信封破損,按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着實花了我不少時間。因為他們的信,照中國人的習慣,只寫日期沒有年代。志清初抵美國,非常節省,用的是劣紙,信紙多有裂痕,字寫得雖清秀,但太小。夾雜的英文又多,一字不誤地解讀他的舊信,實屬不易。為避免錯誤,有時我得去圖書館,我三十年不進圖書館,現在重做研究,別有一番滋味。濟安的信雖然字大,也有看不清的地方,他曾潛心研究橋牌,為了辨認第九十二封信裡的英文字,我特地上網,只花了一塊錢,就買到了橋牌高手Culbertson(1891-1955)的Contract
Bridge Complete —The Golden book of Bidding and Play(Philadelphia. Chicago, The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36),找出“Self
Teacher”這個準則。這本書封面金底紅邊,黑字仍然亮麗。書身寬4¾寸,長7寸,厚1½寸,握在手裡,感觸良多。一本絕版的老書,竟不值一張地鐵的車票,在紐約乘一趟地鐵,還得花上兩二元五角錢呢!
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與志清相識,1969年結婚,對他的家庭,求學的經過,都是從文章裡看來的。他的朋友學生倒是見過不少,留在上海的親戚一個也不認識。信中所提到的親戚,全賴六妹玉瑛指認。感謝季進率領蘇州大學的同學,用最短的時間,排除萬難,把這些字跡模糊的舊信正確地輸入電腦,並且做了七百多條簡要的注解,保證了《書信集》第一卷的如期出版,真是功德無量。我忝為主編,其實是王德威策劃,季進編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沒有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先生的支持,這《書信集》無從問世。志清在天樂觀其願望之實現,對德威、季進、金倫也是非常感激的。我在此代表志清向王德威教授、季進教授、蘇州大學的同學、胡金倫總編輯、聯經出版公司的同仁及六妹玉瑛致以衷心的謝意。
後記
夏濟安(1916-1965)與夏志清(1920-2013)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兩大巨擘。志清先生1961年憑《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英文專著,一舉開下英語世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河。之後的《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更將視野擴及中國古典敘事。他的批評方法一時海內外風行景從,謂之典範的樹立,應非過譽。志清先生治學或論政都有擇善固執的一面,也因此往往引起對立聲音。但不論贊同或反對,我們都難以忽視他半個世紀以來巨大的影響。
與夏志清先生相比,夏濟安先生的學術生涯似乎寂寞了些,爭議性也較小。這或許與他的際遇以及英年早逝不無關係。他唯一的英文專書《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1968)遲至身後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閱讀過此書的讀者都會同意,濟安先生的學問和洞見絕不亞於乃弟,而他文學評論的包容力甚至及於他所批判的對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濟安1950年代曾在臺灣大學任教。不僅調教一批最優秀的學生如劉紹銘、白先勇、李歐梵等,也創辦《文學雜誌》,為日後臺灣現代主義運動奠定基礎。
夏氏兄弟在學術界享有大名,但他們早期的生涯我們所知不多。他們生長在充滿戰亂的193、40年代,日後遷徙海外,種種經歷我們僅能從有限資料如濟安先生的日記、志清先生的回憶文章等獲知。志清先生在2013年底去世後,夏師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這批信件在夏師母監督下,由蘇州大學季進教授率領他的團隊一一打字編注,並得聯經出版公司支持,從2015年—夏濟安先生逝世五十週年—開始陸續出版。
不論就內容或數量而言,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現代中國學術史料的重要事件。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1947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學,終於夏濟安1965年2月23日腦溢血過世前,時間橫跨十八年,從未間斷。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動蕩的時期,夏氏兄弟未能身免。但儘管動如參商,他們通訊不絕,而且相互珍藏對方來信。1965年夏濟安驟逝,所有書信文稿由夏志清攜回保存。五十年後,他們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發送日期編排出版,兄弟兩人再次展開紙上對話,不由讀者不為之感動。
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義。由於戰亂關係,20世紀中期的信件保存殊為不易。夏氏兄弟1947年以後各奔前程,但不論身在何處,總記得互通有無,而且妥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們信件的內容往往極為細密詳盡,家庭瑣事、感情起伏、研究課題、娛樂新聞無不娓娓道來。在這些看似無足輕重的敘述之外,卻是大歷史「惘惘的威脅」。
首輯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濟安1950年準備自港赴台止,正是大陸易色的關鍵時刻,也是夏氏兄弟離散經驗的開始。1946年,夏志清追隨兄長赴北大擔任助教,一年以後獲得李氏獎學金得以出國深造。夏志清赴美時,國共內戰局勢已經逆轉,北京大學人心浮動。未幾夏濟安也感覺北平不穩,下一年離校回到上海另覓出路。但政局每下愈況,夏濟安不得已轉赴香港擔任商職,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上海。
1947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濟安在北大任教,課餘醉心電影京劇,但讓他最魂牽夢縈的卻是一樁又一樁的愛情冒險。從他信裡的自白我們看出儘管在學問上自視甚高,他在感情上卻靦腆缺乏自信。他渴望愛情,卻每每無功而返。他最迷戀的對象竟只有十三、四歲—幾乎是洛麗塔(Lolita)情結!而剛到美國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學若渴,一方面難掩人在異鄉的寂寞。兩人在信中言無不盡,甚至不避諱私密欲望。那樣真切的互動不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間的信任,應是書信集最珍貴的部分。
讀者或許以為既然國難當頭,夏氏兄弟的通訊必定充滿憂患之情。事實不然。世局動蕩固然是揮之不去的陰影,但兩人談學問,談剛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訂做的西裝……林林總總。夏濟安即使逃難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見肘,但對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懷抱興味。而滯留美國的夏志清在奮鬥他的英國文學課程的同時,也不忘到紐約調劑精神。
這也帶出了他們書信來往的第二層意義。或有識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場背景,他們的小資情調、反共立場,無不與「時代」的召喚背道而馳。但這是歷史的後見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現的一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確和我們所熟悉的主流「大敘事」有所不同。但惟其如此,他們信件的內容還原了世紀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段,忠實呈現駁雜的歷史面貌。
1947、48年政局不穩,但彼時的夏氏兄弟仍未經世變,他們直率的表達對政治的立場,也天真地以為戰爭局面過後一切總得回歸常態。然而時局短短一兩年間急轉直下,再回首新政權已經建立,夏氏兄弟發現自己「回不去了」。
比起無數的逃難流亡或清算鬥爭的見證,夏家的經歷畢竟是幸運的。從通信中我們得知四九年以後兄弟兩人遷徙海外,仍與上海家人保持聯絡。但我們也看出他們心境的改變。他們的信裡沒有驚天動地的懷抱,有的是與時俱增的不安。他們關心父親的事業,家庭的經濟,妹妹的教育;匯款回家成為不斷出現的話題,何況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改朝換代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計問題才更為惱人。到了1950年,夏濟安準備離開香港到臺灣去,逐漸承認流亡的現實,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國長居的打算。他們何嘗知道,離散的經驗這才剛剛開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還有第三層意義,那就是在亂世裡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志業。國共內戰期間知識分子不是心存觀望,就是一頭栽進革命的風潮中。兩人信中時常提到的錢學熙就是個例子。但如果僅就夏氏兄弟信中對共產革命的反感就判定他們對政治的好惡,未免小看了他們。作為知識分子,他們的抉擇也來自學術思想的浸潤。
夏氏兄弟傾心西洋文學,並承襲了1930年代以來上海、北平英美現代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到了40年代因為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先後在西南聯大和北大講學而賡續不斷。燕卜蓀在共產革命前夕何去何從,也成為兄弟通信中一個重要的代號。夏志清出國以後,更有機會親炙「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大師如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等。這樣的傳承使他們對任何煽情的事物,不論左派與右派,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對的,他們強調文學是文化與社會的精粹。經過語言形式的提煉,文學可以成為批評人生內容,改變社會氣質的媒介。他們相信文化,而不是革命,才是改變中國的要項。
在紅潮席捲中國的時分,夏氏兄弟的論調毋寧顯得太不實際。他們出走海外,除了「避難」之外,也代表了一種知識(未必總是政治)立場的選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服膺的英美現代批評與其說是形式主義的操練,更不如說是從文學中再現—與發現—充滿扞格的生命情境的實驗。文學與人生張力是他們念玆在玆的話題。
夏氏兄弟的通信風格多少反映了他們的文學信念。他們暢談英美佳作大師之際,往往話鋒一轉,又跳到電影愛情家事國事;字裡行間沒有陳詞高調,穿衣吃飯就是學問。文學形式的思考恰恰來自「作為方法」的現實生活。夏濟安分析自己的情場得失猶如小說評論,夏志清對好萊塢電影認真的程度不亞於讀書。這裡有一種對生活本身的熱切擁抱。惟其如此,日後夏濟安在《黑暗的閘門》裡,對左翼作家的幽暗面才會有如此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發掘了張愛玲筆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在滯留海外的歲月裡,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紙上以蠅頭小字寫下生活點滴,欲望心事,還有種種文學話題。這對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難得的平生知己。我們不禁想到西晉的陸機(261-303)、陸雲(262-303)兄弟俱有文才;陸機更以《文賦》首開中國文論典範。陸氏兄弟嘗以書信談文論藝,至今仍有陸雲《與兄平原書》三十多封書信傳世,成為研究二陸與晉康文化的重要資源。千百年後,在另一個紊亂的歷史時空裡,夏氏兄弟以書信記錄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論文藝,竟然饒有魏晉風雅。我們的時代電郵與簡訊氾濫,隨起隨滅。重讀前人手札,天涯萬里,尺素寸心,寧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