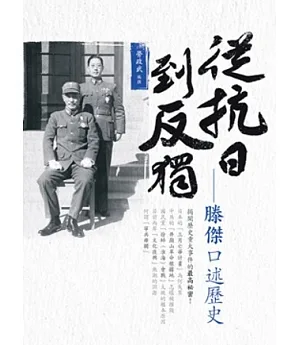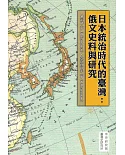作者序
人生原像一篇文章(代序)
講述自傳,原是我研究計畫以外的事。之所以又把它列入計畫之中者,主要是由於一個偶發的原因。
三年前,《龍旗》雜誌社的一批有志青年,為了尋求革命思想的指導,經過張彝鼎、王宜聲
、蔣廉儒三位先生之介紹,來向我請益。他們除要我為之講述反共戰爭問題、兵學問題、哲學問題外,並且要我講述我的自傳,想從我一生的革命經歷中,獲取一些特殊的經驗與教訓。他們忠黨愛國、奮發向上、虛心研究、追求至善的精神,非常難得;尤其處此普遍競相追求物質享受環境中,更顯得特出,令我感動不已!是以不能不應允他們所請。
同時,在我的意識中,也從未排除寫自傳的可能性。我常想:人生原像一篇文章,衹是,這篇文章怎樣寫法各有不同而已。我自己的一生,一直是把握著「報國濟世」這個命題在寫的,並且是結合這個旋乾轉坤、危疑震撼的時代在寫的;有起頭,有過程,也該有個結論。
我這篇文章,已經寫了八十年。其中經過,始終是內外交迫、層層相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錯綜複雜、變化萬千的局面。所幸,在這變化萬千的過程中,我從未迷失過人生的方向。幼時的循性選擇、成年後的理性選擇,兩者能夠自然一致,成就了我一貫地過著理性生活的人生。對此,我自感滿意。
「循性選擇」,泰半出於先天的稟賦。「理性選擇」,則泰半出於後天的認識與決心。我毅然走上了三民主義之建民國進大同的革命大道,就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是從投身於革命洪爐的黃埔軍校開始的。
由於我投身了黃埔軍校,乃獲得了校長、也是革命領袖 蔣公中正特達之知,予以一貫的培植與指引,遂使我有條件得以嚴格的控制住自己,專心一意為革命事業而獻身。六十年來,我已把我的全部時間與精力為這一偉大革命事業而使用了。
又由於我嚴格的過著這樣的革命生活,於是我的處境便很自然的一天一天複雜起來。一面獲得了無數的人對我的關懷、愛護、幫助與期許;一面又引起了無數的人對我的猜忌、誤解、反對與暗算,至於真正的敵人對我的忌恨固無論矣。但不問正面與反面,善因與惡因,對我都是有益的,都是構成我這篇文章之波瀾起伏的必要素材。當然,怎樣才能把這些素材安排得妥當,還是在我自己,此之謂「操之在我」。
那末,我這篇文章寫好了沒有?現在也該作成結論,俾對後世有個交代了。不過,這只是一種懸想,若是沒有意外的觸發,是不會立即決定來講述這部自傳的。
以上就是講述這部自傳的原因。其次,來談談我對寫自傳的一些看法。
寫自傳並不難;因為人生百態,原無一定的範式;而自己講自己的事,更無任何拘束,可以隨心所欲,任意講去。但要寫得好,令人讀之而獲致深刻的印像,且有「如見其人,可友其人,可師其人」的自然反應,那便不是容易的事了。首先,必須要做到「記實傳真」四個字而後可。
胡適之把「記實傳真」四個字作為寫好自傳的標準,確甚允當。惟這四個字應分為「記實」與「傳真」兩個部分來理解。所謂「記實」,就是指的所敍述的事實,必須純然是真情、實事,而不容有絲毫虛假摻雜其間之意。這不謹在表現於外者,該當如此,尤其在無形的心態方面更須如此。這是寫自傳者應取的態度。至所謂「傳真」,係屬方法問題,在求把這真情實事用簡潔生動的筆法恰如其份地表達出來,只須所表達者全屬真誠的流露,自能深印讀者的腦際,而可獲得一個落實的結果。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應該算是一部好的自傳了。
不過僅做到「記實傳真」四個字,只肯定了自傳的「史料價值」,尚未肯定其「社會價值」。一部真正的好自傳,是應該同時具有「社會價值」的。所謂「社會價值」就是「己立立人」的價值,這屬於自傳內容的境界。自傳者真實的人生境界,就是自傳內容的境界。所以一部具有「己立立人」價值的自傳,一定是出自「己立立人」真實的人生。其「己立立人」之境界愈高者,即能給人以高價值的影響。聖賢傳是描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的形成過程,英雄傳是描述英雄之所以為英雄的形成過程;讀聖賢傳英雄傳者,未必即能為聖賢為英雄,但可產生嚮往之心。讀各種有價值的可為楷模的傳記,不管是自傳,還是他傳,所生的影響,大概都會一樣。嚮往之心就是成功之心,所謂「人人可以為堯舜」,所謂「有志者事竟成」,講的都是這個道理。具有如此影響作用的自傳,才是真正有益於世道人心的高價值的自傳。因此,一部高價值自傳的寫作,主要的注意是在其內容之「己立立人」的境界,不僅要做好「寫實傳真」的工夫而已。
寫自傳的正當目的有二:一是自我的人生介紹,另一是自我的人生檢討。前者並非為了自我宣揚,而在符合上面所說的境界,基於為友為師之義,以助人為善、助人向上、助人成就其人之所以為人的美滿人生。後者則在為了自我反省、自我改進,以提高自我的人生境界,以自求人生有一個圓滿的交代。所以,當人們決定依目的去寫自傳的時候,內容的境界為何,殆已不再成為問題;其成為問題者,乃為如何才能做到「記實傳真」。
為什麼「記實傳真」會成為問題?這有三個原因:一是由於過去的事,時間隔得過久,資料不足,僅憑記憶,難免失真。二是由於自己講自己的事,主觀成份難免過重,衡情度理,易有偏差。三是由於隱惡揚善,乃人情之常,且每為現實環境所限,亦不得不然,以致敍事不能周全。凡此,都是達到「記實傳真」要求的自然障礙。
然則,怎樣才能消除這些障礙呢?這須針對原因來分別作答。
為消除第一個原因,要能不厭其煩,多做考證工作。有許多遺忘、疑惑或失真的事,若是得不到可靠的人證或物證,僅從事情之正面、反面或側面之有關的事實中,也有可能考證得出來的;甚至僅用推理方法,也有能得到正確的認定。為消除第二個原因,重在提高處理問題的意境,達到能以歷史眼光與全局眼光來觀察問題,以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來處理問題的地步,而保持一貫的客觀態度,不讓主觀意識有摻雜其間的機會。
對這一、二兩個原因的消除,在有一定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均可得到適當的解決。
真正難以消除的倒是第三個原因。這個原因之難以消除,不在對己,而在對人。對人又不在揚善,而在隱惡。當然,這不是說對他人的「惡」都要隱,而是說有一些惡必須要隱。要隱的惡,往往不止在為避免傷害一個人或一群人,亦在為避免引起政治的或社會的不安。這是從「現實」考慮之所以要隱的理由。同時,隱惡還有其更高的意義。蓋人之秉賦,原有善與惡的兩面,而人之所以為人的進化,即在於向善而去惡,此即老子所謂「為道日損」的道理,其所損者實為秉賦中的惡。因此,隱惡不僅在為人隱惡,亦在導人向善,正符合人類理性發展的趨向。這是從「超現實」考慮之所以要隱的理由。寫一部自傳,必然牽涉到很多人,而隱惡又為勢所不免;是故,任何自傳都不可能做到毫無遺漏的敍述,只可能做到所敍述者沒有不真。
這些都是寫自傳者必然會遭遇到的問題。而自傳能否寫得好,首先就看對這些問題能夠解決到什麼程度,然後才能談到其他。我講述自傳,當然也同樣遭遇到這些問題。那末,我能不能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好些,處理得比較接近理想些,做到「記實」和「傳真」?同時,本書的內容究竟到達了何種境界,能不能給世人以向善向上的影響?這些問題,祇有請讀者去細讀全文,自作判斷了。我自己但求所呈現者,都是一片真誠而已矣。
接著,再談談本書的內容結構。此事雖屬技術層次,看似容易,但做起來並不容易。
梁啟超認為:此事包括兩個要領;一為「剪裁」,一為「排列」。前者好像要把一包羊毛變成呢絨,必須經過爬羅剔抉的取捨功夫,先要達到去蕪存菁的目標。後者猶如良工的藝術製作,雖知規矩方圓,但不一定能有優良的成果;必須要有學力,再加天份,運用各種法門,佈置得宜,詳略得當,才能產生好的作品。
我之全部經歷,如作原則性的描述,那祇講一句話就夠了,就是「我一生都在過著操之在我的理性生活」。但如要詳加描述,那就經緯萬端了。八十年中,我歷經滿清、軍閥、民國,以至播遷來台的四個時期;其境遇之一貫特色,就是錯綜複雜、曲折崎嶇;而欲條理分明地將之描述得清清楚楚,誠非易事。所以本書為此,費了少功夫。
本書共分為十六章,章以下為節,節以內有必要時再分為項或目。原則上,全書章節是以時間先後為排列;但為求事實之終始一貫,在很多地方則採取了「記事本末」體,以作某類人或事的完整敍述。至於剪裁方面,凡無關宏旨者儘量刈除之,對關係較重要的故事、對話則詳細列入,以增加內容輕重起伏之活潑性與可讀性。又為了保持文字謹嚴水準,對於重要之人、事、時等項的解釋或資料來源的說明,其不便列在正文之內者,則以注釋出之。自近代西洋傳記作法傳入以還,自傳作法不再拘泥於一定的傳統;所以本書的結構揉合了各種寫法之所宜,表現了極其自由的形式。這主要出自勞政武賢棣的心裁。至於是否能成為一本結構較為妥善的傳記,當然也只有讀者才能加以評定。
最後,我還應說明本書原稿的產生經過。第一步是講述錄音:此項工作自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起,到次年五月十日止,每週在我寓所講述一次,每次三小時,共講述二十二次。聽講者均為《龍旗》雜誌社有志青年。由於保密需要及其他原因,人數限制在十人以內。講述期間,他們風雨無阻,精神一貫。第二步是翻成文字初稿:此項工作是由謝世濯同志擔任,一字一句地翻下來,約歷半年才告完成。第三步是編撰:此項是勞政武賢棣擔任,包括全文結構之整理,內容之考證、文句修飾增刪等繁複工作;自七十三年二月十日始,到八月十六日止,才告完成;整理成全書約三十萬字。最後,由我親加審閱,又費了近年的時間。是此書原稿從開始講述到最後審定完成,共費四年之久。
滕傑(俊夫)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
寫於臺北市樂利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