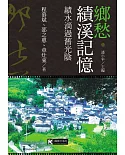後記
吾愛孟夫子 文/呂學海
「然後呢」之後,響起了另一個聲音,說:「沒有然後!」「就是這樣了,沒有然後!小黑之後還有小黑,老孟之後還有老孟,」「宇宙之後還有宇宙,在另一個宇宙小黑一樣奔跑玩耍,老孟一樣生生不已、死死不已,死就是生的一部分,」「永遠都是這樣,沒有然後。」
老孟似乎從年輕時就叫老孟,所有人都叫他老孟,但活了七十二歲,他幾乎生理心理都沒經歷過老,甚至連一顆牙都來不及蛀,就匆匆離開了這世界。很少人弄得清自己跟老孟之間究竟是甚麼關係,因為關係通常由年齡、地位、財富、學問或者關係來決定,可是老孟這些都沒有。平等國小一、二年級的孩子放學走在路上,喜歡興高采烈對著老孟叫:「老孟!」並且慫恿沒叫過的小孩說:「你也叫啊!」當他怯生生試著叫出「老孟」時,大家立刻笑成一團,彷彿經此一叫,這一百八十三公分的白髮老傢伙立刻變成了他們一夥,於是一疊聲的「老孟」「老孟」伴著鬼臉,大家都滿意的蹦跳回家去了!
老孟從不讓人叫他老師,因為自覺不夠格,也因為自知那樣的稱謂下隱含的自滿、無知、與怠惰。他的生命剛健不息,從來不因為地位、財富、學問而停頓。他也從不跟任何人攀關係,不讓人透過關係來了解他,不透過關係去了解人。站在老孟眼前,他只感覺你的「是」,從不過問你的「有」,對任何人來講,那樣的平等相待都是前所未有的釋放和啟迪。
每一個被現代物質文明弄到崎嶇不平、忐忑不安的靈魂,每一個在都會生活中幾乎已經聽不到呼吸心跳的生命,一旦與老孟相遇,試圖了解這個沒有年齡、沒有地位、沒有財富、沒有學問、也沒有關係的老孟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生活時,會像聽到清晨帶露的草叢中輕聲歡唱的螽斯。再沒有比那更真實尖銳的「嘶—嘶—」聲了,可是也沒有比那更恍惚迷離、若有若無的召喚。
老孟的一天可看見的部分是天光透亮開始,他漫步在產業道路,趁上班的車輛尚未駛過,他把柏油路面上還在取暖的一粒粒蝸牛、和一條條蛞蝓仔細的搬回草叢,數十年如一日。老孟廚房牆上掛的鍋碗瓢盆,書房長竿上懸的一面皮鼓和滿室自己紙糊的燈,一器一皿,一桌一几,也都像幾十年來就在那裏,那就是它們在時空中該有的位置。夜晚,月亮有時篩過老孟飯桌旁的窗竹簾,灑落在這群山上孩子們的言笑中,醫學逃兵齊淑英、法文老師藍三靈、小學教師紀淑玲、模特兒范麗、研究員阿香、畫家宿蓮、有時還有隔壁的偶像劇演員小康怡,因為老孟,這群二十幾到五十幾的人都成了信口開河的孩子,跳開年齡、職業以及人生是否順遂,每個不可歸類的生命都發現了生命的自由和可能。老孟在素面相見中教會他們:你就是自己那一類。
而老孟自己又是哪一類呢?考大學時他唯一的志願是台大哲學系,他自喻一生的時間自己都像一根把手腳伸展到天際的天線,想要接收到一些宇宙源起的訊息,在那二百億個銀河中,每個銀河又都有二百億個太陽,因為一輩子無論怎樣調整天線都收不到任何訊息,這男孩經常忍不住哭。他像蟬一樣啼哭著流浪,從一顆樹到另一棵樹,已經是大學哲學系講師了,他辭去職務,從花蓮、到花園新城、到東海別墅、再到花蓮鹽寮、最後來到陽明山平等里的磚房,一生翻譯了一百零五本書。
書的一代翻譯大師一生最恨翻譯。愛、生、死這幾個老孟永恆的主題,他始終拿不定主意該怎麼對待,甚至到了臨終,他還是無法決定該毅然求生,還是求死。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一處一處逃,一個女人一個女人旅行,議者說他沒定性、善變、沒有責任感、甚至敗壞善良風俗,其實都對。但他也真的只是必須不斷調整天線——很認真的調整天線,即使一無所獲。他不能作講台上的哲學教師,甚至不能作哲學家,只能作哲人。他不能作丈夫,只能作情人或是男人。他不是好爸爸,卻是兒子的好朋友,能夠認真諦聽兒子的寂寞與憤怒,疼入心,卻不作判斷或回應。
老孟真誠,真誠到了跟求職的學校校長不敢保證會不會鬧師生戀,真誠到了在自己的茅屋門上張貼「內有色狼」,真誠到了把自己的情史公開寫出來討罵。而這即使不是舉世唯一,也極有可能獨步華人世界的坦誠,最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從來沒有被他玩弄情感,遭受始亂終棄的女人出面舉發?四十年前老孟畫過一陣子油畫,其中僅存的一幅,他把它掛在音響CD那面牆上,謅說是散步時從垃圾堆裡撿回。靛藍底色像是森邈的穹蒼透著光,極簡線條,勾勒出一個平躺漂浮在微光上的男人,光頭,右手上舉左手下垂,皆極柔和而帶有神性,像啟示或被啟示。男人身體下刻鏤著一條細線,一面向左右延伸到畫布以外,使這男人的頭腳更顯長,細線同時向遠處盪,盪到宇宙邊緣,向近處盪,就盪到觀者眼睛上方。這其實就是老孟臨終的姿勢。只是臨終前他不斷上舉的右手像是疲累的花梗,而下垂的左手已經吐盡最後的芬芳,目睹老孟度過生命最後幾分鐘的世光說:那過程非常安祥,五、六分鐘間,花瓣一瓣一瓣落下。一個人的真誠可以到天都願意配合他想要的死法。
老孟始終把宇宙和生命當作同一件事,甚至把性愛也當作同一件事。在生命最後的階段,這個《幻日手記》、《耶穌之繭》的作者已經親口說自己變成一個有神論者了。但他描述得很輕鬆,或說過渡得很輕鬆,似乎沒有意識到其中意義的重大。
更早之前,在剛剛動過腦瘤手術時,黃昏時刻他如常帶著小黑在校門口,看小黑跟另一隻狗撲跌玩樂,一再的奔竄、急停、發出狺狺撕咬的聲音,玩到滿頭大汗。夕陽西下,一批批放學的孩子們背著書包轉入路盡頭去,遠處觀音山即將入夜,小黑還一波波玩得興起,完全不想收手。「這樣起勁啊,小黑!」老孟這麼說,才說完心中立刻浮起一個極熟悉、蒼老的聲音:「然後呢?」然後小黑沒了,小黑的玩伴沒了,周遭一切煙飛灰滅,從年輕時起再熟悉不過的虛無來了,連晚霞夕照、山河大地也都接收了去,成為廢墟。「然後呢?」老孟自己就是那個蒼老的聲音,從年輕起就是。
但是這次有些不同。「然後呢」之後,響起了另一個聲音,說:「沒有然後!」「就是這樣了,沒有然後!小黑之後還有小黑,老孟之後還有老孟,」「宇宙之後還有宇宙,在另一個宇宙小黑一樣奔跑玩耍,老孟一樣生生不已、死死不已,死就是生的一部分,」「永遠都是這樣,沒有然後。」
年輕時翻譯存在主義,其實不是信仰,而是自殘——對於生在一個軍人兼天主教家庭,反抗這雙重父權讓他的青春期充滿恨意,大二時母親又因為一個小中風全無必要的磕倒在台階上,居然就死了。畢業,他翻譯了佛洛姆完整的愛生哲學及至自己寫出自己的《愛生哲學》、《濱海茅屋札記》、《素面相見》,成為台灣簡樸生活的帶動者,和環保生活的實踐者,但是虛無的啃噬從來不曾停止。他所築的巢危如累卵,他所說的一切全部可以一夕作廢,他說起鹽寮開山的經驗,「砍也砍不完的草,一個人揮舞著一支鐮刀,就是瘋狂吼叫也立刻被海風吞沒,被雜草裹死在山裏」。他講禪,肯定直指人心的頓悟法門,可是講完了世界依舊敗壞,連一點點機會都看不出。「然後呢」驅趕著他,本來是魔驅著人的,到後來竟像是人驅著魔,「然後」是人,他是魔。
幾十年了,他掉下淚。總算找回這個說「沒有然後」的聲音,這才是真正的他,虛無走了,留下石階上哭泣的男孩,宇宙和生命終於沒有杆隔,合而為一了。但是老孟仍沒有說明為什麼著作言談中會有那麼多的性呢?
在七、八月的臨終手札中他一面忍受身體的痛楚,一面繫念宇宙。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居然仍細細描述了自己性器最後的狀態,哀嘆陪伴他的L也不再飽滿。緊接著,老孟重寫一遍自己第一次在花蓮看見曇花綻放的盛況。春天無人的夜裡,從入夜到清晨,曇花事實上只有一晚上的機會,可是時間一分一分過去,看起來並沒有任何吸引夜行昆蟲前來傳粉的蹤跡。它還是兀自開著,宇宙的訊息要它在今夜把最美的性器呈現出來,它的雌蕊、雄蕊、和子房。等待極其漫長且焦急,生命繁衍的機會已經注定要錯失了,可是仍然不能辜負它的絕美及渴盼。這時,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來了,老孟拿出他因感動而膨大的性器,跟它交配了。
這是什麼?是宇宙嗎?還是性?當他和女人交配如一朵曇花時,他的真誠既是對女人,也是對宇宙。女人即使不是宇宙,也是讓他最接近宇宙的天線。已經意識到生命尾聲的老孟,顯然有意把這個驚心動魄的夜晚寫進最後的手札,這是他一生的總結。
在一般人無法正視「性」的心理中,老孟找到他打開宇宙的鑰匙。性是生命的源頭,生命是宇宙的本質,脫離這一切即無意義、無靈、亦無神。他是有神論了,其實他一生對宗教、權威、型式、流俗的反叛,就是為了晚年要很自然的過渡到有神論,雖然這神是他的唯一真神,不是哪一個宗教的神。假如一定有人要把他套到哪個教,我看老孟會昂然說:「我是性教,我相信宇宙不斷在繁衍,不斷在性交,不斷在生出小宇宙」。
一位五十年的老朋友形容老孟抗癌是「賈寶玉抗癌記」,老孟其實是並沒有抗,作作樣子之後就一路兵敗如山倒。他太得天獨厚了,中醫師、太極拳老師移樽就教,四、五個鄰居幫他輪流按摩,L也是像喜亦喜、像憂亦憂,早就一副生死相隨的決心。老孟的個性攪進了抗癌過程,很快就來到「生有生的好處,死有死的好處」這種說法,他堅持不修不練,覺得從早到晚為康復做這做那不耐煩,更拒絕帶病延年的說法。難得一致的是他從沒有恐懼、絕望、暴躁種種情緒,算是始終人格完整。
他兒子飛飛和小青一直希望為他找到繼續活下去的動力,他也一度想入世講禪,但是到底沒有那麼大的動力,講禪云云也就像他剛發現肺腺癌時念著要到台東縱谷造屋,或把一輩子沒學好的鋼琴學好一樣。
這是太平洋濱的情癡情種,國共內戰把這補天遺石漂洋過海帶到了台灣,回到他原本該在的地方,浸泡在情海中。老孟沒有年代,沒有具體用途,他只是優雅的行走在花園新城,或東海別墅,或鹽寮海濱,或平等古圳。與他戀愛過的女人都將出現在他的情史中,與他有過性關係的,他已在禱詞中感謝。他用過的器具一一仍掛在牆上,「琴瑟在御,歲月靜好」。
山上的孩子已成孤兒,因為他們原本以為老孟經常會在,「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信手拈來的詩經「關雎」、「桃夭」、「漢廣」、「蒹葭」——幾乎都是老孟寫照。詩而能成經,這次真要感謝老孟教會我們。
這樣留連不捨的人居然也能捨得這世界。老孟死後第二天清早我依舊像往常周二練太極一樣上山,每一個轉彎,一陣清風,一片陽光迷離,幾乎都要讓人停下痛哭一陣。一個典型的成就需要持久不斷的努力,更需要偶然,如同意外掉落懸崖縫隙的種子,掙扎出一朵野地百合。而哲人其萎,就只是一朵白花逕自開得好好的,怎麼說著說著就低下了頭?「老孟啊老孟,死有什麼好呢?」
老孟其實一直沒說清死的好處。直到現在遺憾已成,我們才知道遺憾對人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