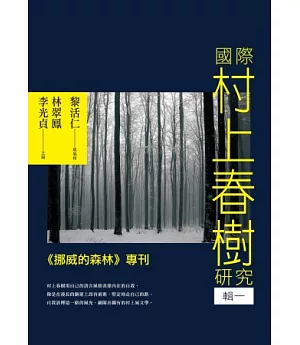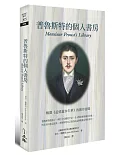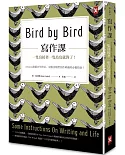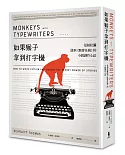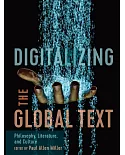序之一
總編輯 黎活仁
《國際魯迅研究》與《國際村上春樹研究》兩種刊物,都是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的,由我擔任總編輯。2013 年3 月12
日,在2013楊逵、路寒袖國際研討會」(2013.03.08)後,踏上歸程之前,《國際魯迅研究》的編委和作者一行二十人,訪問了秀威,因為大家都對電子書的製作感到好奇,想去看個究竟。秀威副總編輯蔡登山先生跟活仁是舊交,而我們剛又在合作《國際魯迅研究》出版事宜,此外,我又在秀威編輯一套《閱讀白靈》、《閱讀向陽》、《閱讀楊逵》的閱讀大師系列經典。那天承發行人宋政坤先生、登山兄、閱讀大師系列經典責任編輯林泰宏先生、《國際魯迅研究》與《國際村上春樹研究》責任編輯廖妘甄女士,和公司上下熱情接待,至為感謝!
其時網上列出研究村上的日文書,已達155 冊,實際上不只此數,可是翻譯到中國去的只有黑古一夫教授、小森陽一教授、河出書房新社《1Q84》論集等較有份量的幾種,秀威登山兄認為村上的小說在台灣極為暢銷,達到驚人的程度,可惜相關研究譯介工作做得很少,說不定短期內村上也會獲諾貝爾文學獎,在台灣將再出現熱潮,建議配合作一些規劃。
坐在旁邊的林翠鳳教授,剛承命執掌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主任,循例要舉辦一些活動,對此至感興趣;翌日離開台北機場時,林主任和活仁再度透過電話就村上春樹議題交換了意見,決定林主任在台灣約稿,活仁則在香港透過網路負責對外聯繫。
初時準備編一些閱讀村上春樹的論文集,但目前的學術評鑑,卻又偏重學術刊物,於是為了給大家提供方便,遂有出版《國際村上春樹研究》之議。村上的書雖然暢銷─《挪威的森林》初版約四百萬冊,但卻遭到扶桑學術界一定程度的冷遇,至今也沒有研究專刊。《國際村上春樹研究》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國際魯迅研究》編委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呂周聚教授給我聯絡了該校日文系李光貞教授,也想不到那麼順利,《國際村上春樹研究》於是由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山東師範大學日文系聯合主辦,稍後,又邀請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方環海教授親率屬下哈佛大學等孔子學院加盟,奠定國際學刊的基礎。李光貞教授代為聯絡東南西北各大高校日文系專家學者,不到兩個月,我們邀約了近二十位研究村上的學者,首先是林少華教授(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葉蕙教授(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兩位是村上作品的中譯者;譯過研究村上著作的楊偉教授(四川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所,內田樹《當心村上春樹》、楊偉、蔣葳合譯)、王海藍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村上春樹:轉換中的迷失》,黑古一夫著,秦剛、王海藍譯)。
以村上研究取得博士的有楊炳菁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文系)、尚一鷗教授(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于桂玲教授(黑龍江大學東語學院)、張明敏教授(健行科技大學應用外文系)、王海藍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楊、張、王三位的博士論文,分別在內地、台灣和日本問世,參考稱便。還有正在攻讀博士的有王靜女士(名古屋大學文學研究科日本文化學專業),王女士擔當我們的「日本之音」,負責提供扶桑的村上研究活動資訊,又承擔部分影印掃瞄工作。在進行相關研究計劃的有張青教授(西北大學文學院)、劉研教授(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和張小玲教授(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
東京大學的村上研究小組中國文學中國語學博士課程的徐子怡會長和東京大學的村上春樹研究小組也惠允加盟;給我們介紹「東京大學的村上研究小組」而目前在日本任教的謝惠貞博士(帝京科學大學綜合教育中心),也應邀擔任了編委。林翠鳳主任透過張明敏博士邀約了藤井省三教授(東京大學中國文學中國語學),藤井教授長期致力兩岸三地的「村上接受史」研究,是彼邦斯學泰斗級人物。
王海藍博士的指導老師黑古一夫教授(筑波大學名譽教授)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黑古教授為創刊號寫了特稿,另外,林翠鳳主任又邀請藤井省三教授和張明敏教授配合《挪威的森林》的專題,把舊作修訂。黑古教授惠允創刊號梓行之日,拜託《朝日新聞》記者給與適當的報導,高義隆情,至為銘感。
到了2013 年8 月,在王靜女士的協助下,團隊已完成《海邊卡夫卡》日文研究論文的蒐集工作,掃瞄為PDF,交大家參考,並開始進行有關《1Q84》的同樣流程。秀威資訊又委託白春燕女士著手對《海邊卡夫卡》日文研究論文中譯。依設定的目標:出版國際學報、系統資料蒐集、與組稿配套的研討會、日文研究論集的中譯等,如果循序漸進,也不必幾個寒暑,當可主導村上春樹研究。
所謂「君子遠庖廚」,不知什麼時候成為大和民族的風尚,男人十指不沾陽春水,年輕人甚至把衣服用快郵「宅急便」寄給母親清洗,以便專心讀書,這是河合隼雄教授所說的「日本的母性病理」,如今村上的男主人公,卻帶有開酒吧當爐的習慣,親自下廚,對外國讀者,未免造成誤導,以為日本大男人都「非君子」,淑女們千萬不要異想天開,以為扶桑紳士都那麼精於烹調,那麼為女性設想。
還有小說主人公常以三明治為主食,實在吃不消,如果天天生魚壽司,「不辭長作東瀛人」!香港的生魚片大概也是空運來的,因為工資和租金較低廉,在超巿所見的價格,確是不可思議的便宜。日本人午餐一般是飯盒,裡面有一塊魚乾,一點沙拉,一兩片以鹽醃製蘿蔔,肉不會多。日本人很少過重,也是事實。
不記得是否加藤典洋教授說的,村上對中華料理的興趣,僅限於麵條,其實他長居於華僑散居的神戶,有機會品嘗有不弱於香港的廣東菜,廣東菜油膩,而扶桑口感又偏好清淡。村上的主人公偶然也吃牛肉,當然不一定是以啤酒和人手推拿培育的「一級棒」「神戶牛柳」,「神戶牛柳」好在那裡,真不知所以然,雞肉則很少提及,《挪威的森林》的「綠」明確說討厭「庭鳥」,雞在日文叫做庭鳥,聽起來較為文雅。我在北美洲旅行時,吃過完全沒有魚味的河鮮。彼邦覺得大和「庭鳥」和蛋味同嚼蠟,長期用科學方法養殖,蛋白也異常稀薄,如稀釋的蠟,想像終於會出現通體透明、薄若寒蟬的家禽,一如外星動物植物,從光熱攝取能源,不必飲食。
日本有四分之一人吸煙,《挪威的森林》中只直子不抽,這一點近於寫實。村上也把天天游泳的習慣,帶進小說,以為日本人都愛游泳、跟以為彼邦人人擅長柔道、劍道、乒乓球,都是對東瀛欠缺理解所致。誤解在後現代有正面意義,誤解即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謂誤讀,凡事例必扭曲來理解,方為上策,才有新意。比方政治家多大話,公民又愛以意逆志,胡亂猜測,離心離德,社會變得紛亂擾攘,人心思變,如是無心插柳,小說家就有了靈感,無益於世道,而有助文章。現代中國人都愛用扶桑的廚房設備。對日本的認知,也止於家品,歷史風土人情文學藝術則欠奉。
如同男女的邂逅,始於誤讀,終於了解。東京的地理,國人可能對歌舞妓町熟知一點,那兒的酒店相對廉宜,而且是不夜天,對旅客有方便之處。村上的〈青蛙救地球〉,把地牛翻動的震央設定在這個旅客常駐足的紅燈區,符合東京人的想像,有一位相熟的東大教授跟我說,這種地方絕對不能涉足,絕對不能去,村上〈青蛙救地球〉想像用火山爆發來救新宿,出發點與東大教授的苦心婆心無二致,都是為東京好。至於不把震央設在燈紅酒綠的六本本或東京鐵塔所在地的「港區」,大概他怕當地的房地產商會找他麻煩吧。
為什麼直子不在旅客較為熟悉的地下街與渡邊散步?為什麼不到公園或動物園去談心?這種問題,常有人知道我在研究村上之後,就來打聽。也只能答非所問,顧左右而言他。地下街的指示較為清晰,路面相對較易迷失方向,變成旅客的迷宮,《挪威的森林》的主人公在不熟悉環境的外國旅客認定的迷宮走來走去,兩小無猜,兩手並不相牽,不知在做什麼?要知,村上的想像力,是在地下鐵地底地心深處,《挪威的森林》的開端,說他在潛水或在潛水艇上,較為合適。也許在《挪威的森林》的續篇,如果有的話,也許就讓他們往地下街走一遭。
《挪威的森林》會有續篇嗎?不知道!綠與渡邊的一段情,小說中沒有交代,說不定鈴子與渡邊春風數度之後,珠胎暗結,多年後來個父子相認─父子相認,是把小說拉長的常見橋段,俄國形式主義如是說。直子可能沒死,她在《尋羊冒險記》不是活過來嗎?論者說她寄住在地獄邊緣,像但丁那樣,出入陰陽界十分方便。誠如帕特莎‧渥厄(Waugh,
Patricia)《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一書說,主人公在小說中隨時會活過來,端賴作者的意願,如《舞‧舞‧舞》的KIKI,死去又還陽,至於愚夫愚婦與主人公同歌同哭,甘受擺弄,是讀者反應的問題。
澤田研二在京都演唱會失足跌下舞台,其時為小三的女友即演《阿信的故事》的田中裕子花了七萬日圓坐計程車,前往探望,雖屬不倫之戀,媒體卻視為美談。渡邊坐新幹線即台灣大陸的高鐵,前往京都阿美寮探望直子,路費以作為大學生的兼職收入,已不便宜,也許這種激情,即要渡邊坐計程車,不大可能。新幹線其時各站停一下的慢車,比較便宜,小說沒有交代渡邊是否坐鈴子所說的「棺材」即新幹線「特急」。國立大學教授的月薪,當時約二十二萬左右,加上在其他學校兼課,不到三十萬,以上數字道聽塗說,而且因年資而異,不是百分之百準確,但可為參照。
「陌生化」理論發明者什克洛斯夫基一篇研究小說如何拉長的短稿中說,逃避預言也是一個常見的方法,譬如俄狄浦斯故事,是為了逃避殺父娶母的神諭,做了很多防禦措施。《海邊的卡夫卡》正用了這一技法,成為情節的骨幹,另外,配以容格的「陰影」、超能力、神通等元小說常用技法,極具匠心。對這西方人殺父殺母的自立過程,東方人應感到震撼,如河合隼雄所說,東方人也許會用較溫和的日出日落以表達,在《挪威的森林》,看官有沒有注意渡邊為升降旗而感到疑惑,這是日出日落的表達方式,渡邊得以成長,全靠這多此一舉的儀禮,否則早就命送黃泉。《海邊的卡夫卡》謀篇的精妙,遠非莫言所能比擬。眾所周知,2012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與村上擦肩而過,給了莫言。
一九八三年,我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資助,重訪闊別五年的京都,其時容格熱已大為流行,我讀了不少河合隼雄教授的著作,河合教授後來與村上有過一次對談,也出了書。從河合教授的容格心理學了解村上作品,變得較為方便。八三年又與官拜國立大學教授的學長重逢,學長親歷村上小說中多次描述過的「大學紛爭」,「大學紛爭」是相當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解放全人類的「宏大敘事」,亦即土居健郎在《依賴心理結構》所說的「『桃太郎』討伐鬼」的成年禮,成年禮對身心成長有正面意義,學長奮不顧身,當年向機動部隊舉起了投槍,雄姿英發,有一次說投襲的是火把,有著「普羅米修斯情結」,把出版部遭衝擊後散遍校園的出版物撿回去,紅袖添香夜讀書,風雅之極。因為有了成年禮,學長才不會變成「永遠的少年」,容格心理學如是說。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古人認為至善至美,莫過如此,時移世易,又有「娶日本老婆,住美國房子,吃中國菜。」的說法,至於《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把大和撫子描寫成閣樓上的瘋女人,直子和鈴子,都瘋了,問題少女小林綠,在大庭廣眾高聲談論男友交歡之事,是名符其實的壞女孩。凡此種種「厭女情結」的筆法,與炎黃子孫的期望有一定落差。香港同學周君,時在京都大學合成化學博班,於「東山三條」附近破廟面壁八年,面壁八年圖破壁,某日中了丘比特一箭,邂逅家在嵐山嶺下住的大和撫子,如今恐已含飴弄孫。
當年雲鬢花顏金步搖,我見猶憐,何況血氣方剛的少年,夫人負笈華盛頓,學得胡兒語,兼擅蟹行書寫,千載搭訕卿我作胡語,亦由今之視昔。遠適異國,昔人所悲,老父棒打鴛鴦,以斷絕往來相脅。無奈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一往情深深幾許,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相偕私奔桂離宮,一索得男,終獲接納,迎歸故里。
大學班上有一個像《挪威的森林》的突擊隊一樣性格的同學,獨來獨往,畢業後有成家立室之念,回來問計於軍師,軍師即平日的酒肉朋友,內容是看電影時應該如何打開話匣子?能否給予惡補?或提供答教?此事自然有好事徒主動獻計,目的不過如渡邊拿他來開玩笑。濶別十多年的同學少年突擊隊後來迷於風水,某一天如村上崇拜的《大亨小傳》作者,自高樓往下一跳,得年四十。比突擊隊年紀小得多的妹妹,在葬禮上一臉惘然地向叔叔阿姨查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畢業後各忙各的,平日並不往來,原因始終成謎?「永遠的少年」突擊隊始終未能走上紅氊,供養父母的責任,丟給弟妹和社會來承擔。
山手線不知坐過多少次,經過五反田,我就想起一個朋友,他一如《舞‧舞‧舞》的五反田,財產全給老婆弄走,身無分文,離婚訴訟纏身,突然而來的壓力,讓他得到癌症,不禁心灰意冷,放棄療程,終於撒手。
又有一位朋友,嫁給如《挪威的森林》的永澤那樣的浪子,苦不堪言,跟她同一運命的,還有守在浪子身邊的為他死忠二三女友。《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對我來說,是寫實小說。
最後要感謝方環海教授、呂周聚教授、李光貞教授和王海藍博士的慨助,海藍博士恩師黑古教授的鼎力扶持,才會在三數月內,出版一本或可主導村上研究的學刊。
甚矣吾衰矣,交遊零落,幸有《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常置左右,以娛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