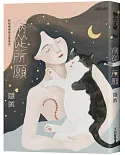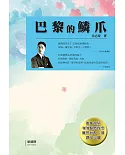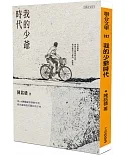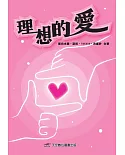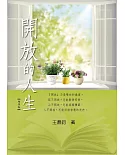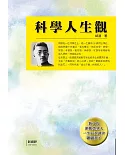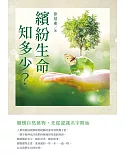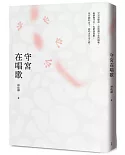序
真正的視野,是心的視野
本書輕鬆真實的呈現在視障特教體制下,一個低視能學生的真實樣貌,從學習到生活到生存的解析,作為視障服務工作者,我很能同理那看似樂觀熱情下對於體制不得不的泰然,完全進入作者幽默寫實的文字中,可能不經意忽略,潛藏在字裡行間所欲揭露體制下的無奈處境,作者幽默地觸探著值得省思的議題。
教育體制建構下,一個視障者必須不斷努力地成為一個符合體制的視障者,以滿足特殊教育與社會的集體期待,然而真實情境中,教育者很少協助視障者去了解自己,於是在還不知如何成為一個人的同時,就努力地成為一個視障者。而我們關心他的「視障」遠大過他的個人主體,於是有權力的人未經同意的取得「視障者」的詮釋權,然後我們開始習慣用「視障者」稱呼他、理解他、定義他,甚至歧視他們,只因為他是視障者。
刻意強調特殊化的論述,先將視障教育邊緣化,然後再用回歸主流的大旗召喚著邊緣處境的孩子回歸主流,而什麼是主流誰又是主流的決定權,從來不在視障者身上,這主流與邊緣往返的適應與後續融入社會的遭遇,最後都得由視障者自己承擔。不論升學或就業,在特殊化的過程都不能忽略個別化的真正意義;在回歸主流環境的過程中,更不能忽略個別化的特殊意義,當我們期許視障者要走進社會時,我們社會準備好了嗎?制度性的障礙與不友善,才是阻礙視障者融入社會的原因,如果作者沒遇到制度上的限制,我實在不認為他是個視障者。
回歸到家庭教育,就可以理解作者何以活潑幽默的面對生活,悲觀的父母很難教養出樂觀的小孩。長期接觸高山峻嶺的父親,自然開展了作者心胸的寬敞度,父母把對眼睛疾病擔心的壓力,轉化到對於作者教育學習的開發上,在這對父母眼中,他只是一個視力不好的人,沒有特權也沒有歧視,也沒讓自己的擔心,成為限制小孩發展未來的可能,尊重並陪伴小孩面對人生的各種過程與壓力,不斷地在身教與言行中,去開展小孩的心胸與視野,豐厚了作者的內涵深度與正面迎向問題的勇氣,這是關心視障孩子的父母應該去思考的議題,自身的家庭教育企圖影響與啟發孩子什麼,這都將成為孩子積累的滋養,會跟著他走進學校、社會、世界,並成為他面對未來的能量與勇氣。
關心視障處境者,不論是家長、老師、社工,應該要回歸本質上的思考,任何服務真正想要促成的結果是什麼,是在成就自己的專業想像,還是發展視障者的主體意識,當幽默樂觀的作者用「神棍」形容白手杖並選擇性的使用,我們能否接受這樣的他,而不評論他心理素質還不夠健康,所以不敢承認自己是視障者?作者面對生活與生存的態度,完美傳神的演繹著「真正的視野,是心的視野」。
謝發財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視障服務處處長)
序
最亮的光在心上
好一個青春的故事!
男孩念書、考試、累到站著也睡著、面試時患得患失。
男孩戀愛、失戀、用MSN把妹、看著心儀的女孩跟前男友重修舊好。
這故事你我都有過。唯一不同的是:這故事中的男孩,看不到。
李堯的眼睛看不到,但心卻看得很清楚。他用青春洋溢的文字,記錄他從小學到就業,一路走來的痕跡。
李堯寫這故事,有三點打動了我。
首先,他描述眼疾,不帶悲情。甚至用幽默的場景,消遣自己的視力。比如說因看不清而誤闖女生宿舍,或是坐椅子時坐到別人身上。
其次,我喜歡他追求愛情的熱情,絲毫不因眼疾而退縮。跟你我一樣,他也會「作替靜純剪腳趾甲的美夢……」「巴望著女同事幫我作CPR……」。書中戀愛的片段,就像任何一個男生的青春日記。視力,不是問題。
但李堯並不逃避視力的問題。這故事動人的第三點,是他坦誠面對視力給他的限制。視力影響了他的人際關係。對於視障,他寫到:「沒有人不在乎,只有不知道,沒有不在乎。」另一段:「然而了解歸了解,他們卻未必想與我互動。」
所以李堯不是盲目地樂觀,他清楚知道人情冷暖、視障心酸。但知道後,選擇用樂觀的態度,來生活,來寫作。
這一點,是這本書,送給盲眼人和明眼人的禮物。
誰沒有障礙呢?有些障礙,別人看得出來。有些障礙,可以掩藏得很好。不管障礙在眼睛、耳朵,或內心,我們都必須與它共存,走過一生。那麼這一生,我們是要「向光飛行」,還是自暴自棄?
讀完書,我一直想起故事中有一段,寫到李堯和朋友到「毒龍潭」(一條被廢水汙染的小溪)划船。他們划啊划,李堯低頭找魚,然後眼鏡掉進水裡。
我把這一段,當作李堯、你、我的人生寓言。我們都在某一條「毒龍潭」上,努力向前划。水被汙染、水中無魚、我們隨時可能失去賴以為生的槳或眼鏡。但沒關係,活著,繼續划就對了。
因為「天使」,其實都在人間。真正的「飛行」,就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划行。最亮的「光」,不是太陽,而在你我的心上。
王文華
(本文作者為知名作家)
前言
希望永遠不滅
記得自己還小的時候,希望的事物很多,最大的希望是去醫院檢查眼睛,醫生會說我狀況很穩定。小學時是在母親駕駛鄰座,看車窗外縱橫延伸的道路兩側,前方來去無定的車流希望著;再大一點,上了國中,則在人群擁擠,常常站在沒有座位的車廂內希望著;三歲的童年就動了第一次刀,比起以後十多次手術,那時真的不算什麼,五歲以前的事我幾乎忘了,圍繞我的醫護人員像群從地獄冒出的綠皮膚惡鬼,我在手術台上躲避翻滾,哭得聲嘶力竭,不曉得他們用了多少糖果把我騙進來,當我發現狀況不妙,已是舉目無親、腹背受敵,他們朝我漸漸逼近,隨即我就人事不醒。
起先一直以為是睫毛倒插的關係,使我覺得眼睛不舒服常去揉它,造成眼睛的感染,連帶影響到視力,小學時又分別動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睫毛倒插手術,近視加深,情況卻未見改善,父母親臉上的憂色愈來愈濃,我似也感到山雨欲來的壓力,但當時的我仍是不知愁滋味的年紀,出診所後,色彩繽紛的事物湧來,快樂和笑聲迅速將淡如雲絲的壓力帶走。
每回去看眼睛,等候看診時,父親常指牆壁上拼圖般密密麻麻有關視力保健的海報告訴我,要好好照顧眼睛;一次,他指向拍有兩幅閃爍藍光圖片的宣導海報慎重說:「這種叫『青光眼』的眼睛疾病很可怕,一得到眼睛都會瞎掉,我們家隔壁的于北北就是得青光眼,眼睛才看不見,你要好好愛護眼睛,不然就會得青光眼。」
記得當時我盯著圖片裡青幽幽的藍,頭一回有股背脊生涼的膽怯,倒不是因為我聽見得這種病眼睛會瞎掉,那時我自認為視力並沒父母說得那樣嚴重,而是圖片中那種藍,使我聯想到恐怖片裡,妖魔鬼怪出現時的雙眼,通常不是紅的、綠的,就是藍的,一個人如果眼睛會發出青色藍光,將是多恐怖的事,我才不要呢!那天醫生檢查完我的眼睛,將父親請到一邊,嚴肅地說道:「李先生,我懷疑你兒子有青光眼的問題,你可能要帶他去台北的大醫院進一步檢查。」
動了第一次青光眼手術,我才明白什麼叫真正痛苦的手術,這是我第四回為治療眼睛而動刀;自從第一次三歲時無助的哭泣,我就再沒因為動手術而哭過,除了想顯示自己的勇敢外,最重要是心底始終有個未曾澆滅,強烈到連我自己都有點不習慣的希望意念,像灰燼中不斷投進的乾柴,總在火苗化作飛煙前及時點燃,就是我相信只要再動這次手術,我的眼睛必會好轉,這一定是最後一次手術,最後一次……但每當我孤身一人被推進開刀房的長廊,父母親均在不能跨越的自動門外,我仍緊張得額上冒汗,即使這兒空調比醫院任何地方來得更涼爽、更為清潔,我卻有股被遺棄的感覺。
車窗外的天色已晦暗不清,圓山飯店的燈火隱隱懸於斜前方的夜幕中,606公車昏昏欲睡的光線照出我奔波的疲憊,眼壓似乎又在升高,我看見眼內彩虹光圈隨車身顛簸騷動,像思緒憂慮眼睛狀況的陰晴不定──它會不會就這樣一直下去,直到看不見為止?上國中後為保護視力,我進入台北啟明學校就讀,檢查眼睛的事變成我孤身的工作,倒不是父母不願陪我,是我不想讓他們那麼麻煩,潛意識中不希望他們一直聽見負面消息,其實我始終畏懼獨自搭公車,我害怕錯過車班,攔錯公車,害怕下錯車站,害怕站在車牌下無止盡的等待。
就讀盲校後,我迷上打籃球,也許是球稍大的關係,我比較少漏接,就算漏接也能及時補救;本以為盲校裡大家都看不見,僅有我眼明手快,再不濟也比他們強些,有股「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鳴得意,豈知盲校絕非個個眼盲,大多數學長同學均為弱視,弱視同學又因病況不同,視力也有所分別,籃球場上一較量,方知視力不佳仍能身手矯捷、百發百中,比起常人自是不足,比起我這隻三腳貓卻遊刃有餘。
那日我與學長比拚力氣,他在抓緊我雙手時,指尖無意擦掠我左眼,由於擔心玩的時候把眼鏡弄壞,當時我沒戴隨身不離的近視眼鏡,只覺左眼有點微微刺痛,也沒在意,胡亂用室友毛巾擦擦就算了。是夜左眼開始很不舒服,頻頻淌淚流膿,我以為忍忍睡一覺就會好,沒驚動宿舍輔導員,待到次晨起身,發現左眼前一片模糊,連同右眼也疼得張不開,才惶恐萬分打電話給父親說:我眼睛看不見了。還記得他氣急敗壞趕到學校時,講出那句令我聞之心碎的話:「送你來讀啟明學校是為了保護你的眼睛,你……你卻在這裡丟掉你最奢侈的視力,嗚……」他再也說不下去,雙手揮擦和他憤怒時一樣澎湃的淚水;如果說我會因為這件自己的疏忽而懊悔,倒不如說我是因為讓父親傷心而深感自責,面對醫生宣判左眼失明的當下,我曾手足無措、百感交集,然而那只是種很短暫的情緒。
出院後拿書一看,終於明白什麼叫作「生動活潑」的文字,它們實在太活潑也太愛動,活潑愛動到像百來隻無頭蒼蠅在紙頁上亂竄。我變得必須先把眼鏡取下,貼近書本才能看清楚寫些什麼,書寫作業也是一樣,不過寫著寫著就從山頂寫到深谷,我無法橫行整齊書寫,每回都得先畫線分行;平常活動依然戴上眼鏡,脫脫戴戴自然麻煩,久了也就習慣。然而我奇異的讀書姿勢卻引起遠在鄉下外公外婆的憂心忡忡,對台灣傳統的農村居民而言,眼睛看不清楚就叫近視,認為戴上眼鏡就會好,戴上眼鏡還看不清楚的就叫瞎子,是悲慘、不能嫁娶,沒有前途的可憐人。
我對親人之於我的疼惜,一則點滴銘記,一則也深感困惑:為什麼人變視障,大家對他的未來都這麼悲觀?我立定考上明星高中,考上公立大學,當時我只能想到考上公立大學是足以驕傲的事,同學朋友這麼說,父母親戚這麼說。可是由於自己中段突然變卦想學音樂,想朝音樂專長發展,忽略正課的學習,加之對視障者高中安置測驗的輕忽,自認自己實力充足能輕易應付,閒暇時也懶於加緊功課,驕傲自大的結果自是慘遭滑鐵盧;我還不死心去參加一般生的聯考,最後連志願卡都不必繳回去,至於樂器也沒學好,參加檢定的水準都不夠,更不用說高中音樂班的考試,什麼都去做的我,什麼名堂也沒拚出來,暑假後仍在雷陣雨的天氣,遮遮掩掩回到啟明校園,只怪自己當時大言不慚誇下海口,但師長似乎忘了,同學好像也忘了,大家依然微笑迎向我,歡迎我在啟明繼續高中生活。
受到父親的影響,我決定大學要讀與文史有關的科系,至於音樂,就作為療傷閒暇迎風弄月的心靈友伴。立下未來肯定的目標需要漫長的經歷和猶豫,如同大學甄試前的苦讀一樣漫長,可是一旦目標立定,三年時光也匆匆像翻過的書頁,放榜時,我考上師大國文系,雖然與清大中文的目標有些小小落差,我仍欣喜得神采奕奕,被快樂沖昏頭的我也在當時作了個最昏頭的錯誤決定。
由於青光眼的日子久了,容易引發白內障;常聽人說,換了人工水晶體,白內障與近視狀況都會消失,視力能變好,不用再戴眼鏡。當確定自己考取師大那天,我同時決定接受更換水晶體的手術。
進入大學,我才曉得視力實際轉變的狀況,比我預期的還要更糟;以前無論右眼震顫如何厲害,只要戴眼鏡,仍能輕鬆看清迎面走來的人是誰,甚至是五官輪廓,可是水晶體一換,我卻再也無法掌握來人長相,尷尬情形隨之發生,每當有同學跟我打招呼,總不知道是哪位經過自己身畔,常常叫錯對方名字,最後迫使我只好對每個向我打招呼的同學,都僅以「哈囉」應答。
我儘量在國文系課程上努力表現,無論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都盡力做到能力所及的最好,為拓展自身專業,把握在學充實的機會,我修習特教作為輔系,除了為將來出路預作準備,還深藏我受特教恩惠的一份感念之情。我們可以將它儲放深層角落或用其他建設性的思維將之淡化,更多人是以「不孤獨」來沖淡自己的寂寞,他們悶著頭擠入人群,似穿花蝴蝶在遠近男女間縱橫來去、熱絡交際,如果「不孤獨」能遣散內心的寂寞,也就不該有「曲終人散」的空虛。
畢業後面臨的第一項抉擇,即大五該去哪所學校實習?對自己來說,如要比較親切輕鬆,自然是回啟明學校,但啟明的實習,卻可能侷限教甄應試的範圍,只因特教孩子不單僅有視障一類,更多的卻為智能障礙學生。我隻身前赴南部一所招收視、聽、智三類障礙學生的特殊學校實習,許多視障的學長姊皆在此修成正果,考取正職特教教師。雖然我曉得來年競爭必是更加險峻,但足踏前人腳步,不禁令我信心倍增;我也從特殊學生,變成特教教師,從被服務者,變成服務者。